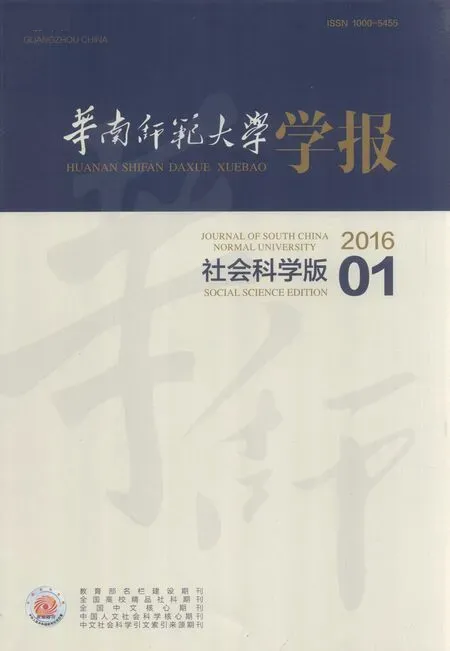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
——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
2016-06-17林岩
林 岩
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
——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
林岩
【摘要】在晚年家居山阴的二十年里,陆游写下了六千余首诗歌。通过对这些诗歌的仔细研读,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基于陆游自己的身份意识。在其诗中,当陆游表述自己离开官场、回乡定居这一事实时,他喜欢使用“退居”一词,而当他提及自己的晚年身份时,则比较明确地将自身定义为“退士”。其次,本文考察了晚年陆游的声望与出处。一方面,他作为声誉卓著的诗人,即使僻处乡野,仍然在诗坛发挥影响力,吸引众多后进诗人登门求教;另一方面,在“庆元党禁”前后,他作为昔日的主战派官僚,既是韩侂胄试图笼络的对象,也是朱熹等在野士大夫观瞻的对象。这说明陆游即使退处乡里,也仍然具有全国性的声望和影响。再次,本文考察了陆游晚年的乡居意识。在其诗歌中,陆游不仅表现出一种“归耕”的意识,喜欢用“老农”来自称;而且也常常在诗中告诫子孙要以耕读传家。这反映出在宋代高度科举竞争的社会中,“仕宦不可常”作为一个社会法则已深深影响到士大夫官员对于子孙的期待。综合这些考察,本文认为,陆游是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一个代表,他晚年的诗歌创作揭示了这一特质。
【关键词】陆游乡居自我意识退居型士大夫
钱钟书曾将陆游的诗歌正确地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同时他也指出,后者的闲适诗在清末之前的很长时期里一直受到文人学士的青睐。然而,随着清末以降国势的艰难,陆游作为一个“爱国诗人”的形象日益凸显出来,反之,他的那些闲适诗倒被有意无意地冷落了。
但是,纵观陆游诗歌的创作历程,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陆游诗歌的绝大部分写于他晚年回到山阴家居之后。在其现存的九千余首诗歌中,他最后二十年在山阴写作的诗歌居然有6 250首之多,也就是说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二以上。*按:在现存85卷的《剑南诗稿》中,自卷21的《醉中作行草数纸》之后,直至卷85的绝笔诗《示儿》,都是其晚年作品。据朱东润先生的计算,总数约在6 470首左右。(朱东润:《陆游研究》,第121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因此,若除去在临安一年所作的216首诗,则晚年在山阴所作,计有6 250首左右。在其晚年诗歌中,固然不乏恢复失地的渴望与英雄迟暮的慨叹,却主要是记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涉及起居饮食、读书吟诗与出游交往,以及家庭生活的一些情形,同时更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凡俗、琐细事物的入诗,使其诗歌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化的气息出现在南宋诗坛,对后来的诗人产生莫大的影响。但怎样去理解和把握这些诗歌,却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学界逐渐将目光转向了陆游的晚年诗歌,但在研究角度上,往往偏重于某一类型的诗歌题材,却很少从整体上去把握陆游晚年诗歌写作的心态与立场。换言之,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站在陆游的立场来思考其晚年的诗歌写作。基于此种考虑,本文以晚年陆游的身份问题为切入点,根据其诗歌中的自我叙述,试图寻绎家居时期陆游的自我意识,及其居乡身份的自我认知;同时结合对陆游晚年在朝野间影响的具体考察,尝试提出一个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概念,并试图勾勒其基本特征。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角度,能为陆游晚年诗歌的整体把握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一、官场与故乡之间:作为“退士”的陆游
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免除了陆游的官职,六十五岁的陆游由此离开官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山阴。此后,直至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二十九日,陆游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家中去世,*按:陆游卒年,有嘉定二年、嘉定三年两种异说,今从于北山考证。于北山:《陆游年谱》,第558—5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他余下的生命时光几乎都是在山阴度过。其间,仅有嘉泰二年(1202)六月十四日,至嘉泰三年(1203)五月十四日,他因为奉召参修国史、实录的缘故,在临安待了整整一年。*按:《剑南诗稿校注》卷53有诗题云《予以壬戌六月十四日入都门,癸亥五月十四日去国,而中有闰月,盖相距正一年矣,慨然有赋》,据此,陆游于嘉泰二年(1202)六月十四日抵达临安,嘉泰三年(1203)五月十四日离开,中间适有闰月,所以前后在临安正好一年时间。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第31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所引陆游诗,如无特别说明,皆出自此书。也就是说,陆游几乎在家乡山阴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那么,在这段漫长的最后时光中,陆游又是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呢?对于重视出处的官僚士大夫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一个居乡的免职官员,陆游在诗歌中提及自己的此种身份时,似乎倾向于使用“退士”一词。淳熙八年(1181)三月,陆游曾遭臣僚弹劾,罢职回乡,前后家居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的诗歌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退士”一词。其《幽居》诗云:
松陵甫里旧家风,晚节何妨号放翁。衰极睡魔殊有力,愁多酒圣欲无功。
一编蠹简晴窗下,数卷疏篱落木中。退士所图惟一饱,诸公好为致年丰。
在这首诗里,罢职的“退士”与在朝的诸公,形成一个出处的对比,而且以“幽居”一词作为诗题,也正好表明了自己远离官场的姿态。这些内涵,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当淳熙十六年(1189)末陆游再次罢职之后,在十余年的家居生活中,他开始多次使用“退士”一词。回乡两年之后,绍熙二年(1191)夏,他在《晚兴》中云:“白布裙襦退士装,短篱幽径独相羊。”又,绍熙四年(1193)秋,他在诗作《癸丑七夕》中云:“民无余力年多恶,退士私忧实万端。”庆元二年(1196)夏,又作《赠童道人盖与予同甲子》,云:“退士一生藜藿食,散人万里江湖天。”在这些诗中所使用的“退士”一词,无疑都是在表述自己远离官场的身份,而且隐约具有与在朝官员相对比的意味在内。而在嘉泰元年(1201)秋的《居三山时,方四十余,今三十六年,久已谢事,而连岁小稔,喜甚有作》一诗中,更显明地表露了这种在野的意识:
自问湖边舍,衰残俛仰中。谋身悲日拙,造物假年丰。税足催科静,禾登债负空。社醅邀里巷,膰肉饫儿童。衣及霜晨赎,炉先雪夜红。陂塘趋版筑,垣屋讫宫功。盗息时雍象,人淳太古风。退夫无一事,皷缶伴邻翁。
此时陆游已经77岁,居乡已有十二年,在诗中他感叹自己的衰老,记述了乡村的一派丰收景象。然而在诗的末尾,却以“退夫”一词来指称自己,无疑是为了凸显自己身在乡野的身份。显然,“退夫”不过是“退士”的另一种表达。
嘉泰三年(1203)夏,陆游离开临安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朝廷,同时他的身体也日益衰老。在其生命最后几年,他较之此前,似乎更喜欢在诗歌中使用“退士”一词。如开禧元年(1205)秋,他有诗云:“衣冠尚作闲身祟,梁肉终非退士宜。惟有褐裘并豆饭,尚能相伴到期颐。”(《自遣》)而在嘉定元年(1208)夏、秋之间,他则连续在三首诗里使用“退士”一词:
退士愤骄虏,闲人忧旱年。耄期身未病,贫困乞犹全。(《自贻》)
退士鬓毛纷似雪,老臣心事炳如丹。(《秋夜》)
浊醪易负寻常债,退士难叨本分官。谢尽浮名更无事,灯前儿女话团圞。(《秋雨》)
而在其去世的嘉定二年(1209),这一年夏天,他在两首诗中也使用了“退士”一词:
“退士自应客少,幽居不厌椽低。”(《夏日六言》)
“退士惟身虑,铭膺岂敢无!”(《书意》)
从诗中的这些例证来看,在陆游家居山阴的二十年光阴里,他几乎一以贯之地用“退士”一词来指称自己离开官场而身处乡野的身份。也就是说,无论是淳熙八年(1181)、淳熙十六年(1189)的免职居乡,还是庆元五年(1199)、嘉泰四年(1204)的两次致仕之后,当他家居山阴之时,他都是用“退士”一词来界定自己脱离官场的身份。
与陆游自称“退士”相呼应的,则是他用“退归”“退休”“退处”这些语词来描述自己离开官场的行为。如以下诸例所示:
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退归亦已晚,饮酒或庶几。(《读陶诗》)
退归久散前三众,迈往欣逢第一流。(《送施武子通判》)
我是仙蓬旧主人,一生常得自由身。退归自合称山长,变化犹应侍帝晨。(《遣兴》)
休退真吾分,无心学息机。(《老民》)
我今虽退休,尝缀廷议末。明恩殊未报,敢自同衣褐?(《书叹》)
宦途昔似伏辕驹,退处今如纵壑鱼。(《自笑》)
有时他也会单用一个“退”字来描述这种脱离了官场的状态,如以下诸例所示:
游宦三十年,所向无一谐,偶然有天幸,自退非人排。(《初春书喜》)
三拜散人号,退志获早遂。(《近村民舍小饮》)
力行虽自许,早退岂人谋?(自注:予年六十余,即退闲故山。)(《远游》)
身退已收清禁梦,里居终出上恩宽。(《初寒》)
从以上诗歌的这些语词用例来看,无论陆游是被弹劾罢职,还是自请致仕,他都将这种离开官场的行为、回乡家居的状态称之为“退”。“退”之一字,因此具有了与官场疏离的意味。当这种离开官场的行为与家居生活的状态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陆游往往会使用“退居”一词来包蕴这双重的意味:
故帽提携二十霜,别裁要作退居装。(《新裁道帽示帽工》)
赐帛更蒙优老诏,此生何以报君恩。(《退居》)
老媿人扶拜,贫无食足谋。退居消日月,大半付庄周。(《书室独夜》)
绝口不谈浮世事,洗心聊策退居勋。(《龟堂晨起》)
宠辱元知不足惊,退居兀兀饯余生。(《书喜》)
虽然在陆游晚年的诗歌中,也常见到他使用“幽居”“村居”“山居”“家居”等字眼来描述自己的归乡家居生活,但这些语词往往都偏向于强调自身在偏僻乡野居住的这一方面,而涉及从官场退却、回到乡间居住这一层意蕴时,他却倾向于使用“退居”一词。
古人有云:“言,心声也”。倘若这一观点可信,那么我们不妨依照陆游诗中这些语词的运用,来推测一下其意识里的自我身份认定。也许在陆游看来,他之离开官场,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是一种“退”的行为。因此,他愿意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退士”。而从离开官场、回乡家居这一角度而言,他的僻处乡里就应视之为“退居”。
值得注意的是,在陆游的诗中,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表述方式来指涉自己离开官场的行为,他称之为“归休”。但在使用这一语词时,它更多是表示一种主动脱离官场的意味。如绍熙二年(1191)秋,他在《寓叹》中有这样的表达:
荷戈常记壮游时,齿豁头童不自知。已分功名非力致,更悲文字与年衰。
端居渐觉从人懒,熟睡偏于听雨宜。自断归休君勿怪,一杯韲糁敌琼糜。
从诗中可见,他将淳熙十六年(1189)自己的罢职,视为一种主动脱离官场的行为。可以说,在使用“归休”一词时,他都多多少少隐含了此种意味在内,如以下诸例所示:
往者收朝迹,亟欲求归休。厚恩许奉祠,得禄岁愈忧。(《岁暮感怀以余年谅无?休日怆已迫为韵》)
莫笑山翁雪鬓繁,归休幸出上恩宽。(《近村暮归》)
胸中万卷书,一字用不著。归休始太息,竟是为农乐。(《秋兴》)
出仕每辞荣,归休但力耕。俭勤贫亦足,戒惧祸终轻。(《自儆》)
归休固已师沮溺,承学犹能陋汉唐。(《夜意》)
君恩许归休,幸与世俗绝。(《冬夜》)
我幸归休在闾巷,灯前感慨不须深。(《杂题》)
莫道归休便无事,时时袯襫伴园丁。(《即事》)
在这些诗句中,“归休”一词不仅意味着陆游自己主动地离开官场,有时还意味着回到乡里,将自己的身份转换成为农者、力耕者,而这反映了家居时期陆游自我意识的另一个层面(将在后文详述)。
Inclusion criteria:subjects who me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hronic gastritis(Chronic gastritis must be diagnosed by western medical fibrogastroscopy and histopathology within 30 d)and do not meet the exclusion criteria.
与“归休”一词相近似的表达方式,则是“归老”。但陆游在使用这个语词时,着重于表达自己回到故乡的意味,几乎毫无例外。这见诸于以下诗句:
衰鬓萧然满镜霜,一庵归老镜湖旁。(《饥坐戏咏》)
久矣微官绊此身,柴车归老亦逢辰。(《遣兴》)
误长僊蓬不满年,恩容归老白云边。(《舟中作》)
两脚走万里,归老樵风溪。(《归老》)
江云漠漠雨昏昏,归老山阴学灌园。(《自开岁阴雨连日不止》)
归老何须乞镜湖,秋来日日饱蓴鲈。(《烟波即事》)
归老家山一幅巾,俗间那可与知闻。(《隠趣》)
这样,陆游在诗中表述自己从官场离开、回到故乡家居这一事实时,他似乎使用了两种语词模式,一种是以“退”字为核心的语词,一种是以“归”字为核心的语词。那么,在这种看似细枝末节的语词差异背后,有着怎样的微妙区别呢?就我的理解而言,陆游在使用“退”字语词模式时,他似乎侧重于表达自己从官场的离开,即以官场为对象;而在使用“归”字语词模式时,他就偏向于表达回归故乡的情感,即以故乡为对象。换言之,“退”与“归”这两种语词模式,代表的是陆游在官场与故乡之间的去与来,脱离与回归。
如果进一步深究,我们会发现陆游在使用这两种语词模式背后,也无意识地透露了南宋官僚士大夫的出处方式。宋代的士人,一般通过科举或荫补的方式,离开家乡出来做官,这在北宋与南宋并无多大差异。但是北宋的官员,在外游宦时,往往会选择在自己任职的地方买地置产,就此定居下来,成为寄居士大夫,而不一定要回到故乡。如欧阳修、王安石虽说是江西人,但从小随父游宦他乡,与家乡的联系并不密切,当他们退休之后,也是分别定居颍州和江宁。苏轼兄弟,从蜀中出来做官之后,就很少回到家乡,最终也都把子女安置在不同地方,而没有返回故乡。但是,南宋的官僚士大夫,无论在外做官多久,一般在离职之后,都会选择回到故乡,如周必大、杨万里、范成大都是如此。因此,南宋的官僚与北宋的官僚,在离职后是否回到故乡这一点上,显然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果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形,那么陆游诗中两种语词模式的使用,恰好体现的是南宋官僚士大夫在官场与故乡之间的出处方式。或者说,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更引发人们兴味的是,陆游在诗歌中很少使用“隐”这一类的字眼来叙述自己离开官场、回乡家居的状态。通过利用电子检索,我在《剑南诗稿》中总共找到两百余条有关“隐”字的条目,通过逐条检核之后,发现真正用于描述陆游家居生活的“隐”字,大概仅有以下数则诗例:
平生玉局经行地,拟乞冰衔隐剡溪。(《双清堂醉卧》)
隐居正欲求吾志,大患元因有此身。(《闲居书事》)
扰扰平生成?事,镜湖归隐老黄冠。(《题斋壁》)
镜湖归隐老黄冠,布褐萧然一室宽。(《雨夜》)
老抱遗书隐故山,镜中衰鬓似霜菅。(《感怀》)
风月宽间地,溪山隐遯身。云边安井臼,竹里过比邻。(《山家》)
故山谁伴隐茅茨,幸有吾家大耳儿。(《示子聿》)
小儿愿与翁偕隐,正恐声名未易逃。(《书志示子聿》)
显然,较之上述引证的“退”与“归”两种语词模式,“隐”这一语词的使用相对较少。但更关键的是,在嘉定二年(1209)秋,即陆游去世前不久,他在《寓叹》中曾写下了如下诗句:“小隐终非隐,休官尚是官。早知农圃乐,不见道途难。故国鸡豚社,贫家菽水欢。至今清夜梦,犹觉畏涛澜。”也就是说,当他回顾自己的家居生活时,他终于意识到他并非一个隐士,过得也不是隐居生活。因为他虽然离开了官场,但仍享有官员的一些待遇。可稍做补述的是,陆游自淳熙十六年(1189)罢职回乡,自绍熙二年(1191)开始,四领祠禄,直至庆元四年(1198)。庆元五年(1199),自请致仕,仍领半俸。嘉泰二年(1202),落致仕重新起用,至嘉泰四年(1204)再乞致仕,又领半俸至嘉定元年(1208)二月。*陆游晚年奉祠家居、致仕的情况,在其诗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一一可按。具体考察,可参看于北山《陆游年谱》相关年份的记载。可见,在陆游家居山阴的二十年光阴里,他仍是一个官员,一个离职官员。也许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在诗中很少使用“隐”字吧。相对于中古文学中“隐逸”主题的流行,我感到这种“隐逸”意识开始在南宋文学中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消退,陆游晚年的诗歌中缺少隐逸之气,即是一例。
综合上述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家居时期的陆游,当他回顾自己离开官场这一事实时,他认为自己是从官场退却,所以这是“退归”“退休”“退处”“退闲”,回到故乡家居,则是“退居”。而当他久居乡村时,他认为自己这种回归故乡的行为是“归休”“归老”。虽然离开官场,但是他又享有官员的一些优待,所以他认为这也算不上是“隐”。当他觉得有必要给自己家居的身份予以明确界定时,他选择了“退士”一词。而且,无论是罢职,还是致仕,他都倾向于使用“退士”一词来指称自己的家居身份。基于陆游的这种自我意识,兼顾其离开官场、回乡定居这两个方面,如果试图给陆游的晚年身份做一个学术化的界定,那么,称其为南宋“退居型士大夫”也许较为适宜。
二、晚年陆游的声望与出处
晚年的陆游虽然身处山阴县一个略显偏僻的村落,但是作为诗坛耆宿,他早已名满天下。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仅受到同辈人的推重,更是受到后生晚辈的崇敬。所以,即使僻处乡野,也不乏登门求教者。与此同时,在陆游家居山阴的岁月里,适逢外戚韩侂胄在朝中独掌大权,他为了压制昔日政敌赵汝愚的支持者,对以朱熹为首的一大批士大夫进行了打击,而陆游的不少朋友恰好属于这个阵营。因此,陆游在晚年的出处动向,也颇受这些同辈士大夫的瞩目,而他与韩侂胄的接近更是饱受争议。这些情形说明,即使作为一个退处乡里的士大夫,陆游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全国性声望。
(一)陆游的晚年声望
在很早的时候,陆游的诗歌才华似乎就已得到认可。据一则宋人笔记说,孝宗皇帝曾向周必大询问:“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而周必大就推荐了陆游,陆游由此得到孝宗赏识。*(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4“陆放翁”条,第71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此后,淳熙十三年(1186),当陆游重新被起用任严州太守时,孝宗曾面谕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宋史》卷395《陆游传》,第1205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又,其《严州到任谢表》云:“勉以属文,时临遣守臣之未有。”可资印证。陆游:《渭南文集》卷1《严州到任谢表》,第1977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而当他自严州召回朝廷时,孝宗又在召对时说:“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宋史》卷395《陆游传》,第12058页。由此可见,孝宗皇帝对于陆游的文学才华一直欣赏有加,这无疑有助于陆游声名的确立。
在同辈的士大夫交游圈子里,陆游作为一个才力超群的诗人,也得到了极大的认可。他在入仕之初,就与周必大结识,两人曾比邻而居,朝夕过从,相知甚深。*陆游:《祭周益公》,见《渭南文集》卷41,第2395—2396页。隆兴元年(1163),当陆游赴任镇江通判时,周必大在送行诗《次韵陆务观送行二首》中就说他:“议论今谁及,词章更可宗。”*(宋)欧阳修:《文忠集》卷3,第47页,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而与他在诗坛上几乎比肩而立的杨万里,也对其诗歌成就极表佩服。淳熙十三年(1186),他曾为陆游的诗稿题跋云:“剑外归乘使者车,浙东新得左鱼符。可怜霜鬓何人问,焉用诗名绝世无!”*(宋)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见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第102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而淳熙十六年(1189),他在一首与陆游的唱和诗中,更是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君诗如精金,入手知价重,铸作鼎及鼒,所向一一中。我如驽并骥,夷途不应共。难追紫蛇电,徒掣青丝鞚。”*(宋)杨万里:《和陆务观见贺归馆之韵》,见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第1375页。在诗中,杨万里以一种谦逊的姿态,表示了自己对于陆游的敬重。而对陆游诗歌最为推崇的则是当时的道学领袖朱熹。据说,朱熹“于当世之文,独取周必大;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5“周文陆诗”条,第319页。这在他本人与别人的议论之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他给徐赓(载叔)的书信中说:“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宋)朱熹:《答徐载叔》,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第2649页,收入《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又在给巩丰(仲至)的书信中说:“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宋)朱熹:《答巩仲至》,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4,第3108页。皆可见出叹服之意。此外,甚至连光宗宠臣而兼诗人的姜特立在《次韵陆郎中》也感叹说:“当今大笔如君少,未用收藏叹陆沉。”*(宋)姜特立:《梅山续稿》卷4,第39页,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这些皆可说明,陆游的诗歌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陆游在当时也成为了后进诗人尊崇的对象。如与他晚年诗歌往还较多的赵蕃在《呈陆严州》中曾有云:
一代诗盟孰主张,试探源委见深长。家声甫里归严瀬,句法茶山出豫章。
千里寸心长炯炯,十年两鬓漫苍苍。扁舟纵欲乘风去,可不一登君子堂。*(宋)赵蕃:《淳熙稿》卷12,第197页,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5册。
无疑,赵蕃是把陆游当成了当时的诗坛主盟人物。而在浙东地区,与陆游有过从,且曾受教于他的年轻后辈,对于陆游的文学成就更是推崇备至。如山阴的苏泂曾亲炙于陆游,在其诗集中,对于陆游多有赞颂之语,或言“先生天下名,有耳谁不知”*苏泂:《送陆放翁赴落致仕修史之命》,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泠然斋集》卷1,第75页。,或言“岂有文章高海内,独将身世老山中”*苏泂:《寿陆放翁三首》,见《泠然斋集》卷5,第112页。,或言“声名固自盖天下,耆老所当留日边”*苏泂:《三山放翁先生朝以筇拄杖为寿一首》,见《泠然斋集》卷5,第112页。,皆是不吝誉词。婺州兰溪的杜旃也曾有诗赞叹说:“四海文章陆放翁,百年渔钓两龟蒙。”*杜旃:《陆务观赴召》,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江湖小集》卷19,第153页。而与陆游同为乡里的杜思恭不仅说:“放翁先生,文章翰墨,凌跨前辈,为一世标准。”而且在自己于广西做官时,于庆元三年(1197)将陆游的作品刻于崖石。*孔凡礼、齐治平编:《陆游资料汇编》引《广西通志》,第38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这些皆是陆游还健在时,年轻后辈所表达出来的敬意。
其实,当陆游晚年家居的时候,他对自己在文坛的声名也抱有相当的自负。如他在晚年的诗中曾说:“平生诗句传天下,白首还家自灌园。”(《秋思绝句》)又在80岁时,为自己的画像作赞说:“名动高皇,语触秦桧。身老空山,文传海外。五十年间,死尽流辈。老子无才,山僧不会。”(《放翁自赞》)虽然晚年的陆游时常感叹功业未遂,但对自己在诗歌上的成就却不乏自信。
正是因为陆游在诗坛已然享有巨大的声誉,遂使其即便退居乡里,也仍然不乏年轻后进追随左右。这其中登门拜访求教的,既有相邻的浙东地区的士人,也有远自江西的士人,同时也有些士人通过寄赠诗卷来请益。山阴的苏氏兄弟,因为与陆游有乡土之谊,所以交往颇为密切。在苏氏兄弟五人(瀛、汭、泂、滨、潞)中,陆游的晚年诗歌中提及了三人。他在赠给苏潞(赵叟)的诗《赠苏赵叟兄弟》中说:
君家真徳门,才杰森衮衮。托契则甚深,所恨相识晩。携文数过我,每读必三反;譬如天廐驹,真是渥洼产。闭门万卷读,更要极源本。才难圣所叹,期子敢不远。*按:钱仲联在题解中,介绍了苏氏五兄弟的名号、排行。
后来当苏潞参加省试时,他也作《送苏赵叟赴省试》相送。而与他过从最密也最受青眼的则是苏泂(召叟)。他在《赠苏召叟》中说:“苏子出俦辈,翩如天际鸿。才华刮眼瞙,文字愈头风。岂止千人见,真当四海空。老夫虽耄矣,此论不妨公。”后来苏泂入蜀,他作《送苏召叟秀才入蜀效宛陵先生体》《简苏邵叟》等诗相送,对苏泂的诗卷赞赏有加。而在现存的苏泂《泠然斋集》中,也有多首诗歌是写给陆游的。此外,陆游也有《题苏虞叟岩壑隐居》一诗赠给苏汭(虞叟)。
同属浙东地区的婺州与绍兴府紧邻,那里兰溪县的杜氏兄弟也与陆游过从甚密。当杜氏兄弟的父亲去世,陆游作《哭杜府君》一诗,记述了他与杜氏兄弟的交往:
叔高初过我,风度何玉立,超然众客中,可慕不待揖。入都多宾友,伯高数来集,质如琮璧润,气等芝兰袭。晩乃过仲高,午日晒行笠,匆匆遽别去,怅望空怏悒。有如此三高,青紫何足拾,岂无知之者,相视莫维絷。穷鱼虽相悯,可愧吐微湿,亦知尊公贤,何止盖乡邑。向风每拳拳,识面真汲汲,秋风忽闻讣,执书叹以泣,造门不自决,追悔今何及。又闻著书富,手泽溢巾笈,哀毁要无益,遗稿勤缀缉。*按:钱仲联在题解中,介绍了杜氏五兄弟的姓字。
杜氏兄弟也是五人(伯高、仲高、叔高、季高、幼高),但陆游在诗中只提及了伯高、仲高和叔高,说明与这三兄弟交往颇多。嘉泰二年(1202)春,杜叔高(杜斿)曾于雨雪天气中拜访了陆游,并在陆游家中留宿一夜。陆游在《杜叔高秀才雨雪中相过留一宿而别口诵此诗送之》一诗中有这样的记述:
久客方知行路难,关山无际水漫漫。风吹欲倒孤城远,雪落如簁野寺寒。
暮挈衣囊投土室,晨沽村酒挂驴鞍。文章一字无人识,胸次徒劳万卷蟠。
显然,诗中对于杜斿的怀才不遇表示了同情。此外,嘉泰二年冬,陆游在临安时,曾作《独坐有怀杜伯高》一诗怀念杜伯高(杜旟)。
另外一位兰溪县的应致远秀才,则在绍熙五年(1194)冬,冒雪拜会了陆游,向其请教诗艺。这位应秀才先前曾拜访了名位甚高的姜特立,而姜特立向他推荐了诗坛耆宿陆游。陆游在《赠应秀才》中叙述了其前来拜访的情形:
过宋不见元城公,渡淮不见陈了翁,当时人人皆太息,至今海内倾高风。老夫七十居乡县,龌龊龙钟何足见;辱君雪里来叩门,自说辛勤求识面。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知君此外无他求,有求宁踏三山路。*按:钱仲联在题解中,考证出应致远曾拜会过姜特立,姜向其推荐了陆游。
大概是有感于应秀才的赤忱,所以陆游写了此首赠诗,并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诗歌写作的看法。除了临近的浙东地区的士人来拜会陆游之外,也有远自江西的士人亲自登门拜访,其中就有一位名叫谢正之的秀才。陆游在《赠谢正之秀才》一诗中说:

从诗中的叙述来看,这位谢秀才先前拜会过杨万里,杨万里并曾为其题诗,*杨万里:《赠旴江谢正之》,见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39,第2050页。后来他又拜会了陆游。这种在诗坛名流之间拜求品题的行为,大概正反映了当时江湖诗人的一种风气吧。
在登门求教之外,也有一些诗人将自己的诗卷寄给陆游,请其品题。如溧阳丞周文璞曾寄来诗卷,陆游在《寄溧阳周丞文璞,周寄诗卷甚可喜》中云:
满握珠玑何自来,晴窗初喜折书开。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异才。
隔阔经年如许进,超腾它日若为陪。山阴道上霜天好,安得相从赋早梅。
从诗中的语气来看,陆游与周文璞早就相识,所以表示出对于其诗艺大进的欣喜之情。另外,他也曾为江西庐陵的萧彦毓的诗卷写了题诗,并发表了自己的诗歌见解。*陆游:《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50,第3020页。
除此之外,晚年家居的陆游,还与当时一些已经成名的后进诗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与远在江西的赵蕃(昌父)、徐文卿(斯远),都有诗歌往还,尤其是写了多首诗歌寄赠赵蕃,表达对这位后进诗人的殷殷期待。*按:陆游晚年家居,寄给徐文卿的诗歌,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如下卷:卷30《寄徐秀才斯远并呈庄贤良器之》,第2057页;卷45《寄赵昌甫并简徐斯远》,第2762页。此外,专门与赵蕃往还的诗歌有:卷55《故人赵昌甫久不相闻,寄三诗皆杰作页,辄以长句奉酬》,第3250页;卷62《读赵昌甫诗卷》,第3550页;卷69《得赵昌甫寄予及子遹诗》,第3854页;卷80《寄赵昌甫》,第4328页。著名的江湖诗人刘过,在陆游家居的时候也曾拜会过他。*按:绍熙四年(1193)春,陆游有诗赠刘过。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27《赠刘改之秀才》,第1878页。又,刘过也有诗述及与陆游的会面,见(宋)刘过撰:《龙洲集》卷5《放翁坐上》,第36页;卷11《水龙吟·寄陆放翁》,第1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这些情形,学界多已熟知,不拟详说。
通过这些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晚年的陆游即使家居乡野,但作为一个享有崇高声望的诗人,仍然在当时诗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二)陆游的晚年出处
晚年的陆游,不仅作为一个诗坛耆宿而存在,作为一个喜言恢复的昔日主战派官僚,他在晚年的政治动向,同样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关注。在陆游晚年家居的岁月里,朝堂政治正发生着变化。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和韩侂胄联手,迫使光宗退位,拥立宁宗,朝廷局势为之一变。但一年半之后,韩侂胄就将赵汝愚贬逐,自己独揽大权。随后,他为了打击政敌赵汝愚的支持者,将朱熹为首的一大批士大夫列入“伪学党籍”,予以禁锢。*关于“庆元党禁”与政治、道学关系的相关研究,参看谢康伦著:《论伪学之禁》,何冠环译,收入[美]海格尔(John W. Haeger)主编:《宋史论文选集》,陶晋升等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版。他的这一极端做法,在朝野间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在这样一个政治局面下,陆游晚年的短暂出仕,尤其是他与韩侂胄的接近,就受到同辈士大夫的瞩目。
陆游在朝为官时,与当时一批名流士大夫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人关系,如周必大、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和朱熹等,他们大体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属于同一阵营的人物。即使当他们在各自退归乡里之后,也仍然声气相通,音信不断。因之,在此政局翻覆之间,个人如何出处,彼此之间也发生着微妙的影响。
陆游离开朝廷之后,在绍熙三年秋,他曾写有一首诗曰《秋夜读书有感》,诗中云:
鬓毛焦秃齿牙疎,老病灯前未废书。卷里光阴能属我,人间声利久忘渠。穷山藏拙犹嫌浅,粝饭支羸不愿余。雨露安能泽枯朽,故人枉是费吹嘘。(自注:时所闻如此。)
据诗中所述,说明在陆游归乡之后,朝廷里仍然有人试图让他重新出来做官,但后来并无什么动静。而在绍熙五年(1194)的春、夏之交,杨万里则写了一首诗寄赠给他,诗中说:
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消息,月明千里两相思。
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杨万里:《寄陆务观》,见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36,第1868页。按:宋人罗大经所撰《鹤林玉露》中载有此诗,解释为杨万里因陆游为韩侂胄撰写《南园记》而作此诗规谏。但经现代学者考证,此说有违事实,不可为据。(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4“陆放翁”条,第71页。于北山的考证,见于北山:《杨万里年谱》,第479页,于蕴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辛更儒的考证,参见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第1867页。
当时杨万里已经辞官居乡有两年之久,从诗中的意思来看,似乎在规讽对方既然已经享有诗坛盛名,也就不必以出仕为念。劝勉的意味相当明显。而就在此诗写后不久,朝廷中就发生拥立宁宗继位的事件,为韩侂胄跻身权位提供了契机。
韩侂胄在独掌大权之后,先于庆元二年(1196)实施“伪学之禁”,接着又于庆元三年(1197)开列“伪学党籍”,*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第269—275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一大批士大夫受到打击,而朱熹作为赵汝愚的主要支持者,则首当其冲。*关于庆元年间朱熹遭受政治禁锢的情形,参看韦政通:《“庆元学禁”中的朱熹》,见钟彩钧:《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上册),第123—14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但在这段艰难岁月里,陆游却与朱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时常有书信往来和诗文应酬。庆元三年,朱熹的朋友严居厚前往浙东做官,他为其题诗云:
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画图中。平章个里无穷事,要见三山老放翁。(自注:谓陆务观。时严居厚之官剡中。)*朱熹:《题严居厚溪庄图》,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第528页。
后来严居厚到了浙东,果然拜访了陆游,而陆游就根据朱熹这首诗写了一首次韵之作。*陆游:《次朱元晦韵题严居厚溪庄图》,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36,第2334页。在这一年的年末,朱熹还给陆游寄了特殊的礼物(纸被),陆游则在答谢的诗中,拜托朱熹为自己的书斋老学庵作铭。其诗《谢朱元晦寄纸被》云:
木枕藜床席见经,卧看飘雪入窗棂。布衾纸被元相似,只欠高人为作铭。
但随着“伪学党籍”的公布,朱熹却犹豫着不敢下笔。*⑤朱熹:《答巩仲至》之四,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4,第3094,3094页。后来在庆元五年(1199),朱熹又多次致书陆游,拜托他为自己学生方士繇的父亲方丰之的诗集作序。*⑥⑨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1387,1367,136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而陆游也遵照要求,写了集序。*陆游:《方德亨诗集序》,见《渭南文集》卷14,第2105页。
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交情,朱熹对于陆游晚年的官场动向表示了极大的关切。这主要见于他给巩丰(仲至)的多封书信中,如他在现存给巩丰的第四封书信中说:
放翁诗书录寄,幸甚。此亦得其近书,笔力愈精健。顷尝忧其迹太近、能太高,或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此晚节,计今决可免矣。此亦非细事也。⑤

放翁近报亦已挂冠,盖自不得不尔。近有人自日边来,云今春议者欲起洪景卢与此老付以史笔,置局湖山,以就闲旷。已而当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寝。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来,亦非细事。*朱熹:《答巩仲至》之五,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4,第3098页。
据考证,此信写于庆元五年五月⑨,而陆游恰在本月致仕*陆游:《五月七日拜致仕勑口号》,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39,第2489页。。也就是说,陆游致仕不久,朱熹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此外,朱熹还听闻当时朝廷中有请陆游出来修史的打算,而他却觉得不合适。庆元六年(1200)闰二月,已经致仕的陆游得以进职华文阁待制。朱熹在随后不久给巩丰的信中提及此事说:“放翁且喜结局,不是小事,尚未得以书贺之。”*朱熹:《答巩仲至》之二十,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4,第3113页。据束景南考证,此信作于庆元六年二月。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1387页。表现出对老友晚年能获此荣衔的欣喜之情,而“结局”二字则显得意味深长。巩丰出身浙东地区,与陆游有着很深的交往。朱熹以这种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许也是间接地希望陆游能知道吧。

关于陆游的晚节问题,后世既多争议,现代学者也多有辩白,可谓聚讼纷纭,非本文所能给出定论。但就陆游晚年的这段出处来看,他无疑也是当时权臣韩侂胄试图笼络的一个对象,也正因为他与韩侂胄的接近,从而引起了部分在野士大夫的非议。也就是说,当时朝野双方都相当看重陆游。
开禧二年(1206)北伐失败,次年韩侂胄即遭到诛杀,史弥远上台,政治局面又为之一变。因为陆游与韩侂胄有过文字上的交往,在新的当权者看来,这明显是政治上的一个污点,从而遭到了“落职”的处分,事在嘉定元年(1208)之春。*关于陆游落职时间的考订,参看邱鸣皋:《陆游评传》,第251—253页。据周密关于此事的记述说:
韩平原南园既成,遂以记属之陆务观,务观辞不获,遂以其归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满溢勇退之意甚婉。韩不能用其语,遂致于败。务观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对,以太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庄兼外制,行词云:“山林之兴方适,已遂挂冠;子孙之累未忘,胡为改节。虽文人不顾于细行,而贤者责备于《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寖跻膴仕。功名已老,潇然鉴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贵甚长安之纸价。岂谓宜休之晩节,蔽于不义之浮云。深刻大书,固可追于前辈;高风劲节,得无愧于古人。时以是而深讥,朕亦为之嘅叹。二疏旣远,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来归,朕岂忘善养之道。勉图终去,服我宽恩。*周密:《浩然斋雅谈》,第5—6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从朝廷颁降的这份诏命来看,不仅陆游晚年的重新出仕被视为改节,他为韩侂胄撰写的《南园记》等文字也是一个主要的罪状。陆游的晚节问题,大概也因为这个“官方意见”而被“定性”了吧。
根据上述考察,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名退居士大夫,陆游即使僻处乡里,也会因其在诗坛享有的声望,而受到后进诗人的崇敬。他不仅能够吸引浙东地区的士人追随左右,甚至连远在江西的诗人也会登门求教或寄赠诗卷。而从他与当时诗坛新秀的密切交往,更可以看出他在诗坛仍然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有声望的昔日官僚,他的晚年政治动向也颇受瞩目。他不仅是当权者试图笼络的对象,也是在野士大夫视为对抗当权者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与韩侂胄的文字应酬,他的晚年出仕,才会被视为是一个政治污点。这些皆足以说明,陆游即使退居乡里,他也不是一个明清史意义上的“乡绅”或“地方精英”,而是具有全国性声望和影响力的南宋“退居型士大夫”。
三、晚年陆游的乡居意识
南宋官员退出官场之后,很多人会选择回乡定居,这几乎是南宋士大夫出处的一个普遍模式。但是这模式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人会定居在城市,如周必大、范成大;有人则定居在乡村,如陆游、杨万里和辛弃疾,后者似乎要多一些。这种居住地的不同,多少会影响到他们的晚年生活方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写作。陆游晚年的诗歌中充溢着乡村气息,无疑就与其长久身居乡村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陆游自己的乡居意识又是如何呢?
在讨论陆游的晚年身份时,我们发现,陆游将自己离开官场这一行为称之为“退归”“退处”“退闲”,而将回到故乡定居称之为“归休”“归老”。这主要是就其与官场、故乡的关系而言。但是,如果从乡居生活这一面来看,我们又会发现,陆游将自己与乡村的关系定义为“归耕”“退耕”或“躬耕”,尤其是庆元五年(1199)致仕之后,这种“归耕”意识越发强烈。
在最初退居乡间的十年间,陆游偶尔会在诗歌中将自己的乡间生活称之“归耕”或“退耕”。如他在绍熙五年冬所写的《三峡歌序》中说:“乾道庚寅,予始入蜀,上下三峡屡矣。后二十五年,归耕山阴。”又在庆元二年(1196)年的《春思》诗中说:“七十老翁身退耕,可怜未减旧风情。”可以说,在最初十年的乡居生活中,陆游并没有很强的“归耕”意识。
但是庆元五年(1199)致仕之后,陆游却开始频繁地在诗中使用“归耕”一词,来指称自己的居乡生活。这在他致仕那年所写的诗歌中立刻表现了出来,如他在该年夏天接到致仕勑文之后所写《致仕后即事》一诗中就说:“归耕所愿杂民编,乍脱朝衫喜欲颠。但得吾儿能力穑,不请半俸更超然。”同年秋天,他又作诗《晨起颇寒,饮少酒,作草数幅》云:“衣食无多悉自营,今年真个是归耕。”从这两首诗来看,致仕对于陆游来说,意味着官员身份的真正失去;尤其是官俸收入的减少,也使自己更依赖于家庭自身的经济收入来源。换言之,他觉得自己更接近于乡野间耕作的平民百姓了。这种意识此后频频流露,见于以下诗例之中:
湖上归耕一病翁,此心非复少年同。(《老病》)
妄出真成错,归耕惜已迟。(《自勉》)
四十余年食太仓,赐骸恩许返耕桑。(《村居书事》)
宦游五十年,天遣还农桑。(《山泽》)
我今余年忽八十,归耕幸得安山林。(《杂言示子聿》)
老荷宽恩许退耕,丝毫无报亦何情。(《书感》)
胎发茸茸绿映巾,归耕犹是太平民。(《自贺》)
退耕镜湖上,风雨有茅屋。(《寄子虡》)
壮志悲垂老,归耕愿太平。(《夜雨》)
从这些诗句中“归耕”一词的使用来看,这明显是用于指称自己的乡居生活。但是考虑到陆游的实际身份和年龄、身体状况,我们其实很难相信陆游会真正参与了农事劳作。我想这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表示自己失去了官员身份,在乡间居住,与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与上述诗句的“归耕”意识相呼应的,则是从退居山阴开始,陆游喜欢在诗中以“老农”一词来自称。这种情形,在致仕以前的十年间只是偶尔出现,计有以下数例:
若耶老农识几字,也与二事日相关。(《饮酒望西山戏咏》)
陆子真老农,破屋依颓垣。(《岁暮风雨》)
莫笑蓬门雀可罗,老农正要养天和。(《蓬门》)
白首老农愁破处,梦回高枕听潺潺。(《喜雨》)
坐令事业见真儒,老农不恨老耕鉏。(《读书》)
但是在陆游致仕之后,尤其是嘉泰三年(1203)再次致仕之后,越是接近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陆游在诗中越是频繁地使用“老农”一词。如嘉泰四年(1204年),他有诗云:
老农手自闢幽圃,土膏如肪水如乳。(《菜羮》)
而在开禧年间(1205—1207),他在诗中以“老农”自称者有:
老农虽瘠喜牛肥,回首红尘万事非。(《谢君寄一犁春雨图求诗,为作绝句》)
谢事还家一老农,悠然高卧听晨舂。(《枕上作》)
龚子吴中第一流,老农何幸接英游。(《寄龚立道》)
老农自得当年乐,痴子方争后世名。(《晓思》)
嘉定元年(1208)、二年(1209),是陆游生命的最后两年,这时他在诗中使用“老农”一词最多:
明诏裕民闻屡下,老农何以报君恩?(《肩舆至湖桑埭》)
稻饭似珠菰似玉,老农此味有谁知?(《邻人送菰菜》)
故里还初服,明恩念老农。(《书壁》)
老农无他求,一饱万事足。(《后杂兴》)
老农饭粟出躬畊,扪腹何殊享大烹。(《种菜》)
我今稽山一老农,百岁不死知何益?(《北窗》)
老农自喜知时节,夜半呼儿起饭牛。(《喜雨》)
从这些诗句来看,随着陆游在乡居居住的时间越长,年岁越大,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介百姓。虽然他实际上不会参与耕作,但从心理上却把自己看成了是一个老农。较之于他中年时期炽热的功名之念,晚年的陆游必定悲哀地意识到建功立业已经不再可能,所以他才会将自己视为是平凡的“老农”。
但是,陆游的这种“归耕”意识,这种自比“老农”的心态,倒也未必全是故作姿态,而是有其现实基础。因为陆游已经意识到,出仕与农耕之间本并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如他曾在《夜过鲁墟》中说道:“士生本耕稼,时来偶卿相。”又曾在《杂兴》中言及:“谋生在衣食,不仕当作农。”也就是说,在陆游看来,士大夫本是出身于农耕阶层,因为偶然的机遇才得以入仕为官,并非天生注定;所以当其离开官场,就应回到田野从事农耕,以此作为经济收入的来源。他的这种意识,反映出自唐代贵族社会衰替之后,新兴的宋代官僚自农耕阶层通过科举跻身官僚阶层一个真实面貌。应当说,正是在经历了唐宋之间的这种社会转型之后,宋代的官僚对于仕宦的不确定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陆游家族自身的兴衰,也给了他对于仕与农之间关系的一个直接启示。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说:
予尝悲士之仕者,苟名位而已,则为负国;必无负焉,则危身害家,忧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业,一舍而去,复其故甚难。予先世本鲁墟农家,自祥符间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穷通显晦所不论,竟无一人得归故业者。室庐、桑麻、果树、沟地之属,悉已芜没。族党散徙四方,盖有不知所之者。过鲁墟,未尝不太息兴怀,至于流涕也。*陆游:《陈氏老传》,见《渭南文集》卷23,第2191页。
又在开禧元年(1205)的另一篇文章中说:
吴越在五代及宋兴,最为安乐少事,然废立诛杀犹如此。方斯时,吾家先世守农桑之业于鲁墟、梅市之间,无一人仕于其国者,真保家之法也。*陆游:《跋吴越备史》,见《渭南文集》卷30,第2276页。
从陆游晚年的这两篇文字中可以看出,陆游的家族在五代时期一直是以农耕为业,直到他的高祖陆轸,才在真宗祥符年间以进士起家,*按:陆游自述:“宋祥符中,赠太傅讳轸以进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馆”。陆游:《奉直大夫陆公墓志铭》,见《渭南文集》卷35,第2329页。至陆游之晚年,已有两百年之久。然而随着家族成员的仕宦流徙,原来的家族聚集地鲁墟反而被荒废了。由此陆游认识到,如果因为出仕而丢弃了耕稼之业,一旦要想恢复就很困难。陆游的这种意识,也流露在他的《示子孙》诗中:
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
吾家世守农桑业,一挂朝衣即力耕。汝但从师勤学问,不须念我叱牛声。
显然,陆游在这首诗中,将世守农桑当成了自己的家风。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陆游才屡屡在诗中表达出世代为农的愿望。其中较为明显者有:
为农世世乐有余,寄语儿曹勿轻舍。(《江村初夏》)
衣食粗足官赋足,何妨世世作耕农。(《龟堂杂题》)
身誓生生辞禄食,家当世世守农耕。(《视东皋归小酌》)
安得子孙常念此,不妨世世业耕桑。(《夜意》)
为农幸有家风在,百世相传更勿疑。(《农家》)
一生衣食财取足,百世何妨常作农。(《春日杂兴》)
在他写给儿孙的一些诗中,也直接表达了希望儿孙辈能够以农耕为业的想法。如他庆元六年(1200)作《读何斯举黄州秋居杂咏次其韵》云:“倚墙有鉏耰,当户有杼轴。虽云生产薄,桑麻亦满目。况承先人教,藏书令汝读。求仁固不远,所要念念熟。喟然语儿子,勿媿藜苋腹,亦勿慕虚名,守此不啻足。”这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以耕读传家。他又在开禧三年(1207)作《示儿孙辈》云:“昔忝诸生后,初非一世豪。但希乡有秩,敢望郡功曹。敛版宁为辱?扶犂亦足高。儿孙勿妄想,底处不徒劳。”这是告诫子孙对于仕宦不要抱有太大奢望,农耕也无不可。他另在嘉定元年(1208)作《短歌示诸稚》云:“向来名宦事,回首如弃唾。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如其尽为农,亦未可吊贺。归耕岂不佳,努力求寡过。”当时陆游身边的孙子辈逐渐长大,他固然希望其中能有读书成材者,但是如果这些孙子能以农耕为业,他也觉得可以接受。
当然,我们会怀疑陆游的这些说法是否只是一种诗人式的矫饰,故作违心之论。但是如果我们结合现存的《放翁家训》来看,发现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现存的《放翁家训》中有这样两条记载:
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杜门穷经,不应举,不求仕,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荣达,策之下也。舍此三者,则无策矣。
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足矣。若能布衣草履从事农圃,足迹不至城市,弥是佳事……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5“放翁家训”条,第153、157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放翁家训》大体带有一种遗嘱的性质,所以其中故作违心之论的可能性很小。根据家训中对于子孙的告诫来看,陆游无疑主张子孙应当读书受教育,令“书种不绝”;但是由于宋代社会高度的科举竞争,“仕宦不可常”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法则,在无法做官的情形下,以农耕为业也可接受,但切不可为市井小人之事。而他提出“农耕为业、杜门穷经、安于小官”三策,也应当是基于这种“仕宦不可常”的前提而做出的一种安排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陆游晚年诗中的“归耕”意识、自比“老农”的表述,并不全是一种故作姿态,而是唐宋社会转型后,宋代科举士大夫所必然面临的一种现实选择。陆游家族自身的兴衰,也给了他一定启示,觉得应当以世守农桑作为家风,代代传承。所以,陆游希望子孙能以农耕为业,并非完全是矫情。从现存的放翁家训中,我们可以发现,陆游的这种意识,其实正是以宋代社会“仕宦不可常”的这一严峻现实为前提,它的背后则是宋代社会的高度竞争与流动性。
四、结语: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
陆游自六十五岁离开官场之后,在家居山阴的近二十年(1189—1209)光阴里,写下了六千多首诗歌,而且越到晚年密度越高,可以说陆游几乎是以写日记的方式在写诗。*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我本以为是自己的独得之秘,但后来发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早已指出这点。[日]吉川幸次郎著:《宋元明诗概说》,第118页,李庆、骆玉明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这样,陆游就将自己的晚年生活,不避琐细地都写入了诗中,展现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其内容之生动、细节之丰富,不仅为考察其晚年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使得我们可以从中寻绎其思想意识的脉络。这样一部近似于日记体式的《剑南诗稿》,几乎可以精确到每首诗写于哪个月份,无疑也为研究南宋众多长期家居的士大夫提供了一份绝佳的样本。正是通过对陆游晚年诗歌的仔细梳理,在考察其晚年声望、出处与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个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概念。
这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基于陆游晚年的自我意识。通过对其诗歌中语词使用的分析,我们发现:当陆游在表述自己脱离官场这一行为时,他喜欢使用“退归”“退处”“退闲”等以“退”字为核心的语词,表现出与官场的距离感;而当涉及回归故乡家居这一事实时,他则倾向于使用“归休”“归老”等以“归”字为核心的语词,表现出对故乡的亲近感。也就是说,陆游在诗歌中使用了两套语词模式来描述自己脱离官场、定居家乡的状态。但是,当陆游提及自己晚年的身份时,他则比较明确地将自身定义为“退士”;当同时涉及脱离官场、回乡定居这两方面情形时,他则喜用“退居”一词。因此,如果依照陆游的自我意识,运用现代学术语言来做界定,陆游应当被称为“南宋退居型士大夫”。
我们进而发现,在陆游所使用的“退”与“归”这两套语词模式背后,反映的正是南宋官僚士大夫的出处模式,即在官场与故乡之间的去与来、脱离与回归。北宋士大夫在游宦生涯中,往往会选择在任职所在地置产定居,不一定回到故乡;而南宋士大夫在退出官场之后,通常是返回故乡定居。这种两宋之际士大夫出处模式的转换,体现在了陆游的诗歌之中。与此同时,陆游诗歌中很少使用“隐”字来描述自己的家居生活,这或许表明那些退出官场后仍然享受祠禄、半俸等待遇的退居士大夫,在意识里已不再把自己的归乡定居视作隐居。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古诗歌里弥漫的山林隐逸气息在南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消退,而村居的田园风味却多了起来。
其次,本文考察了陆游的晚年声望和出处,意在说明即使是作为脱离官场的退居士大夫,他仍然可以享有全国性的声望,甚至在政坛上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发现,作为享有盛誉的诗坛耆宿,陆游即使僻处乡野,也仍然吸引了众多的后进诗人追随左右,不仅浙东地区的士人与之过从甚密,甚至有江西地区的诗人远道而来登门拜访。同时他也与当时的诗坛新秀保持密切的交往。另一方面,在“庆元党禁”的政治氛围下,他既是当权者韩侂胄试图笼络的对象,也是对韩侂胄不满的在野士大夫观瞻、劝阻的对象,朱熹对其晚年出处的关切即说明了这一点。当党禁解除,韩侂胄采取与昔日政敌合作的姿态时,陆游再次出仕,且与韩侂胄有文字交往,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非议。结果,在史弥远上台执政之后,他因此遭到了“落职”的处分。通过对诗坛和政坛这两方面情形的考察,我们当可意识到,陆游作为退居士大夫仍然有着全国性的声望和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因此,陆游这样的南宋“退居型士大夫”,不应等同于明清史意义上的“乡绅”或“地方精英”。
再次,作为长期定居乡间的退居士大夫,陆游的乡居意识如何,也是本文关切的一个要点。通过对其诗中语词使用的考察,我们发现,在陆游初次致仕之后,他的诗中即表现出了一种“归耕”意识,而且此后一直喜用“老农”一词来自称。在我看来,这其中固然有失去官员身份之后的解嘲意味,但也并非全是故作姿态。因为陆游已经意识到:“士生本耕稼,时来偶卿相”,“谋生在衣食,不仕当作农。”宋代士大夫本是出自于农耕阶层,当其离开官场之后,也应继续以农耕为业,仕与农之间并没有什么天然的界限。这种意识的出现,应是唐宋社会转型之后的一个产物。当然,陆游家族自身的兴衰也给了他一个启示,要以世守农桑作为家风世代传承,这体现在他一系列写给儿孙要世代为农的诗作之中。这些虽然看起来似乎有些故作姿态,但是结合现存的陆游家训来看,却反映出在宋代高度科举竞争的社会中,“仕宦不可常”作为一个社会法则已经深深影响到士大夫官员对于子孙的期待,因此,作为一个现实的选择,农耕为业并非不可接受。
简言之,本文认为,陆游是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一个代表。这些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基本特征是:他们曾经长期在朝为官,脱离官场后,基本返回故乡定居;他们虽身处乡野,但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化声望和政治影响力,甚至有可能东山再起;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仕宦不可常”的社会法则,能够接受子孙以农耕为业。我认为,陆游细节丰富的《剑南诗稿》充分揭示了这些特质,倘若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陆游的晚年诗歌,我们或许又会进入一片新天地。
【责任编辑:王建平;实习编辑:杨孟葳】
【收稿日期】2015-10-1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1-0029-14
(作者简介:林岩,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