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路(2015)
2016-06-14
我于1938年1月18日在抗战烽火中艰难出生,苦难成长。少年从拾荒到叫卖,整天在死亡线上挣扎,什么快乐的儿童,上学的少年,在我都是天方夜谭,痴心妄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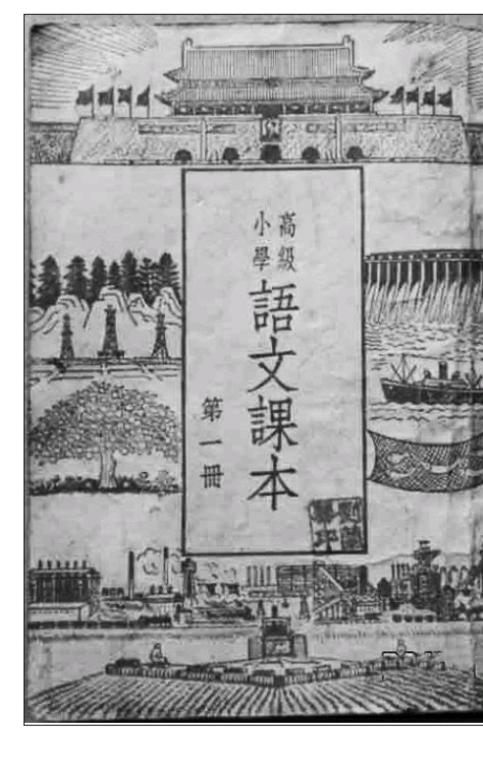
在我的记忆中,河北省肥乡县大西韩村土改前一年(1946年)春天,当时我八岁。村里传出要解放了,小孩可以上学了。学校设在大西韩西街西头路北一个破庙里,先让孩子们去看看,等到把庙里的神像拆掉后,就可开学了。宗礼兄和我一同去的。那天去的人很多。一进大门,看见一个大木板上贴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两个字:人、入。老师赵金山(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文革”中喝敌敌畏自杀身亡)穿着整齐,站在木板旁,指点着那两个字,让来到这里的家长和学生学习,很多人不认识,孩子们更不知所措。在另一老师处,登记上名字,就算报名了。未来的教室里有一些可怕的神像,有的小孩子都吓哭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小学。不久,就开始土改了,我也失去了上小学的机会。
当时的小学学制是一至四年级,五至六年级称为高级小学即高小。我在1949年以后,基本不做小生意了,整天跟着父亲在地里干农活。春耕、播种、锄草、秋收、种菜、打场,样样都干。晚上,到大哥王宗仁办的扫盲班读书识字。1951年冬天,传来肥乡县文教科的消息,要在大西韩村试办民校高级班,相当于高小,招收扫盲班里年龄小的和小学四级毕业没有考上高小的学生,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师和扫盲班教师。我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别人告诉我,只考一个小作文。我请教他怎么写?他说:只要在作文中用上一个名词,就能考上。他让我在作文中,用上“悲观失望”这个词。我在考试时,真用上了:想起自己的前途很悲观失望,但考上民校高级班,就可以学文化,建设新中国了。我果然考上了大西韩民校高级班。在1952年春天开学时,成为一名民校高级班的学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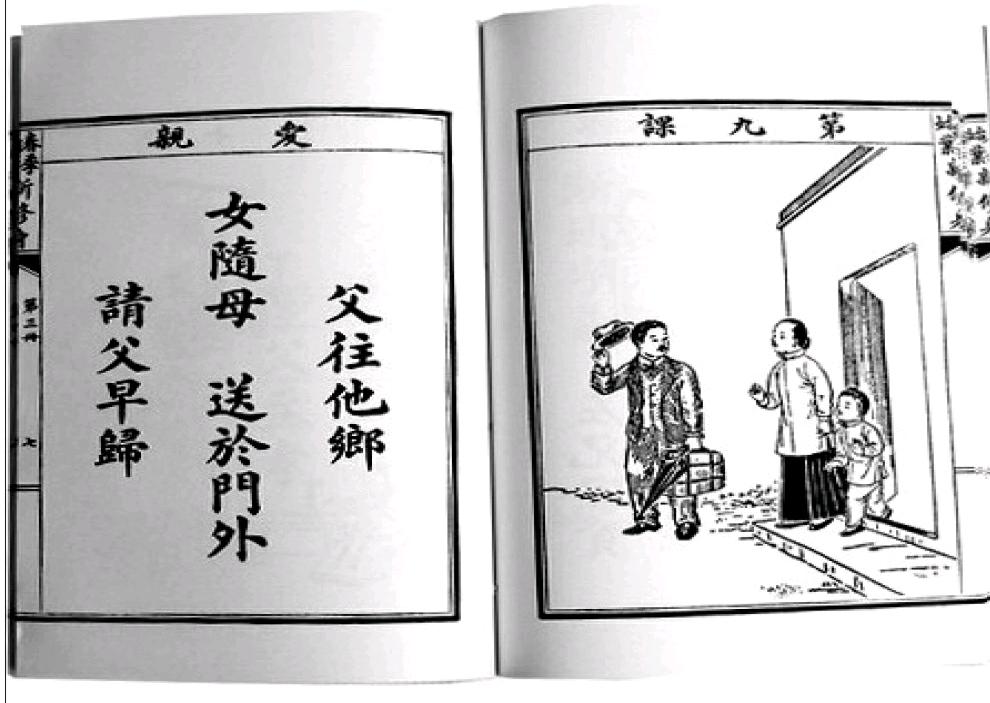
大西韩民校高级班设在北街路东一个土改时被划地主的家里。大西韩小学也设在该院,当年招生四十多人,男女各半。所用教材为正规高小的课本。设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各科。任课教师是从小学挑出的水平较高的老师。教语文的是郭廷信老师,态度和蔼可亲,认真负责。一年后,调到西张庄正式高小任教。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上吊自杀。后来,从县城调来张亚川任语文和历史课老师,听说是国民党中下级军官,镇反时,自杀于肥乡县监狱。教数学的是禄家堡林浩然老师。张亚川老师在和同学们聊天时,告诉我们:在南京等大城市,是不能随便过马路的。我们才第一次知道,过马路要按红绿灯的讯号,让过才能通行。这对我们农村孩子来说,都是特大新闻。学校的教室很简陋,学校没有课桌,十几块长木板用砖架起来当桌子,凳子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搬来的。和小学共同使用一个电铃作为上下课的讯号。没有家庭作业,每位老师都让学生在自己的课堂上写完作业。大部分是走读生,中午回家吃饭,下午两节课后,就放学回家。基本没有体育活动。到1953年春天,校长从县城买来一个篮球,我们才第一次看见篮球,同学们都不知如何玩。更没有排球、乒乓球供同学们进行体育活动了。在读民校高级班时,我住在同学赵华家里,他家养了很多鸽子。春天有很多鸽子都被南街韩姓一家的鸽子井给引走了。一天深夜,夜黑风高,王梦志、赵华和我,去韩家鸽子井偷鸽子。一人放哨,观察动静,一人钻进鸽子井,一人用布将鸽子井口封锁,防止鸽子飞出来。那个下井人,抓了两口袋鸽子,足有六十多只,背回家里,杀死、去毛、开肚,除去内脏,洗干净,放作料,煮了两大锅鸽子肉。我们三人吃了好几天,以示报复韩家有意引诱赵家鸽子之仇。
在民校高级班,没有上足两年,1953年3月,学校接到肥乡县文教科通知,从1953年起,全国改为暑期招生。大西韩民校高级班停办,改为正式高级小学。但是我们的高小课程尚未学完,只好在不足两个月内,匆匆学完高小课程,不用经过毕业考试,就算完成了高小课程,给予毕业。
1953年5月底6月初,老师们两个多月快马加鞭地教完了高小最后一学期课程,学生们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教材,就算高小课程结束了,可以参加各地举行的初中招生考试了。当时各省,一个省内不同地区,同一个地区不同学校,都可以在不同时间独立自主地招生。我们在六月初,十几个男女同学约定一起去河南省安阳一中参加考试。由学校开出介绍信,由年龄较大的同学带队就出发了。由大西韩步行四十五华里到达邯郸市火车站,每个人花两元人民币买了去安阳的火车票。坐火车南行,同学们个个兴高采烈,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省,笫一次坐火车,对于十五六岁的农村学生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了河南省安阳市。步行找到一中,报名、休息、念书、吃饭,学校给集体安排教室住宿。第二天早晨参观了安阳一中美丽的校园,处处绿树、青草、鲜花,我幻想着,期待着,若能来这里读三年初中该有多好啊!招生考试开始了,上午考语文、数学,中午12:30分看第一榜。找来找去,我们来的十六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榜上有名。看完榜,十一个人直奔火车站,四个同学去参观袁世凯墓,我一个人留下参加下午的考试。下午,先进行了体检和面试,然后考历史、地理和自然。晚上,参观袁世凯墓的四个同学回到学校,找一个空教室住了一夜。第二天带的钱都不够买回邯郸的火车票了,他们决定先步行一段,再买车票回邯郸。五个十四五岁的农村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出省远行,真不知如何回邯郸。走出安阳沿铁路北行,边走边问路,到中午才到漳河南岸。漳河是河南省与河北省的分界线,河水不宽,水流不急,但也不知深浅。找到河南岸的摆渡船,才把我们摆渡过河。到了河北省,大家有了亲切感,脸上有了笑容,紧张的心情才得以缓解。找到火车站,每人一元火车票,顺利回到邯郸市。在从邯郸市步行四十五回家的路上,一个同学问我:“你是如何用‘从容一词造句的?”我说我根本不知这个词含义是什么,只能胡编乱造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看见河水,第一次过河,第一次坐船,这可是终生难忘的啊!回到家里,学校放暑假了,老师回家了,同学也解散了。我幻想着能收到安阳一中的录取通知书,但一个月过去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一考不中,无功而返。千辛万苦,一无所获!
1953年5月赴河南安阳考初中无功而返。很多同学灰心丧气,认为民校高级班白念了。住校的同学取走了被褥和凳子,回家不来了。本村同学也很少见面,只有一条约定:今后若得到通知哪里有招生考试,一定相互转告,寻找新的求学之路。 我回到家之后。天天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在家无事可干。宗礼兄从西张庄高小毕业,考进了邯郸市国棉一厂当电工。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在夜深人静时,可隐约听到邯郸市火车汽笛的鸣叫声 ,白天十二点可听到邯郸国棉一厂工人上下班的拉笛声,这都是对我的召唤,离开农村,到城市上班,成为我当时唯一的强烈愿望和希望。任何小生意都不想干了,我毕竟是高小毕业的文化人啊!做买卖,沿街叫卖,是被人轻视的。但出走无门,万般无奈,我只能跟着父亲扛着锄头去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锄地,干杂活。成年人一天记10个分工,早晨2分,上午4分,下午4分。秋后按分计酬。我年少无力,一天累死累活只给记5分。晚上 ,我住在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小土屋里,屋里有一块长方形的大石板 ,两头用土坯架起来,就算我的书桌。地上放块破木板,就是我的床铺,没有枕头,没有被褥 ,夜晚只有一块破布盖在身上御寒。晚上点个小小的煤油灯,可以照亮书上的字。我无目的地翻看在学校学过的课本,过着孤独冷清的日子。我父亲有一天对我说:你这是铺着地,盖着天,头底下枕着半截砖。父亲的话,言犹在耳,记忆犹新啊!天热了,我到房顶上睡觉,有时在家外寨墙边的空地上过夜,前半夜蚊虫咬,后半夜露水凉。早晨醒来时,头发都是湿的。有时就和保安弟睡在院子里的草席上。
1953年6月20日左右传来信息,河北邢台市二中,邯郸县苏曹中学招生,可以去参加考试。我们聚集了十名同学,从村里开了介绍信,步行四十五里到邯郸火车站购票北上邢台,找到二中,报名,考试,看榜,回家。结果与安阳考试一样,中午第一榜我榜上有名。另九个同学一试未中,只好乘车回家。下午考常识(含地理、历史、自然),经过体检和面试,天就黑了。我告别了建筑齐整、绿树成荫的邢台二中,跑步到火车站,万万没有想到当天已经没有去邯郸的火车了。邢台到邯郸一百二十多里路 ,我没有胆量步行夜奔邯郸,只好夜宿火车站,等待第二天的命运。天热,人多,噪声高,蚊子咬,一夜未敢睡觉,夜两点就排队,第一个买到车票,赶上八点从北京方向开来的火车 ,当车到邯郸时已九点多了。马上跑步到苏曹,却已经错过了语文考试的时间,我找到学校负责人,他很客气地说:你数学考试成绩即使是满分,语文没有分,也考不上。回家吧!以后有机会再说。我无可奈何。在邯郸纱厂休息一天,就扫兴而归。
经过两次失败的初中升学考试,我在无路可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感觉自己出身地主是未被录取的最大障碍。大西韩在冀南老解放区。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整个河北南部、中部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未来及占领,就成为解放区了,并在1946—1947年进行了土改,地主富农成为头号敌人,地富分子就是专政的对象,大会批判,小会点名,只许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对他们的子弟在升学、入团、参军、找工作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内部规定。一般不收,个别除外,把他作为体现“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一个实例。我高小毕业,在初级农业合作社连个小队记工员都不让当。可以想象,地主子弟升初中,没有高出贫下中农子弟的突出成绩,是很难被录取的。当时全国正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一些新解放的地区,土改正在进行当中。对于地富子女升学就业的政策正在严格执行。其次,民校高级班虽采用高小正式教材,但是,学生基础、教师水平很难与正规高小毕业生相比,再说大西韩民校高级班仅仅学习了一年半,教材内容都没有按部就班学完,更没有进行系统总复习和升学考试的严格训练。学生的学习成绩、应考经验都没法与正式高小毕业生,在同一个水平上竞争。在邢台二中常识考试中,有一考题是为什么夏天穿白衣服,冬天穿黑衣服?我回答是人们的习惯,不了解一点光学常识。
当时,虽说各地招生考试行将结束,我还是开始了勤奋学习、分秒必争的复习功课的新阶段。 天气炎热,身在小屋,心想上学,矢志不移。晚上集中精神学语文,午休时念数学。早晨、上午、下午干农活时学历史、地理、自然。学历史时背朝代,背国都,背开朝皇帝,背农民起义领袖……学地理时背河流,背山脉,背平原,背省会,背特产,背铁路……锄地休息时,就在地头划地图。去地里干活时,扛着锄头,念着书。一块干活的农民,都叫我考学迷,上班狂。到八月份,有人通知,河北永年城内招两个初中二部制班。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二部制,只要有学上,什么都可以。对于家庭出身地主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临出发时,才想起一个办法,不敢对任何人说。我偷偷来到王计文爷爷家,对他说:我要去考中学,想借我叔叔的军属证用一用,保证丢不了,用后就还。王计文爷爷有个儿子叫王梦祥,我父亲叫王梦奇,名字就像亲兄弟。梦祥叔叔当时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身为空军营长,当然有军属证。尽管出身地主,但如果家里有人对革命有贡献,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这在家人升学就业上,会有很大帮助。王计文爷爷平时知道我的为人,对我也有好的印象,就满口答应了。拿到军属证,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保护好。和十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四十五里路去永年城参加初中升学考试。这次考试如同在安阳一中、邢台二中考试一样,第一榜榜上有名。其他同学当天下午就回家了。我参加了体检、面试和常识考试。尽管天色已晚,我在黑暗中独自一人快跑加慢跑,克服了劳累和恐惧,终于在午夜时分回到了家。一个月以后的中秋节,宗礼兄高小时的同学杜江给我送来了曙光,我才得以进入新的天地。
1953年中秋节的上午十点,我和一群社员在农田收割玉米,远处传来喊我的声音,让我赶快回家,有人找我。我马上放下镰刀,急忙往家里跑。跑到村边,有人告诉我,永年中学来人,有事找你。我急忙找到那个人,他对我说:“你是王宗智吧?你被永年中学录取为备取第一。正取生有一人未报到,你要去的话,今天必须马上报到。明天就要通知备取第二名了,你就没机会了。”我惊喜地大喊:“我马上去!”
我跑回家,妈妈帮我整理好简单的行李。来不及吃午饭,下午一点,我就踏上了去永年中学的路程。
永年中学距我村四十五华里。在路上我才知道,来找我的人叫杜江,他和我哥哥是上高小时的要好同学,我哥叫王宗礼。我家起名排字:仁、义、礼、智、信。他猜想我是王宗礼的弟弟,才来通知我,顺便来他外祖母家过中秋节。他今天如不来叫我,备取生又不发录取通知书,我是不可能上初中的。
我家在土改时被没收房子、扫地出门。为了养家糊口,我必须下地干活,做小买卖,挣钱养家,从没上过小学,只是在夜校扫盲班读过书认过字。1952年,村里成立民校高级班,相当于高小(小学五、六年级)。我在高级班学习一年半,就让毕业。1953年暑期考初中,我到邢台、安阳、成安参加考试,均未录取。原因是:1.地主出身;2.没学完高小课程,考试成绩太差。当年八月,又参加永年初中升学考试,我借了“军属证”。尽管出身不好,但因家里有人为国参军有功,才勉强考上备取第一名。这是我能上学的第一关。我当年十五岁。从此才走出家门,正式走上求学之路。
对于一个从小没上过正规学校,家庭出身不好的农村孩子来说,要想学习成绩跟上同学们,各方面表现好,是很困难的。我刚到学校,只知道上课、背书、写作业,早晚跑步练身体。课间操时县城的同学跳集体舞,我们农村学生只站在旁边看。第一次出门,想家了,周日就到城墙上向南(我的家在永年城的南面四十五华里)眺望。一次,学校的音乐老师要从新生中挑几个吹洋号的,我报了名,被录取了。每天早晨都在城墙根练习吹号。后来,我就成了学校鼓号队的成员。初一年级的冬天,我主动为同学们干好事,下午两节课后,我到宿舍生好炉火。晚自习后,同学们回来睡觉时就不冷了。这件事,我一干就是三个冬天。
1954年8月上初二时,班主任郭秀柏老师把我推荐到学校团总支当委员。经过全校团员的选举,我当上了永年中学团总支宣传部长。我可以单独召开全校16个班的团支委会议,可以在全校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到初中三年级,我当了全校军乐队的总指挥。还是化学课代表,组织主持全校化学晚会。看来我这个农村学生,在永年中学真的稍有点名气了。
1956年暑期,我即将初中毕业。当年,永年中学成立高中。学校保送我和一个学生会主席免试上高中。这时,我听了化学老师荣吉一的话,要求保送我到邯郸市第一中学上高中。学校答应了我的要求。
1956年6月,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感恩的心情,离开了教我成人、促我成长的古老的永年城,至今五十九年了,我再没有回去看过她。她只活在我的心中和梦中。
1956年7月,我从永年中学初中毕业,又有更好的高中可上,心里非常高兴。我们大西韩1953年毕业的五十名民校高级班的同学,只有我一人考上初中,并被保送邯郸市一中,这在全村,在同学中,都是特大新闻。
在五十天的暑假中,我拼命为生产队割草喂牲口。即使下大雨,大水把村四周围困,我也照样到地里割草。十八岁的我,年轻力壮。身背一百斤重的湿草,走在一米多深的水里,浑身是汗水、雨水、杂草,一般人实在难以忍受,但我坚持住了。五十天的奋战,挣了七元人民币,够交高中一个月的伙食费。
开学了,我满怀欣喜,提前到邯郸一中报到。一个月后,我被选为学校团委会宣传部长。
这时,我的伙食费交不起了。家里只有父母能挣工分,秋后分到的粮食不够全家吃四个月的,四个弟弟年小,不能下地干活。我哥的工资,根本不能养活全家。我哥认为,如果我上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全靠他的工资,是没办法解决的。如果我放弃高中,上中专、技校,两三年即可毕业,就可分担家中生计重负。
我思前想后,百般无奈,又不敢和同学、朋友讲此事,因读高中是我自己选择并要求的。苦闷至极,夜不能寐,最后决定放弃上高中,另谋他路。
这时,偶遇山西太原技校在邯市招生。我秘密报名,参加考试、体检。不到一周,就被录取。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到一中,告诉班主任,他很惋惜,但也无可奈何。我找到校团委书记,他说向上反映,当天毫无结果。同学们得知此事,一片惊愕,不忍和我握手告别。
我最后去找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钧平。我万分悲痛地告诉他:我是永年中学的保送生,因交不起饭费,只好退学,去上技校。
老校长上下打量着我,很长时间,才慢慢地说:“永年中学的曲校长是我地下革命时的战友。我把你放走,以后无法再见我的生死朋友。你不就是没钱吃饭吗?学校每月给你七元助学金,够你吃饭的,高二再说。”我深深向老校长鞠了一躬,含泪离开了校长室。
我以感激、感恩的心情,继续留在邯郸市一中读高中。我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从此处处、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工作、锻炼身体、社会活动……我都竭尽全力,出色完成。我是校团委会宣传部长、学校军乐队指挥;我曾代表学校参加邯市中学生运动会,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出席胡耀邦对邯市中学生的接见;参加邯市中学生歌咏比赛,是一中主演《黄河大合唱》的演员;获得各种荣誉证书。同学们给我起的外号有“冒险家”、“哲学家”、“纸老虎”……总之,在当时的学生中,我是比较突出的一员(今天看来,这些外号,不知哪个更本质一些,但在不同程度上都看准了我身上的某种特质)。
1957年底到1958年初,国家开始“大跃进”,学校也不能幸免。高二第二学期,高三第一学期,学校就断续停课,学生被要求到社会上捡废铁,搞勤工俭学。到1958年中,学校全部停课,搞大炼钢铁。
班主任张家仁带领我和其他两名同学,赴磁山学习炼铁。我在十五天中,学会了垒炼铁高炉、选料、配料等整个炼铁技术。回校后,就成了一中大炼钢铁的主力。我是三个带班长之一。全体师生齐动员,轰轰烈烈,昼夜苦战。整整搞了五个多月,才慢慢停下。我的学业荒废了,但我被评为“邯郸市大炼钢铁积极分子”,学校给的各种荣誉,不计其数。
高三第二学期,我才全身心投入高考的学习和复习之中。高中毕业考后,才分文理科,我选择了文科。
我参加了1959年的全国高考,最终以第十七志愿被录取到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这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趋向。
1959年8月,我到北京上大学。临行前班主任告诉我,你的高考成绩是很好的,但你的总评语上写着“此人不能录取机要学校”,这是党的决定。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你在初中高中的表现都很好,才考上了大学,应该庆幸,清醒。啊,我明白了。我班的班长、书记,平时表现不好的,学习成绩再好,都没考上大学。从1958年开始,大学不按高考成绩录取了。高考成了一种政治资源分配。
资料写作者:王宗智,退休教师,现居美国。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