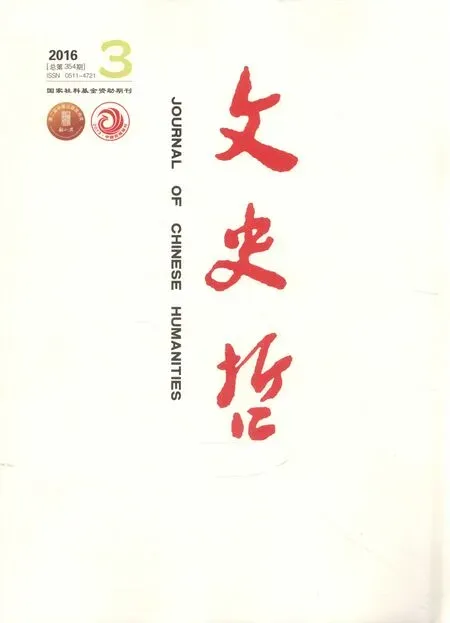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2016-06-06许结
许 结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许结
摘要: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关键词:东汉;辞赋创作;京都与纪行;历史化
前人评述汉代学术与文章,或谓秉承三代,如阮元云:“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①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与友人论古文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9页。;或谓大汉继周,如李光地云:“秦恶流毒万世,复浮于莽……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②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1页。两说均合论两汉,可是后一则说明西汉惩“亡秦”教训与东汉继“莽后”复汉,已有所区分。考两汉制度,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落实到文章,又如清人何焯评张衡《东京赋》所云:“东京之本于周,犹西京之本于秦也,所以推周制以为发端”③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锡山启秀堂重刻本,第211页。,亦影写制度。由此看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也有所不同,其中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内含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历史的思考,尤其是针对“亡秦”与“新莽”的教训表现出对宗法的归复与礼制的构建,当与赋家创作思想向儒学观转变相关,并昭示了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一、从西汉末年的两篇赋谈起
对两汉赋风的变化,前贤多从语言艺术着眼。如沈瑞清《读赋卮言序》论汉赋艺术之变迁:“贾有荀心,马兼宋骨,以若枚叔《菟园》,扬生《羽猎》,靡不穷文极貌,虎视西京。炎运既东,兹格少变,班密张妍,崔雄蔡逸,各营心匠,共吐意珠,铺陈之体,大开骈俪之途,渐导魏晋六代。”④沈瑞清:《读赋卮言序》,王芑孙:《读赋卮言》卷首,清嘉庆八年(1803)邗上刊刻本。以“密”、“妍”、“雄”、“逸”区分诸家特色,以“骈俪”明东京赋格之变。如果换个视角,从赋体描述内涵之变看东京赋格之变,就会发现东汉赋家更多地超越现实需求而转向史学审思,赋体本身的历史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赋风的走向。而这一征兆实际是从西汉后期特别是元、成以后出现的,与当时的政治与学术紧密关联。
考察赋体历史化如何体现于政治与学术,要在两点:一是儒学渐次当路,朝廷盛行以儒术缘饰吏治之风,特别是元、成两朝有关庙制的论争,既表达了学者对建设当朝宗法圣统的关注,又显示了一种对宗法圣统的历史反思与重构;二是西汉盛世言语侍从地位的渐次堕落,辞赋退于文学一途,与儒术缘饰吏治亦渐分离,而经学尚“古”之风的肇兴,又表现出对通经致用的“博士官”系统的挑战。由此看扬雄撰写于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的《长杨赋》与刘歆撰写于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的《遂初赋》,实与上述两点对应。为说明问题,试作分述。
先说第一点。这里又有两个节点,即儒术缘饰吏治与庙制之争。王应麟《玉海·汉制篇》记述西汉举人,以“御史大夫贡禹除诸葛丰为属”、“御史大夫萧望之除薛广德为属”与“丞相武安侯召(张)汤为史”等区分其“德行志节”、“经学”、“文法”,多方举士*王应麟:《玉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以儒术缘吏治为一要项。然则“儒生政治”在汉代的确立,以元帝用“醇儒”倡“德治”为肇始。这其中牵涉到朝廷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元成庙议”*按:有关庙制之议,详见《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在旷时日久的庙制“亲疏迭毁”之争议中确定了高帝(太祖)、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庙祭的“不祧之宗”的地位。至于元成庙议的性质,显然与西汉到元、成之世重构刘汉宗法圣统有关。如果我们对照扬雄《长杨赋》的书写内涵与论述结构,尤其是戒淫史观与德教准则,正是以元成庙议为动因并形成其赋体论辩化特征的*详参蒋晓光、许结:《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其中赋文主体就是对“高祖奉命……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的高帝之“天德”、“圣文……躬服节俭,绨衣不敝”的文帝之“俭德”、“圣武勃怒,爰整其旅……猎乎王庭……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的武帝之“功德”与“今上”(成帝)之“纯德”的描写,并以“颂”而寄“讽”,表达作者的史观。例如写成帝一段:



与司马迁评相如赋“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98页。、汉宣帝评赋“大者与古诗同义”*班固:《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9页。比较,扬雄的“丽则”归雅之论与“孔门用赋”的赋家谱系,已同前此简单地以经义衡赋不同,更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


刘勰论“事类”,意在“援古以证今”,落实于赋文,对《遂初赋》“历述于纪传”的写法改变前人(屈宋及西汉赋家)而开启后世(东汉赋家)作用的提摄,颇具深意。解读这篇被赋史奉为第一篇“纪行赋”的创作,要有三点:其一,该赋创作源自作者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经古学”,并上《移让太常博士书》而获罪于大司空师丹等权贵,于是“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徙守五原”,故作赋纪事述怀*有关刘歆“求出”事详见《汉书》本传。按:《遂初赋》收载《古文苑》,《艺文类聚》录有赋句,前有《小序》记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求出补吏……经历故晋之城,感今思古,遂作斯赋”(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490页),是取《汉书》本传说法并冠于赋作本事。。其二,该赋引述《左传》事典八次,皆多晋国旧事,与作者谪贬之途“历故晋之城”相关,略举两例如次:
赋文:“执孙蒯于屯留兮,救王师于余吾。”事见《左传·襄公十七年》:孙蒯为春秋末年卫国大夫,出使途中于屯留被晋人所俘。
赋文:“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事见《左传·昭公三年》:“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详见许结、王思豪:《汉赋用经考》,《文史》2011年第2辑;王思豪:《〈遂初赋〉用〈左传〉事典的学术史意义发微》,《文学研究》第1卷第2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这说明了赋引事典的地域化特征。其三,由于作者议立“左氏”而遭贬,故赋中多引《左传》事,又因“历故晋之城”而多引晋国旧事,这也使刘勰所评“叙于纪传”具有了双重意味,即“古典”(历史)与“今事”(现实)。而赋家无论是述史,或纪行,均采用纵向的思维与描述方式,诚如刘熙载《赋概》所言“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8页。,“竖义”的加强,正表明赋体载史的书写特征。
由元、成之间,庙议产生的扬雄《长杨赋》的描述与议论,由议立“左氏”而产生的刘歆《遂初赋》的古典与今事,其中的原古、崇儒、尚礼以及议论化色彩与纵向描写的方法,无不指向赋体的历史化。而这一创作现象在东汉时代的京都赋与述行赋写作中得以发展,并大其堂庑。
二、京都赋的礼德宗旨
西汉赋的创作,骚体以抒写个人遭际与不遇情怀为主,散体大篇则以“游猎”题材为重镇,其代表作是孔臧《谏格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与扬雄的《羽猎》、《长杨》等,皆以夸张场景,谏王淫游为主旨。相比之下,东汉赋出现了极为鲜明的两大系列题材,分别是“京都”与“纪行”,其中或寓王朝之兴衰而以古鉴今,或述个人之行止而咏史寄怀,其书写方式均呈纵向思路,考论其因,就是赋体的历史化倾向。
关于东汉京都赋的产生,有赋体的创作前源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创作前源当属西汉的宫廷游猎赋与地方都城赋(如扬雄的《蜀都赋》),一取宫廷,一取城市,然比较而言,西汉游猎、都城赋或以场景描绘以寄讽,或以形势与物产的夸饰以寄意,甚少史事抒写;相反,东汉京都赋虽得前者“宫廷”之旨与城市之形,却更多贯通古今的事类描述。就当时的政治背景而言,东汉京都赋的开山是杜笃的《论都赋》,其赋序谓“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又《后汉书》卷八十《文苑列传·杜笃》载:“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范晔:《后汉书》,第2595页。显然,杜赋是因光武帝巡行西京之举而作,主张迁都西京而反对建都东洛。继此之后,今存东汉京都赋含残篇有傅毅《洛都》、《反都》,崔骃《反都》,班固《两都》与张衡《二京》,基本都是反对杜赋主张而赞成定都洛邑的。只是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东、西定都之争的现实性渐渐淡褪,而演变成东、西之辨与礼制之争,其中内含了对东汉王朝合法(合“礼”)性的考虑。正因如此,东汉的京都赋作无不以史学的眼光考察问题,将现实之精神寄托于历史的思考。对这类赋的历史化现象,前人已有关注。如清人汪琬《乔石林赋草序》就赋体与史才关系陈论:
或谓:赋家宜于侈靡,史家宜于简直,二者之学不同。今使石林以赋才司纂修,得毋用违其长与?琬曰:非也。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之所谓大夫者,求诸《周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之属皆在焉,不必其无兼才也。刘向、扬雄之于汉也,盖尝葺天汉以后诸故实讫于元、成、哀、平,以续《史记》矣。及考其骚赋之作,则又卓然有名。如向之《九叹》,雄之《长杨》、《校猎》、《反骚》诸文是也。世称班固《汉书》“文赡事详”,过于史迁,而东、西都赋则又叙述山川之险,都邑之雄,宫阙掖庭之丽,而究归于灵台、辟雍、明堂风化之盛,其辞闳深灏衍……。*汪琬撰、林佶编:《尧峰文钞》卷二十九《乔石林赋草序》,清康熙三十年(1691)西园书屋刻本。
这虽然通论“赋”与“史”的关系,而以乔氏史职“纂修”且作赋为说,然其言有两点与本文论题相合,一则所举赋家史才以西汉元、成以降之刘、扬为主,其中隐喻赋体向史体的变迁;二则举班固《两都赋》为例,所述于“山川”、“都邑”、“宫阙”之后归于“辟雍”、“明堂”,又寓含京都赋的思想主旨由描绘形胜向书写礼制的转移。与此相关,两汉铺陈大赋形成了两种抒写模式,一种模式以西汉“游猎”赋为主,重在“省祸福”,主题为“训诫”、“改作”;另一模式以东汉“京都”赋为主,归于“观威仪”,主题为“昭德”、“宣威”*参见蒋晓光、许结:《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区分赋家的创作主旨,则前者偏重经学的微言大义,后者更重史学的古今鉴识。

正因为班、张赋分写两都,以宾衬主,所以赋写东都绝不似西汉赋家如枚乘《七发》、相如《上林》的写法,即使如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东汉赋风的扬雄,其“祭祀”类(如《甘泉》)与“都邑”类(如《蜀都》)赋亦非班、张赋主旨所承效,相反,却是“游猎”类的《长杨赋》为其描写模式的蓝本。对此,近人胡朴安论班固文赋,已差得其意:
东京之文,兰台体最绵密,以《汉书》拟《史记》,虽乏龙门之奇,而核实过之。《两都》典丽堂皇,平子、太冲拟之皆有逊色。《西都》极众人之所眩曜,《东都》折以今之法度,宾主开合,极有抑扬。所以《西都》不见铺排之迹,《东都》不知议论之多。核其大体,一脱胎相如《上林》,一脱胎子云《长杨》。*胡朴安:《读汉文记》,收入《朴学斋丛刊》1923年刊本。
为什么《东都》“脱胎”于《长杨》,其实前之《论都》与后之《东京》亦同此传系,不仅在折衷“法度”与“宾主开合”,而且源于赋家对儒术的高扬与礼制的探寻,落实到创作文本,就是推尊汉德与礼义,故采用以“古”鉴“今”的思想方法。
这又可以提出一反问:东汉京都赋为何多损“眩曜”而重“法度”,轻铺陈而重议论,好为以“古”鉴“今”的历史思考?如果着眼于创作内涵而促变创作形式,关键在于一个问题即东汉建都之政权的合法性,并由此衍射的两个面向:“明德”与“尚礼”。
首先,东汉京都赋的“明德”观,既源自古代王者需“有德者居之”的传统思想,又与赋家到班、张笔下“宾、主”东、西两都的制度相关。比如张衡《东京赋》叙写“昔先王之经邑也……审曲面势,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一段,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于此录有两则眉批,分别是孙“东都形势,亦自周来”,与何焯“东京之本于周,犹西京之本于秦也。所以推周制以为发端”*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上册,第211页。。尽管二人所论重点在“洛邑”制度,即东京法周制,西京法秦制,然其间的文化内涵却鲜明地判别了两京的极大差异。可以说,西汉是承秦制而法楚文,所以辞赋中的雄张之气与幽婉之情正呈示其两翼;而东汉则更多地法周制(尤其是东周周公定洛之礼制),故亦法周文,辞赋创作转向雅颂之途与赡偶之风。仅就“明德”而论,所谓“大汉继周”在西汉时因废弃“暴秦”之“德”已有言说,而元、成之后儒术昌明,周德渐为汉人尊奉,亦为不争史实,然则在赋体文学中真正彰明“汉德”以继“周德”的,却是京都赋创制者中的“东都派”。如前所述,东汉京都赋的叙写模式源自扬雄《长杨赋》,但扬雄在赋中取法《尚书·无逸》周公谏成王荒怠之语以警时君的同时*有关《无逸》周公戒成王,详见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30634页。,因影写当时学者力争“世宗庙”(武帝)不可废的情形,而对武帝之“功烈”大加赞赏,诸如“圣武勃怒,爰整其旅”、“疾如奔星,击如雷霆”、“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乎王廷”等等*张震泽:《扬雄集校注》,第124页。,充分显示出对“势”、“力”、“功”的张扬。而秉承其意,如杜笃《论都赋》彰显“西京”,依仗的是山川“险阻”而“惧关门之反拒”,夸耀的则是“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鼓吹武功,而轻于文德。
与之不同,“东都派”的赋家如班、张之赋,无不以“德”为居位之首要依据,并由汉德追溯周德,梳理出德化途径与王权统绪。如班固的《东都赋》附《明堂》等诗五首,以彰赋意,其中“圣皇宗祀,穆穆煌煌”、“抑抑威仪,孝友光明”、“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等,无非“礼”、“德”二字,尤其是“皇德”侔“周成”之说,揭破了大汉承周的东都礼德观。而在赋文中,班氏在大量描述光武帝、明帝之“德教”后,则借“东都主人”之口批评“西都宾”夸耀西京势力而未识德教真谛云: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8页。
其中论述关键在“汉德之所由”,即非泥于旧典的“驰骋乎末流”,而是大汉继周的生动活泼的礼德实践,其中内蕴着“精古今之清浊”之历史教训与经验对现实的指导与拷问。
这种历史意识在张衡的《东京赋》彰显汉德时尤为明显。张赋颂扬东都的主旨是“文德既昭,武节是宣”,所以他论及迁邑东都更加注重“古今之清浊”的历史意识: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民去末而反本,咸怀忠而抱悫。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祎而。”*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56、157页。
文中所引《斯干》,《诗·小雅》篇名,《文选》薛综注:“《斯干》谓周宣王俭宫室之诗也,今汉光武帝改西京奢华,而就俭约,合《斯干》之美。”*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8页。很显然,张衡从“俭德”的视角赞美汉光武帝东都宫室之制,正取法“周德”,同时又以盘庚迁殷与黄轩之德明其传统,因俭而刺奢,意味深永。而东汉京都赋之所以大加赞美“汉德”继周,还源自两大“乱世”教训,即“亡秦”与“莽政”,这正是理解东汉京都赋“明德”思想的历史根源。
其次,东汉京都赋的“尚礼”思想,既是“明德”观的基础,也是其外化的形态。在班、张描写“东都”的赋中有一突出现象,就是对汉明帝“礼德”成就的赞美*对汉明帝“永平之治”的赞美,成为东汉赋学一明显标志,如傅毅《七激》中托“玄通子”之言“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一段,可与京都赋相关内容对读。。这突出表现于因礼宣威的方式。如班固《东都赋》所述光武帝、明帝之德,归乎“制礼”,其中有现实施行的礼仪,包括国家践行的制度。其论“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增周旧,修洛邑”一节,则归于“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如写“朝会”之礼:

描写德教与贡物之“羁縻”盛况,全然一派以礼宣威的气象。这在张衡《东京赋》中主旨尤明,如其对明帝时朝觐礼的描写,着意宣扬大汉帝国四海臣服、万邦来朝的盛况,如描写天子出场时的肃穆、雄壮:
是时称警跸已,下雕辇于东厢。冠通天,佩玉玺,纡皇组,要干将。负斧扆,次席纷纯,左右玉几,而南面以听矣。然后百辟乃入,司仪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贽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礼礼之。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16页。
因礼仪制度而彰显汉家威仪,与周天子朝享诸侯之礼相同,在具体的描绘中完成了大汉继周之礼德思想的传递。赋家通过对礼制、威仪的宣扬,是希望读者能够对礼仪纲常存有服畏之心,当然也为了达到讽规统治者行为之目的。这也就出现了东汉赋家“尚礼”的另一面向,即因礼鉴戒。张衡在《东京赋》中批评“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代表了他以“礼”谏“奢”的思想基调。试举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评张衡《东京赋》数则为例:
“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此句是作家手段。彼云同宅西秦,岂不诡哉?却说六王皆以奢丽自亡,则据雍自强,不攻自破。
“经始勿亟”至“居之者逸”。对《西京》中“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弗殊”四句。
“尔乃卒岁大傩”至“罔有不韪”。“大傩”一段,对前“角抵百戏”。言虽戏,亦祖宗之旧仪,先王之典礼也。西京尚武功,好远略,故铺陈角抵;东京宦者专权,故寓旨于侲童,皆有为言之也。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至“则齐德乎黄轩”。此称帝之作为同于数圣。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至“忽下叛而生忧也”。此皆托以讽谏之旨。

其中何论之精义,要在以东京之礼制对应西京之奢侈,以历史的鉴戒来警示当时(永元中)“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的行为,这也使赋家的礼德观与讽谏观得以结合。
清人王之绩比较相如、扬雄与班固赋风时说:“《子虚》、《上林》创见亦佳,后再蹈袭,则堆塞可厌矣。子云《甘泉》,加以诡谲,更不足法。孟坚《两都》,虽用铺张,犹不甚贪,其自谓义正扬雄,事实相如,亦实录也。”*王之绩:《铁立文起·前编》卷十,清康熙刊本。以“堆塞”与“诡谲”之弊衬托班固京都赋创作的“义正”与“事实”,其中“实录”之谓,正与东汉京都赋重礼德观的历史化有着关联。
三、纪行赋的历史沉思

余最爱唐眉山《诗话》云:“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词,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学赋造词者不可不知。*姜学渐:《味竹轩赋话》,附载氏编《资中赋钞》,清同治六年(1867)刊本。
此引宋人唐庚《子西文录》中论诗语,以喻作赋之道理,其中最要紧者在“因事以陈词”,而这一点恰在东汉纪行赋中有明显表现。换言之,东汉纪行赋之所以异乎西汉“纪行”之虚幻描写而为真实且具体的抒发,诚如前引刘勰于《文心雕龙·事类》中称颂“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并以崔(骃)、班(固)、张(衡)、蔡(邕)踵武其后,所谓“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关键在赋中“人事”的提升,内含的也正是历史化的成分。

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愆。*班彪:《北征赋》,引自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43页。
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征。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班昭(曹大家):《东征赋》,引自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45页。
班彪赋作于刘玄更始三年(25),即光武帝建武元年,时赤眉军杀更始,为避三辅之乱,作者由长安往安定,投依凉州隗嚣,赋中所写,乃途中因所见而感发。上引一段赋文,是作者途经安定(西汉治所在高平)所述,先取《诗》义以叹行役之苦*按:赋文“日晻晻其将暮兮”四句取辞《诗·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取意则如《六臣注文选》铣曰:“言思君子为怨旷,嗟行役为叹时。”,继则历述“亡秦”教训,包括蒙恬筑长城以劳民,结果被赐死而身首异处的下场,赵高与李斯矫诏赐死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以致昏庸乱政,秦政败亡诸史事,以古鉴今,抒写对现实形势的忧患与思考。班昭赋虽自言“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以《东征》摹写其父的《北征》,然作赋“因事”,则缘于作者从洛阳往其子任所陈留,故途中见闻,亦多自我之感发。上引赋文,写作者过“蒲城”(卫地)思古论今,叙写子路为蒲大夫“死而冠不免”、蘧伯玉贤德而不被卫灵公所用、吴公子季札“适卫”说蘧瑗、史鰌等谓“卫多君子,未有患也”,以及卫终败于翟等史事*有关子路、蘧伯玉、季札及古卫国的衰亡,详见《论语·卫灵公》,《左传》之《襄公十四年》、《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九年》,以及《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记载。,并以“知性命”与“忠恕”诸经义*按:赋文“知性命之在天”四句取意于《论语·颜渊》:“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礼记·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充分展示了赋家因事陈词蕴含的历史忧患与现实担当。而合观班氏父女的纪行之赋,如所引之段落,均因史事而引发现实慨叹,且终归于政治之“耀德”与品格之“令德”,这又与东汉京都赋的主旨切合,其中又暗含了赋家述“行”由西汉之尚“神”而骋“力”向东汉之重“事”而明“德”的转变。
与之相比,蔡邕的《述行赋》引述经义较少,抒写史事尤多。该赋写于桓帝延熹二年(159)秋,作者感于当时朝廷的戚、宦乱政,正直遭灾的现实,通过自己“有行于京洛”的行止,将途中所见与自己心中的情感融织起来,通过历史事件的追溯,彰显其“因事陈词”之纪行赋的表达。如赋中先写到达“大梁”时的情形云:
久余宿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忽朱亥之篡军。*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66页。按,引赋四句所述史事,详见《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
作者至梁地而忆史事,论及战国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窃符救赵”,尤其是对其使朱亥椎杀晋鄙而夺其军的行为,一改史家对其机智的赞许,而以“诮”、“哀”、“篡”诸字眼,将其视为阴谋诡计而予谴责。而这一赋家笔法,反映的正是作者对当时乱政僭越的讽谏,也表明了东汉纪行赋家以古“典”诠释今“事”的咏史而写志的手法。如赋中继写行历云:
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宁越之裔胄兮,藐仿佛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悟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
其地名则有“中牟”、“圃田”、“管邑”、“荥阳”,而所述历史人物则因地而忆,则有宁越勤诚为人、卫康叔封疆治邑、管叔与蔡叔谋反被杀、汉高祖因纪信诈降计而得脱于项羽军围等历史人物与事件。这不仅是作者因史事而写心境,即蔡氏赋前所述“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赋“乱”所言“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而且其史事的拼接,可以给读者以更为广阔的历史之想象空间。于是我们阅读东汉纪行赋,往往淡化了赋家纪行之本身(包括景观与情境),而更多去诠释与理解其中串联起来的史事,只有通过历史的写照,才能进一步参透赋者的用心与情志。
由于东汉赋在总体上的历史化趋向,所以一些言志赋与地名赋也具有纪行体的特征,其中较多咏史之目的与史学化的描写。例如冯衍的《显志赋》叙写家世,包括追述曾祖冯奉世(先将军)的功业,以彰显“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可赋中描写,却完全超越了家世与情志,而成为颂扬道德功业以惩戒败政的古史。如写“颂德”之功:
尧舜焕其荡荡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终悇憛而洞疑。高阳藐其超远兮,世孰可与论兹?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歌声。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与为朋;苗裔纷其条畅兮,至汤、武而勃兴。
写“败德”之政:
恶丛巧之乱世兮,毒从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灭先王之法则兮,祸浸淫而弘大。*范晔:《后汉书》,第992、994页。
前则以尧禹汤武等圣王以彰功德,后则以战国之乱、秦政之暴以惩戒其非,其美德与败德,均非“事”而不显,这也成就了该赋以史为纲的叙写方法。而作为关隘胜迹,如李尤的《函谷关赋》写法也很奇特,除描写地舆景观,便以先秦、汉武、汉光武与汉明帝“四朝”之变迁为主构,如“自周辙之东迁,秦虎视乎中州”、“大汉承弊以建德,革厥旧而运修”、“中兴再受,二祖同勋。永平承绪,钦明奉循”*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第376页。,完全同于扬雄《长杨赋》、班固《东都赋》与张衡《东京赋》的描写以及彰显“汉德”的方式,同是“大汉继周”史学观的体现。
东汉纪行赋的历史化倾向,也不仅限于人生行历赋的兴起,即使在赋家描写“神游”(天际游行)时,也能呈示出两汉赋风的不同。以司马相如《大人赋》与张衡《思玄赋》为例,两赋虽创作动机不同,一因汉武帝好神仙方术,所谓“见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赋》”,一因汉顺帝时宦官当道,并以张衡“为其患”而谗之,衡因“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后汉书·张衡列传》);成赋后的结果亦不同,前者赋奏,“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后赋写就,不久“出为河间相”;然两赋均描写超现实的天际“游行”,则是相承且相同的。但是辨别其创作内涵,又有一明显区分,即相如赋写得飘忽神奇,其追述过往,鲜有真实事件,所及人物,除提到尧、舜,皆为神话,如“应龙”、“玄冥”、“含雷”、“祝融”、“句芒”、“玉女”、“西王母”等,所谓“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左玄冥而右含雷兮”、“祝融警而跸御兮”、“使句芒其将行兮”、“载玉女而与之归”、“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等,取材以《山海经》为主,完全是一诸神的世界。张衡《思玄赋》也是通过幻想空际游历,拟状超俗情志,但如赋中“出紫宫之肃肃兮”一段,连用了“紫宫”、“太微”、“王良”、“驷”、“罔车”、“青林”、“威弧”、“封狼”、“壁垒”、“北落”、“河鼓”、“天潢”、“招摇”、“开阳”等星座名,显示了作者熟谙天文的科学性与征实性,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张氏追述过往,则更多地引用史书,同样具有“因事而陈词”的特点。试以赋中描写的顺序略举八例如次:
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说之生殷。

心犹与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摅情。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
朝吾行于旸谷兮,从伯禹乎稽山。集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
窦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庑。王肆侈于汉廷兮,卒衔恤而绝绪。尉尨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
穆负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文断袪而忌伯兮,阉谒贼而宁后。
嬴擿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

上引事例,包括古史七则与汉史一则,古史引典包括《尚书》、《左传》、《国语》、《史记》、《吕氏春秋》等,史事依赋序涉及高阳氏、舜、傅说、周公、周文王、夏禹、叔孙豹、晋文公、嬴政、胡亥、商汤、宋景公、晋大夫魏颗、皋陶等人物与事件,要在赞其懿德之美,而戒其败德之政。“窦号行于代路”数句,史料源自《汉书》之《外戚传》、《王莽传》、《佞幸传(董贤)》及《汉武故事》,其引述事件皆为汉代戚、宦乱政,充分表达了赋家的政治态度与现实情怀。
如果说相如《大人赋》主旨是讽喻武帝“游仙”,其描写仙界以隐喻其不可居,则张衡《思玄赋》通过其人生的思考以反思天界,阐发的是“天不可阶仙夫希”的不可信,前者多经师的微言大义,后者重史家的征实考信。由此一端,也可看出东汉赋家的纪行,无论“行路”还是“巡天”,皆多引史以证今,其中的历史化与具象化的描写,不仅促进了赋风的演变,也可引发我们对赋论的一些思考。
四、史学视域与赋的批评
汉人有关赋的批评,基本属于功用论范畴,考察两汉的赋用思想,又有很大差异,从某种意义来看,东汉赋用论的逻辑起点是对西汉赋创作的反省。在诸家论述中,王充、班固、张衡、王符的评赋语较为典型。如王充对西汉赋虚浮的批评,与他对当世文章的赞美相维系,其《论衡·定贤篇》指责赋体之失“实”云: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46页。
而在《谴告篇》中他对相如、扬雄赋的非议更为突出:
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而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之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刘盼遂:《论衡集解》,第298页。按:文中之“仙仙”,刘氏集解引孙人和曰:“《史记》、《汉书》作飘飘,《扬雄传》作缥缥。飘、缥音同,飘飘、仙仙义近。”
将扬雄《甘泉赋》与相如《大人赋》并称,以罪二子之“赋颂”,这与扬雄批评“赋劝不止”的思想类似,只是王充对西汉赋虚夸的批判与他对当朝赋求“实”的颂扬并存。如《须颂篇》对班固赋中美明帝之“德”的赞赏:
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刘盼遂:《论衡集解》,第406页。
姑不论王氏“誉得其实”是否真实,然其评赋与东汉京都赋创作指向完全一致。班固文学致用观包括了赋对当朝的美颂功能,故与王充论点一样,以批评西汉赋中的虚夸为前提,如《汉书》批评相如赋之“用寡”云:“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班固:《汉书》卷一○○《叙传》,第4255页。如果与《汉志》批评相如等人赋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相比,这里显然增添了对相如赋“有可观采”的美意,所以批评“文艳用寡”,关键仍在实用。
张衡于赋鲜有专论,唯《东京赋》中一段批评相如、扬雄赋作文字,具有反奢侈、寓教训的“讽谏”之义:
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颓墙填堑,乱以收罝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64页。
他认为赋达不到劝美刺恶的目的,起不到讽谏的作用,虽有美词,也于世无补。就这层意义而言,刘熙载《赋概》认为汉赋“至班、张则揄扬之意胜,讽谏之义鲜”*刘熙载:《艺概》,第95页。,明张承班义,不乏胜义,而落实于东汉赋家的致用观,则又不无偏颇。因为东汉赋家无论“美”与“刺”,均与以史喻今的实用思想相维系。又如王符《潜夫论·务本》一则合论诗、赋的文献:
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王符:《潜夫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诸子集成》本,第八册,第8页。
其论着眼于“教训”,以证“道术”与“德义”为文之要则,以批评赋家陈“无然之事”,尽管王氏所指并非仅属西汉,但其求实而致用的赋论,则与东汉诸家的论点一致。
略举数则东汉人评赋语,其求“实”而反“虚”的赋论观中始终存在因“教训”而明“德政”的思想线索,如果我们以史学的眼光看待赋学批评由西而东的变移,我想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汉代的赋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附从于经学批评,这体现于汉人作赋用经与以经衡赋,又可从两个方面表明两汉赋论思想的区别。一方面,汉人倡导“赋者,古诗之流”,实缘赋本《诗经》的赋用论,然观西汉赋作与赋评,则重“风诗”,所以无论是“与《诗》之风谏无异”,还是赞美“诗人之赋”,以戒惕“辞人之赋”的“欲讽反劝”或“劝百讽一”,皆因“风”而尊赋体。东汉赋家在认同前人赋附于《诗》而有“讽谏”之用的同时,却更多地是针对《诗》之“雅”、“颂”的历史追忆与现实诉求。如赋中用《诗》,则多“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高声”、“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臣虽顽卤,慕《小雅·斯干》叹咏之美”、“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分别引自班彪《北征赋》、冯衍《显志赋》、班昭《大雀赋》、李尤《东观赋》、张衡《东京赋》与《思玄赋》。,无论引《诗》篇目,还是咏叹《诗》意,均归之“雅”。这种对雅颂的推扬,落实于赋论,最典型的就是班固《两都赋序》所论赋体“抒下情”与“宣上德”之用,其“雍容揄扬”,是“雅颂之亚”的理义。祝尧赋主“宗汉”,然却区别两汉赋用,不乏精思:
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眩矅,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

前一条论西汉马、扬赋之“风”(讽)义,东汉班固赋之“雅颂”义,后一条专论《两都赋》兼“雅颂”,论“用”则甚得其“体”。我想补充的是,西汉赋家重“风”义,要在风诗主“情”,用之于赋,更多的是彰显“铺采摛文”中的微言大义;而东汉人重“雅颂”,要在雅颂之诗多述“事”,用之于赋,则更多地表现于借“事”明“理”,与赋家因“古”喻“今”的史学精神潜符默契。



赋中诸多象声词与连绵词,以烘托天子郊祀的阵容与形象。再看张衡《东京赋》所写:

其中大量引述周礼,如首取《周礼》“以正月上辛,郊祀告于上帝,祭天而郊,以报去年土地之功”义*《文选》李善注“祀天郊,报地功”引《白虎通》曰:“祭天必在郊者,天体至清,故祭必于郊,取其清洁也。”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11页。,至于《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夏官·弁师》“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曲礼》“天子穆穆”等,皆融织于赋文意旨,突出的是礼仪与秩序。究其原因,其一是西汉赋家多精小学(如相如、扬雄),东汉赋家多职史官(如班固、张衡),故前者赋中有关“天子礼”的描写犹如《春秋》笔法,取微言大义,而后者赋中将“天子礼”融入制度,从而彰显其历史的变迁与承祧。刘勰《诠赋》评相如“繁类以成艳”、扬雄“构深玮之风”、班固“明绚以雅赡”、张衡“迅发以宏富”,风格区分,当与前述之学术变移相关。

东京文士,彪炳史编,然章奏书牍之文,咸通畅明达,虽属词枝繁,然铨贯有序,论辩之文亦然。(如班彪《王命论》、朱穆《崇厚论》是。)若词赋一体,则孟坚之作,虽近扬、马,然征材聚事,取精用弘,《吕览》类辑之义也。蔡邕之作似之。平子之作,杰格拮摋,俶佹可观,荀卿《成相》之遗也。王延寿之作似之。即有自成一家言者,亦辞直义畅,雅懿深醇。(如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是。)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屏绝不观;骚经之文,治者亦鲜;故所作之文,偏于记事析理。(如《幽通》、《思玄》各赋,以及《申鉴》、《潜夫论》之文,皆析理之文也。若夫《两都》、《鲁灵光》各赋,则记事之文。)而骋辞抒情之作,嗣响无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原载《国粹学报》第一年第1期,引自《刘申叔遗书》上《南北学派不同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1页。
所言屏绝“纵横”,鲜及“骚经”,以及改变“骋辞抒情”而为“记事析理”,于“东京文士”的创作思潮把握精到,然其中“士崇儒术”之说,更宜为思考。可以说,东汉赋家崇儒明经,渊承西汉元、成之世,这也是我以两赋(扬雄《长杨》、刘歆《遂初》)引起论述之由,而东汉赋创作因尊“礼”而主“事”,其于“汉德”承继“周德”的描述中,以史为鉴的精神不仅在制度化的京都赋中得以彰显,而且在具有文人创作之个性化的纪行赋中也有体现,个中原由与理义,或许才是表象的文风变移中的深层结构。
[责任编辑刘培]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辞赋理论通史”(09BZW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