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访问纪行(下)
2016-06-05张良仁
文 图/张良仁
英国访问纪行(下)
文 图/张良仁
谢菲尔德大学
回到谢菲尔德大学,开始我们的学术访问。说起来很巧,谢菲尔德大学几年前就和南京大学签了合作协议,合建电子工程实验室。这两年有一位南京籍的学生钱多多进入谢菲尔德考古系学习,然后就极力“撺掇”他的导师都楠教授与南大历史学院合作。正好都楠在俄罗斯乌拉尔山的田野项目要收尾,正在寻找新的项目,于是就答应了。这样都楠和同事代(Peter Day)今年1月访问南大,然后约好4月我们回访。都楠说校长本涅特(Keith Burnett)是个中国通,认识副总理刘延东和南大校长陈骏,习近平主席访英时曾经参与会见。对于我们两校的考古合作,校长非常支持。不过这次很遗憾他正在美国访问,无法会面。
没来英国之前,我还真不了解谢菲尔德大学的情况。这是一所1897年由三所学校合并而成的大学,时称谢菲尔德大学学院,1905年改为现名。在英国和世界都享有盛誉,拥有5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全球排名第80(QS世界大学排名2015~2016年),英国排名第16。2011年因学生体验优秀获得《泰晤士高等教育》“年度大学”称号。该校考古系成立于1964年,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曾经在这里工作过7年,后来去了剑桥大学。前几年伦敦大学学院花重金挖走了4名教师,其中有发掘巨石阵遗址的皮特森教授(Mike Peterson)。历年来该系毕业的博士生到剑桥、牛津和其他高校工作,成为各机构的骨干力量。

谢菲尔德大学校舍
考古系在谢菲尔德大学是个大院系,原来拥有两栋楼,这几年因为经济危机,失去了一栋楼。我们参观了整栋楼,除了教室,还有众多标本室。
该系从一开始,就注重收集标本,现有人骨、动物骨骼、鱼类、植物标本室,占据了大楼的大部分空间。动物骨骼标本室有马、牛和羊等各种动物各个部位的骨骼。这些标本室是该系的宝贝,吸引了英国和欧洲的考古学家前来访问和研究。
该系还有许多实验室,除了上述标本室附带的实验室,还有都楠和代教授的岩相、金相和扫描电镜实验室。实验室没有专门的实验员,研究生们经过导师的训练后,自己动手做实验,自己分析数据。此外,都楠还搞了一些实验考古学,让学生自己冶炼、铸造金属器和烧制陶器。在参观期间,我们看到学生在制作铜斧的木柄。教师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或者合用一间办公室,或者只有一间小办公室。
由于可以接触标本和充分的动手机会,该系很受世界各地学生的欢迎。目前共有4位中国学生,我与他们随便聊了几句。他们在国内学的是财会、化学、艺术史等,很喜欢这里的实验教学。在今年公布的QS考古学学科排名中,该系为全球13强,在英国排名第2,仅次于伦敦大学学院。

谢菲尔德大学的动物标本室

谢菲尔德市传统铸剑作坊的打剑房
我们还见到了搞动物考古的阿尔巴雷拉(Umberto Albarella)教授,也见到了搞植物考古的琼斯(Glynis Jones)教授。琼斯教授在土耳其的加泰土丘(Chatal Hoyuk)工作过,但是主要在欧洲工作,研究农作物的传播。她有个学生对我们的伊朗项目很感兴趣。我之前担心英伊关系,都楠为此咨询过别人,英国在伊朗有个研究所,只不过伊斯兰革命以后人员收缩,但是还在运作。
谢菲尔德始建于罗马时期,是个历史名城,也是个钢铁城市,还是不锈钢的发源地。 现在钢铁产业已经衰落,不过文化遗产还是不少。离开谢菲尔德的早上,都楠特意带我们去了一家传统的制剑作坊。
谢菲尔德过去有很多铸剑作坊,现在只剩下一家,成了博物馆。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打剑房,由水轮驱动巨大的齿轮,带动硕大的铁锤将铁剑锤打成形。旁边是炼铁炉,坩埚用本地特有的土壤制作,用一次就废,所以积攒了很多新坩埚。其形状为炮弹形,类似于炼锌的坩埚。做坩埚时他们用铁质模子,塞进浆土后,用铁杵一次挤压成形。打剑房旁边还有加工铁剑和磨剑的场所。
都楠说这里的手工剑是礼仪用剑,客户大多是各国的国家元首和将军。他们有时会亲自来这里看加工过程,所以成了本地的一景。

剑桥大学图书馆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教堂
一大早作坊里只有一个人上班,伺候炉子,加工剑的配件。我们礼貌地与他聊了几句,正要转身离去,都楠揭开了桌上的一张纸,原来是两把精美的小刀,是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是他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惊喜。谁说英国男人只会打个雨伞戴个礼帽扮绅士,没有情调和幽默?
剑桥
虽然剑桥大学的名气如雷贯耳,但我对其了解也不多。都楠一路介绍了剑桥的一些情况,回国后我自己又上维基百科补课。
当年一部分牛津大学的学者不满国王,跑到剑桥这个平坦潮湿的沼泽地,于1209年成立了剑桥大学校。1231年,金雀花王朝亨利三世给予剑桥自主管理权利以及和牛津一样的垄断地位。因此一直到19世纪,英国只有这两所大学。15世纪,人文主义思想传播到剑桥,带来了希腊和希伯来语言学和文学。从此剑桥不仅培养牧师,也培养学者。17世纪,剑桥已经成为一个思想活跃、辩论盛行的地方。
剑桥大学的管理体制非常独特。它拥有31所学院,学院高度自治,但是遵守统一的章程,因此也可以说剑桥是一个松散的学院联合体。剑桥大学拥有114个图书馆,分布在各个学院、系和研究所。最大的是大学图书馆,拥有800万册图书,它也是一座“版权图书馆”,全英国的出版社都要寄一本新出的书给它。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第二大的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5万册图书、学术期刊和教材,向大学上缴不菲的收益。只是图书定价太高,很让学者们诟病。
徜徉在剑桥大学校园,移步易景,处处是古老而精致的哥特式建筑。大片而整齐的草坪,让人流连忘返。都楠说剑桥不似人间,我很赞同。我们这次没有矫情,直接奔往国王学院前面的康河和草坪,那里是徐志摩写《再别康桥》的地方,也是林徽因驻足的地方,我们没有找到林徽因的脚印,但是看到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徐志摩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在担任过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国王学院的教堂。此教堂在亨利七世以后经历三代国王、前后历时90年修建而成。屋顶高敞,线条精细,两侧窗户装了很多色彩斑斓的玻璃画。这些都是原来的天主教留下来的,剑桥是基督教改革的中心,教堂原先的雕像都拆掉了。这里的唱诗班很有名,每年BBC都会来直播。
我们本来想参观麦当劳考古研究所,结果那天还在放假,没有见到伦福儒和琼斯教授,也没有看成实验室。
剑桥大学还有许多博物馆和独立的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师正在这里访问,她说她所在的古代印度和伊朗信托(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有许多中亚和伊朗的藏书,所以约了她去参观。路上经过菲兹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鉴于时间有限,我们只迅速进去看了一眼,里面的近东和埃及文物不少。
古代印度和伊朗信托在一栋小楼里,里面陈放着五个学者收藏的图书,覆盖印度、中亚和伊朗。1978年,他们觉得英国学术界忽略了这些区域,既缺少研究机构,也缺少教席,所以就买了这栋楼,成立这个信托,借以推动这些领域的研究发展。他们把自己的图书集中放在这里,举办学术会议和讲座,接待访问学者,甚至资助了几个研究项目如巴基斯坦考古发掘、《摩尼教字典》和《大夏年代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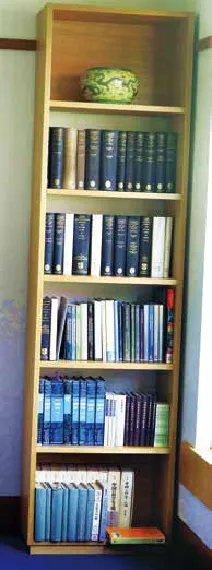
27本已出版的《中国科技与文明》
这里的书很多,放了好几间屋子,还有不少重本、抽印本、手稿等。由于缺乏经费,他们把后面的一套房屋出租了,人大老师就住在那里,方便用图书馆。她整天泡在图书馆,研究国内发现的粟特文书。来国外访问的国内学者中不少忙着生孩子逛风景,让外国同行非常厌恶,而她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类中国学者。
在剑桥访问,当然不能错过蜚声中国的李约瑟研究所。研究所坐落在一个小花园内,里面樱花正烂漫地开着。李约瑟原本从事生物化学,早年因出版《化学胚胎学》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3~1946年,李约瑟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华,长途旅行,收集资料,并结识了郭沫若和竺可桢。在中国助手王铃等的帮助下,出版了15卷《中国科学与文明》(后面几卷由其他学者完成),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赞誉。1971当选为人文科学院院士,1992年获得女王颁发的荣誉同伴者勋衔,集三项荣誉于一身,在英国学术界罕见。梅建军教授带我们参观了整个研究所。他说《中国科技和文明》已经出了27本,现在他在编写有色金属卷。
李约瑟时代的陈设都还在,办公楼后面是一个花园,走廊曲折,小桥流水,竹木扶疏,深得中国花园的精髓。梅建军说该研究所也是个独立的单位,自负盈亏。其成立就是有人捐款买了地,又修了楼,捐款者大多为华人。现在的运转就是基金在支撑,当然研究所还要继续募捐,以求发展。该所现在每年都会邀请一些博士后和学者来访问,今年邀请的大多数是搞中国建筑史的。

古代冶金工作坊
牛津
离开剑桥,我们前往牛津大学。和剑桥一样,牛津是个大学城;但和剑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更像人间,绿地不多,街道拥挤。因为拥挤,学生宿舍和实验室都在步行或者自行车可达范围。
牛津创立年代不明,但有证据表明1096年就有人在此教书,因此它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大学。1167年,由于亨利二世禁止英格兰学生去巴黎大学上学,他们别无选择,牛津因此发展迅速。
与剑桥一样,它起初是个教会大学,许多教派在这里生根发展,同时一些贵族捐资建立学院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5世纪以后,文艺复兴思想的流入带来了希腊语研究。在英国内战期间(1642~1649),牛津曾经是保王党的堡垒,但是18世纪以后,它就不卷入政治了。19世纪以后,经过一系列改革,神学要求(信仰和崇拜)逐渐退出,科学和医学研究得到强化。现在它拥有38个独立学院,其运作方式与剑桥相同。与剑桥不同的是,该校为研究生提供奖学金,这里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
牛津大学的罗森教授(Dame Jessica Rawson)是举世闻名的汉学家,研究兴趣很广,从西周青铜器到汉代玉器,都曾耕耘,成果颇丰。她原先在大英博物馆工作,1994年到牛津大学,2010年退休。但是退休以后,她继续做研究,而且将自己的研究地域扩展到了欧亚草原。
为了接待我们,她专门安排了为期一天的工作坊,原来西北大学的学生刘睿良在等候我们。他说留学前曾经咨询我,我说的一句“要自信”,让他记忆至今。在实验室稍坐一会儿,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师妹安可(Anke Hein)、罗森、台湾来的留学生徐幼刚和其导师帕拉德(Mark Pollard)陆续来到。简单介绍之后,就到楼下报告厅。我先讲新疆东部的古代冶金,主要讲分期和人群迁徙问题。罗森和帕拉德(Mark Pollard)不断插话,说对我的分期没有意见,但可以用他们的方法来回答我的问题,让人很想知道他们的方法。后来根据都楠的提议,我又介绍了我们去年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工作。
下午继续报告。帕拉德讲了他们的火焰(FLAME)计划,目的是要做器物群的历史,意思是要追踪器物的变迁史,即金属器的再利用和重熔。做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数据。在这方面他们拥有欧洲的5万个数据,俄罗斯有5000多,伊朗和阿富汗也有一些。他们的方法是把含砷(As)等4种元素组合的铜器分了16组。其中第二组砷铜在欧洲的分布很有意思,它集中分布在西班牙和希腊,也就是欧洲的东、西两端,说明两个区域各有原料来源。在中国,刘睿良收集整理了7000个数据(其中赛克勒的较多),分别做了商和西周铜器组的分布图,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在欧亚草原,徐幼刚整理了一些数据,得到了一些结果。他们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取样难,数据少。他承认重熔金属(recycling)很复杂,但是他似乎有了办法。他用了一个案例,说明用锶同位素可以揭示两个来源的铜器重熔混合以后得到了一个新产品。之后我讲了卡拉苏克文化冶金技术向中国北方传播的路线问题,罗森大概听了很高兴,还问我发表了没有。
巨石阵
巨石阵举世闻名,好奇心驱使我们把它列入我们的参观项目之一。我们访问了牛津大学之后,就前往巨石阵。
出了古香古色的牛津,就是一望无际的低山丘陵。随着道路的盘旋起伏,一片片泛绿的草地和一条条篱笆树迎面而来,里面的羊群或吃草或休憩,悠闲自得。英国从中世纪开始就把草场分隔成豆腐块,然后种篱笆树或垒砌石墙,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些大农场,为了便于大规模经营,拔掉了篱笆树,拆掉了石墙,形成了大片的农田。
巨大的天空像个穹隆盖住了整个大地,一簇簇雪堆絮叠的云团遮挡着蓝天,一如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今天天气不好,一大早就乌云密布,时而飘来雨滴,寒风阵阵,让人不胜寒冷。在英国呆了几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阴雨天气。而阳光和热量不足,恐怕是英国农田和人口稀少的原因。
我们的汽车走了2个小时,就到了威尔特郡的巨石阵。Stonehenge一名见于11世纪的英国文献,时称“Stanheng”,意为悬挂的石头。遗址位于萨里斯伯里平原小岗之上,周围人烟稀少,“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不过巨石阵举世闻名,引来了一辆又一辆的旅游大巴。现在一家公司经营着这处遗址,修了旅游中心,买了中巴,把游客送到离巨石阵附近。一下车就看见了高大的巨石阵,游客熙熙攘攘,沿着规划好的路线观赏拍照。
巨石阵因其壮观而引人注目。17世纪,就有一些古物学家发掘这个遗址。20世纪以后一些考古学家又做了更为仔细的发掘,对它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发现它是一个埋葬和祭祀遗址。
在这里最早出现的是细石器时代的4根或5根木柱(公元前8000年),木柱已经腐烂,只留下柱洞。它们位于巨石阵附近,洞径很大,达75厘米。这样的遗迹在英国只此一例,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现若干。公元前3100年前后,也就是新石器时代,人们开挖了一圈环壕,直径110米;又用挖出的白垩土堆成了一圈土堤,但是留出了南北两个通道。环壕内可见一圈56个土坑,直径1米。它们原来也许栽了木柱,形成一个柱圈,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这些土坑埋了63具火葬人骨, 经过性别和年龄鉴定,里面有成年男女和儿童。发掘者发现土坑底部经过重压,因此推测原来埋过石柱,用于标记墓葬位置。公元前3000年,由南北通道往里又埋了一排木柱,同时25个前期柱洞内又埋入了火葬人骨,此外还有30处火葬遗迹,因此环壕内成了火葬墓地。
真正的巨石阵始建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此时人们抛弃了木柱,改用石柱。他们在中央挖了两周柱坑,这些柱坑原来埋了80根石柱,今天只见到43根。所用的石柱为蓝色,每根高2米,重2吨,是从240公里以外的威尔士的普蕾瑟利山(Preseli Hills)运来的。2011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巨大的采石场,证实了巨石阵蓝色石柱的来源地。此时北门得到扩建,以便观察夏至日出和冬至日落时的阳光。此门内外可能还立了别的石柱。同时一条通向阿旺(Avon)河的大道(Stonehenge Avenue)修成。此路由平行的浅沟和土棱构成,长达3公里。 皮特森教授认为,古人沿着这条道路到巨石阵祭祀祖先。在此后的公元前2600~前2400年期间,75根巨型沙岩石材相继运到这里,形成了巨石阵。它们可能来自以北40公里处的马波若山(Marlborough Downs)。石柱经过加工,上面像木柱和木梁那样做出榫和卯,然后立起,顶部再加30根沙岩横梁。每根石柱4.1米高,25吨重,两根石柱的间距是1米。这样的石圈直径为33米。在石圈内,还有5组双石柱加横梁,形成一个马蹄形,开口向东北方向。这些石材更大,重达50吨,高6~7.3米不等。在其中一些沙岩石柱上雕刻出了短剑和斧子,其雕刻年代不明,但是器形是青铜时代的。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研究者发现,部分石块在敲击之后发出很大的不断变化的回声。
公元前2400年以后,当地就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阶段人们把精力集中在巨石阵的蓝石圈上。他们首先在外圈沙岩石柱之间立了一圈蓝石柱,其顶部也加工出榫,说明上面原先也有横梁。后来又在内外圈沙岩石柱之间立了一圈蓝石柱,在内圈以内立了一圈马蹄形蓝石柱,其上没有经过修整,原来没有横梁。在此圈蓝石柱内移入了一块祭石。但是本期蓝石柱根基不稳,很快就倒了。不过在巨石阵周围出现了很多土冢。再往后(公元前1930~前1600年),蓝石柱圈的东北部分移走,形成一个马蹄形,与中心的沙岩石柱圈对应。

巨石阵
埃夫伯里
巨石阵不是本地区唯一的此类遗址。我们在巨石阵之前,已经看过了北面17公里的埃夫伯里(Avebury)遗址。其年代也是新石器时代,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旅游胜地,但是另有一番味道。遗址周围同样为低山丘陵,如今为成片的草场,但是在细石器时代(公元前9600~前5800年)这里是一片片森林。在此时期,英国与欧洲大陆交流密切,居住着狩猎—采集人群。遗迹和遗物都很少,只是在埃夫伯里以西300米处发现了一些细石器,表明这里原有他们的宿营地。
公元前4000年,农作物和家畜传入英国,人们开始定居,过去的森林带逐渐退缩。这里也出现了石器、动物骨骼和陶器。埃夫伯里遗址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拥有农业生产,否则无法投入浩大的人力物力到遗址的建设中。外围挖一圈宽12~15米、深达10米的环壕,挖出的土堆在环壕以外形成土堤,里面有一圈巨石组成的圆圈,直径331米,是英国最大的石圈。有人认为石圈原有98块砂岩石柱,高达6米,重达40吨有余。其建造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870~前2200年之间。人们发现,这些巨石可以发出回声。中央又有两个小石圈,北面的直径98米,但是今天只剩下了4根,其中只有2根是立着的。其内侧还有3根石柱,开口向东北。南面的直径108米,石柱保存的更少。究其原因,就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对本地的异教遗迹深感烦恼,所以搞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由环壕向两侧延伸出两条胡须般的道路,道路竖立两排巨石。
在大石圈以南,还有一个大型土山西尔伯里(Silbury),高达40米左右,据Lonely Planet说,它是欧洲最大的土方工程。遗址没有出土重要的器物,其用途不得而知。尽管缺乏遗物,与巨石阵一样,人们推测整个遗址群是一个祭祀用的。

新石器时代长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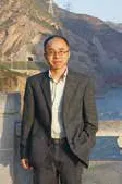
作者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参加陕西长安沣西、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发掘,2010~2013年主持甘肃张掖黑水国遗址的发掘。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和欧亚大陆(含中亚)史前考古,同时致力于中国与国外学者的合作研究,多次访问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学术机构与博物馆。出版专著Ancient Society and Metallurgy,组织并参与翻译俄文著作3部,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写作的《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获得夏鼐奖一等奖(2005年)。
西肯尼特长冢
在大型土堆以南不远处,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西肯尼特长冢(West Kennet Long Barrow)。墓葬位于山岗上,公元前3500年开始建造,遗址连续使用到公元前2500年。整个长冢像根法式长棍,形体很长,达100米,是英格兰最大的一座。入口处用巨石搭建墓口,里面有一条通道,两侧对称分布着若干大石块砌筑的石室,放置人骨。19世纪的古物学家做了发掘,发现了46具人骨,其中有婴儿和老年人。这些人骨杂乱无章,部分头骨和肢骨已经遗失,说明古人定期把人骨移出长冢,然后再捡拾部分骨骼放回原处。在青铜时代,人们又在墓口处立了几块巨石,将其封堵,结束了长期的埋葬行为。
结语
看完西肯特长冢,我们继续上路,向伦敦希斯罗机场方向前进。中途看了一个早期铁器时代的城址和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长冢,晚上在一个斯温顿(Swindon)的小镇过夜,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一家中餐厅。第二天,我们中的一部分去了温莎城堡,我则去了大英博物馆,继续我的使命, 都楠也该回谢菲尔德大学上课了。第三天,我们带着满满的英国考古、博物馆、大学和风土人情方面的新知识,踏上了返回南京的飞机,我们历时14天的访问也就结束了。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