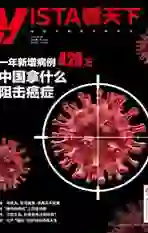名叫拉斐尔的女孩子
2016-05-30
我一直想问,为何她一个韩国姑娘,会起个外语名叫拉斐尔。每次都是事后想起“忘了问”,见面时好奇心又被礼貌压抑了。何况,拉斐尔并不喜欢说话。
直到,再也没机会问了。
拉斐尔来自仁川,头发染成橘色,扎着马尾,表情常显得天真中带惊异,衣服常是白底配各色花纹。她在巴黎,似乎学各色稀奇古怪的功课。每次教授们讲到偏门别类的科目,其他人听得兴味索然,她便睁着惊异的眼睛,眼镜快滑落到鼻尖了,抱着笔记本狂记,俨然抱着橡果的松鼠。我看过一次她的笔记:秩序井然,色彩纷呈,一目了然,我只好叹为观止。我夸过一次,拉斐尔一声不吭地抿嘴笑一笑。
我很怀疑拉斐尔的爱好是逛街。因为我在歌剧院大道和圣日耳曼大道晃荡时,都遇到过她。巴黎虽然不大,但也不小。以我逛街的频率,还能遇到她两次,很可能她总是在到处奔走。细想来,的确:她很少穿宽大的裤裙,总是瘦腿裤和球鞋,仿佛随时预备着冲出室外,开始在街上暴走。
某个秋天的阴雨黄昏,教授的讲座来人寥寥,确切地说,只有我和拉斐尔去了。教授倒也没怎么不开心,就走下来与我们聊。教授说,他年少时是电影迷,于是来巴黎疯狂地看电影;某天,他与邻座的英国姑娘看对了眼。“所以我们结婚了。”我和拉斐尔鼓起掌来,教授不好意思地起身一鞠躬,仿佛歌剧演员谢幕。
“那么,说说你们。”
说完我的,教授回头看拉斐尔。拉斐尔眨了眨眼睛,抿了抿嘴。现在想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那天的室内格外幽暗。本来,十月份,巴黎也起码到八点才天黑,但那个黄昏,黑云压天,仿佛夜晚了。
拉斐尔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先是几句熟练的自我简单介绍,之后,开始一个个往外蹦词:
来巴黎,是为了,待在巴黎;但在巴黎的时间,不长了,来年夏天就要回去了;韩国,职场,婚姻,韩国女性的压力很大,韩国的女性权利跟巴黎的不同……
她说着,教授听着,偶尔帮她说出她想表达但不知道如何念的法语词,拉斐尔就点头嗯一声,然后继续说下去,到后来法语夹杂着英语,以及韩语。
她喜欢巴黎的春夏,因为有阳光;她梦想过做芭蕾舞演员,被爸爸阻断了;仁川有海,但是到了冬天就很少出太阳;她喜欢K-Mart超市里的五花碎肉和年糕……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拉斐尔。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样的拉斐尔。
转过年的春天,我偶然听人说起,拉斐尔去世了。四个朋友提供了四个不同的说法。当然,也很快过去了。
后来,我与那位教授再次相遇,自然说到拉斐尔去世。教授沉默了一会儿。“ (车祸,还是自杀)我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更糟。”教授说。我说,我也不知道。虽然,一个人出车祸过世,似乎比起自杀者要少一些绝望,但我们谁都不是当事人。谁都无法为她安排命运。
我偶尔还是想得起她那天在幽暗的室内,滔滔不绝,仿佛独白似的,说着自己的事。我能够从她描绘的词句里想象出一些片段,但我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要去想。
某个周日,我在体育场下车,看见一大批学生闹嚷嚷地上车,灿然欢笑,其中一个女孩子,拿着笔记本,梳着橘色的马尾,穿着白底红花的毛衣。我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车门已经关上了。我下意识跟着车走了两步。旁边的黑人小伙子诧异地看着我。
应该是看错了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