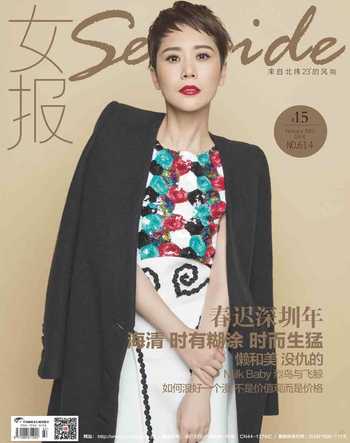春迟深圳年
2016-05-30
宜
全身簇新、洗邋遢;
生猛鲤鱼祭神名;
谢灶君,两碌长蔗做天梯;
责年,食鲮鱼、葱、芹、蒜;
卖懒,卖懒,买到年卅晚,人懒我唔懒;
舞狮、游神、飘色游行、做大戏。
忌
以汤淘饭;
打破物品;
水土出门;
吃药、理发。
【盆菜】
盆菜是源自宋朝的岭南传统节庆大菜,主要食材为萝卜、支竹、冬菇、油豆腐、鱿鱼、木耳、芹菜、干猪肉皮、门鳝干、五花肉、蚝、鲜门鳝、鱼丸、鸡、鸭等十五种,各种食材按传统工艺加工好后,分六层装在一个大盆中,食客自上至下一层一层吃下去,越吃越好吃,吃到最后,垫底的萝卜吸足了上层美味的汤汁,无比鲜美。
传说,大盆菜与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有关。八岁的小皇帝被元军追赶,走投无路,逃到了香港新界地面,老百姓见皇帝来了,凑齐家中的好东西,一锅煮了,装在木盆中献给皇上,于是就有了大盆菜,一吃就是六百多年。赵昺与大盆菜到底有没有关系,不能考证,但真正让大盆菜名扬天下的是下沙村。
一盆吃了六百年的年夜饭
“舌尖上的中国”成了中国吃货的美食地图,循着舌尖弥漫开来的香味找过去,吃货们总能收获几分惊喜。
2014年5月,深圳下沙村的大盆菜也在“舌尖”露了两分钟的脸。我打电话咨询一个吃遍深圳的朋友,哪里能找到比较正宗的下沙大盆菜。朋友脱口而出:稳记。
下沙村毗邻香港,港人出没便利,常来这里风花雪月,多年前曾是深圳著名的“二奶村”和红灯区。城中村的特点是人多、路窄,三轮车、电单车和豪华小车竞相奔驰。小巷紧挨菜市场,难免污水横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左冲右突,终于抵达稳记酒楼。传说中的稳记很不起眼,只是城中村挨挨挤挤的农民房中的一幢,门前很是局促,紧贴台阶,只可勉强容下两个车位。
稳记的老板与老板娘黄金稳、黄桂兰同属下沙村村民,1969年结婚。下沙村城市化以后,黄氏夫妇分得了一块宅基地。1995年,他们向亲戚朋友借贷五十多万,加上积蓄五十多万,修建了六层楼房,楼上自住,楼下打算自己做生意。
其时,深圳村民各村开始慢慢恢复逢年过节以及婚嫁喜事吃大盆菜的风俗,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盆菜师傅。会做大盆菜的人本来就不多,加上村民富起来后,也不愿意耗时再做盆菜了。黄氏夫妇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商机。
黄桂兰的盆菜手艺,是从小跟妈妈学来的。如今母亲已八十多岁,年关时还会亲自坐镇,在店里下厨帮她。母女俩早就可以享受生活,过过游山玩水的日子,但她们就喜欢做菜。
黄桂兰说,稳记的盆菜没有什么秘方,分层放菜的技巧、食材和高汤炖煮的时间,全凭上一辈人的烹饪经验传到这一辈,再手把手教予店里的盆菜师傅。从管理人员到服务员,他们都在稳记做了十年以上,与老板早就成了朋友,从不担心跳槽或是偷师。
江添富是广东五华人,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跟着黄老板做大盆菜,现在已是副总经理。他从冷冻库房拿出一片两米多长的门鳝干:看盆菜是不是正宗,先看食材用得是否厚道。“门鳝是海里的,有的小店制作盆菜会用黄鳝干,就是淡水鳝鱼。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从香港元朗采购的。盆菜摆在一起,打开来,不用吃就知道哪一盆是正宗的。”
稳记从不做推广,全凭客人之间口口相传。从年关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八,是稳记最忙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店里不再接待堂食,全是拿号外带盆菜的客人,叫号要叫到七八百号。有个马来西亚的客人,吃过盆菜后觉得好吃,要打包带回国内的家人吃,黄桂兰没有答应。“他带回马来西亚,肯定不新鲜了,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也坏了稳记的招牌。”
许多香港客人都爱来稳记,包括蔡澜和洪金宝这样的名人。他们都很低调,先打电话来,订一间房,要一个车位,下车后,用手挡着脸低头进房间,吃完就走。稳记开业时只用了两层楼,生意做开后慢慢扩大,现在已扩展到第五层。
与此同时,1996年,下沙村村长找到同为下沙人、人脉颇广的港商黄兴,委托他办一届全下沙人参加、在下沙祠堂举办的盆菜大会。
黄兴比黄桂兰小几岁,1972年去了香港,1979年作为港商回到下沙村,专门负责下沙的黄氏宗亲会。
那一年席开950席,赴宴者一共9000多人,主要为下沙村民和世界各地的黄氏宗亲代表。之后规模越来越大,至2001年,盆菜宴已席开3500席。盆菜引起全深圳轰动,下沙村领导决定把它打造成下沙的文化名片。如何让大盆菜在国际一鸣惊人?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冲击世界吉尼斯纪录。
3800席就能破吉尼斯纪录,只差300席了,冲!
先是请客,世界黄氏宗亲会成员,市、区、街道各级领导,下沙村全体村民全部算上。领导动员村民,把各家各户的亲戚朋友全都请来。
提前一个月,黄兴就开始采购煮盆菜所需的木柴。他强调说,做大盆菜必须用柴火,最好是荔枝木劈柴,最差也得是锯木厂的边角料。用煤或煤气绝对不行,那样会有异味。
2002年2月23日(正月十二),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云集下沙村,广场一角架起150口直径1米多的大铁锅,同时开炒。1000多个帮厨者各司其职,洗菜的、切菜的、配菜的、炒菜的、装盆的,往来穿梭,热热闹闹,却也有条不紊。
中午12点,鞭炮炸响,象征黄氏气象的黄龙舞动起来,盆菜大宴正式开始。
意外的是,3800盆菜全部端出去之后,客人还在源源不断而来。好在黄兴早有预备,备好了充足的食材,热灶热锅,加工起来倒也快。桌子不够,后来的客人便等前一批吃完了,自己动手收拾桌子,接着吃。
那一天,下沙村端出了5319份大盆菜,赴宴者达60000多人,大破吉尼斯最大规模的民间宴席纪录。2009年,下沙大盆菜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了下沙村当之无愧的文化符号。
一年到头的盆菜大宴,是下沙村最热闹的时候。你拿着碗筷在盆的一头,家人朋友亲人们在另一头。大家聊着过去、现在和将来,聊着父辈、子女和旧情人。
那一刻,是黄兴最开心的时刻,也是如今已六十多岁的他,每年耗时耗力操办盆菜大宴的初衷。“让四面八方的和固守在这里的村民们团聚,让上一辈和天南海北的下一辈们团聚,这才是过年。”
而对于黄桂兰来说,每年过年,是大年初一凌晨过后,客人们的盆菜全都顺利送走,他们会关上店门,和店里的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尝一尝自己亲手做的盆菜。
这盆菜,是老天爷赏给他们的一碗饭。他们会高高兴兴地、百感交集地、充满感恩地吃下去。
【鱼灯舞】
沙头角鱼灯舞起源于清初乾隆年间,流行于沙头角、盐田及香港新界等地,为渔民逢年过节、拜神祭祖必备节目。鱼灯用竹篾扎成鱼状,糊纸绘彩再涂上桐油,下装短棍 ,举棍起舞穿梭如海中鱼群。伴奏乐器有锣、鼓、钹、唢呐、螺号等。传统的鱼灯舞共有二十五条鱼,现今精简为十八条。鱼灯舞一度面临失传,二零零三年间经过村民进行发掘、整理、排练后,终能传承下来。“沙头角鱼灯舞” 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弦月 鱼灯舞
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边境沙头角,每年正月十五都会有一队人擎着鱼灯,在具有传奇色彩的中英街上走马而过。街道两旁是低矮陈旧的毛坯房,和悬挂着国旗的白色门廊。鱼儿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繁体字的霓虹招牌在闪烁,走在队伍前面的吴观球老人说,眼前的情景和几十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
74岁的吴观球来自沙栏吓村,村里村民只有300多人,但迁往香港、海外的却有一千多人。具有三百年历史的鱼灯舞一度流行于沙头角和香港新界一带,是客家渔民文化的重要载体。“吴”姓在沙头角是大姓,在客家话里与“鱼”同音,作为吴氏家族第三代传人的吴观球和先辈一样,对鱼灯舞有着深厚的情结。
元宵节入夜,他带领13个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在中英街的回归广场上表演鱼灯舞,这场表演要持续一个多小时。锣、鼓、钹先热热闹闹地起乐,随着一声唢呐,表演者们俯低身板,手擎各类鱼灯排列舞出。鱼灯的肚子里燃着蜡烛,夜色如水,烛光透过色彩斑斓的砂纸析出,能够分辨得出鲤鱼、丁公、石斑、沙鸡等不下十几种鱼,放眼望去迷幻又美丽。村民们模仿鱼儿摆动的姿势,扎着马步交叉回环,速度时快时慢,让人应接不暇。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途杀入鱼群的一只凶猛的黄鳢角(俗称“霸王鱼”),它企图吃掉小鱼,却不料被群起而攻之,最后只得仓皇逃离。吴观球说,这样的情节源于清朝沙头角的先民打鱼时常遭到海盗劫掠,而朝廷难平寇祸。渔民于是创作了这一故事和表演形式,祈求天后主持公义,赐福降恩。现在,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寄意,转变为表现吉庆有余(鱼)和丰收的喜悦。
“表演鱼灯舞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出鱼儿们的喜、怒、哀、乐。”鱼群从自在游弋到四下惊逃,从同心协力到胜利后的欢喜,都要靠人的步伐动作去体现。吴观球从17岁起便跟随长辈学习鱼灯舞的知识,那个年代还没有排练室,为了不弄坏纸糊的鱼灯,他和一群年轻人在沙滩上举着扫把和稻草,练习扎马步、俯身、曲背等动作,顶着深圳半年多的暴晒,一天要练五六个小时。临近过年,冬天的海浪阵阵拍击在礁石上,他们却大汗淋漓,一直要练到能把握鱼灯舞的神韵为止。
和鱼灯舞一同流传下来的还有鱼灯的制作技艺。鱼灯长1~2米,分为三节,节与节的连接处可以摆动。通常先用竹篾扎架,砂纸粘黏,然后描线着色、糊上桐油防水,最后在鱼头内装上两个两寸竹节用来插蜡烛。“不熟悉鱼习性的人舞起鱼灯来,可能使烛火烧到砂纸,而我们不会。”做好的鱼灯要先送去村里的祠堂、天后宫烧香开光,只有开过光的鱼灯才能拿出来表演。
在说话的间隙里,吴观球对排练室里的鱼灯逐个检查,发现有破损的地方,立刻找材料修补。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做新的鱼灯,他说:“这些鱼灯都是祖辈传下来的,用了很久了,纸、粘胶、竹篾,都沾上了亲人的气息。就让它们继续传下去,为什么要浪费呢?”
可还是有一种鱼现在已经没法做出来了——尾巴会喷火的墨鱼。吴观球年轻时学过,墨鱼的肚子里有特殊的小装置可以喷射火焰。这项技艺之所以流失,是因为当年中英街一街两制的风波,懂行的老艺人相继谢世,鱼灯舞整整沉寂了四十多年。
直到2002年村长吴天其上任,他请求村里了解鱼灯舞的老人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吴观球等人才重新“出山”。他和同村以及香港新界的同辈一起,根据回忆重新写下曲谱并编排鱼灯舞的动作。在众人的努力下,2008年鱼灯舞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深圳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沙栏吓村的春节也因此变得更加热闹——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元宵节舞鱼灯成了盛事。为了这一天的演出,大家要提前准备,村里不少年轻人都以开车跑运输和卖菜为生,工作辛苦,但每周至少有两三个晚上他们会抽出时间排练,之后休息一个小时,凌晨两点再开车去香港卖菜。
村里有不少家庭是儿辈、孙辈一起学鱼灯舞的。元宵节鱼灯游街的时候,两三岁的小孩都在路边观看,走路摇摇晃晃,却在认真地模仿大人的舞姿。吴观球遇到了,就会笑眯眯地教他们扎马步。吴观球也会给驻扎在中英街的武警官兵和深大的学生上课:“有生之年,想教给人们关于鱼灯舞的一切知识。我毫无保留,只希望这个传统能永远流传下去。”
问吴观球过去的岁月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年春节是怎样的——他沉思了半晌,出神地看着前方,仿佛穿透一阵弥漫四十多年的大雾,看到了曾经锣鼓喧闹、鱼灯璀璨的夜晚。但他到底没有说出过去的盛景,而是提到了2013年应澳大利亚政府的邀请到悉尼作春节表演。那一年沙栏吓村村民们手擎鱼灯,第一次全体走在异国的街道上。有围观的华裔市民问:“你们是不是来自深圳?”那一刻吴观球心里充满了自豪,也有许多无法说出来的感慨。
春节 快要冻掉鼻子的冷也是珍贵
喜喜 服装业 来深19年
老家的朋友在朋友圈晒银杏照片,金灿灿一天一地。我赞了个好,朋友问我啥时回,答:恐怕又要错过这一季。
错过是常态。
最近几年,恰巧都是在11月前后因事回去。那时路上人少,飞机航班也不繁忙,回家也无须会晤太多半熟面孔,在家陪老人走走看看说说闲话,再到公园里吹吹风晒晒太阳喝喝茶,一天就是一天,一秒也不虚度。
不像春节回去,到处是人海茫茫。
十多年来,大多数春节都是在深圳过的。人少,街道清冷干净,不堵车,一辆接一辆飞驰而过的公交车上也没几个人。那时的深圳,慢慢开始回到一个普通城市应有的样子,不慌不忙,路上经常可以见到一家老小出行,年轻人扶着老人慢慢走,阳光很好,照在道路两旁的树上,树叶闪闪发亮,像一只只小哨子在吹响——薄寒中的深圳,在春节里,呈现出南方城市最清新的模样。
春节前可以逛花市。你可以在远处花市举着大束的银柳、剑兰和黄金果回家,也可以在小区外面的街角让工人把金橘或者水仙帮你搬上楼。年三十的晚上,远处一样可以传来鞭炮声,只是自家小区够安静祥和,楼下大堂的灯笼映得你眼花。
初一去海边,初二去爬山,初三去拜年,初四去看博物馆。这是你的深圳,空气新鲜,食物也可口,人人脸上带笑,不再提着一口气匆匆赶路。
遇上暖冬,你可以穿条薄裙子到处晃。如果是严寒加下雨,穿得厚厚的走在明晃晃的水洼边看寂静四周千山鸟飞绝,快要冻掉鼻子的冷也是珍贵。
偶尔也有让人啼笑皆非的。
有一次过年,父母来深圳,一家人去小梅沙玩。午饭时间,记得当时小梅沙公园门口的对面有一溜海鲜餐馆,家家爆满。进去一家,好不容易寻到一个和人拼桌的机会,点完菜就开始坐等。当其时,拥挤店堂内有不少服务生在忙前跑后,但就是乱,顾得了这桌顾不了那桌,食客们不耐烦的催菜声此起彼伏。
等了一小时,菜还迟迟不见踪影,大家饿得连“他们是不是孵小鸡/种菜苗/杀猪去了”这样的无聊话都没力气说了。实在按捺不住,穿过拥挤人群跑到后厨捉出一个服务生,细看其眉眼,感觉这帮人哪里是服务生,明明是一帮小白领。拷问之下,果然是,一间设计公司的一帮年轻同事,趁过年放假不回家,集体出来顶了人家的餐馆临时做一段——老板和服务员统统都回家过年去了。
本想赚点小钱,没承想把自己搞得手忙脚乱。
那天最后的情况是,我们自己上阵跑后厨端菜,就差上灶台去亲手掌勺了——终于吃到了滋味奇特的一餐。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再退回到二十多年前,1992年的春节,我们还在广州工作。年初三的时候,一位深圳的同学开车过来广州,把我们接到深圳玩。记得当时住在红荔路附近,刚到那晚,这座移民新城市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餐馆也关门闭户,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东北饺子馆,一碗饺子12元,数了数正好12个——一元一只饺子的物价,让来自省城的我们有点发呆,以至于两天后回到广州,迫不及待地在站前路附近一家川菜馆大吃大喝了一顿,结账28元。对,那晚在深圳的酒店房间里第一次看到香港电视,明珠930正在播放的电影正是我爱的《查林十字街84号》,自此对香港有了向往。
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移民城市,已经不能再叫做移民城市了吧。人们安居乐业,一拨又一拨的孩子在这里出生。这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春节童年记忆,从此只与这座城市有关。
没有雪,没有乡道泥泞,没有熏腊肉香肠的浓烟,没有地上厚厚的红纸屑。
可是有花,有海,有艳阳,还有坐火车一小时就到的香港。
春节 远离兵荒马乱 ,远离久别重逢
张二宅 媒体业 来深五年
这是我在深圳度过的第五年,我即将又一次远离兵荒马乱,远离久别重逢。
深圳在诲人不倦这方面真是不遗余力。这座城市不仅在平日教你生存的许多法则,即便到了全城打烊时也要尽职地告诉你,别总想着好事占尽。你逃离了举国沸腾的抢票、塞车、返程等一系列战乱,那请你也别惦记着脚踏乡土的朗朗温情。
我明白。所以,我一边冷静地看着同事朋友们与12306的验证码斗智斗勇,一边等着过年慢慢变成一种公式化的提醒。提醒我时间真的飞快,提醒我记得关心亲友,提醒我仍旧远在他乡。这种提醒跟桌上的日历、枕边的闹钟、贴在冰箱上的便笺纸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提醒透着成功学惯有的虚伪。
我以为过年的意义也就如此了,然而,朋友带来了他的过年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老邱,快要三十岁。我们平时没有太多嘘寒问暖,得闲时约出来喝两杯,然后各自奔忙。前几天我们照例吃了个饭,没想到是散伙饭。
“过完今年这个春节,明年就不来了。”他说出这句话时,有妥协,有不甘,也有释怀。老邱是东北人,三流设计专业毕业来到深圳,在辗转多个招聘会后终于向现实妥协,当了一名售楼先生。然后与所有来深圳的小年轻们一样,加班、搬家、加班、搬家,直到对温馨屋舍的憧憬暂时消失,最后只能寄情于工作,努力赚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年头,只有不怎么在意房子的人才买得起房子,真正需要房子的人只能望楼兴叹”。
他唯一的幸运是已经成婚,成家。当然,在深圳这也许并不算幸运,或者这份幸运有些贵。
所有的童话故事总是以“王子与公主终于在一起并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结束。这正是现实给我们的第一个巴掌,生活不会结束,婚后的日子才更趋于生活的本质,这种本质区别于小桥流水与阳春白雪,带着浓厚的战斗气息,你要重新打满鸡血,为了下一代百炼成钢。
“我最近每天都在考虑应该怎么办,有了孩子以后,许多决定变得复杂而谨慎,我要寻找最稳妥的方向……”这是我第一次听老邱说这么多不知所措的话,男人与男人之间很少会有这种情况,除非真的十万火急,不可调和。我尝试安慰他,“深圳就是这个节奏,普通人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他颓然反驳,“不想将就,当初不想在老家将就日子而来到深圳,以后也不想将就在逼仄的空间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那种穷尽两家人民币在深圳买个二手房的事情太伤人了。”
我不再劝阻,也许他并不需要我的挽留,诉说只是另一种说服自己的过程。况且,我能说什么呢?说他顶不住压力?临阵退缩?不敢挑战?我们都只是在寻找最好的出路而已。所有人都在打拼,选择继续留在深圳需要勇气,愿意打道回府的,担当都藏在心里。可惜的只是,翻过2015这个年头,在本就前途叵测,交情难求的深圳,我又少了一个谈得来的朋友。至于老邱在深圳的这个春节,也只能打上缅怀与告别的烙印。
转眼又快春节,我一度以为过年就只是过年,甚至会慢慢变得不是过年。哪会如此单薄,那里面有无数的故事,在燃烧、滚烫、灼人。
希望老邱即将出生的孩子幸福安康。
春节 零点后的《花田喜事》年初二的李小龙专辑
犀牛 设计业 来深28年
我是1988年夏天到深圳的,89年的农历年,同样来自西安的三家新移民在市区聚餐,一桌子北方菜中间添了盆酿豆腐,主人说这是本地同事送的,大家尝尝。大人们喝酒,小孩分到一人一瓶菠萝啤。聚会下午开始,我在主人家第一次玩游戏机,《魂斗罗》,《超级玛丽》,因为知道父母不会答应家里也添置一台,心里充满嫉妒。
五点开饭,为的是八点能准时坐在沙发上看春晚,陈佩斯穿着棉大衣表演吃面条,记忆中客厅里的都是短袖衫。父亲说深圳这地方真热,过年连棉袄都省了。午夜倒数前男士们把鞭炮绑在竹竿上伸出门缝,“5、4、3、2、……”,一根香烟凑近引线,楼道成了扩音器,真正的震耳欲聋。我捂着耳朵往茶几那儿退,没有外套,裤子口袋塞不进太多糖果。十二点过后聚会散了,回家需要骑大约四十分钟的自行车,从西丽到南头只有一条柏油路,连路灯都没有。
1996年大年夜,七点左右,我骑车往医院赶,车把上挂着装热粥的饭盒,我侄女在那晚十点半左右出生。记忆中也是那年开始,大年夜变冷了,要穿外套秋裤。晚饭照旧是几家人聚餐,大人们的重点是酒、饺子和春晚,我的重点是压岁钱。那天下午有本地同学邀请我年初二去村里拜年,说全村人都在广场上吃盆菜。我婉拒了。对我来说,过年就是赖在沙发上吃零食,看香港电视台播放的旧电影——大年夜零点后肯定是《花田喜事》,年初二是李小龙专辑。
年初一不能出门,不能洗头、剪发,我的年关因为一个秘密忙碌万分:当时我已经进入漫画公司做兼职主笔,两个月后就会发表处女作,当下手里同时谋划着几篇不同风格的漫画短篇。这秘密让我自觉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学会要工作不要娱乐。
因为失恋,2000年的年三十下午,我用一把剪刀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当时我的头发长至肩膀)。年夜饭第一次在酒店里吃,大人们说这样多好,不用费劲张罗,不用洗碗,也不用吃好几天剩菜。同桌的叔叔娶了本地媳妇,她说现在村里一样,去酒楼吃年夜饭,多打包一条鱼回去就行,年年有余嘛。那年开始我会为饭后时光提前准备一本小说,春晚节目已经没那么吸引人了,因为收视惯性,年夜饭还是八点前结束。
新年钟声敲完后,跟父母道句新年快乐,我出门跟几个朋友闲晃。朋友说发现没有,一到过年深圳就成了空城。我说对,但不管它空不空,这儿已经是我们的家乡了。
2010年,我在谈一段异地恋,过年时她那边大家族聚餐,一人半斤白酒;我这里剩爷俩在家,母亲回北京探亲。我说晚上就烫点青菜好了,再煮四两挂面。父亲一脸委屈地捧出半锅红烧肉,过年嘛,不能那么寒碜。春晚开始后我拿出手提电脑抄剧本,老爸说现在放鞭炮都不能在市区点了,西丽那边开辟专门的地方放,你有兴趣么?我摇头,不去,那么远,折腾。
但年初三我就出门折腾去了,一个朋友在郊区买了房,暖房趴上无事可做,学着打麻将。朋友说以前村里初一拜神祭祖,烧几千几万响炮仗,现在个个都出国玩。你们外地人以前过年回家乡,现在把家人朋友接过来过冬,到处都是人。我笑说明年干脆组团一起出国算了,省得在家听唠叨啥时候结婚生子。
2015年,我和四个朋友跑去印度,年三十晚上印度当地朋友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他母亲特意做了扬州炒饭,外带意大利冰淇淋。因为时差,晚上九点回到酒店,国内倒数已经结束。四个小伙伴躺在大床房看手机直播,感慨说在国外过年还是清静,没人催婚,也不用拼酒。不过下次选个别的国家吧,印度人吃全素,过年也没肉吃。
代表中国胃说一句,那还算是过年吗。
春节 忌酗酒 忌号啕大哭
鳄鱼 医美业 来深3年
年末大撤离,就像一场考试,批了假的同事,和不怕死的同事,优先交卷跑了。其他人都忐忑不安地等deadline。不幸的是,我是那个没抢到票的倒霉鬼。
我当时住的是单位分的两室一厅的宿舍,另外一间住着一对年轻小夫妻。年关前曾经反复地跟我打听,“你过年回家吗?”
“回家啊!过年不回家,我爸会打断我的腿。”
结果我没抢到火车票,说好的拼车回湖南也被放了鸽子,年二十六当晚,我躲在房间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凌晨2点钟,门口忽然有窸窸窣窣的声音,隔壁妹子兴高采烈地嚷道:“爸、妈!”
“哟,你们这屋这么小,我们有地住吗?”
“没事,同事回老家过年去了,你们住她房间就行了,等她回来前再收拾一下,还原……”
她“还原”还没说话,一把推开我的房门,我从床上弹起来,我们面面相觑地望着对方,尴尬了……早知道,走路也应该走回去过年的。
事已至此,隔壁小夫妻只好在客厅里架了个床铺安顿老人。就搭在我门口,我进出门时,老人都要深深地望我一眼,无声的谴责。
大年二十八,他们一家四口开始欢天喜地搞大扫除,然后全家出门采办年货,拖着行李车去梅林农批市场买水果。
我出门一趟,感觉可怕,小区楼下的热干面和卷饼摊不见了,各种店铺统统关门,连人影都很少。作为一只盒饭狗,真是要命。
大家几时见过深圳地铁和公交空荡荡的感觉,整个城市就跟寂静岭一样,悄无声息,死寂一般。相熟的人基本都离开深圳了,条件好点的在朋友圈里晒海外游,条件次点的在香港血拼,我这种吃土的平民,只好躲在天台上晒太阳,逗猫玩。
终于熬到了除夕夜。同事一家四口咚咚地敲我的房门,“一起来看春晚吧,包了饺子呢。”去也不好,不去不好,只好坐在角落边全神贯注地假装看电视。
一切都坏在了喝酒。小青年和岳父吃着饺子,忽然敬起了酒,说着客套的祝福。
“我会好好照顾你女儿。”
“希望你升职加薪,早日在深圳买房。”
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精浓度高的五粮液。男同事忽然将酒杯一甩,号啕:“是我没用,在深圳买不起房子,大过年的害你们睡地铺。”
岳父也醉了,拽着他的领口,醉醺醺地说:“是当爸爸的没用,没给你们攒点家底!”两个人像铆上了,相互数落自己的不是。母女俩在旁边,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女方跟我说:“别介意啊!”我连连点头。
每到过年的时候,人的失意总会无限的放大,失意啊、孤独啊、都会藏不住,想粉饰太平都会如鲠在喉。我走到楼顶透气,深圳禁烟花,可是楼顶上还是不断地飘起了孔明灯,24点一到,寂静的小区里忽然燃起了爆竹声,此刻才真正有点过年的气氛。电话忽然响了,是我爸。
“你一个人在深圳还习惯吗?”
“很好啊!和同事一家过年,很热闹。”
“哦,家里今年冷,我们在烤火,斗地主,春晚是越来越没意思了……”老爸在电话那边唠叨着,我绷不住,心里一滞,就要哭出声来。
我们总觉得这漫长一生,能捱过孤独,其实甚至不能捱过一个没有家人陪伴的除夕。
【最后的晚餐】
从前,腊月二十五,开厂的、开店的就该放假了。放假的前一晚,老板照例会请员工吃饭。老板行事喜欢拐弯抹角,他如果对某个员工不满意,明年不想再雇他了,不会直接下逐客令,而是在这最后的晚餐中,夹给他一个鸡脚,意思是“伙计,你该走路了”。吃过鸡脚的员工,心知肚明,第二年就不会再来了。如果你是老板,可别随便请员工吃鸡脚,员工吃在嘴里,可能吃不出凤爪的味道。
【穷鬼日】
大年初三,老派的广东人不随便串门拜年,也不给人派利市,因为这一天是“赤口日”,出门容易惹是非。还有一说是,这一天是穷鬼日,要赶“五穷”(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如果你不是特别阔气有身份的人,在大年初三到广东人家里拜年讨利市,可能会像穷鬼一样不受欢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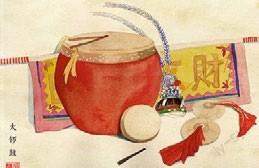
【偷青】
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叫中国情人节。从前的这一天,姑娘们会在天黑以后,钻到别人的菜地里,偷一把青菜。偷到葱,意味自己会越来越聪明,偷到南瓜(金瓜)会发财,偷到芹菜很勤劳,总之,偷来好运气。而且,姑娘们只偷自己喜欢的人种的菜。那一夜,小伙子会埋伏在自己家的菜地里,看喜欢自己的姑娘多不多,看到自己也喜欢的姑娘来偷菜,就一跃而出,大惊小怪,嘻嘻哈哈,于是,偷青就成了“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