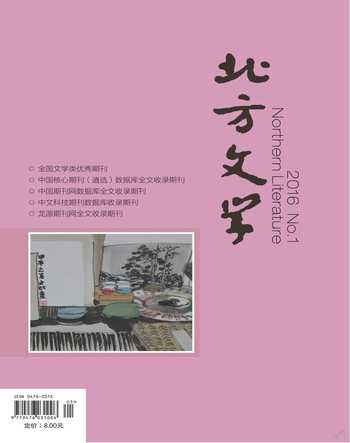沃尔·索因卡在中国的译介
2016-05-30汪琳邱晓杨
汪琳 邱晓杨
摘 要: 自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因卡及其作品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本文分析其戏剧、诗歌、小说与传记三个主要写作体裁,从作品译作以及相关研究两个方面出发,来总结索因卡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索因卡作品译作数量较少,多数作品未有汉译本,且版本较单一。国内学者主要集中研究其戏剧作品,诗歌、小说与传记体裁的作品相关研究较少。总体而言,索因卡及其作品在国内的译介虽卓著成效,但仍存在问题,需要继续深入。
关键词:沃尔·索因卡;非洲文学;尼日利亚;译介;研究
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 –),尼日利亚著名剧作家、诗人、小说家,1934年7月13日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一个开明的西化家庭,后留学英国。1960年回国,创作《沼泽地居民》(The Swamp Dwellers, 1958)、《狮子与宝石》(The Lion and the Jewel, 1959)等戏剧。1986年,因“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的戏剧”,索因卡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沃尔·索因卡以多部剧作和一本《狱中诗抄》(Poems from Prison, 1969)而闻名。他不仅仅是一位非洲乡土作家,还以深厚的西方戏剧知识和素养赢得了“非洲的莎士比亚”之美称。索因卡至今已发表二十多部剧本、两部长篇小说、多本诗集、三卷本自传,还有不少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
从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开始,索因卡的名字就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激发了人们了解、研究他的兴趣。仅从1986到1987一年间,就有二十余篇推介性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各大报纸、杂志和高校学报上。本文试图从戏剧、诗歌、小说与传记三个方面,来总结和阐述国内对索因卡的译介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国内的译介发展趋势。
一、索因卡戏剧的译介
索因卡很早就以剧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他探索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因为它与非洲的素材、非洲语言形式以及笑剧创作联系紧密。他的戏剧频繁而又驾轻就熟地使用许多手法,如舞蹈、典礼、假面戏、哑剧、节奏、音乐、慷慨激昂的演说、戏中戏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舞台艺术而又真正植根于非洲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持续至今。他的戏剧创作体现了他对殖民文化以及非洲传统的态度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索因卡积极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把非洲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外来文化。他相继发表了《凯菲的生日宴》(Keffi's Birthday Treat, 1954)、《新发明》(The Invention, 1957)、《沼泽地居民》、《暴力品质》(AQuality of Violence, 1959)、《狮子与宝石》这些作品,对非洲传统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表现出明显的亲欧倾向。60年代,非洲各国相继独立。索因卡敏锐地察觉到对于非洲而言,西方人的文化殖民更为危险,于是开始肯定并大力宣扬非洲传统文化。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裘罗教士的磨难》(The Trials of Brother Jero, 1960)、《森林舞蹈》(A Dance of the Forests,1960)、《我父亲的负担》(My Father's Burden,1960)、《强种》(The Strong Breed, 1963)、《停电之前》(Before the Blackout, 1964)、《孔其的收获》(Kongi's Harvest,1965)和《路》(The Road, 1965)。70年代,面对非洲的混乱现实,索因卡看到非洲传统文化的局限和不足,因而发表了《疯子与专家》(Madmen and Specialists, 1970)、《死亡与国王的侍从》(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 1970)、《欧里庇德斯的酒神女伴》(TheBacchae of Euripides, 1973)、《紫木叶》(Camwood on the Leaves, 1973)、《杰如的蜕变》(Jero's Metamorphosis, 1973)、《文尧西歌剧》(Opera Wonyosi, 1977)等,决意反思非洲传统,并企图融合西方文化,以寻求对非洲传统的超越 。80年代以后,经历了种种精神上的徘徊游离之后,索因卡最终又回归约鲁巴传统。他把希望寄托于非洲神话世界,认为传统和过去更有意义,提倡一种“神话整体主义”,相继发表了《未来学家的安魂曲》(Requiem for a Futurologist, 1983)、《巨人的游戏》(A Play of Giants, 1984)、《空地男孩的受福》(The Beatification of Area Boy, 1996)等。
通过归纳索因卡戏剧的写作特色,学界一般认为其戏剧创作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早期多半为喜剧,格调轻松诙谐,富于幽默和讽刺。而1960年后,他的写作呈现了一种更为悲剧的性质。精神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冲突显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险恶;对善与恶的记录,对破坏力和建设力的记录,也越来越含糊不清,他的戏剧含义变得模棱两可。其剧作以讽喻或讽刺的形式,采用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神话式的戏剧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旨上以揭示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的社会现实为主,风格上逐渐变得隐晦、荒诞。尤其在《路》与《疯子与专家》里,其“荒诞的倾向就显得非常突出,以致不少西方评论家拿他和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贝克特比”(邵殿生 1987:55)。
国内对于索因卡戏剧作品的翻译比较集中,数量较少,版本单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出现最早的索因卡戏剧作品是由李耒、王勋翻译的《路》,收录在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戏剧选》中。随后,1986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杂志刊载了由邵殿生翻译的《沼泽地居民》。1987年第7期《外国文学》杂志刊载了由钟国岭、张中民翻译的《森林舞蹈》,进一步推动了索因卡作品在中国的传播。1990年邵殿生等翻译出版了收录有《路》、《沼泽地居民》、《狮子与宝石》、《森林舞蹈》、《裘罗教士的磨难》、《疯子与专家》等作品的戏剧选集《狮子与宝石》(漓江出版社),该书较为系统地向中国读者展示了索因卡的戏剧作品。最近一部翻译的戏剧是由200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蔡宜刚翻译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
自索因卡1986年获得诺贝尔奖,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后,国内对索因卡及其作品的研究也逐步升温。据有记载的资料显示,《读者》第1期率先译介了索因卡的评论性原文作品。王三槐发表《奥因·奥贡巴<变革运动>》,翻译并总结了尼日利亚评论家O·奥贡巴评论索因卡戏剧的著作《转变的运动——索因卡戏剧研究》(Oyin Ogunba: The Movement of Transition, A Study of the Plays of Wole Soyinka, Ibadan University Press,lbadan, 1975)。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及其戏剧进行的评论。同时发表在《读者》第1期上的还有朱世达的《我是非洲文学的一部分——记沃莱·索因卡》,向国内读者简介了索因卡的生平及其戏剧作品特色。吴保和在1987年同时发表了两篇有关索因卡的文章,分别是《上海戏剧》第2期上的《非洲的“黑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渥尔·索因卡和他的戏剧创作》,以及《艺术百家》第2期上的《非洲文坛的一颗明珠——诺尔文学奖获得者渥尔·索因卡》,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及其戏剧艺术。
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于索因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索因卡生平及其戏剧作品概论的简介,尚未出现对其戏剧作品进行文本研究的文章。直到1992年,王燕在一次會议上从《路》这一作品出发,探讨了索因卡戏剧的形式。该讲话以《探<路>谈艺——索因卡戏剧形式刍论》为题,被收录在了会议录《东方丛刊》第4辑中。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具体的戏剧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研究索因卡戏剧文本的先河。
此后,从文化角度对索因卡的戏剧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戏剧作品的悲剧精神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和戏剧中的民族文化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而《森林舞蹈》、《路》、《狮子与宝石》和《疯子与专家》的研究较少,目前尚未出现针对《沼泽地居民》、《裘罗教士的磨难》的专门性研究。
针对《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的研究,学者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和悲剧精神为研究切入点。如韩丹在《后殖民视角下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中,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进行研究,指出戏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表现了作者对国王陪葬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以及西方殖民下的外来文化存在着既支持又反对的两种观点。而赫荣菊在《从<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看索因卡的悲剧精神》一文中,则通过对剧中人物艾勒辛的伪美学悲剧性和欧朗弟的悲剧性超越进行分析,认为索因卡创作该剧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张扬以约鲁巴文化为主体的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高文惠在《索因卡的“第四舞台”和“仪式悲剧”——以<死亡与国王的马夫>为例》一文中同样对其悲剧精神进行研究,认为索因卡对约鲁巴传统悲剧的原型、实质、美学效果、约鲁巴玄学体系的意义及在现代戏剧舞台上如何表现等方面做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也有学者从宗教文化视角进行研究。马建军与王进发表的《<死亡与国王的马夫> 中雅西宗教文化冲突》一文,“围绕非洲约鲁巴民族及其宗教死亡仪式,成功地再现了1946年约鲁巴人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史实性文化冲突,以当代后殖民主义及文化研究理论,从宗教文化角度重新解读《死亡和国王的马夫》,批判了剧作者所持的“普适”人性观点及其对人物悲剧的狭隘解释,赋予剧中的悲剧以新的文化内涵。”(马建军、王进 2005:161)
对索因卡其它剧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后殖民领域和民族文化领域。如余嘉发表了《森林之舞:后殖民语境下的索因卡剧作研究》,探讨了索因卡戏剧作品中表现出的具有后殖民性的两大特征:本土性与政治性和抵制西方文化殖民、弘扬本土文化的精神。黄坚、禹伟玲在《<森林之舞>与<路>的后殖民主义解读》中指出,《森林之舞》和《路》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殖民困境的真实写照,探讨历史、现在与未来这个主题。王慧也在《论<狮子与宝石>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中指出,该剧既表达了索因卡对欧洲外来文化的嘲讽,也表露了其对非洲本土文化的推崇。通过这些作品,索因卡努力地在后殖民文化背景下,在欧洲现代文化与非洲传统文化的碰撞中探索传统非洲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上述译介为国内学者进行索因卡戏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索因卡的其它戏剧作品,如《凯菲的生日宴》、《暴力品质》、《我父亲的负担》、《停电之前》、《紫木叶》、《未来学家的安魂曲》、《巨人的游戏》、《空地男孩的受福》等戏剧原文却仍没有学者进行研究。
二、索因卡诗歌的译介
索因卡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7年索因卡出版了《艾丹勒及其他诗作》 (Idanre and Other Poems, 1967),那个时期尼日利亚西部发生了选举暴乱(1964-1965),66年1月进而发生了军事政变,66年5月北部地区又发生骚乱,接着是66年9月的大屠杀,67—70年的三年内战紧随其后。索因卡在《艾丹勒及其他诗作》中以“66年10月”的标题直接表现了那次大屠杀。而在1972年发表的 《地穴之梭》 (A Shuttle in the Crypt, 1972)则记录了军事政变和三年内战。到1976年《奥冈,阿比比曼》 (Ogun Abibiman, 1976)发表时,索因卡以非洲“奥冈萨卡”(Ogun-Shaka)的神话传说构成全诗,借以表达他对非洲政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不久之后,这首诗成为南非最终取得反种族歧视斗争胜利的预言和序曲。到1989年的诗集《曼德拉的土地及其他诗作》(Mandela's Earth and other poems, 1988),则表达了诗人庄严的政治承诺,即为了把种族隔离这一殖民主义势力在非洲的最后残余彻底地驱逐出去,必须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拒绝以妥协换取自由,诗人为此发出欢呼。2002年发表的《撒马尔干市集》(Samarkand and Other Markets I Have Known, 2002)是索因卡最新的一部诗集。
在台湾地区,对索因卡诗歌的译介和研究相对较早。1986年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台湾的《幼狮文艺》就曾刊载过两首他的狱中诗。随后有唐山、倾向联合出版的贝岭编、黄灿然和王浩威翻译的《狱中诗抄——索因卡诗选》(2003)、杨泽翻译的《萨马尔干市集——索因卡诗选》(2003,时报文化出版社)。而在中国大陆,直到2000年后,才出现汪剑钊译的《非洲现代诗选》(2003,河北教育出版社),以及发表在《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期刊上的诗歌,如“致我初生的白发”、“死后”和“资本”、“献给祖国的花束”等等十几首短诗。关玉培认为索因卡的“诗和他的剧作一样,手法多样化和针对社会现实”(关玉培1987:70)。在《非洲现代诗选》的导言中,汪剑钊综述了索因卡诗歌的基本特点,认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渗透着强烈的使命感。许多基调不同的作品证明,他不愧为大师级的非洲作家,……他既表现忧郁、悲伤、沮丧,也善于用讽刺的笔墨进行调侃、揶揄,更擅长以抒情的反思来亲切地追忆似水年华”(汪剑钊2003:12)。
相较索因卡的戏剧,国内对于其诗歌的研究较少,已有的文章主要从后殖民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宋志明发表论文《“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提出索因卡的詩歌创作本质上是一部“奴隶叙事”,充满了殖民地作家的反抗精神,具有显著的后殖民性。远洋于2015年5月在文艺报上发表《老虎索因卡的愤怒之诗》,对《给我最早的白发》、《黎明》、《死于黎明》等多首短诗进行了分析概括,认为他的诗在殖民背景下深入挖掘非洲文化,自觉担当启蒙重任。
总结而言,国内对于索因卡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狱中诗抄》,而对于他的其它诗歌如诗集《艾丹勒及其他诗作》、《曼德拉的土地及其他诗作》以及《地穴之梭》、叙事诗《奥贡·阿比比曼》等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
三、索因卡小说传记的译介
从20世纪60年代起,索因卡相继发表《痴心与浊水》(The Interpreters,1965)、《此人已死:狱中笔记》(The Man Died: Prison Notes, 1971)、《反常的季节》(Season of Anomy,1972)和《在阿凯的童年时光》(Aké: The Years of Childhood, 1981)等一系列小说传记类作品,显示了非凡的文学叙事创造力。
小说中文译著的成果较少。主要有沈静和石羽山翻译的《痴心与浊水》(1987, 外国文学出版社)。同年,敦理出版社出版了张国祯和颜斯华翻译的版本,并将题名译为《诠释者》。2001年,由冯国超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百部》(2001,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录了周辉翻译的《阐释者》,是该小说的最新译本。在沈静和石羽山的译本序和译后记中,他们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尼日利亚的社会背景和索因卡的创作历程,同时指出,他的小说“不但蕴含有极深刻的哲理,还处处发出宗教的气息”(沈静、石羽山1987:382),更具真实性。此外,译者还对小说中的五个主要人物进行了逐一评述,不仅分析了索因卡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还揭示了抨击和讽刺时政的深厚主题内涵。而索因卡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反常的季节》,国内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及译著。
对于索因卡小说作品的研究,始于刘合生1989年发表的《传统与背叛——沃尔·索因卡<痴心与浊水>主题初探》。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小说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开启了索因卡小说研究的先河。由于译本出现相对较早,针对《痴心与浊水》这部小说的文本研究已经较成熟。国内学者主要从女性主义、文化构成、殖民主义等理论与视角出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文本分析。有学者专门对《痴心与浊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研究。如周声在《民族寓言的讲述困境——以<痴心与浊水>中的性别叙事为中心》中从性别叙事的角度出发,对这部小说进行“再解读”,分析了该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刘江在《<痴心与浊水>中女性“他者”形象的解读》中以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角度,分析男权制度的压迫是造成女主人公们“他者”形象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女性以“自欺”的方式去解决面临的困境,只会固化“他者”形象,进而提出只有反抗才会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自我解放。还有学者从文化结构进行了论述。王燕发表《两种异质文化的兼容与整合——从<痴心与浊水>解读索因卡小说的二元文化构成》,从索因卡思想上二元文化结构的成因及在其小说叙事中的表现出发,分析小说叙事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也有学者从殖民主义等视角对《痴心与浊水》进行了细致解读。在《殖民主义残存与历史中的希望——从<痴心与浊水>看尼日利亚历史与未来》中,李阳在殖民主义视角下分析了主人公的婚姻形态、传统宗教信仰和死亡观。秦银国在《诗性、哲性与神性的融合——从<解释者>谈沃里·索因卡的叙述艺术》中对小说的时空关系处理进行分析,阐释了索因卡叙述艺术的文化哲学。
国内对于索因卡传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阿凯的童年时光》。邵殿生选译了传记《阿凯——童年纪事》,发表在《世界文学》1987年第4期上。文章提到这部传记曾被评为1982年英语文学最佳作品之一。此传记于2008年由谭莲香重新完整翻译,并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改为《在阿凯的童年时光》。高文惠于2011年发表《精神的试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阿凯:童年岁月>的自传价值及其自传意识》,从价值和自传意识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这部自传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隐藏在叙述背后的作者的自传意识,高度评价其为一部成功的艺术自传。
对于索因卡的另外几部传记,如《此人已死:狱中笔记》、《伊巴丹:潘克雷米斯年代》(Ibadan: The Penkelemes Years: a memoir 1946-65, 1989)和《艾沙拉:漫游书简》(Isara: A Voyage around Essay, 1990)等,国内至今没有译介。
四、问题与展望
纵观沃尔·索因卡在国内的研究,可以看到国内对其的研究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索因卡的名字在国内译介中有沃列·肖英卡、沃勒·索因卡、沃莱·索因卡等多达十几种译法。索因卡的民族Yoruba也有“约鲁巴”、“雅鲁巴”或“约卢巴”等多种译法。对于索因卡的诸多作品的译名,研究过程中也没有进行统一。如《The Strong Breed》,有学者将之译为《强种》,也有学者将之译为《良种》;再如《A Dance of the Forests》也有《森林舞蹈》、《森林之舞》等多种译法。这反映出我国研究者之间缺乏接触、传承、沟通与交流,没有形成研究组群。
二是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并不全面。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范围大致局限在《路》、《沼泽地居民》、《森林舞蹈》等汉译本中,而《凯菲的生日宴》、《伊丹里和其他诗篇》、《此人已死:狱中笔记》等没有汉译本的原著,国内也少有学者研究。同时研究的形式也局限在文化角度,尚未涉及《艺术、对话和愤慨》(Art, Dialogue and Outrage, 1988)《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 1976),《记忆的负担:宽恕之鼠》(The Burden of Memory, the Muse of Forgiveness, 1999)等索因卡的文论作品。
同尼日利亚的另一位颇具盛名的作家阿契贝相比,索因卡虽获得诺贝尔奖,但仍非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兴趣点所在。阿契贝的五部长篇小说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且译本数量可观。而其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的译文也都零散收录在各杂志、小说集、散文集、诗集中,学者的研究视角多样。与之对比,索因卡作品的中文译本较少,且版本单一,学者研究视角受限。应该说索因卡的国内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首先是作品的解析范围,国内学者的眼界可以从汉译本拓宽到原文文论作品。其次可以建立专门的研究组群,加强交流与合作。使索因卡的研究更具系统性。
参考文献:
[1]陈梦. 从戏剧创作看索因卡对待非洲传统的态度[J].青年文学家,2014 (9): 47-50.
[2]关玉培. 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勒肖英卡[J]. 外国文学报道,1987 (1): 69-70.
[3]高文惠.索因卡的 “第四舞台” 和 “仪式悲剧”——以《死亡与国王的马夫》 为例[J]. 外国文学研究,2011,33(3): 127-134.
[4]高文惠.精神的试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阿凯: 童年岁月》 的自传价值及其自传意识[J]. 山东社会科学,2011 (9): 103-121.
[5]赫荣菊. 从《死亡与国王的侍从》 看索因卡的悲剧精神[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29(6): 29-32.
[6]韩丹.后殖民视角下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J]. 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3: 1-32.
[7]黄坚,禹伟玲.《森林之舞》 与《路》 的后殖民主义解读[J].当代戏剧,2015 (3): 36-38.
[8]刘合生. 传统与背叛——沃尔· 索因卡《痴心与浊水》 主题初探[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1989,4: 81-83.
[9]刘江. 《痴心与浊水》 中女性 “他者” 形象的解读[J].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7(2): 102-105.
[10]李阳.殖民主义残存与历史中的希望——从《痴心与浊水》 看尼日利亚历史与未来[J].青春岁月,2012,24: 016.
[11]马建军,王进. 《死亡与国王的马夫》 中的雅西宗教文化冲突[J].外国文学研究,2005 (5): 161-166.
[12]秦银国.诗性,哲性与神性的融合——从《解释者》 谈沃里· 索因卡的叙述艺术[J].小说评论,2010 (S1): 160-164.
[13]邵殿生.沼澤地居民[J].世界文学,1986 (2).
[14]邵殿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W. 索因卡[J]. 国外社会科学,1987 (6): 55-59.
[15]宋志明.尼日利亚戏剧与宗教神话[J].外国文学评论,1999 (1): 38-44.
[16]宋志明. “奴隶叙事” 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 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3,5: 113-118.
[17]沃尔·索因卡.痴心与浊水[M].沈静,石羽山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382-384.
[18]沃尔·索因卡. 死亡与国王的侍从[M]. 蔡宜刚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003.
[19]沃尔·索因卡.钟国岭,等.森林舞蹈[J].外国文学,1987 (7): 1-36.
[20]吴保和.非洲的 “黑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渥尔· 索因卡和他的戏剧创作[J].上海戏剧,1987,2: 13-14.
[21]吴保和.非洲文坛的一颗明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渥尔·索因卡[J].艺术百家,1987 (2): 59-64.
[22]王三槐.奥因· 奥贡巴《变革运动》[J].读书,1987,1: 139-142.
[23]王燕. 探《路》 谈艺——索因卡戏剧形式刍论[J].东方丛刊,1992 (4): 162-171.
[24]王燕. 关于索因卡戏剧《路》 的一点思考[J].外国文学评论,,2005 (3): 48-49.
[25]王燕. 两种异质文化的兼容与整合——从《痴心与浊水》 解读索因卡小说的二元文化构成[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24(4): 79-83.
[26]王慧.论《狮子与宝石》 中的民族文化认同[J]. 戏剧之家, 2014, 9: 66-70.
[27]王慧.浅论《疯子和专家》中的荒诞因素[J].戏剧之家,2014,12: 035.
[28]汪剑钊.非洲现代诗选[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012.
[29]余嘉.森林之舞: 后殖民语境下的索因卡剧作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02: 1-33.
[30]远洋.老虎索因卡的愤怒之诗[N].文艺报,2015-5-22.
[31]朱世达. "我是非洲文学的一部分"——记沃莱· 索因卡[J].读书,1987,1: 135-138.
[32]周声. 民族寓言的讲述困境——以《痴心与浊水》中的性别叙事为中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5(4): 13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