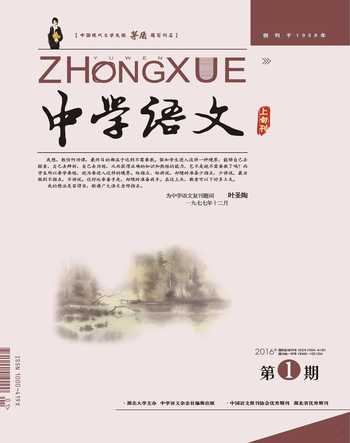韩李之争,分歧何在?
2016-05-30张卓君
张卓君
2014年10月李华平教授在《语文教学通讯》发表了《迷失在学科丛林的语文课——兼评特级教师韩军〈背影〉教学课例》,接着,韩军老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背影〉课七说》予以回应。此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线教师看韩军老师上课,心潮澎湃;读李教授文章,字字在理。剩下许多困惑,谁对谁错,何去何从?
仔细看这两篇文章,我们发现:李教授的评论对象在语文课和韩军老师的《背影》课之间徘徊;韩老师的“七说”着力于对李教授等的个别语句辩驳,各“说”自成一体。除了结论不同,二者行文有打太极的味道。二者分歧究竟在哪?就争论而言,对象明确、焦点集中才能展开,才能将真理越辩越明,推动语文教学研究的发展。本文依据课堂实录(包括文字版和视频课堂)和文章,分析两位大师产生争论的原因,梳理其中对语文教学有价值的焦点。参考视频为韩军老师在山东潍坊上的一节《背影》课,时常58分钟;参考文章为李华平教授的《迷失在学科丛林的语文课——兼评特级教师韩军〈背影〉教学课例》(以下简称称《迷》)以及韩军的《〈背影〉课七说》(以下简称《七说》)和《〈背影〉课堂实录》(以下称《实录》)。
这场论争得到广大语文人的关注,源于李教授由评析韩军老师的《背影》上升至对语文教学的评论,广大一线老师无法置身事外,视若无睹。笔者基于语文教学的立场分析,认为二人的分歧主要在语文课的界定标准、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文本解读方式上。引起争论的本质在于教学逻辑。
一、语文课的界定标准
语文是语言还是文学?是文本内容还是文本形式?李教授援引叶圣陶、朱自清等前辈大家的话表明:“语文教学的基本功能是教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李华平《迷》)韩老师反驳,“三说:《背影》课是精到、精彩的语文训练课。”(韩军《七说》)并列举《背影》课堂“丰富、系统的九大环节语言训练”。二人所持论据相同,结论却大相径庭。问题在哪?
考量李教授的论述。他对“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没有详细阐释,对韩《背影》课未能教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也未作分析。他对《背影》教学定位是:“教《背影》,眼睛应该看着散文学习的道路,致力于学生能够自己读懂散文。教师要在引导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的基础上,相机教给学生现当代散文的特点——重在表达‘我之心,如《背影》重在表达‘我对父亲的忏悔;给学生指点阅读的门径、重点,如《背影》中开头、结尾段落中的抒情议论性句子,辨析、品味反复出现的‘不见,特别是那个‘不字的深沉含义。”李教授的分析着眼于如何读懂散文,即“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在《背影》教学中表现为通过引导学生、通过散文阅读方法探讨作者意图。
考量韩老师的论述,“《背影》课是精到、精彩的语文训练课。”《背影》课的九大环节语言训练:“一,识字解词,积累字词。二,背诵文段,积累语言训练。三,阅读文本,辨识人物的阅读训练。 四,深悟人物角色和关系的阅读理解训练。五,咬文嚼字,推敲文字,理解人物的阅读训练。六,有创意的,汉字审美、联想、想像训练。七,用‘背字概括课文文段的语言训练。八,不断‘重命名标题的语言训练。九,贯穿课堂始终的富有感情的朗读、默读训练。”(韩军《<背影>课七说》)韩老师所列举的环节皆是语言活动,认为“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即语言活动。
比较可知,在《背影》教学中,“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李教授定位于如何阅读散文,韩老师统而言之为语言活动。前者是文学的角度,后者是语言的角度。究竟何者是语文课?还是都是语文课?这个问题不言自明。韩老师上的自然是汉语课,不是英语课、法语课等。韩老师从语言符号上定位语文课意义并不大。而李教授的论述又过于笼统,韩老师的课为什么不是在教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为什么说散文阅读方法是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内容也是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真正要争论和探讨的是“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涵义和内容体系,也就是语文课的界定标准和语文课程体系的建构。这是廓清部分语文教学过于随意的关键,也是一线老师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另外,李教授有这样一段话:“一部分学术视野较宽的语文名师(含网络上的名师)所上语文课迷失在了哲学、美学、生命教育等学科丛林中,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正道,失却了语文教学的味道。”笔者不太明白“偏离语文教学的正道”是否意味着不是语文课,若该论断成立,其逻辑前提便是教学内容决定课程名称,课堂上讲哲学、美学、生命教育,那么就是哲学、美学和生命教育课。韩老师反驳:“既然你把‘生命与死亡‘生命情深划给哲学课、生命课,那么,你理应把‘父爱‘父慈子孝‘父子情深划给伦理学课、家庭亲情课才是。”虽然尖刻,但其逻辑也成立。如果以文字表达的内容作为标准,那么只有语言学或者文学理论文本才能进入语文课堂了。而高中并不是大学中文系预科,高中培养的是社会公民,需要阅读的文字涉及各个领域。语文试卷上除了文学文本,论述类文本涉及哲学、社会学,实用类文本涉及地理、生物、美学等各科内容。语文是实践性学科,各个领域用语言文字表达,语文课堂要提高学生阅读各科文字的能力。其他科目也需要用到语文阅读能力,就像物理和化学课也经常要用到数学计算能力,以文本内容来界定是否为语文课脱离现实。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
如果抛开语文课的界定问题,假定韩老师的课是语文课(说假定是出于论证逻辑的考虑,不代表笔者立场),那么两位大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存在分歧。一篇文本有多方面的价值,选入教材之后则有其教学价值。教学价值又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教师选择教学内容时需考虑文本、学情和课程等方面,以下就这三个方面探讨二人教学内容选择的分歧。
从文本来说,二人教学目标选择思考的方向不同。李教授将《背影》定位在散文阅读把握作者的情感上,认为《背影》重在表达“我”对父亲的忏悔。韩老师则着力于解读《背影》中的生命和死亡哲学,“我《背影》课没有否定亲情,却深化了对亲情的理解。”“《背影》文本里,处处充溢着‘生命与死亡意识。”“须高扬、鼓励深刻,警惕反深刻、反文明逆流浊浪。”前者从感性的维度丰富学生的情感,后者从理性的维度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方向不同,范畴不同,结论当然不同,但在各自立论的范畴内都成立。所以,要讨论的恐怕不是《背影》里有没有生命和死亡意识,也不是《背影》里有没有亲情或其他思想感情,而是在一定的教材体系中,在基础教育的课堂里,教学《背影》该选择什么。
从学情来讲,二者对学生能否接受生命和死亡意识的判断不同。李教授说:“十二三岁的孩子那颗幼小的心灵是无论如何也盛不下韩老师五十年风风雨雨的。不从学情出发,只管自顾自地灌输,这是一种多么落后的教学。”认为韩老师选择教学内容时是以教师为中心,而忽视学生的理解的。韩老师回答,“儿童有强烈的生命和死亡意识。”并从心理学、儿童文学作品、基础教育和儿童游戏等角度论证。其实二人讨论的均是抽象概念的“初中生”的理解能力。王荣生教授在《根据学生学情选择教学内容》说得非常精当:“了解学情,并不是指对学生的情况泛泛而论,而是要针对某一篇具体的课文,去探测学生的学习经验——哪些地方读懂了,哪些地方没读懂,哪些地方能读好,哪些地方可能读不好。”①对《背影》教学,真正的学情是所执教班级的学生究竟怎么看《背影》,据此选定的教学内容才是最科学的。二者根据学情选择教学内容均是出于抽象的学生观。
从课程角度看,不同语文课程观导致了不同的教学选择。二者对语文课的界定标准不同导致对《背影》的课程价值选择不同。第一部分已作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但以下几个问题仍旧值得思考:韩老师探讨的主旨(生之背,死之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是语文课程内容,但探寻主旨的方式是不是语文课程内容?韩老师让学生品味父亲爬月台那段的“蹒跚、慢慢、探身、攀、缩、微倾、努力”等词语,悟出父亲小心翼翼、腿短、体胖、年老体衰、老态龙钟、风烛残年之情状。该环节是不是语文课程内容?能不能仅从知识目标的角度判定整堂课的课程价值?能否承认局部课堂的课程价值?
对于语文课程,一是要建构语文学科内容体系;二是要建构符合学生各阶段认知的序列。在散文阅读教学中,《背影》的文体教学价值是什么?作为经典散文,《背影》区别于其他散文的独特的课程价值又是什么?针对特定阶段的学生,《背影》给他们哪方面的精神滋养和语言提高最为合适?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线教师最想知道的。
王荣生教授有言: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更重要。若因教学内容选择上的分歧导致结论不同,还是推本溯源探讨教学内容选择观吧。
三、文本解读的分歧
李教授在《迷》中认为韩老师的文本解读是“感受谬见”和“起因谬见”结合的怪胎。“一是考古式地从作者身上和时代背景中寻找解读依据,二是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代替了对文本的解读。”皆是从文本之外对文本进行解读。《七说》中没有解释文本解读方式,不过,韩老师曾在《生之背,死之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文中对《背影》进行新解码。我们可以从该文和课堂实录来窥探韩老师的文本解读路径。鉴于李教授以对《背影》的解读错误作为重要论据证明韩军老师的课偏离了语文的正道,笔者认为很有探讨必要。
关于“起因谬见”,李教授说:“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本不是一个哲学文本,作者不是在给我们讲解有关‘生与死的哲学问题。”“我们不能用一个人的学习背景简单地去‘套读他写作的文本。”这的确不错,但从课堂教学过程来看,韩老师得出《背影》写“生与死”的结论是从祖母、父亲、朱自清、朱子构成的生命链条得出的,并非从朱自清的学习背景中套读来的。相反,这个结论看上去很符合李教授所说的重视文本的观点。对于“生命与死亡”这个主题的解读事实上不存在“起因谬见”(用对作者的研究代替对文本的解读)的问题。
韩老师“生命的虚幻”这一主题并非从《背影》中得出,而是从《匆匆》《毁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比较中得出的,得出之后再“回到《背影》,能否悟出朱自清先生的意念,就是,背,是一种肉体的、躯体的活生生的实在,影是一种虚在、虚幻、空无、转瞬即逝的影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补充内容,生命的虚幻在《背影》中很难直接读出来,作者的其他作品已经参与了课堂的意义建构,“生命的虚幻”是这一系列作品的某个角度的解读,并非对《背影》的解读。也许这就是李老师所说的“起因谬见”了(前提是将起因谬见从“作者的学习背景”拓展到与作者有关的材料)。这种解读方式得出的结论确实有待商榷。
以上可知,如果把“起因谬见”定义为“用一个人的学习背景简单地去‘套读他写作的文本”,韩军老师的《生之背,死之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确实存在,《实录》中并未出现朱自清的学习背景,说其“起因谬见”是没有依据的。但如果把“起因谬见”扩展为作者研究,谈用作者的相关材料(不单是学习背景,还包括其他作品,比如本课中的《匆匆》《毁灭》等)对文本解读的作用就值得探讨了。汪洋老师在《有人文味的语文才是真语文》中提到韩军老师采用的方法不过是知人论世②。李教授自己也说:“解读行为允许暂时离开文本到作者身上去找答案,允许读者展开想象,但必须受文本的制约,要落脚到文本上。”可见,李教授并不排斥文本解读时的作者研究,只是强调对作者的研究要落脚到文本上。那么,争论的真正的焦点是:文本解读时对作者的研究怎样选择才是“受文本制约”的。
至于“感受谬见”,李教授说:“韩军关于‘生与死的生命感悟,其实不是来自《背影》,而是他年过半百的人生感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他此时思想的主线,于是他便作如此解读。这与《背影》何干?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韩老师针锋相对地援引2004年12期《名作欣赏》就有《〈背影〉:被‘死亡照亮的世界》一文回应:“从学界到中学生,皆认同《背影》充溢生命与死亡意识。‘生命的脆弱与短暂‘生命情深‘生命与死亡意识,这是朱自清的和朱自清的《背影》文本本身的,不是韩军的。”既然韩老师否认生命与死亡意识是他自己现在的感受,旁观者没有必要争论。
那么,韩老师的解读为什么不被李教授认可?韩老师的解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可从韩老师的课堂流程来探寻他的解读途径。“生命的脆弱与短暂”这个主题是这样得出来的:研读朱自清四次流泪,分析原因。第一次流泪因为祖母死了;第二次缘于父亲老了;第三次是父亲走了;最后一次由于父将大去。由此可见本文是喟叹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这个推理确实成立。《背影》中确实有生命和死亡意识。写《“七说”何以七错》的潘璋荣老师也承认:“《背影》中的确包含或隐含着作者的‘生命意识,或者对生与死的感悟。”③不过,潘老师又明确表态:“综观全文内容,我认为这种作者的生命意识,相对说是隐性的和次要的。文章中更适合使用‘充溢这个词的是父子深情——一种天然的人伦和亲情。”④潘老师用“隐性和次要”来定位韩老师的解读,也就是韩老师解读的是《背影》的部分内容,不是整体。
那么《背影》整篇文章表达了什么?
从叙事学来说,作者的意图决定了文本的叙述方式。生活是多维立体的,文字是一维的,单维的文字要反应多维的世界,那么维度的选择和叙述的展开方式取决于作者的意图。读者可以从文本的叙述方式反推作者本意。就《背影》而言,作者采用倒叙,以“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起笔,提示读者思考“我”对父亲的看法和情感。然后描述买桔子这个件事中父亲的背影。为了叙事清晰,交代了这是父亲送我北上时发生的事。而之前祖母死去,父亲的差事交卸等皆是为此作铺垫。最后首尾呼应,重提背影。本文的叙述主线是“我”对父亲爱子之情的感动和对自己曾经行为的忏悔。这种叙事方式指向的是“背影”,是“我”对父亲的情感。韩老师的解读路径并没有遵循作者的叙述结构。如果作者想表达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就该像韩老师上课那样叙述:以四次流泪为线索,先写祖母死了,再写父亲老了,再写父亲走了,最后写我的儿子出生了。文本的第4和第5小节父亲坚持要送“我”的文字没必要写,第1小节也没必要。最后一节只需写父亲牵挂“我”的儿子。“我”对父亲的情感不必写,“我”对生命的哲理思考才是重要的。事实上朱自清写《背影》不是按照这样的结构展开的,结构是“沟通写作行为和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⑤,韩老师在课堂上的解读没有遵循文本自身的叙述结构,而是将其解构,然后将相关内容重组,类似“超链接”。这种解读路径通常由文学研究者采用,解读出来的是文本的内蕴,未必是作者意图。韩老师教的是“《背影》中的生命和死亡意识”,不是《背影》。不遵循文本结构的解读结论往往不是作者的写作意图。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教学生读懂文本,理解作者的意图。李教授称之为“理解作者的理解”。《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目标”部分中说:“在阅读中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文章基本的表达方法。”⑥中学生语文课堂上学习经典文本,需要梳理文本整体结构,把握作者思路,由此理解文本大意。同时,还要了解和欣赏文本的“‘模仿结构——按照历史和文化已建立的‘优秀标准掌握优秀文化、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珀维斯)⑦。现代接受美学有个“理想的读者”的概念。“‘理想读者只愿意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其阅读目的是获取语篇的大意;‘理想读者对具体语篇中的具体事件不熟悉,但拥有成人所具有的‘基本背景知识”⑧。教师面对的中学生大多也是“理想读者”。他们初读文章时不会任意选择文中的词句建构意义,韩老师的解读方式不符合大多数中学生读文本的思路。
不过,当代语文教学也提倡研究性阅读,作为义务教育语文教学总纲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提出:“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说,“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阅读,对优秀作品能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在《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苏卷)说明》说:“探究F(1)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丰富意蕴,以及内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3)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⑨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还是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抑或《考试说明》都涉及研究性阅读,中学课堂能否拒绝?说《背影》全文主要表达作者对生与死的思考固然不对,但也不能否认这是它某个角度或某个层次的含义。这种研究性解读是课程标准认可的。
当然,研究性解读和作者意图、文本大意不能有矛盾之处,研究性解读的结论必须有理有据,它是从文本的不同角度或层次对文本的观照,而不是对文本的否定。说《背影》中有生与死,也有父子深情是研究性阅读;而认为《背影》说的是生与死,而不是父子深情则有失偏颇。
所以,两位大师在文本解读上的分歧是:课堂教学中解读文本的思路是遵循文本结构还是自主组合?把握文本主旨和研究性阅读在教学中如何平衡?即文本说了什么和“我”读出了什么在教学中怎么处理?探讨这些问题比争论谁是谁非更有价值。
四、教学逻辑
这个问题韩老师在《七说》里似乎没有涉及,李教授在《迷》一文中也没有展开。不过笔者认为,对韩老师的课的争议多是缘于教学逻辑的问题。
广义的教学逻辑指“教学系统中主客体之间的动态转换逻辑”⑩。它促使各个教学要素“通过波动而有序”?輥?輯?訛。朱德全教授认为,教学系统涉及学科知识逻辑、教学逻辑、学习逻辑和认知逻辑四个层面。教学效果取决于这四个逻辑层面的共振、共享和共赢。狭义的教学逻辑特指教的逻辑。笔者这里讨论狭义的教学逻辑。“教的逻辑是教师组织安排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活动顺序的思路和线索。”?輥?輰?訛教的逻辑是否合理甚至高效,取决于它是否遵循教学本质,是否符合学科逻辑和认知逻辑。
从教学本质来看,韩老师的教的逻辑不能促进学生与文本的对话。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的本质是交往实践,“只有在交往过程中,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关于现实的新知识,也只有在交往过程中才能传授社会历史经验。”?輥?輱?訛交往对话分成两种:一是教师与学生的直接对话,一种“在场”的、横向的显性交往,二是教学主体和人类文化之间的间接对话,一种“不在场”的、纵向的隐性交往。李教授认为韩老师在“灌输”,用自己的人生感悟代替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即课堂缺少“不在场”的隐性交往。而散文教学的本质是促进学生与文本的隐性交往的。课堂上的显性交往也是服务于促进隐性交往的。品读父亲爬月台买桔子部分时,韩老师深沉的语调引导学生体味朱自清的感受:父亲苍老太早,衰老太快。学生都沉浸在感伤中,这种显性对话是有效的。但有些地方却未必:在体会“背”“背负”“背债”的含义时,韩老师引导大家唱起了《蜗牛和黄鹂鸟》的歌词。韩老师想用蜗牛的形象来形容承受生活重压的父亲,但唱起的歌曲却是欢快而有趣味的,与隐性对话所需的课堂气氛完全相反,给人极不和谐之感,阻碍了隐性对话的深入。视频实录第32分钟是探讨生命的脆弱和短暂,韩老师分析完之后来了句:“来点掌声吧!”第36分钟小结主旨为喟叹生命脆弱与短暂后,课堂非常安静,学生正努力沉浸其中或者正为此伤感,韩老师却突然唱:“掌声响起来……”于是学生纷纷鼓掌。热烈的气氛一下子让之前的沉痛感遁于无形。韩老师的课堂气氛很活跃,却依然给李教授“灌输”的感觉,因为学生课堂上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与文本的对话不够,根源就是韩老师的教的逻辑没有契合阅读教学的本质。
从学科逻辑来看,评判教的逻辑是否科学要依据教学内容自身的标准。对生命和死亡意识这样的理性认知,教学内容和活动展开要遵循理性认知逻辑。而如果是教学生体验作者对自己行为的忏悔和对父亲爱子之情的感动,则要遵循情感教育的逻辑。如果以情感体验的逻辑去评判理性认知逻辑,结论并不恰当;反之亦然。韩李论争颇有此味道。
从认知逻辑来看,认知逻辑指学生认知事物的基本过程和合理顺序。如果教的逻辑符合学的逻辑,学生就能轻松跟上教师的思路;反之,会觉得晦涩难懂。韩老师教的逻辑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逻辑呢?
从大的教学流程来看:韩老师的课堂先由四世同文得出生命的幻灭;再从四次流泪得喟叹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接着从“生之背,死之影”对标题——“背影”的理解,归结为生命的短暂、脆弱和虚幻。最后是文学幽默:出示朱自清的短信,以证解读正确。前面三大主要环节,各部分自成一体,都得出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的主题,三个环节没有思维上的递进,只是量的叠加,类似并列式结构的议论文。各部分在逻辑上是自成一体的封闭式结构,学生活动无法撼动教学流程,即使答出了“不和谐”的答案,老师也会巧妙地引导出“理想”的回答。课堂上,学生并非像辩论赛上般站在老师的对立面,而是努力与老师合作理解文本,结果课堂上必然只有老师的“声音”。李教授说:“将自己的观点‘精彩地演绎一番”,称其为“灌输”也就不足为怪了。
韩老师想让学生思维从一切生命都将逝转到研读朱自清的四次流泪。但从学生的思维流程看:流泪是想到生命终将消逝之后悲伤的表现,问有几次流泪即问有几处涉及生命终将消逝。但要找的四次流泪都是生命将逝吗?且不谈将四次流泪的原因归结为——父亲(走)了和父亲(大去)了是否正确,就看第三次流泪:和父亲分别是不是生命的将逝?学生此时该怎么想?要么无所适从,要么放弃前面所有的努力,重新跟上节奏。而无论哪种情况,之前的思考努力都已停滞,无法达到课堂效率的最大化。
所以,不管是得出主旨的教学片断,还是教学流程的几个大环节,韩老师教的逻辑和学生学的逻辑的匹配度不高。学生能够积极发言,但与文本对话还是零碎的。被李教授认定为灌输式教学,根本原因还是教的逻辑出了问题。灌输作为一种教学方式本无所谓优劣,但不遵循在学生认知规律的灌输断然不可,根本问题是教学逻辑。个人认为这也是教学上最本质的问题,非常值得深入探讨。也许有人认为如此分析教学过程有些苛刻,但设身处地想想:要求学生认真听讲,教师语言怎可随意?教学过程所应遵循的逻辑是不可忽视的。
结语
诚如李华平教授在《不拿语文做人情》中所言,这场讨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语文人,都要努力参与其中,切忌置身事外”?輥?輲?訛。讨论热烈,进展不大的根源是焦点不集中,产生分歧的根源不明。厘清分歧,梳理焦点是推进争论的必要工作。笔者认为,两位大师的分歧主要在:语文课的界定标准以及语文课程体系的具体内容;经典文本(如《背影》)教学价值、作者研究如何算是受文本制约、把握文本主旨和研究性阅读在教学中如何平衡等问题。从教学实施看,二者的争论多源于教学逻辑。如果大家能在这些问题上深入探讨,将更能促进语文教学研究的发展。
————————
参考文献
①王荣生:《根据学生学情选择教学内容》,《语文学习》,2009年第2期。
②汪洋:《有人文味的语文才是真语文》,《中学语文》,2015年第7期。
③④潘璋荣:《“七说”何以七错》,《语文教学通讯(B刊)》,2015年第6期。
⑤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⑦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⑧黄忠伟:《理想读者视角下的批评话语分析》,《宁波工程学院》,2013年第2期。
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苏卷)说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期。
⑩朱德全,张家琼:《论教学逻辑》,《教育研究》,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