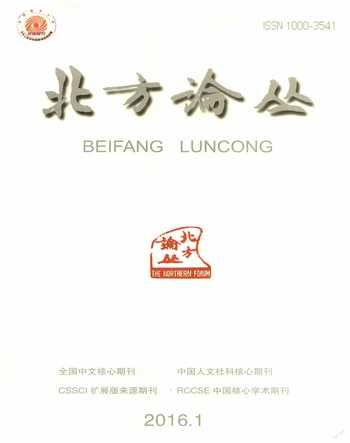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2016-05-30吴方基袁海瑛
吴方基 袁海瑛
[摘 要]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汉代;灾异思想;“天人”;“人”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79-06
Abstract: In the “Heaven and Human” Problem, Scholars always explore the “Heaven” for many, discuss the “Human” is minimal. The content of “Human” in the “Heaven and human” has been changing constantly with the times. The “Heaven and Human” problem reflected in Calamity Theory among Han dynasty. Han Calamity Theory had seen the content of “Human” in the “Heaven and Human” constantly evolving.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content of “Human” in the “Heaven and Human” was monarchs.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the content of “Human” first added the courtiers and after added the people. To the Eastern Han, the content of “Human”—— monarchs,courtiers and people had Changed in the proportion. At this time, courtiers and people is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Han “Heaven and Human” thought was to service in deification the monarch, so early content of “Human” was monarchs. However, with the frequent Calamity, monarchs can not afford to so many Heaven's condemnations, therefore the courtiers must also share the blame. Then, people added the content of “Human”,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an political ideology. This means not only Heaven decided if monarch was appointed by Heaven, but people became the important factor which decided if the monarch would be admitted.
Key words:Han Dynasty; calamity theory; “Heaven and Human”;“Human”
汉代所说“灾异”,是指代表天意的自然或人为灾害、天文异常和社会异象。灾异思想形成于西汉,是在认识、解释进而消除灾异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系统之观念。汉代灾异思想渊源于先秦的天人思想,是天人思想在汉代的发展。天人问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此问题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天”的探讨颇多,对“人”的讨论甚少。关于“天人”中“人”的含义,学者们意见较为一致,一般都认为“人”即人类,是自然存在的人。然学界只注意到“天人”之中“人”的一般性,天人思想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的具体性凸显,“人”的内容的差异展现出来,以往学者未予关注。特别是两汉时期,天人思想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中,“天人”中“人”的内容随灾异思想的发展而演变。故而,本文拟从灾异思想的角度,揭示汉代“天人”中“人”的内容的演变。
一、西汉前期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
灾异思想是在“天人感应”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天人感应”观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天通过与人互动,以祥瑞或灾异的形式体现赏善罚恶的功能。灾异思想在西汉高祖时业已出现。陆贾在《新语·明诫第十一》中言:“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贤君智则知随变而改,缘类而试思之,于□□□变。”[1](p.155)依陆贾之见,君主治国有失,天即变生灾异,此反映的天人关系是有意志的天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文帝时期,贾谊也有这种思想,他的《新书·大政上》说:“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 [2](p.150);《新书·大政下》又言:“故治国家者,行道之谓,国家必宁,信道而不为,国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选也,而道不可离也。呜呼,戒之哉!离道而灾至矣” [3](p.154)文帝二年日食,诏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3](《汉书·文帝纪》)天有变异,文帝归咎于自己,反映的天人关系亦是天与君主的关系。
天人关系是天与君主的关系,这种观念在西汉前期普遍存在。活跃于景帝、武帝时期的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言:“宋大水。鲁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于粢盛,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弔。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仁,斋戒不修,使民不时。天加以灾,又遗君忧,拜命之辱。”[4](p.99)此中指出,天加灾于宋国,是宋君的过失所造成。传中又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地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使末逆本,使人诡天,气鞠而不信,郁而不宜,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4](p.262)韩婴同样把天降灾异与君主联系起来。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诏问灾异的缘起,董仲舒对策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3](《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还是把灾异的出现归咎于人君,体现的天人关系同是天与君主的关系,这在《春秋繁露》中更为多见: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5](《王道》)。
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其音角也,故应之以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霹雳者,金气也,其音商也,故应之以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电者,火气也,其音徵也,故应之以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气也,其音羽也,故应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气也,其音宫也,故应之以雷。[5](《五行五事》)
所闻曰:“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5](《郊语》)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多次强调上天与王或天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君主及其行为是上天是否降灾的依据,同样,上天是否降灾也表露了君主及其行为。
以上可见,西汉前期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天人关系是有意志的天与君主的关系。
二、西汉中后期灾异思想发展与“天人”中“人”的内容变化
西汉中期,灾异思想在继续关注君主的同时,臣子也渐成它关注的对象,“天人”中“人”的内容随之发生变化。昌邑王时,夏侯胜善说灾异,“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夏侯)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3](《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认为,下臣的行为感应到天,使天久阴而不雨。宣帝初期,大将军霍光颛政二十年,张敞认为:“月朓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3](《汉书·张敞传》),即是指霍光颛政引发灾异。同样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京师大雨雹,大行丞东海萧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专权之所致”[6](《资治通鉴》卷二五,宣帝地节三年)。魏相为丞相时也曾上书宣帝曰:“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3](《汉书·魏相传》)这亦是大臣承担天降灾异之责。灾异思想关注的对象由君到臣的演变,导致西汉大臣之间利用灾异而相互倾轧。元帝时,夏季寒冷,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3](《汉书·楚元王传·刘向》)。弘恭、石显等人即是因灾异倾轧周堪、张猛。西汉中期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除了君主之外,还包括臣子,天人关系是有意志的天与君、臣的关系。
元帝以后,灾异思想关注的对象进一步复杂。当时灾异思想认为,灾异不仅是由君、臣感应上天而生,“民”也能与天发生感应,致使灾异出现。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懬,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3](《汉书·元帝纪》)诏书指出,百姓失望,感应皇天,出现星变异象。“民”成为灾异关注的对象,元帝时还只是个别情况,成帝时此类事例逐渐增多。例如,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诏曰:“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3](《汉书·成帝纪》)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诏曰:“朕承太祖鸿业,奉宗庙二十五年,德不能绥理宇内,百姓怨恨者众。不蒙天佑,至今未有继嗣,天下无所系心。”[3](《汉书·成帝纪》)谷永上疏成帝言:“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娄降,饥馑仍臻。”[3](《汉书·谷永传》)谷永指出,民众愁恨感应上天,使灾异频发。
成帝时期,“民”成为灾异思想关注的对象,与民众的武装反抗关系密切。西汉自建国到成帝即位,民众的武装反抗活动极少。据记载,武帝时发生一次,即“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3](《汉书·武帝纪》)。成帝当政后,民众的武装反抗陡然增多: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
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
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广汉郑躬等党与寖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称将军……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3](《汉书·成帝纪》)
短短8年(公元前22年至公元前14年),爆发四次较大规模民众武装反抗。面对民众武装反抗,成帝多次下诏责己: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诏曰:“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绥,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闵焉。”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诏曰:“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讫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诏曰:“乃者,龙见于东莱,日有蚀之。天著变异,以显朕邮,朕甚惧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有可省减便安百姓者,条奏。”同年,诏曰:“前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积土增高,多赋敛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诏曰:“天灾仍重,朕甚惧焉。惟民之失职,临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问耆老,民所疾苦。”[3](《汉书·成帝纪》)
成帝诏书围绕的中心内容,即是民众与灾异。民众武装反抗,使皇帝看到了“民”的力量存在,导致“民”的观念兴起,“民”成为灾异思想的关注对象势所必然。
至哀帝,“民”继续为灾异思想所关注。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息夫躬上疏言:“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3](《汉书·息夫躬传》)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鲍宣上疏亦指出:“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连阴不雨,此天有忧结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3](《汉书·鲍宣传》)息夫躬与鲍宣都提出,“民”与“天”存在着感应关系,天降灾异是“民”的因素导致的结果。
西汉中后期,灾异思想不断发展,“天人”中“人”的内容随之演变,它由西汉前期的君、臣增加到君、臣、民。天人关系不仅仅是天与君、臣的关系,而且是天与民的关系。
三、东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
东汉时期,灾异思想关注的对象依然是君、臣、民,“天人”中“人”的内容与之对应,天人关系是有意志的天与君、臣、民的关系。然而较之西汉,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在所占比重上有所不同:
其一,东汉灾异思想对“臣”的关注显然增多,“臣”在“人”的内容中所占比重变大。东汉灾异发生,君主虽依然承担其咎,然更多的是责备臣子,“臣”承担灾异之咎的情况逐渐增多。明帝时,“会连有变异,意复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经术,郊祀天地,畏敬鬼神,忧恤黎元,劳心不怠。而天气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7](《后汉书·钟离意传》)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是时窦太后临政,宪兄弟各擅威权。鸿因日食,上封事曰:‘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亏,君之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7](《后汉书·丁鸿传》)丁鸿认为,日食的发生即是外戚擅权所致。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日有食之。时帝遵肃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师,有司以日食阴盛,奏遣诸王就国”[6](《资治通鉴》卷四八,和帝永元十五年)。安帝时,(陈)忠上疏曰:“臣闻位非其人,则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则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责臣司,臣司狃恩,莫以为负。”[7](《后汉书·陈宠传·陈忠》)延光元年(公元122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7](《后汉书·儒林传上》)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5年),杨震因地震,上疏曰:“臣蒙恩备台辅,不能奉宣政化,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7](《后汉书·杨震传》)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戊子,客星出天苑。辛卯,诏曰:‘间者以来,吏政不勤,故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7](《后汉书·顺帝纪》)“顺帝时,屡见,阳嘉二年正月,公车征,顗乃诣阙拜章曰:‘……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7](《后汉书·郎顗传》)郎顗指出,“寒阴反节”是三公之责。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李固对策曰:“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7](《后汉书·李固传》)同是阳嘉年间,衡因上疏陈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继体承天……而阴阳未和,灾眚屡见,神明幽远,冥鉴在兹。福仁祸淫,景响而应,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虽远,吉凶可见,近世郑、蔡、江、樊、周广、王圣,皆为效矣。”[7](《后汉书·张衡传》)张衡同样认为,灾异发生是因为臣有作威作福。桓帝“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7](《后汉书·梁统传·梁冀》)灵帝时日食,陈蕃说窦武曰:“……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7](《后汉书·窦武传》)这些事例均是把灾异的发生归咎于臣子。此例甚多,不胜枚举。
东汉安帝以后,“臣”承担灾异之咎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多因灾异而策免“三公”。安帝即位后,以灾异寇贼策免太尉徐防,“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7](《后汉书·徐防传》)。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3年),司空尹勤“以雨水伤稼,策免就国”[7](《后汉书·陈宠传》)。永初五年(公元108年),太尉张禹“以阴阳不和策免”[7](《后汉书·张禹传》)。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司空张晧“以阴阳不和策免”[7](《后汉书·张晧传》)。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51年),(杜乔)代胡广为太尉……在位数月,以地震免”[7](《后汉书·杜乔传》)。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90年),司空黄琼“会以地动策免”,“永兴元年,(黄琼)迁司徒,转太尉……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其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7](《后汉书·黄琼传》)。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王畅)迁司空,数月,以水灾策免”[7](《后汉书·王龚传·王畅》)。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刘宠)代王畅为司空,频迁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归乡里。”[7](《后汉书·循吏列传·刘宠》)“灵帝初,(刘矩)代周景为太尉……复以日食免。” [7](《后汉书·循吏列传·刘矩》)“(熹平)六年,迁(陈)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复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以日食免”[7](《后汉书·陈球传》)。献帝初平元年,“(种拂)代荀爽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7](《后汉书·种暠传·种拂》)。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朱俊)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明年秋,以日食免”[7](《后汉书·朱俊传》)。
“臣”在“人”的内容中所占比重加大,与当时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尤其东汉中后期,“政事渐损,权移于下” [7](《后汉书·张衡传》),“贵臣擅权,母后党盛” [7](《后汉书·儒林列传上·孔僖》),“国政多失,内官专宠” [7](《后汉书·窦武传》)。正如东汉末政论家仲长统所言: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也。[7](《后汉书·仲长统传》)
东汉中后期,“戚宦之臣”权力嚣煊,“臣”在“人”之内容中地位提升,引起灾异思想过多关注,使地位高而无实权的“三公”李代桃僵,成为“戚宦之臣”承担灾异之咎的替罪羊。
其二,“民”在“人”的内容中地位越发重要,其与天的关系越发紧密。东汉初,王常言:“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 [7](《后汉书·王常传》)光武帝即皇帝位,其祝文也曰:“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 [7](《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和帝初立,鲁恭上疏曰:“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 [7](《后汉书·鲁恭传》)和帝永元七年(公元95年),皇帝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 [7](《后汉书·和帝纪》)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皇帝使人对策,马融对曰:“今科条品制,四时禁令,所以承天顺民者,备矣,悉矣,不可加矣。”[6](卷五一)
“民”的地位提升的另一个表现,是灾异思想在刑罚上的积极实践。刑罚与灾异的关系,西汉董仲舒在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对策时就有论述:“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3](《汉书·董仲舒传》)即是说刑罚失度使“邪气”生,导致阴阳失和,产生灾异。然而,董仲舒提出灾异缘起刑罚不中的思想,在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对刑罚的实践产生影响,直至元帝时,此种灾异思想以诏书的形式,才真正在刑罚上实践起来。上文所引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发生星变异象,诏书指出是百姓失望感应皇天所致,为此,元帝“省刑罚七十余事” [3](《汉书·元帝纪》) 。成帝当政,灾异思想在刑罚上的实践多于元帝之时。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春二月,皇帝下诏曰:“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绥,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闵焉。” [3](《汉书·成帝纪》)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春正月,皇帝又下诏曰:“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讫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 [3](《汉书·成帝纪》)刑罚不中,众人怨恨,引发灾异,成帝诏告有关部门,刑罚务行宽大。民众是刑罚的主要对象,正如宣帝诏书所言:“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 [3](《汉书·宣帝纪》)。刑罚成为灾异思想关注的内容,正是由于灾异思想关注到民众,“天人”中“人”的内容加入“民”的成分。
东汉时,“民”在“人”的内容中地位提升,使东汉刑罚宽和起来。章帝时,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7](《后汉书·章帝纪》)和帝时,诏曰:“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有司不念宽和,而竞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下济元元也。” [7](《后汉书·和帝纪》)顺帝诏曰:“朕讬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庶狱弥繁,忧悴永叹,疢如疾首……嘉与海内洗心自新。其赦天下。从甲寅赦令已来复秩属籍,三年正月已来还赎……务崇宽和,敬顺时令,遵典去苛,以称朕意。” [7](《后汉书·顺帝纪》)质帝时,梁太后临朝听政,诏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不久,又下诏“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以崇在宽”[7](《后汉书·质帝纪》)。
东汉宽和刑罚主要有两种措施:
一是减轻刑罚或无罪释放。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30年),天下久旱,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 [7](《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光武帝明确表示,民众的愁怨感动上天,以致旱灾,故而无罪释放了大量囚徒。此后,历代继位的皇帝仿照而行,多遇旱灾,或减轻刑罚,或无罪释放囚徒。例如,明帝时天旱,“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6](《资治通鉴》卷四五,明帝永平十四年)。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大旱,杨终以为是“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所致,章帝听从杨终的话,让徙者归还 [7](《后汉书·杨终传》) 。和帝时京师发生旱灾,“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7](《后汉书·和帝纪》)。安帝时久旱,当时邓太后临朝听政,“太后比三日幸洛阳,录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余减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7](《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顺帝时,“诏以久旱,京师诸狱无轻重皆且勿考竟,须得澍雨。” [7](《后汉书·顺帝纪》)质帝时,“自春涉夏,大旱炎赫”,皇帝“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 [7](《后汉书·质帝纪》)。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49年)日食,诏曰:“间者,日食毁缺,阳光晦暗,朕祗惧潜思,匪遑启处。《传》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 [7](《后汉书·桓帝纪》)献帝时三辅大旱,皇帝“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 [7](《后汉书·献帝纪》)。此例甚多,兹不赘举。
二是大赦天下。东汉因灾异发生而“大赦天下”的次数非常多:光武帝时日食,下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 [7](《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09年),司隶、豫、兖、徐、青、冀六州发生蝗虫之灾,大赦天下;永初六年(公元111年),豫章、员溪、原山崩,大赦天下 [7](《后汉书·安帝纪》) 。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出现疾疫之灾,诏曰:“奸慝缘间,人庶怨讟,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盖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阳嘉三年(公元134年)因大旱又制诏曰:“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 [7](《后汉书·顺帝纪》)桓帝“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又“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癸酉,大赦天下” [7](《后汉书·桓帝纪》)。灵帝时,“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颎并下狱死。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 [7](《后汉书·灵帝纪》)。献帝初平“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大赦天下” [7](《后汉书·献帝纪》)。
四、结论
灾异思想与天人思想关系密切,灾异思想渊源于天人思想,天人思想在灾异思想中得到集中体现。两汉时期,随着灾异思想的发展,天人思想不断地变化,“天人”中“人”的内容也在逐渐地演变。西汉前期,灾异思想关注的是君主及其行为,“天人”中“人”的内容则为君主,天人关系是有意志的天与君主的关系。西汉中后期,灾异思想关注对象由君主增加到君、臣、民,“天人”中“人”的内容随之扩增,天人关系为有意志的天与君、臣、民的关系。此时期,“民”的成分加入“天人”中“人”的内容,是“民”的观念兴起所致,与民众武装反抗密切相关。至东汉,“天人”中“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在所占比重上出现变化:一是灾异思想对“臣”的关注显然增多,“臣”在“人”的内容中所占比重加大,此与当时“戚宦之臣”擅权的政治环境有关;二是“民”在“人”的内容中地位越发重要,直接导致东汉刑罚宽和。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及其统治,故初期天人关系是有意志的天与君主的关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个人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为君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成为灾异思想关注的对象,“民”的成分加入“天人”中“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及其统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参 考 文 献]
[1]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贾谊.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吴方基:长江大学讲师,历史学博士;袁海瑛: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