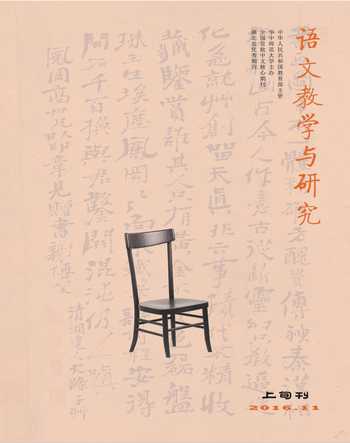《小石潭记》之“清”流探幽
2016-05-30祁艳
《小石潭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写的著名的《永州八记》中的一篇。全文以作者的行踪为线索,经历了“闻声寻潭——伐竹见潭——小潭揽胜——悄怆离潭”几个历程。全文以小石潭“水尤清洌”为正式游览之起点,以柳氏“以其境过清,乃记之而去”为游览之尾声,一个“清”字穿梭于首尾,一字立骨,立起了全文的“清”流神韵。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给“清”字作如下解释:“清,朖也。澂水之皃。朖者,明也。澂而後明。故云澂水之皃。引伸之,凡潔曰淸。凡人潔之亦曰淸,同瀞。《说文》:澂,清也。从水,徵省声。”水清而静。后作‘澄。”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版)的《古代汉语词典》上关于“清”字的解释,有这样的一个义项:“冷清”。据此,“清”字可以做以下几种理解:①清澈,明朗,不浑浊;②清静,清幽;③洁净,高洁;④清爽,寒凉。
本文拟根据“清”字的这几个内涵,寻找与《小石潭记》相关的契合点,从潭水之清澈、环境之清幽、意境之凄清、品格之清高四个方面来探索《小石潭记》通往柳氏内心的通幽曲径。
一、潭水之清澈
文章开篇就写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簧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未见潭水,先闻水声。此声“如鸣佩环”,“佩环”本是玉制配饰,供人随系身边,走起路时摇曳轻碰,遂发出清脆悦耳之声,此乃水声之“清脆”。“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则泉水之“水皆缥碧,千丈见底”之清澈即可想见。
接着作者写道“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正面写潭水之清澈透明。“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潭中游鱼历历可数,在水中若“空游”,所谓“空”,即什么都没有,鱼儿怎么可能“空游”呢?这里明写水中游鱼,实则意在“烘云托月”、“背面傅粉”、“注此写彼”,以游鱼游于水中似“空游无所依”来烘托潭水之清澈,也能将人带入欣赏游鱼空游、与人逗乐的清雅意趣中去。
二、环境之清幽
小石潭之得名,全由“石”字而来。“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石质坚硬,流水不腐,因此潭水清澈。涓涓溪流从石上流过,便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雅兴。
小潭周围“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更是翠色欲滴,人迹罕至,极其清幽。“青”、“绿”这样的色彩本就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安宁、舒适之感,“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入目青翠之色,让人尘心荡尽,寡欲清心。
“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此处再一次写到小潭周围的环境,似与前面“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有重复之嫌,其实不然。此处具体地选择周围“青树翠蔓”中的“竹”来渲染清幽、深邃的意境,与文章开篇“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遥相呼应,大有让人心生“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超脱之情怀,此处虽无“崇山峻岭”,但有“茂林修竹”,泉水叮咚,环境之清幽脱俗,也足以让人陶醉、留恋了。
三、意境之凄清
发现小石潭的过程,本就是曲折的,“……隔篁竹,闻水声……伐竹取道,下见小潭……”。这里面起码隐含两点信息:其一,小石潭所在之处,必是极其荒远偏僻之所;其二,作者此刻的处境,必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时。这与苏轼在《后赤壁赋》中的探险句子极其相似,“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中国古代士大夫往往于失意苦闷时选择探幽揽胜,寄情山水,而这背后,却意在掩盖内心的凄凉。
潭中游鱼,兀自欢乐,“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昔者孟子见齐宣王,问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曰:“不若与人。”此处的游鱼似乎有意与游者分享欢乐,然而此时的柳氏似乎怎么也走不进鱼儿无忧无虑的欢乐里,始终萦绕于字里行间的,是“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落寞与感伤。
小石潭的岸势“犬牙差互”,这个喻体毫无美感,甚至给人以阴森恐怖之感,“不可知其源”,一种不可知、没来由的惶惑和恐惧感在心底暗暗滋生,并在全身蔓延。这给本就地处荒僻之地的小石潭营造了幽静深邃的境界和清冷凄迷的氛围。
最后作者再次绘写小潭的环境,“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正面写其凄清寂寥,令人不由产生“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之感,最终深感“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离开。
作者正是通过对小石潭发现的过程、小石潭自身的特点及其周围环境的叙写,为全文营造出一种难以明察的凄清的意境。
四、品格之清高
小石潭的水流之声“如鸣佩环”,叮咚清脆。“佩环”皆由玉制,“玉”在中国文化中一直以纯洁无瑕的特点为人所钟爱。“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将自己为官的清正廉洁之冰心寄托在“玉壶”之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传达出的是为气节而献身的不屈的精神;屈原放逐,形容枯槁,行吟泽畔,却依然“怀瑾握瑜”,宁赴江流,葬身鱼腹,也不愿随波逐流,其品行更是如美玉般洁白无瑕,光耀千古。小石潭的流水声在柳氏听来“如鸣环佩”,正流露出作者内心对美玉般高洁的品行的坚守。
小石潭“水尤清冽”,正面写潭水之清澈,即写自己此心亦如潭水般澄澈。“皆若空游无所依”则言自己心如潭水一般空阔、敞亮,不含杂质,可任游鱼嬉戏,可凭日月照鉴。此心清白、高洁,便如此水。
柳氏发现小潭是“隔篁竹”而闻水声,小潭所在之处“四面竹树环合”,可以说小石潭是坐落于茂林修竹的怀抱之中。“竹”在中国文化中,以其特有的风姿品性,在中国古人的审美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庄子·秋水》言凤凰“非竹食不食”,就以竹来衬托凤凰的鄙视功名的高洁不凡;邵渴《金谷园怀古》有“竹死不变节”,白居易《养竹记》中“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都是以竹来表示文人伟岸清高的气节和不屈的风骨。这里柳氏便以竹来渲染幽僻凄清的环境氛围,以表明人内心的淡泊与个性的清高。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小石潭记》中的一山一水,一花一竹就都有着鲜明的“我之色彩”。作者柳宗元参与王叔文集团的变革,失败后被贬于蛮荒之地,失意苦闷自不必说,然其内心的不屈与高洁却始终倔强地伴随着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氏在《江雪》中所画的这个寒江独钓、孤独倔强、高洁不群的渔翁形象便是自己。他的这份孤寂、清高如同小石潭之清流一般,或直接或委婉地流露与永州山水之间,“斗折蛇行,明灭可见”。我们便可以循着这或显或隐之石潭“清”流,去窥探柳氏内心的深幽之境。
参考文献:
[1]王力《竹意象的产生及文化内涵》,《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1期。
[2]尚永亮《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和美学追求》,《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3]代保民,丁雪梅《潭就是我,我就是潭》,《语文建设》,2010年第5期。
[4]孙绍振《可欣赏而不可久居》,语文建设,2007年第9期。
祁艳,教师,现居江苏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