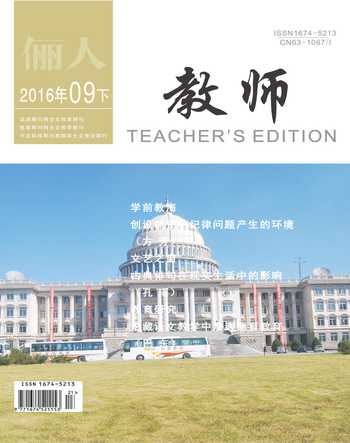岗格尔肖合力雪山
2016-05-30法土麻
法土麻
皎皎空中月,皑皑山上雪,明月下交相辉映的白色,给月夜带来了更深沉的静谧。这一抹白色如面纱般遮住了层峦叠嶂的山峰,晕染了山峰的神秘,这静谧中的神秘让这山有了一种神圣之感,奇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征使这座山成为雪域文化的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了人们向往,信徒崇拜的圣山,这就是享誉藏区的岗格尔肖合力雪山。
岗格尔肖合力雪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木里镇和苏力镇的交界处,是祁连山中段,也属疏勒南山东段。岗格尔肖合力雪山是青海湖环湖十三名山之一,主峰海拔为5174米,是大通河、布哈河、疏勒河、北大河和黑河的发源地,故有“五河之源”之称。
寂静的岗格尔肖合力雪山上有雪有月还有远处苍穹中璀璨的星星,在辽阔的雪域上成为了一幅美丽的动态画,朝拜者的影子如贝多芬手中的音符,滑出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远方帐篷中的灯火明明灭灭,衬托了雪山的寂静,而山底一条溪水的声音也能流的很远很远,为昭示这个季节,清冽的水面上漂浮着几根枯草叶。
地处雪域高原上的岗格尔肖合力雪山经常会有风雪的杀戮,会袭来的狂舞的雪,吹来肆虐的风,但这风,割不断人们的生命,这雪,扑不灭雪域民族的信仰,在风雪之中蹒跚的足迹,印下了走向春天的憧憬。
岗格尔肖合力雪山所在的天峻县有蒙古族、藏族、撒拉族、回族、汉族等民族聚居,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而因属高寒气候区,以藏族和蒙古族为主,故藏传佛教在此传播发展,因自然环境因素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信仰以圣山圣水崇拜居多。
自古以来生息在青海高原上的各个民族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有先秦时期的羌人,两汉的小月氏,有从魏晋南北朝经隋唐至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秃发、乙弗等诸鲜卑部族,党项、白兰、多弥、女国等诸羌部族和吐蕃,有元、明、清时的蒙古族、回族、藏族(西番)、撒拉族等,以及从西汉时期屯田世居青海的汉族。这些民族和政权的建立或多或少的以不同的形式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天峻,不论是西汉时期汉族的屯田,吐谷浑政权的建立,还是元朝的蒙古西征和清末的西北回民起义都成为了天峻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又以横向的某一政权和民族的社会在这一地区成为某一具体时期的横切面,而这些横向和纵向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状为现在的天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人文环境。史籍记载曾经有“三危”、“昆仑之丘”、“问摩黎山”、“关角二郎洞”、“西王母石室”等。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处在古代诸羌游牧区域的中心地带,而天峻地区正处于羌之中心。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却是天峻县集多种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代表。
岗格尔肖合力雪山是环湖十三名山之一,是享誉藏区的著名圣山,也是“昆仑之丘”地望之源。在《山海经 大荒西经》中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焰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甘肃通志稿》载:“阿木你厄枯山,在青海西北二百余里。其山甚大,亦十三山之一”。所谓“厄枯”就是“姆枯”的谐音,译为“紫山”。先秦时期,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周边是一个许多政权、国家和民族更替繁衍生息的区域。汉代,昆仑之丘周边是“化戎所交都会”的区域。昆仑之丘周边留下了吐谷浑、回鹘、靺鞨、鲜卑、羌、蒙古等许多民族的历史足迹。《甘肃通志稿》同样记载:“布喀河在青海西,源出青海西北三百余里阿母枯山南”。《青海地质略》记载:“布喀河,源出青海西北阿母泥额枯山南”。这里所提的“阿木你厄枯”以及《佛图西域志》“阿米辰达山,其上有大渊水,即昆仑山”中的“阿米辰达”,均指岗格尔肖合力雪山。有史料记载就有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也有多个版本,一传说为大尊者拿若巴大师来中国传教,圆寂在中国,当时的皇帝派大军护送其遗体回印度,当护送大军路过岗格尔肖合力神山时天色已晚,护送大军决定当晚在此安营扎寨,半夜时,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直到天明。第二天准备上路时,发现灵柩里的遗体不见了,后来传说,其遗体被岗格尔肖合力山神留下,化入了岗格尔肖合力神山。另一传说为岗格尔肖合力是《格萨尔王传》中霍尔国白帐王的灵山,而大名鼎鼎的霍尔国的白帐王是岗格尔肖合力神山的山神,而山神不仅仅是白帐王一位,而是他们夫妇。从这两个传说可以得出,这里的山神不仅有之前羌人的山神,有后面被山神留下的佛教大尊者拿若巴大师,以及藏族某部落的首领白帐王,岗格尔肖合力雪山成为集多种文化为一身的圣山。
先秦时期的党项羌在此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到汉代,这座山成为羌人之神山,叫羌日姆枯神山,不同民族的人们有自己的方式朝拜着它。雪山崇拜的自然崇拜、苯教对山水的崇拜、藏传佛教对山水的崇拜,以及民间信仰的山神信仰,是民间主要以汉族为主体的人们对山水的信仰。
岗格尔肖合力雪山是集多民族多元文化为一体的雪山信仰,从羌人的“紫山”到藏传佛教山水的崇拜和其他民族对山神的崇拜和认同。岗格尔肖合力雪山从神山的崇拜,提升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后到山神的崇拜,多种文化让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在人们的精神层面有不同层次的认识和信仰,这里有自然崇拜,多神崇拜,体现了万物有灵论和泛灵论,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山水的敬畏和崇拜保持了人与自然的平衡。
岗格尔肖合力雪山下分布着大片的高原沼泽湿地草原,在这里有一种原生态之美,达到了“仁”的境界,使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这里有角斗的牦牛,悠闲的咀嚼着青草的牛羊群,帐蓬边藏獒信信的望着这一切,慵懒的闭上它的双眼,穿梭于牛羊群中的牧人传来的声声口哨,这一场景是雪山下牧场中的自然美和常态美。
岗格尔肖合力雪山雪线下的基岩以结晶灰岩、砂岩夹石英岩为主。冰川下面流出众多河流,有深有浅,有宽有窄。每当进入暖季,冰雪消融,众多水流自雪山中涌流奔腾而下,注入河流之中。苏里河的源头就在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北麓的冰川下,苏里河出青海境流入甘肃境内叫疏勒河。山底还有许多银灰色的干河床。在冰川面积大,雪山被银装素裹的时代,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北麓曾是河流众多,沼泽遍布的区域。这座雪山下流向西北方向的疏勒河,曾经养育了浩瀚的罗布泊,黑河末端的额济纳旗是水草丰美的地方,布哈河则注入到青海湖,让青海湖成为了高原上的龙之泪。
作为五河之源的岗格尔肖合力雪山,近年来在人类频繁的活动和全球变暖下,雪山上的冰川逐年消融,疏勒河补给的罗布泊已经完全干涸,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戈壁,而曾是水草丰美黑河末端的额济纳旗,现在生态环境恶化,胡杨林大量消失,成为了沙尘暴发源地之一,而布哈河注入青海湖的面积一直在缩减。
近年来,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冰川消融速度加快,规模较大冰川分解,而规模较小的冰川消失,短期内冰川的消融有利于增加河流径流量,但同时也会导致冰川型泥石流和冰湖溃决洪水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增大。随着冰川规模的变小,其所能提供的河流补给最终将会减少,冰川融水补给的减少很有可能恶化该地区水资源紧张的局面,面对雪山如此严峻的形式,必须做好应对措施,综合利用,减少污染,提高节水技术,更好地保护水资源。
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因它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在雪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圣山,它不仅是精神层面的信仰和崇拜,对于藏族人民更是一种视觉和表象的信仰象征。这里的人们让生活与艺术相结合,让生活与信仰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