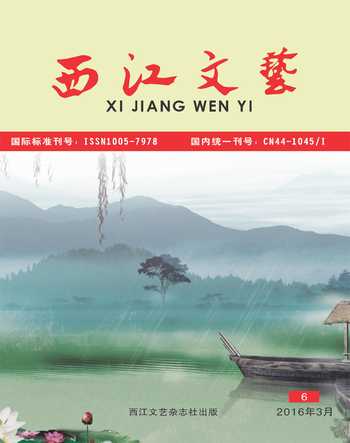简论刘庆邦《神木》文学叙事中的悲剧意识
2016-05-30李梦珠
李梦珠
【摘要】:悲剧意识是贯穿《神木》全文始末的一股暗流。从人性泯灭到自我救赎,再到人生希望的出现,小说于平淡的叙事语言中透出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而结尾留给读者元凤鸣将何去何从的疑问必然引发受众对于悲剧问题的思考,进而从简单的善恶判断走向人生的终极关怀,提升自身的精神层次。
【关键词】:刘庆邦;《神木》;悲剧意识
《神木》作为刘庆邦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作品,曾荣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作品主要讲述了李西民和赵上河两个窑工疲于奔波,难以忍受生存的苦难,走上以人命诈取金钱的邪恶道路,最终被一纯洁的少年所救赎。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论述刘庆邦小说的人文关怀,而对作品的悲剧意识没有足够关注。笔者试图通过对李西民、赵上河、元清平、元凤鸣这四个人物形象的深入分析,从悲剧美学角度挖掘底层民众生活悲剧的根源。
一、人性泯灭——刘庆邦《神木》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始动机
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刘庆邦在谈及《神木》创作背景时曾说:“罪犯把外出打工的无辜青年骗到小煤窑下杀死,伪造事故现场,然后以死者亲人的名义向窑主诈钱,这是发生在我国南北煤矿的真实的恶性案件。……报纸报道了这个案件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正像俗话说的肝儿都颤了。……震惊之余,我就想以这个案件为素材写成小说。……必须从社会性和人性的结合上,对素材进行心灵化和艺术化处理。”[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城市化的急速转型期,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日渐脱节。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失业人口的增多,教育事业的萎缩,物质生活的贫乏,道德精神的沦丧……这一系列社会暗潮的涌动,必然带来人性的惶恐与扭曲。由此,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标准,到1998年末,中国农村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约1.06亿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2]贫苦使得体力劳作已不能维持日常生计,在困窘的生活环境中,面对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生活重压,以李西民和赵上河为代表的农村外出务工者会走去哪里?
小说初始就交代了临近过年,李西民和赵上河仍逗留在一个小型火车站去物色下一个点子,以期诈取一笔票子过个肥年。透过他们的眼睛,你会发现在这是一个只有金钱与肉欲的黑暗世界。“由保健羊肉汤便想到保健野鸡汤,看到落单的打工者就想到会移动的票子,同样处于社会底层为生存挣扎的民众,何以他们就觉得元清平这种老实蛋子的命就该被他们拿来换钱用呢?”[3]金钱比人命更有价值,这是何等的悲哀。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农民阶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乏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对于李西民,赵上河这些正当壮年,没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而言,做高风险,高回报的煤矿工作似乎是最好的選择。当目睹老乡轻松的敲碎一颗人头就从窑主那里顺利拿到平常两年的工资之时,李西民和赵上河并不发力就轻易获得一千块钱,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怎能不让他们动心。长期的生活奔波,频繁的更换姓名,精准的谋算表演,他们的人性在一次次的金钱交易中泯灭了。
二、自我救赎——刘庆邦《神木》人性的颠覆与回归
找回生命悲剧意识不一定能予人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但拒绝正视生命悲剧意识的人在人格精神上必然不幸。赵上河凭借身农村外出打工者的身份,在煤窑上工作过的经历,对窑主忌讳与习惯的熟知,让他一次次策划诈钱成功。但是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恐惧与悲情。过年回家面对妻子对金钱来源的疑问,他内心的恐惧与隐痛一发不可收拾,邻居赵铁军的杳无音讯,村支书的敲山震虎,都加剧了他内心的煎熬。他一遍遍的告诫自己点子的营生不能再做了,但在过完年村里人都外出打工时,已经习惯了吃人恶习的他仍是半夜摸黑出走了。
此次离家,赵上河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顶多再办一个点子,等存够五万块钱应对家庭生活及孩子上学问题就罢手,偏偏是这最后一个点子让他走上了绝路。在看到李西民领会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时,赵上河并不满意,内心残存的一丝良知告诉自己不能对一个孩子下手,但迫于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只能一切照旧。当得知元凤鸣与上一个点子是父子关系时,他的心开始动摇;在看了元凤鸣的家信时,他的同情心逐渐上涌;在带了元凤鸣发市之后,元凤鸣抱着他哭的举动更是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他从心里根本不想动手了;在李西民多次准备办了元凤鸣时,他次次出手阻挠;在假顶制作成功后,慌乱中他意外打死李西民,元凤鸣的恐惧与呼号终于让他承受不住自己所犯的过错及内心的重压,自动走向了毁灭。
毁灭对他们这些以杀戮别人的生命为生的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只是李西民到死仍活在杀戮与金钱的黑暗世界里,赵上河则站在自己制作的假顶下,怀着对下一代的希望与嘱托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这种受尽折磨不得善终的悲剧人生自有一股悲凉的人生意味。悲哀,是中国文化的底色。死亡,是人生的颠覆与重来。
三、希望毁灭——刘庆邦《神木》对赤裸人性的悲剧揭露
任何伟大的悲剧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悲观的,因为它表现恶的最可怕的方面,而且并不总是让善和正义获得全胜。元清平不过是远离家乡,谋求生存的底层民众中最普通的一员。他并没有什么文化,靠的只是体力与勤劳,虽然经过层层盘剥,并无多少剩余去维持家庭生计,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在火车站的时候偷偷去检查别人丢下的空烟盒,期望有一根烟卷或一卷钱;在听到宋金明说有钱可挣时内心的激动与迫切;在看到唐宋两人的亲情表演时误以为真,极力去承担一个兄长应尽的责任;在跟别人生气时,从不跟活儿赌气,仍然恪守一个劳动者的职责。他是努力靠自己的双手吃饭的人,但他却不明白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靠头脑和手段挣钱的世界。如此形势下,如他一样勤劳朴实的劳动者是不该存在的,只配被别人当点子换笔票子用,这是怎样的悲哀。这种浓重的悲剧意识弥漫在整个矿区世界里,生活的苦难与悲凉压得在这些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们根本无法向前一步。
父亲外出打工久不回家,交不起学费,妹妹还要上学,面对家庭的重担,身为男孩子的高一学生元凤鸣不得不辍学回家,背着铺盖卷沿着父亲的足迹走向远方。初入社会,十七岁的元凤鸣看待一切人事都是含羞带怯的。他错信了所谓的“好人”,走向了充满死亡气息的矿区。在他从煤窑里刨出一块带有树叶印记的煤块时,他欣喜若狂;在他跟家人写平安信时,他斗志昂扬;在他第一次跟女人亲密接触后,他羞愧欲死。这是一个纯真善良的少年,在他目睹了最丑恶人间惨剧时,他并没有向黑暗屈服。但是在既找到父亲,又没挣到钱的情况下,他要怎么办呢?回家么,是啊,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父亲已死,妹妹还要上学,悔悟的人已然死去,手握财富的人仍执着于自己的敛财之道,黑暗虽有崩裂,但曙光何时才会真正到来呢?
结语
真正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置身于社会环境中,既为己言又为人言,总是关心着如何去解决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刘庆邦作为底层文学叙事的代表,有着少年时苦难人生的积淀,更能以一种温情的眼光看待人世间的一切丑与美。他的文字并不张扬,无论世事有多丑恶,由他道来,似乎都很平常。但当你回味他的叙述时,自能生出一股悲凉的人生意味。作者的悲悯情怀与悲剧意识是交缠在平淡的语言叙述中的,这正是他深知生活的苦悲。
参考文献:
[1] 刘庆邦.给人心一点希望[J].十月.2004,(05)
[2] 孙立平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4.
[3] 刘庆邦.神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