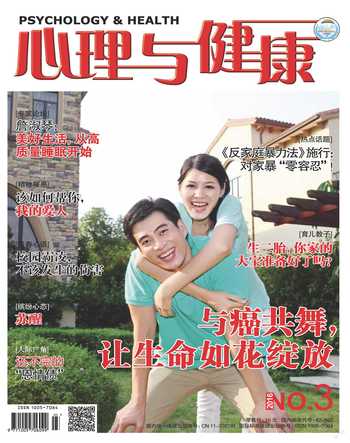《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对家暴“零容忍”!
2016-05-30但淑华
但淑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于2015年12月27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并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请随本刊记者一起关注法律学者的专业解读吧。
家庭暴力
不再是“家务事”
Q《反家庭暴力法》经过多年酝酿终于出臺并于今年3月1日开始施行,您觉得这部法律的施行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A2015年是北京95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也是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20周年。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诞生”的,确实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反家庭暴力法》的施行,将会给社会民众的观念带来巨大的改变。以前大家觉得家庭暴力是家务事,国家和法律是不能干预的。不光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社会也有“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法谚。就是说公和私是泾渭分明的,对于像在家庭这种私领域发生的事情,国家公权力是不能去干预的。但是最近几十年,西方国家的立法理念有了一些变化,公权力可以基于一些正当的理由进入家庭领域,比如保护家庭成员的权益,救济弱者等。家庭不是一个孤岛,不是隔离在社会之外的。《反家庭暴力法》就是突破家庭绝对自治的一个成果,从此家庭暴力不再是私事,无论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还是陌生人之间的暴力,施暴者都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最大“亮点”:
促进家庭和谐
Q您觉得这部法律最突出的“亮点”有哪些?
A第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反家庭暴力法》在总则里提到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一开始在启动反家暴法的立法程序时,其实是有一些反对声音的。有人认为反家暴立法可能会激化家庭矛盾,是在鼓励受害人离婚,那反家暴法就会成为破坏家庭关系的法律。反家暴法的立法目的表明,这是一部和谐促进法,是一部人权保障法。这就有力地回应了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其次,这部法律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经验,吸收了很多学者的意见,构建了反家庭暴力有效的制度体系,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原来国务院法制办的征求意见稿里并非一个独立程序,是依附于离婚、赡养、抚养、收养、继承等民事诉讼存在的。但是,现在反家暴法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案由,受害人不需要提起诉讼,只要他遭受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他就可以去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再比如,近年来,发生在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屡见不鲜,反家暴法采纳了学者建议,基于同居暴力与传统的家庭成员间暴力行为的相似性,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准用该法。这既扩大了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又不会扩大“家庭”的内涵,破坏法律体系的一致性。
另外,该法还有一些制度上的创新,是国外没有的。比如告诫制度。有一些家庭暴力行为情节比较轻微,还没有达到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度,但是公安机关在出警以后,他如果确认了施暴的事实,那他就可以对施暴人出具告诫书。告诫书中包括施暴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和禁止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公安机关除将告诫书送交施暴人、受害人之外,还应通知居委会、村委会。这对施暴人构成有力的震慑,并且可以通过居委会、村委会的查访,有效监督施暴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事实上,告诫书还有助于解决受害人举证难的问题。家庭暴力因为发生在家庭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实践中往往因为缺乏足够有效的证据而难以被认定。但是有了告诫书之后,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就可以有所减轻。目前重庆、河北鹿泉等地法院已经有在离婚诉讼中依据告诫书来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先例。
缺憾:没有给
“性暴力”专门立法
Q很多关注反家暴法的学者曾建议,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不能仅仅限定在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上,还应包括性暴力。但遗憾的是,这次正式法律出台依然没能将“性暴力”写入该条文,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A性暴力就是指违背当事人的意愿,采用强迫、恐吓等手段与之发生性关系或使其接受令其感到痛苦、屈辱的性行为,或者对其性器官实施伤害行为。这次未能将性暴力明确立法,可能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性是一个羞于启齿的话题,对性暴力有一种“欲语还休”的情况。
从国际立法经验来看,就会发现,在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文件中,性暴力都是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例如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美洲国际防止、处罚、消灭对妇女施暴公约》、《欧洲理事会防止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等。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立法里也都将性暴力明确作为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但是像在东方比较传统的国家或地区,比如韩国,还有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没有明确将性暴力写入法律,只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扩张性解释,将性暴力纳入到家庭暴力的范畴。
性暴力绝大多数发生在夫妻之间,最常见的是丈夫对妻子的性暴力。这也是最典型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对女性来讲,性暴力给她造成的心身伤害,让她感受到的那种屈辱,可能是其他形式的身体暴力无法比的。在非常严重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性暴力往往成为以暴制暴的直接诱因。性暴力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是特别羞于启齿的,很多受害妇女长期遭受丈夫的性暴力,又不能向人诉说苦楚,积累的结果就是受害人忍无可忍,靠自力救济(比如杀害丈夫)来寻求解脱。这种以暴制暴的案件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和警示。
因此,这次反家暴法未能在家庭暴力概念中明确性暴力这一表现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继续将性暴力作为身体暴力或精神暴力予以处置,难以体现性暴力的特殊性和危害性。
“棍棒教育”?
后果很严重!
Q《反家庭暴力法》将家庭暴力规定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定情形。这对很多信奉“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A在有些父母的教育观念里,他们不觉得打孩子是损害孩子心身健康的做法,仍然坚持认为孩子“不打不成材”,这是非常错误的。《反家庭暴力法》要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并要求学校和幼儿园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教育。对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施暴有严格的惩罚措施,比如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等等。这些都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挑战。
另外,根据反家暴法的相关规定,对家庭暴力国家是有主动发现和介入的机制的。如果学校、幼儿园的老师或医院的医生等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就应该要报警,因为他们都有强制报告义务。如果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人不履行这些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他们可能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心理矫治:
扼杀家暴的“源头”
Q《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后确实能给施暴者一定的震慑作用。除了大力惩治家庭暴力,是否能从源头上防范施暴行为的发生呢?
A反家暴法从内容上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预防,一是处置。处置是针对已经发生的家庭暴力如何制止,预防是针对还没有发生的家暴,如何去防范;或者是已经发生的家暴,如何预防再次发生。预防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在立法原则里,反家暴法就强调预防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
家庭暴力的预防,除了在社會上加强反家暴宣传教育,还要通过社区的配合,比如通过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早期发现,早期处置,尽早将家庭暴力扼杀在摇篮里。
更重要的防治措施是对施暴人心理的矫治。比如心理辅导,或认知矫治,但目前国内做得还不够,现在我们主要针对非常严重的、在监狱服刑的或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那些施暴人进行强制矫治。但是对于一般的施暴人,现在法律就没有强调强制辅导的环节,只规定必要时可以对其进行心理辅导。
相比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重视对施暴人和受害人进行帮助和辅导,这是能够有效扼杀家庭暴力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比如我去台湾时参加了他们对施暴者的认知辅导,感觉收获很大。他们的工作流程通常是这样的:先由法院下裁定,根据施暴者的施暴行为的严重程度,要求他们去接受时间不等的心理辅导或者认知辅导,然后施暴者去法院指定的机构接受辅导。主要是帮助施暴者认识这种暴力行为的根源,怎么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等等。比如有的施暴人可能因为酗酒或吸毒而实施家暴,辅导机构就会帮助他们戒酒、戒毒;还有的人是因为经济上的失败或失业后没有经济收入,感觉自己在家庭的地位受到威胁而发生家庭暴力,辅导机构就会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技能,甚至帮助寻找工作机会等等。另外还会有社工定期对受害人和施暴人进行回访。这些措施对预防施暴者再次施暴有很大作用。而相应的,我国台湾地区对警察、社工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已经成体系了,他们的入职培训、平时的业务培训都会涉及到反家暴的内容,所以他们的反家暴力意识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这种反家暴的大好环境和氛围,是我们大陆内地目前无法企及的。
但是我们也正在努力,而且这些努力的效果也正日益显现。比如我在江苏、上海调研时,了解到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家暴案件的处置当中引入社工,根据家庭暴力行为的不同严重程度,由社工进行相应的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等。这些对家暴进行危险评估、分级干预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防治家暴的措施有望在全国逐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