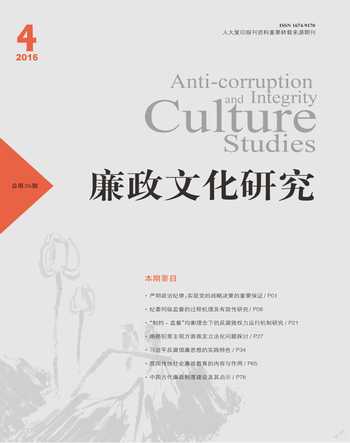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建设廉洁型执政党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教训
2016-05-30吴世丽
吴世丽
摘 要:保持自身的廉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建设廉洁型执政党作为党建目标和根本要求,厉行廉洁政治,努力将自己锻造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六十多年持续不断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总体上保持了自身的廉洁性,并以此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奠定了雄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主要是严厉惩治腐败的意志坚决、重视党内思想理论教育、严防党内产生“贵族阶层”、充分依靠群众进行监督;缺憾的是过于倚重政治运动、实行制度治党方略比较周折、党内权力结构改革有待加强。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今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关键词:廉洁型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6)04-0015-06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腐化堕落中实现长期执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先进也要注重保持自身的廉洁性,惟此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牢牢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才能开拓出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始终把建设廉洁型执政党作为党建目标和根本要求,努力将自己锻造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严格要求,在中共执政的60多年来,从总体上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廉洁型的政党,因而在总体上,中共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雄厚的。”[1]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廉洁型执政党的实践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一、建设廉洁型执政党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在野的革命党成为“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执政党。角色和地位的深刻转变给党的建设带来严峻挑战,如不时刻保持警惕很容易产生腐化现象。从当时全国情况看,蜕化腐朽倾向“正在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很严重”,“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2]158-159面对严峻形势,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当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以“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3]256。随着整党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被揭发出来,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开展“三反”运动。与整党运动相结合,“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内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廉洁奉公教育,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客观来说,廉洁型执政党建设在建国初期开局良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来说,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党的工作经验是更加丰富和全面了,党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4]263-264这是党的主要方面,但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如“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4]272党的八大在要求“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的同时,提出一系列加强廉洁型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二是从思想教育和制度两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三是“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2]215八大后,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防止干部特殊化、防止党内产生“特权阶层”的思想。为防止党腐化变质,毛泽东认为,“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5],就是党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整风”。他明确宣布从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着力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6]整风运动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反对干部特殊化形成一种制度。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要求有劳动能力的党员干部每年抽出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参加体力劳动。随后,由于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不切实际的估量,党风廉政建设在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裹挟下,日益走上阶级斗争的歪路。如中共中央强调“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7]。直至“文革”爆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方针,使党风廉政建设彻底陷入困境。这一时期,廉洁型执政党建设呈现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既有成功的做法,又有值得反思的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对党员干部形成严峻考验,因“可能有意志薄弱的人被收买”[8],进而腐化堕落。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警告说:实行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9]402。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经过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方面都比以前有较大改变,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重要经验。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邓小平分析认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10]300。他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党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0]313-314“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0]380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廉洁型执政党建设在回归正常的同时,又面临着亟待破解的新考题。
党的十四大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状况人民群众还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11]8。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11]49,要扎实加以解决。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十五届中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败方略,既要克服已发生的腐败现象,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一方略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作,强调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的治本功能。2000年11月,江泽民在十五届中纪委五中全会上指出:“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工作一起抓的工作格局,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抓起,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12]176 2001年9月,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从“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廉洁型执政党建设达到新的高度。
进入新世纪新时期,廉洁型执政党建设面临着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肯定过去“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的同时,党的十六大报告毫不隐讳地指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倾向已“相对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江泽民在这次大会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12]573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3]的战略任务。尽管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力度持续加大,但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党的十七大重申十六大以来“坚持方略、构建体系、拓展领域”的反腐败总体思路,提出要继续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将其列入反腐倡廉工作整体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14]遵照这一要求,新形势下廉洁型执政党建设坚持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为切入口,着力构建“作风、纪律、惩腐”三位一体的反腐倡廉大格局,采取“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三大重要举措,取得显著成效。
二、建设廉洁型执政党的成功经验
第一,严厉惩治腐败的意志坚决。在反腐败问题上,党始终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毛泽东认为,腐败分子是“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15]。反腐败是一场“大战争”,关系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是全党一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反腐败斗争上从未懈怠。在建设廉洁型执政党过程中,党“坚决揭露和惩处腐败分子,包括严惩了少数违纪犯罪的很高级别的干部”。江泽民认为:“是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就要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我们这样做,正是我们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12]18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党风廉政建设提到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吹响“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冲锋号,坚持“虎蝇齐打”,宣示出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誓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第二,重视党内思想理论教育。思想上建党,是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始终不放松思想教育。概括起来,“主要特点是:其一,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声势浩大,形成强大的舆论优势,不留死角;其二,坚持以党员干部作为教育的重点对象;其三,树立先进典型,进行典型教育,如60年代进行的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的活动;其四,最高领导层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16]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强思想教育筑牢党员干部的廉洁之基这一做法得到了继承和发扬。1978年以来党领导开展了至少八次大规模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1983年到1984年的整党活动、1996年至2000年的“三讲”教育活动、2000年底至2002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2005年至2006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至2010年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13年至2014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总之,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对于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17]118,“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坚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坚决同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用实际行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18]起到极重要的作用。
第三,严防党内产生“贵族阶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对此,党始终有着清醒认识。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专门就此进行讨论。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19]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说: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20]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很长时间里倡导实行两项重要制度:一是干部的节俭保廉制度。毛泽东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要实行巴黎公社的低薪原则,防止干部产生升官发财的动机。二是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可以克服干部中官僚作风和特殊化现象,“打掉官风”,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提出通过改革制度和厉行法制克服特权现象。江泽民指出:“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党就必然要失败”。[2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坚定不移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
第四,充分依靠群众进行监督。毛泽东认为,加强群众监督,是建设廉洁型执政党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3]190,以此确保这种公开批评不受压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明确提出依靠群众支持和积极参与但不搞群众运动的方针,“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9]404。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出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过整合自身资源,倾力打造集信息公开、新闻发布、政策阐释、民意倾听、网络举报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为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三、建设廉洁型执政党需深刻反思的主要教训
第一,过于倚重政治运动。频繁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这种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治理形式,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有学者初步统计,从1949年至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20世纪50年代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十年期间先后发动了31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21]这种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治理形式用于党风廉政建设,适应了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既有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功能,更有净化社会风气,形成社会崇廉氛围的社会文化功能。单就反腐败的效果而言,它确实能够“使得大量腐败分子无所遁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比较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发生”[22]。然而,随着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改革开放之后,政治运动逐渐退场,但运动式专项治理仍尾大不掉,反腐败斗争呈现周期性特征。
第二,实行制度治党方略比较周折。依靠制度治腐是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路径。建国初,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私有制和封建专制制度是万恶之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限制了大规模腐败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党制定出一系列包括惩治和预防腐败功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取得良好效果。党的八大对制度治党形成共识,并将依靠制度反腐的工作思路载入党章。但之后随着左倾思想的泛滥,运动治党取代了制度治党,制度建设在反腐败问题上日渐退场,终酿成“文革”悲剧。改革开放后,鉴于以前的党建误区,邓小平多次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332。他坚决反对制度因人而变、因事而异,“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333。即使如此,依靠制度反腐在很长时间内仍未达成共识。直至2010年初,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23],依靠制度反腐的方略才真正开始成为主流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党内权力结构改革有待加强。“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24]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过分集中”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性。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这种存在着巨大政治风险权力的体制早有深刻认识,并且已着手改变。党的八大曾尝试党内分权,设立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党内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书记处)、党内最高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这种方案没有落地生根。相反,在“文革”期间,党内最高监督机关被正式撤销,党内权力在原有“议行合一”体制的基础上愈来愈集中,变成“议行监合一”。改革开放后,深知“权力过分集中”之害的邓小平大声疾呼:“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的情形,已经很不利于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9]146党的十六大后,党中央屡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17]25,但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尚待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再探索。
参考文献:
[1] 郝宇青.自律:廉洁型政党建设的道德之困[J].社会科学研究,2012(5):13-14.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6.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27.
[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22.
[8]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8.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2]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1.
[14]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7.
[1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35.
[16] 邵景均.中国反腐倡廉之路[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59.
[17]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8]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2.
[19] 刘少奇.要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J].党的文献,1988(5).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05.
[21] 叶敏.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5-81.
[22] 过勇.经济转轨、制度与腐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3.
[23] 胡锦涛.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J].共产党员,2010(03).
[24] 李永忠.反腐治本:试点改革权力结构[N].南方周末,2014-08-15.
责任编校 王学青
Historical Proces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CPC in Its Construction of Clean Ruling Party
WU Shil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Maintaining integr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realize the long-term ruling status for a Marxist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PC has always taken as its aim and basic requirement to construct a clean ruling party, strictly implementing clean politics, so as to mold itself into a true Marxist party. Through continuously promot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ore than sixty years, CPC has maintained integrity itself in general, and has won th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the mass and laid a solid legitimacy foundation. In this process, determinat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corruption, attachment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strict prevention of the growth of “aristocracy” in the Party, and full dependence on the mass to supervise are among the experience leading to success. Excessive emphasis on political movements, too many twists and turns in implementing systematic strategies, and reform of power structure to be strengthened are among the deficiencies. These carry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s for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y today.
Key words: clean ruling party; CPC; basic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