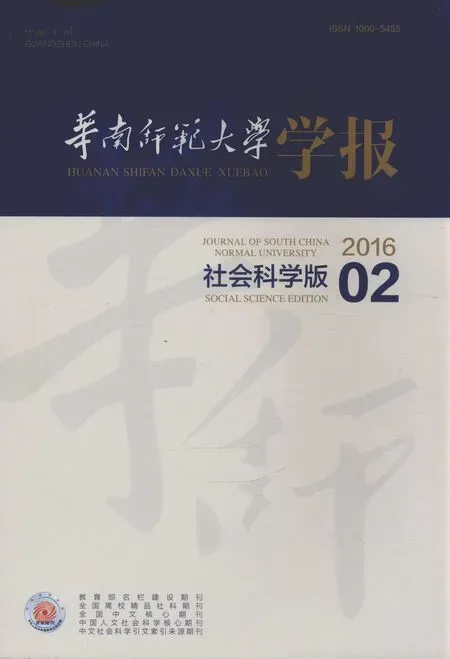论王维诗中不遇感书写方式的新变
2016-05-28管琴
管 琴
论王维诗中不遇感书写方式的新变
管琴
【摘要】不遇感在王维诗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王维关于不遇感的书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篇直接吟咏或者托古写今,属于直抒胸臆式写法;另一种则是与风景相结合的间接书写。在后一种方式中,他常以用禅观静照或者客观描述的方式来表现山水,同时表达失意情绪,形成一种山水与情绪相互消弥的特征,这一特征与王维诗的“清”“秀整”“雅净”等整体风格相照应,其长处在于往往能够消泯掉浓烈的情感的直接抒发,表现出情感的节制与诗意的蕴藉。王维的这部分有咏怀意味的山水田园诗作,部分改造了通篇咏怀或是通篇重在情绪营造的传统,形成了一种较为新鲜的结撰方式。风景与自我在王维诗中的结合方式,应作为一种较突出的现象加以留意。它们显示出,盛唐时期由王、孟诗派推向高峰的山水田园诗歌,不仅在山水田园的写作技巧与呈现形式方面达到了极大的拓展,而且在风景与心志相结合的途径方面也有一定的新变。
【关键词】王维不遇感山水诗田园诗
在诗歌中吟咏不遇,是从《诗经》《楚辞》就延续下来的写作传统。汉代以来,随着辞赋的兴盛,还出现了专门书写文人失意不遇的赋作,如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等等。到了唐代,寒门文人虽然通过科举考试有了一定的上升途径,但大多数人还是仕途偃蹇。胡应麟在《诗薮》中引用《明皇杂录》中的话:“天宝末,刘希夷、王泠然、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张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刘慎虚、崔曙、杜甫,虽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唐上》,第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这种普遍的现世挫折延续了文人不遇的写作传统,体现在诗歌中,形成了许多关于不遇的书写。
王维虽未被列入《诗薮》所列诗人之不遇者的名单,但他一生沉浮于官场,进退失据,失意的情绪始终存在。开元九年(721),因舞黄狮子事件,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任中书令,王维作诗请求擢引,后被任为右拾遗。从这些经历来看,他与多数文人一样,有着较强的用世之心。但开元后期张九龄的遭贬,使他体会到政治与世路的复杂;安史之乱期间的陷伪事件更使他意志消沉,趋向于禅寂。总体来看,不遇或者说自伤之感在王维的诗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陈贻焮先生在《论王维的诗》中说:“王维这种怀才不遇、反对权贵、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在边塞、游侠、送别、田园山水诗中都有流露。”见陈贻焮:《唐诗论丛》,第12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王维诗中不遇感的书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篇直接吟咏或者托古写今,属于直抒胸臆式写法;一种则是与风景相结合的间接书写。前一种以他的一些集中吟咏贤人失志与不遇之感的诗歌为例,如《济上四贤咏》《寓言》《不遇咏》《洛阳女儿行》《偶然作》《陇头吟》《老将行》等等。这些诗歌多为古风,大多沿用汉魏六朝乐府的主题与写作手法,抒发贤人失志的坎壈不平之气,体现了王维对魏晋风骨的全面继承。除了拟古或假托之外,他还常在诗中直接抒发自己仕宦上的偃蹇之感,如《被出济州》等。这种不遇感的抒发是普遍的,像《酌酒与裴迪》中的“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早秋山中作》中的“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等等,均是对不遇之失意与愤慨的直接抒发。
本文重点论述的是后一种书写方式,即论述他在山水田园诗中如何将不遇感融入进来。一般来说,传统的山水、田园诗歌中,山水与田园往往具备一种感兴的意味,与情绪形成较好的呼应。王维除了很好地传承了这种手法之外,还采取了另一种较为特殊的手法,即是用禅观静照或者客观描述的方式来表现山水;而在此描写中,失意等情绪的表达同时并存。这种写法变物的感发为情绪上的消解,形成一种山水与情绪相互消弥的形式。客观地说,他的这部分有咏怀意味的山水田园诗作,部分改造了通篇咏怀或是通篇重在情绪营造的传统,形成了一种较为新鲜的结撰方式,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
日本学者入谷仙介曾经指出,王维的《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一诗“表现了王维的两个主题——怀才不遇和自然风景——的融合。对王维来说,自然是解脱的妙方。当只身一人在冷酷的官场备受压抑时,等待他的自然,就成了他向往的抚慰心灵创伤的乐土”*[日]入谷仙介:《王维研究》(节译本),第101页,卢燕平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这是很精炼的概括。不遇与风景这两种主题像是音乐上的复调,虽然旋律不同,却又追随、融合在一起,往往在同一首作品中共同出现。
诗歌中的自然风景包括山水与田园两大内容。唐代以来,山水田园诗的景物描写在羁旅、登临一类的题材中表现较多,疆域的拓展与政治中心的北移,使得六朝以来以南方风景为主的山水田园诗歌拥有了更多可以汲引入诗的内容;而且唐代文人对汉魏风骨的标举,也对六朝诗风的绮丽有所挽救,常常能够在诗歌中体现出一种阔大的情思。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风格上,山水田园诗的兴盛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就山水诗的发展过程而言,谢灵运开创了一种以登临纪览为主体模式、以秀密严整为主要风格的山水诗写作;之后谢朓以降的山水诗,变严整为圆转,进一步发展了诗歌语言的流动性,在此过程中玄言的意味逐渐消散。至齐梁时,写景的对句艺术进一步成熟,何逊、阴铿、庾信的诗作中都有一些出色的尝试。但在南朝,山水主要还是作为诗歌的观赏对象与审美主体,不能说山水诗中没有个人心志的流露,但将文人的不遇感与山水的描写结合在一起的现象,还是很少见到的。
田园诗的发展过程较山水诗为沉寂。陶渊明的田园诗多写隐逸生活,旷达直率,不遇之感多已被田园之乐取代。到了初唐时期,王绩继承了陶诗的写作风格,他的《野望》等诗中已暗含文人视角。发展到盛唐时代,田园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王维、储光羲都是其中翘楚。王维的《新晴野望》《渭川田家》《春中田园作》等诗,在内容与形式上对初唐以来的田园诗歌类型有所拓展。王维虽然对陶渊明有很大的兴趣,但他本人毕竟是与贵族圈过从甚密的文人,渊明以葛巾漉酒的贫士生活并不是他想仿效的。当然,这也并不影响他对陶渊明的学习,何况陶诗中寄托理想的田园生活本身也是文人雅赏的对象与排遣世虑的标志性的范本。王维集中有一些仿陶的作品,风格和写法都模拟陶潜。举《济州过赵叟家宴》一诗为例,这首诗的前部分写赵叟的隐居情志与悠然自得的隐居环境,诗中的隐居者虽然住在高门深巷中,但“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余”,从行事与言谈来看,隐者乃是一有道之士。后四句结构上模拟陶潜《饮酒》其九,分成前后两片叙述。王维通过所叙人物身份的转换,突破了诗歌的线性结构,使整体形式更富于变化。另如《赠裴十迪》一诗,也采用了类似的结构。王维这类诗歌虽然模仿渊明,但究其本质,与渊明的田园之作有很大区别,它们叙写的是一种典型的贬官生涯中文人式的田园生活。这种田园生活是吏隐的一种典型表现,无论是诗歌描述的视角还是诗歌流露的情感,都出于半官半隐的文人。所以,虽然王维的诗歌保留了陶潜诗歌的清腴,但陶诗的真厚已转化为文士的典雅,陶诗描写自然的生新活泼也转化为彩笔山水的清远。两者的性质有着很大的区别。
到了晚年,王维的心境愈发沉寂,写归隐的诗作也发生了变化。《酬诸公见过》一诗,已淡去旁观者的游赏心理,而表现出生活中更贴近田园的一面,也更贴近渊明:“晨往东皋,草露未晞。暮看烟火,负担来归。”似乎已沉浸在这种田园之乐中了,但结尾仍是王维式的,回复到自我的抒发:“还复幽独,重欷累叹。”王维的许多诗歌都采用这样的结构,《辋川闲居》末云:“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园”,以自事躬耕的隐居者自比。《归辋川作》末云:“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顾可久评此诗乃“仕而不得意之作,含蓄不露”,指出在诗歌背后隐藏的,仍是一个因仕宦不得意而隐居的文人形象。《田家》一诗用“住处名愚谷,何烦问是非”这样的句子作结,仍然代表了误缨尘网的文人对世事的心悸。我们可以将它与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横石三五片”一诗对照。庾信说:“君见愚公谷,真言此谷愚。”他还是就愚谷这个名字生发议论,而王维由愚谷想到处世之愚拙,而且他的诗与庾信相比,不纯为咏怀,也多了景物描写,更增添了一种借景遣怀的味道。因此可以看出,虽然王维的田园诗到了晚期风格变得更为含蓄,但自身这一个寂寞的失意者的形象一直或多或少地存在。
葛晓音先生说:“行役和田园题材的结合,是王维田园诗的一大创造。”*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23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王维早期所作羁旅类型的诗歌中,宦情的不遇之感与山水、田园的吟咏,部分采用了一种较新鲜的结撰方式。以《宿郑州》一诗为例: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
这首诗以行旅为中心,由孤客的漂泊转至田园风光,具有较强的叙事色彩。诗人描写的田园作为旅行憩脚的地方存在,好像并未映射诗人穷途易感的心情,还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味。“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繁忙的田园是如此亲切,好像纾解了旅行的孤单与惆怅。“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田园生活的适宜与满足,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抚慰,短暂支撑着诗人的苦旅;但诗人终须离开了,在这种眷眷不舍的思绪之下,“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结尾回到现实,点明自身暗淡的处境,传达出前途未知的愤激与无奈。刘辰翁说这首诗传达出“蔼然恋阙之情”,可谓的当;但这种本身很充沛的失意情感已被之前描述的环境稀释过了,因此没有过分浓烈的感觉。
作于同一时期的《早入荥阳界》《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渡河到清河作》等羁旅题材的诗作,均采用了这样的结构。王维是一个写法富于变化的诗人,他不仅写自身所看到的景物,有时还拓展至联想中的景物,如寄赠友人的《送严秀才还蜀》云:“宁亲为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末句有无可奈何之意,也是接续风景的描摹而来,使这种无可奈何之意融入于天地之间,余韵悠远绵长。
再如《积雨辋川庄作》一诗,前六句描写清新的夏日田园景象,尾联“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又回到现实,语中含讽,但怨而不怒,蕴含了文人现实中的不遇与性情上的孤耿。这种自我的情绪在自然景物的映衬之下,得以淡化。
这种写作方式看似风景与自我相交融,但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分离式的结构。在将山水拟人化的诗歌中,王维也采取了这种分离式结构。如《华岳》一诗:
西岳出浮云,积翠在太清。连天凝黛色,百里遥青冥。白日为之寒,森沉华阴城。昔闻乾坤闭,造化生巨灵。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天地忽开拆,大河注东溟。遂为西峙岳,雄雄镇秦京。大君包覆载,至德被群生。上帝佇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幸久,何独禅云亭。
这首诗先是以如椽之笔描写华山之巍峨,赋予华山人格化的特征,赞颂其德性之广阔;末四句则笔势一转,愤慨于华山失遇于时,之前描述的华山之美于此也切合了“不遇”的题旨,体现了作者的别有所托。这首诗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如果去掉后面的四句,《华岳》也不失为一首神完气足的写景诗。也就是说,此篇的前半与后半部分并无一种必须具备的内容上的照应,连情绪上的呼唤也很难看出来。此类诗歌的写法近于汉赋的铺陈与点题,但因诗人重笔势的变化,很少转折时的平板与生硬。从情理上说,美与不遇/失意本来就是可以共存的,但诗歌中往往需要铺垫,需要烘托;而王维的这首诗在思想与技巧上都体现了很高的成熟性,因此即便是转折,也并不突兀。这种反转、对比式结构,吸收了初唐四杰歌行体的写法。四杰的歌行体很多都采用这种架构,先是大肆铺陈,再于结尾转折,类似于赋体。王维也摹仿卢照邻《长安古意》等诗的结构,先是铺陈繁华,结尾写到贤士的孤寂即落笔。他的乐府体《洛阳女儿行》,铺陈洛阳女儿生活的繁华,结尾云:“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将“君子不遇”的讽意烘托出来*“结尾况君子不遇也,与《西施咏》同一寄托。”见(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第124页,李克和等校点,岳麓书社1998年版。。顾可久曰:“初唐王、杨之体如此,俊丽,结斩绝。”王维在此类诗歌中很好地继承了四杰歌行体等先铺陈再斩绝的写作方式。只不过他将铺陈之景物代以具象的风景描写,形成一种纡徐委备而曲终奏雅的风格。
这种善于反转、对比,在山水田园中融入不遇感的写法,在其诗作中反复使用。举《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别业四首》其二为例:
郊居杜陵下,永日同携手。人里蔼川阳,平原见峰首。园庐鸣春鸠,林薄媚新柳。上卿始登席,故老前为寿。临当游南陂,约略执杯酒。归欤绌微官,惆怅心自咎。
这是一种典型的将田园与不遇要素相结合的结构。别业的幽闲仍然不能让诗人脱略世事,反倒使他陷入了更深的惆怅。王维在诗中反复叙写这种不能摆脱是非的烦恼。《赠刘蓝田》末云:“讵肯无公事,烦君问是非。”《韦给事山居》末云:“即事辞轩冕,谁云病未能?”《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辋川闲居》《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等诗也都是这样的结构。从以上诗作可以看出,王维在写隐居生活的诗中,即便是以风景描写为主,仍然不能令主体淡出。
二
风景与自我在诗歌中的结合方式,是诗歌传统中一个久远的也颇为复杂的问题。以景感兴,借景抒情,是从《诗经》《楚辞》以来就开始的诗歌传统。但在文人诗的传统中,风景具化为田园、山水的描摹,自我缩小为与宦情相关的失意之志的抒发,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魏晋时期就开始了这种文人失意的抒发,西晋时陆机的《赴洛道中作诗二首》即是将感物与失志相融合。但当时的山水,并未作为审美对象入诗。到了南朝,玄言诗被山水诗逐渐取代后,诗歌进入了一个将风景与自我同时呈现的高峰期。谢灵运的《过白岸亭》等诗都流露出关于“荣粹”或是“穷通”的个人感受,而且这些诗歌呈现出的个人感受与山水描写往往是分离的。齐梁以后,山水景物的描摹技巧大大提高,在与人事的结合方面,庾信的《山斋诗》《望野诗》等都在通篇景物描写之外写一笔人事。而这种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像其《赠周处士诗》等写归隐的诗作,则游仙意味尚存。
初唐以来的诗歌在涉及羁旅、行役、登览内容时,重点常放在物侯的变替与怀抱的孤寂。在加入景物描写时,往往沿着谢灵运《游南亭》等诗的写法,感物兴情,直接在风景中书写不遇的笔墨很少出现。开元以后,张九龄等人在写宦情与羁旅等题材的诗歌时,尝试将风景与不遇之感相结合。张九龄的《南还湘水言怀》一诗云:“拙宦今何有,劳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别悔前行。归去田园老,傥来轩冕轻。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时哉苟不达,取乐遂吾情。”七八两句写时下景物,首尾则直接抒情。其他如《初发道中寄远》《巡属县道中作》等诗则以叙事与抒情为主,虽也涉及不遇之感,但写景物往往是点明时序与物侯,并不多费笔墨。四杰中,杨炯的羁旅诗也间有景物描写,或即题而作,或拟汉魏咏怀诗写法,多写游宦思归之心情;王勃的行役诗亦写游子思归主题,也有全篇写景之作;骆宾王的《晚憩田家》《海曲书情》《晚泊河曲》等羁旅之作基本是抒写旅人的浮萍泛梗之感,即使是写到不遇与归隐的如《过张平子墓》,也略去景物的具体描写,以心志的抒发为主。宋之问的《入崖口五渡寄李适》《宿云门寺》、刘希夷的《春日行歌》等诗更于清山僻水中加入寻仙内容。陈子昂在怀古题材的诗歌中加入山水景物的描写,多烘托临物怀想、苍茫悠远之意,其行役诗风格与骆宾王相似,均重在描摹壮丽或幽凄的山水奇致。与王维同时代的诗人中,岑参等人也在行役诗中写景,但山水与不遇的结合还是很少出现的。
一般而言,盛唐诗人在诗歌中抒发不遇时,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抒情,另一种则是采用情景互感式的写法。前者如高适,他的《封丘作》等名篇都是直接抒情,情感饱满热烈;后者如孟浩然,其《岁暮归南山》一诗抒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现实悲哀,以“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结束,幽清之景是诗人愁绪的投射,与情绪之间形成强烈的互感。杜甫则擅用千钧之笔写此类情绪,融入更多社会生活的内容,开创出新的气象与模式。“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送路六侍御入朝》),笔力何等劲健;《旅夜书怀》也写不遇之感,景物由小及大,气象阔大;《曲江三首》虽是“自伤不遇”*(唐)杜甫:《杜诗详注》卷二,第137页,(清)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但亦充满了一种清拔之气。杜甫此类诗中的佳构往往不以实写取胜,而多是描摹、烘托一种气象阔大且具备很强时空转换的景物与氛围,开创出一种诗歌美学上的“老境”。
王维在写景诗中书写不遇感所体现出的特点,与其诗的“清”“秀整”“雅净”“舂容”等整体特点相照应,其长处在于往往能够消泯掉浓烈情感的直接抒发,表现出情感的节制与诗意的蕴藉,所谓“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筯骨”*(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60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洛阳女儿行》这类讽谕之作意在言外,写法非常克制;而即便是直接抒写不遇感的《不遇咏》这样的作品,也在高洁中带有刚健之气。《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说:“作不遇诗,辄多怨尤,语易腐。此独破胆选声,入云出渊。”*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四库全书本。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结语悠远,王维的不遇诗都没有超出怨而不怒的诗歌传统。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他本身就是情感内敛的诗人,其诗作也整体体现出了怨怒而不失雅正的诗歌美学。历代诗评家在这方面多有品评,明代何良俊称王维诗有“格调”*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第22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清代管世铭称其诗为“正雅”(老杜为“变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下册,第15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唐诗品》称王维诗是《小雅》之流,等等,都注意到王维的诗歌怨而不怒的特点。另一方面,王维的写景之作中,不遇感常常从景物的描摹中延伸出来,从客观上说,诗歌前一部分的写景已多少稀释了这种不遇感。所以与其他诗人相比,尽管他们表达的可能是同一主题,但抒发与表述途径多有不同。王维诗歌写景的客观化与不遇之感的融合,可以说是对传统不遇题材的诗歌风格的一种开拓。
当然,虽然常常书写不遇,但王维的诗歌并不遵循单一的写作方式,而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结撰。在他的寄赠之作中,往往还贯穿着劝勉、寄言的主题,风格也变得劲健,较少对风物的平实描绘,古风较为明显。可见他相当注意寄赠诗在交流与抒情方面的功能。《赠祖三咏》一诗,学习《诗经》中常用的感兴手法,写人则是:“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对祖咏不遇的愤慨与友人的深沉的情感并存。《过沈居士山居哭之》痛悼友人的弃世,“野花愁对客,泉水咽迎人。善卷明时隐,黔娄在日贫”,则又采用了感物兴情的手法。而且王维的后期诗作往往诗风苍健,《酌酒与裴迪》一诗说:“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早秋山中作》等写寂寞之感,景物似乎都带着悲凄之意。
三
王维对前人的学习是多方面的。代宗推许其诗“抗行周《雅》,长揖《楚词》”*《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见《全唐文》,第1册,第51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即指出他对传统文学的继承。王维也擅长在骚体诗中抒发人生偃蹇与归隐之意。《登楼歌》云:“舍人下兮青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兮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望终南赠徐中书》云:“驻马兮双树,望青山兮不归。”深得楚骚遗意。另如《送友人归山歌二首》,则仍然不失景物的铺陈与对偶式写法,其一末尾云:“愧不才兮妨贤,嫌既老兮贪禄。誓解印兮相从,何詹尹兮可卜!”又从擅长的风景回到归隐上面来。刘辰翁评其“不用楚调,自适目前”,即是指出作者写的其实还是眼前之景与心中之事。因此,虽然王维的诗文有意效仿《楚辞》,但他无论是现世的自我还是诗歌中的自我,都没有走向《楚辞》中主人公的自我放逐,而是变为不彻底的归隐。
王维诗歌中自我的投射,多在他选取的一些汉魏六朝人物身上有所反映。王维诗中出现得较多的有司马相如、扬雄、冯唐等,均是深为历代文人所咏叹的失意人物。王维常以相如献赋比喻求官取仕,以相如老病于茂陵比喻一代才人的仕途蹭蹬与晚景凄凉。《冬日游览》在铺陈景物之后说:“相如方老病,独归茂陵宿。”与前面描写的景物的壮阔形成对照,心志的点明也使全诗旨意得到了升华,故潘德舆评论该诗“全赖此结”*《养一斋诗话》附《王摩诘诗评点》,第539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在赠友之作中,他也以相如作类比。《送严秀才还蜀》一诗云:“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送孟六归襄阳》云:“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虽然托言旷达,其目的在于纾解友人仕宦失途之忧思,实则也隐寓了不遇之意。汉时人物,除了司马相如,王维常用于自比与他比的还有贾谊、汲黯、扬雄、冯唐等人。他的《上张令公》一诗云:“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以贾谊与汲黯自比,虽然表面上示以不敢怨怼之意,但其中寓含的不遇感还是非常显豁的。初唐以来,诗歌中涉及扬雄的多突出他的献赋十年而不遇。王维的《重酬苑郎中》一诗云:“扬子《解嘲》徒自遣,冯唐已老复何论!”也用此意。另外,他在用到扬雄的典故之时还从其才学的方面着眼,《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首联云:“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将杨氏比作扬雄,称赞他为引经谈玄之高士,此处并没有吟咏词人寂寥之意。可见王维往往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使用人物与典故。
在与友人赠答、涉及文人的生活时,他较喜欢用金谷诗人、竹林诗人的意象,这些都与魏晋时期文人结游、聚饮的风气有关,不失为对六朝优游的士人风气的一种欣赏与自比。《哭祖六自虚》一诗云:“花时金谷饮,月夜竹林眠。满地传都赋,倾朝看药船。”用西晋金谷园与魏时竹林七贤的故实,追忆与祖自虚的交游,并且用晋时左思与夏统的典故表现祖自虚之志趣。《宿郑州》《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等诗都采用了类似的六朝典故。
无论是司马相如还是竹林诗人、金谷诗人等诗人群体,都有一段诗酒风流的现世生活,但又多被卷入政治集团,与浊世沉浮;即便避世隐居,也不能够真正地遗世而独立。以他所咏的司马相如为例,虽然其仕履进退如鲍照所说,“相如达生旨,能屯复能跃”(《蜀四贤咏》),但最后还是归于寂寞,老病于茂陵。王维写相如其实不仅是自比,也是自伤,是不遇之感的一种表现。王维虽不属于宫廷诗人,但他青年时期即在岐王府等贵族场合获得声名,与上层集团始终保持密切联系,《新唐书》甚至视其为侍从酬奉一类文人*《新唐书·文艺传序》论唐时的文艺繁荣局面说:“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第572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这里将王维划为宫廷侍从而不是诗人,较为特殊。在《旧唐书·文艺传序》中,论“雕虫”时是将王维与杜甫并列的(第498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为何《新唐书》要这样分类?笔者分析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王维确实是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在岐王府等核心传播唱和获得声名,如《旧唐书》所说“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第5052页)。而且他诗名甚盛,还受到代宗的推崇,因此被《新唐书》归为侍从文人一类。第二,从元和时期开始,李、杜的诗歌被韩愈并尊,其后的元稹、白居易等人继续宣扬李、杜,并且更以杜甫为尊,李、杜在盛唐诗坛的核心地位被确认。欧阳修生活的北宋前期,完全尊奉此种观点,而且杜甫的地位有越来越高之势。第三,《新唐书》的这段写法是模仿《汉书》而作的一种平衡与调整。《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其余不可胜纪。”(第263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新唐书》的这段有可能是为了平衡各类所举人数而产生的权宜写法,并非否认王维的诗人地位。而且上段序论在“言诗”后面紧跟着又论“谲怪”的诗人,转而为诗歌风格的分类,与前面的诗歌职能有着较大的区别,写法较为随意。。即便是短暂地归隐,也并不能忘怀世事。因此,王维是根据他自己的人生体验来选取相关题材。一般来说,才华希世、受时代雅赏,但命途多舛的汉魏六朝文人较多地成为其诗中出现的吟咏对象。他的此类诗歌往往突出不遇与不能忘怀世事的烦恼,而并非突出主人公之“贤”或是“隐”。

王维写景诗择取的意象与采用的这种新的结撰方式,对同时与其后的诗人都产生了影响。与王维有交谊的卢象等人,也在诗中将田园风光描写与归隐心志结合,如卢象的《送祖咏》与王维的同类型诗的写法类似,均于末尾寄寓言归之意。钱起《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在写景之后,尾联曰:“闻道甘泉能献赋,悬知独有子云才”,则以扬雄献赋作比。《唐贤三昧集笺注》评论说:“此种都是盛唐正轨。”*黄培芳:《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上,翰墨园重刊本。因此,王维采用的这种新的方式,也奠定了盛唐时期山水诗写作的正宗模式。
四
以上所论王维诗歌的书写不遇,并不在于他在诗歌中表达新的情绪或是体现出超过前人的强烈鲜明的个性,而是他的表现方式有一定的创新之处。而这种创新的原因,倒也不是诗人主观上的创新,如林庚先生评论时王维时说的,“他并不超越时代,而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将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新鲜气氛传达出来”*林庚:《唐诗综论》,第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种诗歌特点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也是很多学者指出的,王维受禅宗的影响很深,这大大影响了他的观物方式;第二,这种诗歌特点也与山水田园诗歌呈现出的新的时代特点有关。王维既善于学习前人,包括对汉魏六朝诗风的广泛学习,并且他还善于融入新的时代风气。综上种种,王维此种类型的诗作,显示出一种情感与艺术上相互调节后达到的诗歌状态,其结果是以情感来映射山水,以山水来慰藉情感,归之于雅正。他的诗歌中风景与自我的融入,一方面是“赖谙山水趣,稍解别离情”(《晓行巴峡》),另一方面是“颓思茅檐下,弥伤好风景”(《林园即事寄舍弟》)。作者既对山水入诗的功能有一种自觉的体认,心里又有一种在与世相殊的风景中依然不能忘却世事的自责、迷茫等复杂的感情。风景与咏怀作为诗歌的吟咏内容与情感支撑,在王维的许多诗中共同存在。其中,山水/田园代表审美的趣味/理想,咏怀代表主体直接抒发的情绪/情感,风景与自我间或融在一起,又或呈分离之态。在后一种状态形成的诗境之中,他的大多基于想象与出于旁观者视野的田园诗在现实方面的贫弱,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补。赵殿成曾称王维“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王右丞集笺注序》)。完全胶滞于世事是一种浊,与“清妙”无关,而诗歌本身即是具有超越性的一种文学体式,以“无竞”之心运之,庶可达到“脱弃凡近”之感。在这一种诗歌情绪中,王维诗中时隐时现的文士面目仍然存在,但这一位文士即使是处于坎坷不遇的境遇中,也不会表现出强烈的孤寂与自伤,而是体现了一种性情上的雅正。可以说,这是对以往文人诗歌传统中风景与自我的融入方式的一种开拓。
作为王维诗歌的老境的,则是属于他集中吟咏辋川风景的组诗。它们不但选择的意象更迷惘,写法更疏淡,咏怀的元素也淡化于无形中了。这些偏于感觉、偏于氛围营造的写作方式,更发挥了王维在艺术上精细入微的长处,景物描写中处处体现了情感上的节制,并且蕴含着一种接续六朝诗歌的风华之美,而其中的禅学之味则是属于盛唐时代的。因为具备了传统与时代的多重质素,王维的诗歌即便是写虚空之景象,也无孤寂之感,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情绪与人生意味上的蕴藉与圆满。
应该说,风景与自我在王维诗中的结合是多方面的,但风景与自我相互消弥的状态,应作为一种较为突出的现象加以留意。它也显示出,盛唐时期由王、孟诗派推向高峰的山水田园诗歌,不仅在山水田园的写作技巧与呈现形式方面达到了极大的拓展,而且在风景与心志相结合的途径方面也有一定的新变。在传统的感物兴情方式之外,还可以有其他方式的呈现。
将风景与自我复调般地融在一起,是一种诗歌平衡性的最高体现。盛唐诗人中,无论是写景造象还是传情表意,在诸多诗歌功能的体现上,王维都体现了一种很高的平衡性。盛唐时期的诗人中,有些因诗歌表现出的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丰沛饱满的诗歌情感而迥出一时,如王昌龄、李白;有些则因某一类题材的大量写作而开拓出新的题材与风格,成为一时之选,如高适、岑参;有些则善以时事入诗,显出博大浑灏的特色,如杜甫,等等。王维虽然常与孟浩然一起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但他不仅仅在诗中描写山水田园,还延续了写文人不遇的传统,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他的诗以“清”、以“秀”等整体风格与意境闻名,不仅“为文已变当时体”(苑咸《酬王维》),而且“最传秀句寰区满”(杜甫《解闷十二首》之八),在诗歌的炼句方面也非常出色。这些都体现出他已具备一种较为成熟、全面的素质。而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中,风景与自我的融入方式产生的新变,也使他达到了唐代文人诗歌中山水田园一派诗歌写作的顶峰。
【责任编辑:赵小华】
(作者简介:管琴,江苏南通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2-0151-07
【收稿日期】201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