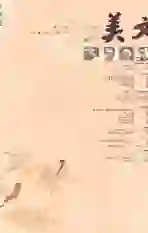大悲凉
2016-05-25王冰
王冰
前几天受邀与一帮作家谈散文,说着说着就聊到生死上了,于是我前前后后、古古今今说了一通,然后就冒了汗,心却越来越凉。因为像往常一样,只要一想到人是必有一死的这个结局来,我,我想包括其他人,每个人心里就凉了半截,因此,在平时的日子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尽量让生的诸多事情填满每一天,以便尽量使自己不去想这个话题,然后就会安心地很幸福地生活了。在这点上,就连孔老夫子也不能免俗,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总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当樊迟来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务农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而当季路“问事鬼神”的时候,夫子是这样回答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论语·述而》也记述到:“子不语怪、力、乱、神。”对此,鲁迅曾在《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评价道:“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我的理解倒是与周先生不同,孔夫子应该也是在回避,能不谈就不去谈罢了。因为无论是谁,一旦触及这个话题,就像刚才说的,一种悲凉之感顿时就会从心头升腾起来。由此,按照这样一种路径加以反向推导,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想让文学作品中有一种大悲凉,作家在创作中就不能不去触及这个话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学创作,包括散文创作,就是一遍遍抒写大悲凉的文学历程。对此,下面就不吝其烦罗列一二,一是为了证明这个话题的正确性和历史连贯性,二是也顺便偷偷懒,因为有时候学会偷懒也是一生的一大境界,是对付生,也是对付死的一种好办法。
曹操的《短歌行》早就为我们熟知了,其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更是会让我们在突然之间就能对着酒杯发一阵愣。到了魏晋南北朝,历年的战争和动乱,折腾得那堆文人不断地感叹生死之间的短促与无常,而《古诗十九首》更是纠结于此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王羲之也在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3月3日,召集一帮朋友,包括谢安在内的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在山阴,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的兰亭“修禊”,喝酒沉醉,恣意无状,于是《兰亭集序》就有了这样的句子:“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时间跨到唐代,这种情绪一直延续着,李白在《将进酒》大发感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因此有人就开始思乡了,“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除夜作》);有人也就悲秋与送春了,“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辛弃疾《摸鱼儿》),“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欧阳修的《蝶恋花》;作为宋代的一代宗师,柳宗元在《钻鉧潭西小丘记》也自欺欺人地道:“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作为文坛大才子,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自己都“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了,于是就像前面的那几位一样去喝酒,然后“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最后发了一通议论,“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我一直认为《后赤壁赋》之所以比不上《前赤壁赋》,也只是因为其中所写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人虽然依旧寂寥,但似乎是从死生的忧惧中退出来了。
这些文章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们对于生死认识的通透,因为通透而忧惧,因为忧惧而沉醉享乐此生了,但内心又是不甘的,于是一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不像现在的作家,能想到的、能写到的,都是些世俗中琐碎的事情,显得他们不但是眼界狭窄,同时也还是近视眼,但现在的作家毕竟脑子好使,最终依旧为自己的写作生生硬造出了一种合理性与合法性,将自己的写作美其名曰为“现实主义”了。其实,没有死生观念的写作,怎么写也不会透彻,永远不会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也永远不会有大悲凉。而我一直认为,好的作品都是来写大悲凉的,上面举到的作品是,《红楼梦》是,《水浒传》是,《三国演义》是,《西游记》虽然似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悟空成佛的经历不也是自我根性泯灭的过程吗,难道不是一样的悲凉吗?这几部书都是生死之书,也是一些大悲凉之书。这种大悲凉来源于人类一种永久的生命焦虑和无可奈何的宿命感,这类似于古希腊悲剧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研究者称之为“命运悲剧”的样态。
后来写的东西,除了我们所说的四大名著之外,渐渐就不行了,原因是这些作品只剩下一半的悲剧了,其表现之一就是这些作品都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大量地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大团圆”的作品林林总总,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描写的过程多么跌宕起伏,最后总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或是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好人平反,恶人伏诛,神灵显圣,天理昭彰;或是用圆梦、仙化、复仇、冥判、敕赐等形式,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结局,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团圆理想,即使元曲中出现了“四大悲剧”——《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也已经是与一种大悲凉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没有正视的勇气。”“从他们的作品上来看,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机,他们总要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急躁。”“中国人向来因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论睁了眼睛看》)
而现在的作家,很多已经不单是不懂得死生,就是连“团圆”也不会了,硬硬的,成了四不像。他们已经成为消费时代的一颗同样的螺丝钉,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知识分子了。应该说,八十年代的个人,是一个物欲与精神兼具的个体,但九十年代后期以后,人的本性被单面化,成了纯粹的被物欲所控制的人,他们拥有发达的“经济理性”,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所在,善于以最有效的手段,实现最大效益的目的,占有更多的物品和资源,从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当现在的作家也一样蜕变成这种样态的时候,他会看到大众知识水平之上的东西吗?
于是,很多作家也已经成为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塑造出的世俗时代的那个人了,他充满着欲望想象,具有无限的物欲追求。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市民阶层在人数上的扩展,这种消费主义所塑造出的经济价值一元化考量标准,也慢慢在作家中也获得了相当普遍的认同。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个人的独立和主体的重新发现和确认,作为曾经的重新启蒙的成果,到如今却成为了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了。在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给人们带来普遍的解放感和兴奋感,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却蜕变为愈来愈强烈的焦虑和不安,那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为市民阶层中唯我的、物欲的个人主义提供的这种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来应该成为作家反思和批判的主题之一,到如今,却似乎成了作家所要证明的正当性了,这与一个作家的本性是相悖的。在此种状态下进行创作的作家已经不是一个道德主体了,他与公众一样,在孤独地面对这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的时候,失去了道德的分辨能力和价值的判断水准,那么对浸泡在此种环境中的作家,我们还能期望他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来吗?更甚的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中,个人与时代一起将这种状态推向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于是,遍地的琐碎与悲哀,一下子就成了现代人灵魂中所浸透的另一种悲剧感,这种悲剧感与死生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与人的欲望勾连,所以,以此为中心的写作总是低那么一个层次,最终的结果是这些作家的创作只能滑向悲观主义,而不是悲剧命运的方向了。
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死生之中去,将两者贴在一起考量,有了这,才会有了一种更大的视野和境界,散文才能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正因为如此,史铁生的散文才显得难能可贵,因为他承接了这样的思想一脉,力图要解释一些人生的困惑,摆脱因困惑而来的困境,他在《答自己问》中做了这样的思考,“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可以说史铁生的散文归到最后,还是触及到了死生问题,所以他的文章是好的。
因此,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无疑要呈现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人在生死困境中所进行的突围,在揭示人的沉落处境的同时,展示人永恒生的理想和希望,那么我要问的是,当下的散文创作是不是缺少了这种大悲凉以及产生这种大悲凉的智慧背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