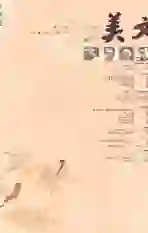陕西乡村记事
2016-05-25罗宾·吉尔班克胡宗锋
罗宾·吉尔班克 胡宗锋

农民是不朽的中国。在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尊汉代墓葬的石雕,是一个人赶着牛拉的独角犁在犁地。在城外,也可以看到被上演了两千多年的这一幕景象。在田野里,一群群的人弯着腰,在没完没了地辛劳着……不论到哪里,不论人们用什么工具,风景里永远是草帽下弯着腰的人。
——引自芭芭拉·W·塔奇曼著《来自中国的函件》第17页
四十年前,在毛泽东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打开僵局会晤的前夕,美国有名的历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调查性的访问,目的在于让自己的同胞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陕西可能以其丰富的古迹和当代中国西部粮仓的声誉被选为她造访的地方,她的分析带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塔奇曼着眼于拂去当地复杂的历史尘埃,把以前受奴役的农民和“被解放了的农民”后代分开了。前者是受自我认识束缚,被孔子称为是“小人”,是维持这个庞大帝国蝼蚁般的芸芸众生。而后者则是接受了宣传和教育,认为每动一锨土和每种一粒粮都会使自己更加靠近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老百姓长期以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休止地劳作。在我心里,毛姆在引用庄子语录的时候,对此做过更加精辟的阐述。他说:
“在中国,驮负重担的是活生生的人,‘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引自毛姆著《在中国屏风上》“驮兽”
这种观点现在早已过时了,现代的乡村男女把自己从父辈的生活困境中解脱了出来。
关中平原的现有人口超过了两千五百万(比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都多),但除了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等城市外,到处还是弥漫着农村的气息。沿着高速公路前行,映入眼帘的一切新颖而别致。忽然就冒出了许多独立的和半独立的住宅,屋顶上通常都装着小型的太阳能设施。唯一高点的地方是丘陵、黄土高坡和古代皇帝们的墓冢。单调的平川地带上,点缀着瓷砖装饰、古香古色的楼房。农民新建的房子几乎都是不协调地装着两扇大门,每扇门上都镶着门套和很大的门环,上面有主人喜欢的标志。很少有麒麟,因为人们不期望有不吉利的访客。大多数人家的门口宽大,可以让电动车和农用拖车出入,农用拖车晚上就很安全地停放在院子里。
生死轮回在这里不可避免地上演着,在地上的角落和田野的空间都可以看到一簇簇的墓碑,好像各有各的特色。简单一些的就只有一个墓堆,而在有的地方则有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有与逝者有关的后人名字。新坟不难辨认,普通的花圈通常都是一个大的同心圆,周围是纸做的花和彩带,中间挂着挽联。在我看来,这些多姿多彩的花圈怪怪的,让人会联想到射箭用的靶标。不管如何,仔细一想,城里人的生死极限既安全又卫生。在西安的一些特定的地方,特别是在文昌门里边附近的花卉街和买戏衣的街道,还有人在做花圈。但这些商品很少见到与死亡相关,在毛泽东时代,城市里就在严格执行火葬,这一点从未变过。火葬场和墓地都是建在远郊。
只要是到了乡下,就会亲眼看到对逝者的敬畏依旧是那么隆重。葬礼的色调是白色,而不是黑色。从人去世到最后下葬,有七天的哀悼日。礼仪规定逝者的亲属要从头到脚都着白色,头上戴的帽子和平时医生和年长的穆斯林女人戴的一样。悲痛与日俱增,当一个人的最后一位父母离世的时候,其子女有责任尽孝,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得无比悲痛,连日常事务都没法打理,比如要趿拉着鞋,不能全穿上。
我的一个朋友,家住在秦岭脚下,他给我讲过一个传奇故事,说他们一大家为了哀悼长辈和高寿的姑奶奶,沿用旧礼仪,姑奶奶却死而复生了。他姑奶奶当时已九十多岁了,还保留着新中国建立前女人愚昧的“三寸金莲”。她不用人扶,可以战战巍巍地走到几米远的木凳跟前并坐下来。一天早晨,她的侄女发现姑姑窗前的百叶窗没有被掀起,遂进屋一看,发现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墙角里。下葬前安排有七天的哀悼日,放灵柩的是上个世纪的一张老长桌,旁边堆满了白玫瑰和康乃馨。邻居们来的来,去的去,所有来的人都是给一碗面,但大多数人都没有动。几天过去后,姑奶奶的面容变得更加扭曲和不起眼了,不像桌子上方黑白照片中的她那样相对富有活力了。于是人们决定应当再给她的脸上蒙一层遮面的薄纱,这样既可以让人看清她的脸,但却不至于露出她没有表情的面容。当面纱接触到她的额头时,姑奶奶的眉毛抽搐了起来。由于不清楚这是不是人死后的罕见反应,其侄子和侄女都退到了边上。过了一分钟,她的喉头也动了,接着便咳嗽了一声,“复活”后,老太太又活了两年。在她最终离世后,家里人花钱从城里请了两位有经验的医生过来证实她确实是“不在了”。
在关中农村,孝道和迷信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正如弗朗西斯·亨利·尼科尔斯所言,从婴儿一来到这个世界,勉强糊口的父母就会绞尽脑汁地想,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避祸祛邪:
陕西孩子的脖子上戴一个用绳子拴着的“长命锁”,认为这可“锁”住其魂,不让厉鬼偷走。孩子特为此自豪,只要跟人一认识,就会常常拿起来让人看。虽然孩子的名字来自于“起名手册”,但父母很少叫孩子的名字,而是经常给孩子起一个低级动物的小名,如“癞疙宝”或“亥娃”。这也是为了防找孩子魂的厉鬼,鬼不会对一个叫“癞疙宝”的孩子像对其他叫真名的孩子那样有兴趣。陕西的男娃几乎刚会走路,就会把头顶剃光,只留一小撮头发,预备以后编辫子。
——引自弗朗西斯·亨利·尼科尔斯
《穿越神秘的陕西》第134页
以前,婴儿死亡率很高,人死后无子乃是最大的不幸,故做父母的认为采取这些古老的做法很管用。
儒、释、道的融合以及本土信念形成了老一辈人对宇宙和周围环境的认识。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供奉的是父母的相片、太上老君或是土地公。土地公的名字就意味着他是“地神”,其长相接近圣诞老人——是一位慈眉善目,白须像餐巾一样垂肚的老人。土地公掌管土地及其生长的万物,土地公和土地婆偶尔也有收礼的嗜好,要是有人家庆祝大丰收,让门边喜洋洋的神像同乐也没有什么坏处。毕竟农民是靠土地在过日子,其归宿也是脚下的黄土。土地公既不用神权报复人,也不反对人们以他的名义,修建华丽的庙宇祭祀他。
英国传教士和英语教师威尼弗雷德·加尔布雷斯注意到:“对中国人生活比任何宗教影响都大的是对土地的观念和乡土生活的重要性。”(见加尔布雷斯著《中国人》第四章)泥土气息是关中民间文化和幽默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许多荒诞的笑话都和夫妻生活有关,如夫妻为了要孩子而产生的误会。由于一大家人都是睡在同一个炕上(炕就是用土坯垒起来,底下有加热通道的床),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黄色笑话。常常是新娘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爱人(陕西方言称之为老汉),但却命中注定和一个比自己小得多的男孩订婚,有一首歌谣表达的就是这种黄色但却辛酸的情景:
十八大姐八岁郎,
晚上睡觉抱上炕,
年龄太小不是郎,
说是儿子不叫娘,
等到郎大妹又老,
等到花开叶又黄。
新娘的这种感受显然是以前的事情了,国家现在法定的结婚年龄是女性二十,男性二十二。即便如此,这种泥土的气息又有了新版本。一个有名的笑话是,县上的领导去看一个村长,领导非常想知道经济发展对农村人生活的影响,就直接问:“村里的GDP有多少?”村长仿佛既迷惑不解,又很尴尬,满脸通红地说:“天啊!那当然是太多了,我们能不能先开始数马的和牛的?”用陕西话说GDP(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外来词)听起来跟“鸡的P”一样。GD就是英文的chickens(鸡的),而P就是指母鸡身上的生殖器官了。
关中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是很奇特的,在有些方面是共栖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离开农村的家,去打工和追求高等教育。这些人也许依旧保持着对家里人的孝顺,给家里很大方地寄自己的工资。然而,实际上除了过年和节假日,没有几个人重回黄土地。年轻人的愿望是能拿到一个城市户口,长期在那里待下来,并成家立业,像城里的西安人一样享受教育、福利和其他一切。
类似版本的故事在无数次地被演绎着。在公交车上和生人说话,人有时感到这并不是在听某一个人的身世。现在,这样的故事少了。过去十几年来,乡下又成了人们休闲和创业的地方。原先人们觉得活在乡下是个耻辱,而现在却成了自豪的象征。要是愿意,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在火车上,一位衣着光鲜的城里人不得不坐在一位邋遢的生人对面,其身上还带着一丝肥料味。火车导轨的时候,他们的膝盖就会碰在一起。那位乡下人从他的脏短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响铃的苹果手机,他对面的人惊讶得都不会说话了,于是屈尊问人家:“你是农民吗?”对方的郑重回答是:“不是,我是农夫。”接着便会拉起袖子,露出自己的瑞士手表,那也许值城里人一个月的工资。坦率地讲,他想传达的信息是他是个农民企业家——一个找到了赚钱窍门的人,用不着每天都去种地了。
旅游指南和日常生活中现在最“火”的词是“农家乐”,不好翻译成英语。政府的媒体倾向于用带有美国味的蹩脚缩略语“agri-tainment”(是把农业和娱乐两个词合在了一起),其他的翻译有“joy in the farmhouse”(农舍里的乐趣)和“merry farm-hostel”(快乐农家旅馆)。我个人喜欢有基本元素的“country fare”(乡村行)。这个词包括围绕着乡下农户的多种活动,如钻树林、进田地、嬉水和爬山。十年前,农村人的年收入大约是在9000 至10000元人民币(900-1000镑),要是家里可以提供钓鱼、摘果、采菇和教一些传统手工艺,其收入也许可以翻十倍。“农家乐”刚开始就是搞个活动,或者是个农家小饭馆。一旦开始源源不断地赚钱,下一步就是把外面的房子改为可以过夜的住处。渴望一年毛收入达到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农民,就会想着搭个台子唱秦腔或跳民间舞。
也有吓人的故事,说外国人兴高采烈地摘了半天核桃,等把袋子拿去一称,才发现不得不交几千块钱。一般说来,“农家乐”让人舒适,甚至让人有一种怀旧感。食品掺假在城里是个炙热的话题,最近的谣言说市场上有为了看起来鲜黄,被硫黄熏过的生姜,和被撒上了石灰粉的柿饼。好多客户,从厌倦了生活的企业高管,到没有孩子拖累的父母在周末终于有了空闲,这些人便陆陆续续出门,去品尝从不远处的地里和窝里拿来的东西所做的饭菜。
我初次感受陕西的乡村味,是到旬邑县一个种苹果的村子——唐家村,那儿是咸阳的管辖区,但还是开车在危险的山路上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邀请我的几个同事和熟人的是咸阳文物局的副局长庞联昌先生,当他听说我是英国人时,就很遗憾地说他才上任几个月,错过了随“兵马俑”去伦敦的机会,“兵马俑”曾在大英图书馆被短期展览过。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秦始皇兵马俑”当时的展出情况。我告诉他那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葬展览后最吸引人的一次展览。因为游客都想和“兵马俑”面对面,主办方就采取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办法。他们在古老的像蜘蛛网形状的阅读室书桌上面装了现成的地板,来支撑“兵马俑”和青铜器的重量。对英国人来说,这个空间意义非凡,因为过去有无数作家曾在那里做过研究。卡尔·马克思就是在那里完成了《资本论》。庞先生感慨道:“啊,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缔造者聚在了同一所屋檐下。”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那次的一日游是典型的“农家乐”游。在看了几处上百年的老砖房和玻璃柜台中做工粗,价格高的手工鞋、绣花鞋垫和坐垫后,我们就被带到了路边的饭店里。
这次旅行物有所值不仅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农村,也是我第一次为中国酒陶醉了。穆涛先生是西安有名的文学编辑,他伙同另一位教授想用当地的酒使我上脸,把我灌醉。这种酒一般为45度,而且一次干杯要喝三小杯,这个任务没法推辞。
穆先生的一个强项是引经据典,内容总是带色,说话的方式重在吓唬人。他问我知不知道晋朝的王羲之,这在英国的综合院校里不是必修的课程,但我喜欢他其雄逸矫健、中和典雅的书风,其书法如人所言“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穆先生说的轶事如下:“有一本文人雅士作于绍兴兰亭的诗集,王羲之以行书为序,原作上有四十枚精美的印章。此作为历代人所敬仰,三百多年后,唐太宗尤爱,特想得到原作,便派一大臣向珍藏原作的和尚索要。这当然不容易了,那个大臣化装成一个潦倒的书生,与和尚闲聊,并从其眼皮下骗走了这一宝物。当然,人若知之为宝皆想盗也!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风雅聚会的产物。当时有四十二位文人雅士在兰亭‘修禊事也,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一觞一咏。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名士“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直到酩酊大醉。清醒后,王羲之又写过多幅,均无第一幅的神韵。还有人说王羲之养鹅,根据鹅的体形及行姿练习执笔和运笔。”穆先生有意吸了吸鼻子,咳嗽了一声,扶了扶眼镜,左手拍了一下我胳膊。然后右手像鸭脖子一样扭了扭就端起了酒杯,他人若是这样就显得有点“娘娘腔”了。
随着一声“干杯”就要一饮而尽。中国人,尤其是陕西人饮酒的礼数可以追溯到《周礼》。《周礼》成书的时间也许在周后几百年,但却是中国文化的基石经典。乡饮酒礼在《周礼》中是单列出来的,为了表示对主人和同伴的尊重,大家要一起共饮三杯,然后是桌上的人逐个相互敬酒,根据人的职务或年龄打关。有时候酒到一半,也有不守规矩或至少是走样的。如没有任何理由,我都要和庞先生与穆先生各喝三杯。在大口吃鸡蛋的间隙(这被证明能化解酒),我的肚子开始不舒服了。有人把这比作是喉咙上了火,但让外国客人多喝点的习俗还是没有变,直到把瓶子喝干。
如果说我的消化道已经对我的嘴不满意了,那我的“下水道”还不知道下来会发生什么?一打听,村子里的卫生设施就是在外屋放一个铁通,用一个布帘子遮着。虽然味道不大,但当时桶里的黄铜色液体已经快满了,大概是好多人膀胱喷涌的结果,只要再加一点,就会溢到地面。我犹豫着挥了挥手,便又把手插进了上衣口袋。这时,布帘拉开了,是穆先生,他的脸红红的,那是因为喝酒,而不是因为尴尬。到今天我也不清楚,他到底也是来尿的,还是来看外国人能不能像当地人那样蹲坑。
那个屎尿桶的景象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我们来到一个果园,我才幸运地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堆满了干草的田地,这就方便多了。每个排队的游客都有两箱自己从树枝上摘来的大红苹果,一位胡子焦黄的老汉(胡子可能是被一直吊在嘴角的烟头熏黄的)在用胶带封上箱子前都要检查一下。他从眼镜上瞄了我一眼说:“我看,你是第一个来旬邑的外国人,你回去以后宣传我们的产品很重要。”“我中午喝了18、21,有可能是24杯酒。”我说,“我也有可能是死在这里的第一个外国人。”
如果习惯了乡下的简朴和舒适,那就是有很好的机会来清洗被西安的空气所污染的肺了。我去农村最多的一个避难所是宝鸡东边凤翔县的一个村子,凤翔有几处值得推荐给游客的特色去处。这里曾经是被城墙围着的雍城,从公元前677年到383年是西周人的首都,现在上了五十岁的人还能想起城墙完好时的情景。与后来的汉长安城不同,雍城的城墙历史更加悠久,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方圆三公里的土地不再有任何防卫的意义,城里边到处是搭建的破旧房屋,农民们不得不躲避冬天的寒风。偶尔,也有附近着黑衣的农民,放下手中的农活,与家人一起到这里来。也许他们是想看看从孔子时代就留下来的这片古迹,也许这种长途跋涉会使他们很容易地蹭口馒头或苞谷珍子。
今天凤翔驰名的东西有四样,每一样都各具特色。据传说,六营村的名字来源于明朝初期驻扎在那儿的一支部队,其士兵祖籍乃中国陶瓷工业的中心江西。随着与当地妇女的通婚,士兵们教自己的邻居做泥塑,以便增加收入。泥塑的动物或面具风干后,再在白色的表面涂上鲜艳的色彩,以大红、大绿和黄色为主。
西凤酒是陕西名酒,这儿人的酒量能把人的肝喝爆,一般都是一边打麻将或扑克,一直喝到深夜。当地的一句话是“凤翔的老鼠也能喝二两”。西凤酒中的高端产品“华山论剑”系列就针对的是消费者的男人气概。其包装独特,酒瓶是一个圆球体,瓶底凸显的浮雕是道教圣地华山。在参观了“兵马俑”之后,阿诺德·施瓦辛格被聘为“华山”的最新代言人,所以一路上的广告牌里都是他的形象。
凤翔的另两个产品也和家畜有关:一个是吃的,一个是装饰品。毛驴一旦过了出力的年龄,就会被宰杀,驴肉经过加工就成了“品牌特产腊驴肉”。驴皮被剥下来,加工成薄片,用来制作传统的“皮影”。在屏幕后边用灯照着,辅助纤细的竹棍,这些连接在一起的“皮影”就可以演绎传奇和古典的浪漫。在西安的书院门,就曾经有一位姓梁的女士缠了我大半个小时,让我掏三百元钱来买她的一张“皮影”,说她父亲是“皮影大王”,曾为外国元首及其家人表演过。她说的最多的是二十年前,希拉里就曾接受过她父亲赠送的“皮影”,并答应回国后“试玩”。“你想想,先生,希拉里女士都拿着这只龙在白宫和克林顿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乐呢!也许布莱尔首相和你们的女王也会看到。”虽然让“州长侠”饮几杯“华山论剑”还说得过去,但让前第一夫人和现在的国务卿脱掉鞋子,蹲在地上在白宫表演动物的阴影就让人难以置信了。
喝酒(无法避免)是我在隐居乡下四重奏中日常唯一不变的节目。在胡奶奶家的时候。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永远好客的女主人怕我冷,会给我加好几床被子,并用柳枝赶走毛毛虫。在秋天,村里的街巷上都是为冬天做准备的农村妇女,她们忙着把玉米剥开,再用这自然的包装把玉米紧紧地绑成可以挂起来的串。垂直挂起来的金色玉米串和瀑布般下垂的红辣椒串相映成辉。
当我躺在一间与世无争的房间里时,不论是窗帘挂得比窗户高三十厘米或六十厘米,还是门楣和门框配不配套,我的脑海里萦绕着两个思绪:一个是没完没了的面条,从早晨、中午到晚上。年逾八十的胡奶奶一定为她的长辈做了五万锅臊子面,接着又为自己的丈夫和子孙做。二一个是为什么历史的影子在乡下是那么悠长,胡奶奶在2013年去世的时候,前来悼念和送挽联的有作家、诗人和大学里的领导,这也显示出了其住在城里的子女所收获的人脉。然而,她被安葬在了村委会指定的墓地里,在土地被分田到户的三十年后,她依旧是生产队里的一员,这就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宿命。
纽带:乡下的儒教
2012年,根据陈忠实小说 《白鹿原》改编的电影开篇展示的是苟延残喘的帝制华夏时代。关中一个村里的人集体站在祖宗的祠堂前,齐声吟诵孝道。在那个时代,每个家庭都秉承家训——有遗传下来的家规或代代相传的至理名言。这些有的出自《论语》,有的已经变得无法考证了。
这部电影大体上讲的是地方上两个家族——白家和鹿家的命运变迁,这两个家族之间的密谋、争斗以及欺骗可以说验证了一句老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白嘉轩和家族里的其他老者坚守传统,而教师出身的鹿兆鹏则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人。剧情的高潮是革命者为了破除旧习,捣毁了鹿家最神圣的祠堂。祠堂中供桌上的鹿被掀翻打碎在地上,意在表明和过去决裂。对祖先的敬重虽然没有上升到宗教的地位,但实际上却一直是中国最流行的崇拜仪式。同样,革命者为了显示反抗封建统治,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古典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闪现在《白鹿原》中,弥漫在中国乡下的角落里。在陕西,地处渭河北岸的渭北包括大荔、澄城与合阳等地,这些地方的殷实人家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坚守就是杰出的例证。
渭北一个比较大的地区是蒲城,县城坐落在具有清朝风格的达人巷,很有十九世纪的独特景致。这里有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清代考院。一千三百年来(从公元605年到1905年),除了十二世纪简短的中断外,严格的科举考试一直是人们进入政府机构的万能钥匙。虽然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科考项目,但一成不变的概念就是(以圣人之言)人不分贫富贵贱,只要有才华就有机会出人头地。
虽然蒲城考院早就被改造成了一所私塾,但其兵营式的建筑里依旧保留着几处文生参加科考的狭窄“号舍”。在参加考试的三天两夜里,考试文生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号舍”里,直到写完高质量的“ 八股文”。考生所带的东西,诸如菜肴、馒头和取暖的木炭都要切成不到三厘米,以防作弊者藏匿夹带。在有些地方的博物馆,如“半坡博物馆”(实际上是指西安半坡博物馆和上海嘉定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国科举文化展”——译者注)里就展有一件作弊的麻布坎肩,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有预备答案好几万字。由于检查的人不会对考生进行全裸检查,所以有些无耻的考生便会不用纸做夹带,而是在外套下穿件切身的短袖坎肩。潜在的回报之高让考生觉得值得一赌。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能通过考试成为“举人”,然后再参加下一轮的“会试”,直到京城参加“殿试”。
蒲城人的后代有一个他们渴望效法的榜样,那就是出生在达人巷的王鼎(1768-1842),他走出了渭北的死水,成为一代名家和高官。王鼎在位时,曾主持政府的几大工程,如用现代方法治理河南的洪水。然而,他让人记忆颇深的是对清政府有学者良知的外交家林则徐(1785-1850)的影响。林则徐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其“忍”(为了大众利益宁愿放弃个人的舒适)的性格。在道光皇帝令其监管广东的海关时,正是他发起了大规模的收缴鸦片和烟枪。他也在舆论上反对英国,发表了致维多利亚女王的公开信。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得到消息刊登此信后,也一定是最终引起了女王陛下的关注。林总督在信中说:
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
大家可以猜想英国的编辑觉得这封信有新闻价值,是因为林则徐目空一切的口吻,而不是因为害怕愤怒的东方人报复。不久,正直的林则徐就被描绘成了伦敦舞台上的滑稽人物。讽刺杂志《笨拙》出现的是他的辫子和鸡爪似的手指,而杜莎夫人蜡像馆里也出现了同样形象的蜡像。
林则徐的光辉形象很快就消失了,他被指责明知英国海军要发动进攻,但却没有及时提醒当地的江浙总督。他周围的政敌意识到他即将倒台,而清朝的皇帝则又像以前那样保守,让不明就里的改革者成了“替罪羊”,林则徐被发配到了离中英海上冲突最远的新疆伊利。1845年,虽然不如以前风光,他再次成为总督。他任陕甘总督(后来由左宗棠接任)的时光留在了今天凤翔县东湖岸边的大柳树上。
林则徐的老师王鼎却从没有看到林的官复原职,在听到林则徐被发配的消息后,王鼎在失望之中,想到了后来被孔子赞扬的春秋战国时的史鱼,便于1842年六月八日自缢于圆明园。他死后81天,《南京条约》就被签订了,割让香港给英国155年。王鼎的政敌向皇上隐瞒了其自缢真相,皇上还以为这位老臣是“卒暴”了。
从蒲城沿着去邻省山西的高速路走一个多小时,人们便会再次回到黄河旅游线上来。韩城北边的党家村有一百多处的明清民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古老的的四合院两层楼,中间有院子。一小部分人家里也有家族的祠堂,通常是墙上挂着几十年来的相片,或者是装在相框里挂在祭桌的上方。香和季节性的装饰,如一盆樱花显示出人们对逝者的记忆依旧鲜活。
游访此处的最佳季节是早秋时候,这时早霜还未降临,空气中弥漫着明显的花椒味道,树枝上挂着像布袋一样熟透了的柿子。要是不介意像母鸡那样蹲在路边的青石边上,就可以花一两元钱吃一碗用麦面做的,带有芫荽汤的“鱼鱼”。我第一次享受这种礼遇时,远处传来的一阵鞭炮声差点让我把勺子埋到了碗里,把碗扣在地上。那是村子的另一头在办婚礼,胡同小巷里到处撒的是红纸屑,纸屑塞满了路上的石缝,沾到了大门上的黄铜门环上。五彩纸屑飞到了公鸡的爪子和尾巴上,溜进了路边的菜园里。园子里蓬松的牡丹、莴苣和巨大的白萝卜在繁星缠绕下旋成了一片花浪。没有人在意纸屑让自己化成了“红人”,也许是又一个党家人嫁给了贾家人,也许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朝代的联姻正在进行。从那些洗碗人喜悦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唯一离开举行婚礼大院的乡亲也许是因为他们要排队去领赏钱。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普遍认为党家村的人属于当地的有闲阶层。他们的先辈用从黄河上运木头积攒的钱修起了这些砖砌的古典而宏伟的院落。每家的木门槛都如膝高,因为据说在地上拖着脚走路的野鬼翻不过这样高的门槛。但从偶尔出现的戏台和艺术雕刻来看,人们也不清楚这里的家家户户到底信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满足,还是孔夫子的节俭。其中的门庭家训有:
心欲小 智欲大 行欲方 能欲多 事欲鲜
言有教 动有法 昼有为 宵有得 息有养 瞬有存
无益之书勿读 无益之话勿说 无益之事勿为 无益之人勿亲
行事要谨慎 谦恭节俭择交友 存心要公平 孝悌忠厚择邻居
事能知足心常惬 人到无求品自高
傲不可长 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 乐不可极
动莫若敬 居莫若俭 德莫若让 事莫若咨
富时不俭贫时悔 见时不学用时悔 醉后失言醒时悔 健不保养病时悔
岁月流逝,美德凝固在了高大的碑林里。在村校园的中心有一座“文星阁”,那里供奉着圣人孔子以及其10位高徒的牌位。村里人说这儿也藏有“避尘珠”,保护村民不受尘暴的侵扰。沿着操场走,又会解开另一个谜。不论是在门槛旁边,还是在花圃里,大多数人家都有一堆灰烬,这么多的灰不可能是因为烧香或烧纸钱。小学里的公厕(也许各家各户也一样)是斜坡式的一个坑,各家里掏出来的灰是为了掩盖粪便及其臭味,并以防粪便散落到街道上。
最宏伟的一座建筑是上个世纪的,当时清朝政府受“八国联军”的威胁,慈禧太后和宫里的人逃往西安时曾路过这里。慈禧太后御驾逃难留宿的地方在华北有好几处,都是忠臣的营地,而且周围的自然环境和防御必须安全。河北的驿站“鸡鸣驿”给人印象颇深的是其锯齿状的围墙,但慈禧太后给这里的御赐显然不及给陕西的主人。她给党家村忠实的臣民亲赐了“福”和“寿”两个大字,第一个字潇洒开放,即便是被雕刻在大理石也是如此。第二个字笔画纤弱,仿佛赐字的慈禧太后也对自己能否躲过一劫而心有余悸。相形之下,光绪皇帝却想的是表彰臣民的妇德。“节孝碑”就是他下令为党伟烈的夫人牛孺人而修的。实际上,对于知道内情的人来说,碑上的铭文说的是牛孺人一生所受的艰辛。说到底。她就是一个传统封建婚姻的牺牲品。
党家村人的事业心和商业头脑也许肯定挡不住这儿的发展。像临近的韩城一样,这个古老的村庄也在计划建一个保护区。在旁边的山上,已经开始修建现代化的水泥住宅和娱乐设施。在磨面机的轧轧声停止后,伴随着从大厅后面的屋子传来的麻将声,游客依旧能感受到这个古老乡村那宁静而黝黑的夜景。与此同时,当地人也过上了现代农民的生活,坐在豪华的沙发上喝着“娃哈哈”。我们离开的时候,在“新村”鹅塘碰到了三个80多岁的老人。其中一位老妇人(她说自己88岁了)用她弯曲的拐杖戳着黄土地说:“你们看到太史第门楼了吗?你们知道安乐居碑吗?你们知道不,我是小姑娘的时候,那些石头刻的老虎把我吓得乱叫。我觉得现在没有那些胡里花哨的东西也行,把老玩意放在外面就是在招贼。”她的话被证明是有先见的,2015年11月的一条电视新闻说有一个叫党瑞的家伙被捕入狱,他从韩城附近的门边偷走了几百个石狮子,想拿到黑市上去卖。显而易见,这个“哈怂”(陕西方言意思为“坏小子”)没有把儒家对祖先的崇敬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