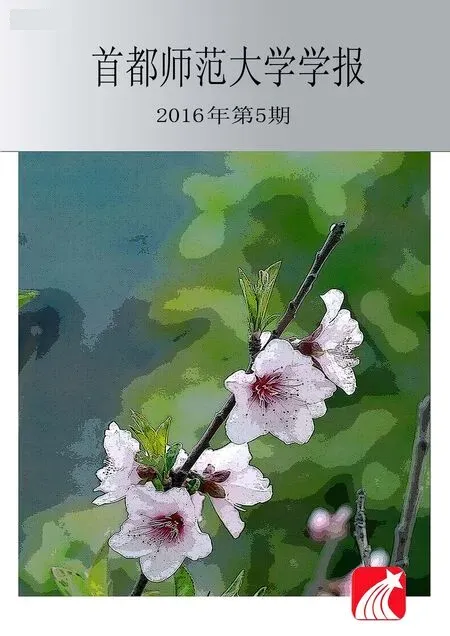城市儿童与父母分离后的抗逆力重组研究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基线调查结果
2016-05-20同雪莉彭华民
同雪莉 彭华民
一、引言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备受瞩目,然而城市或城镇留守儿童(文中统称为城市留守儿童),却因其户籍不在农村被认为拥有更多的资源而被忽视。诚然,城市留守儿童除了“留守”这一风险之外,拥有着相对优越的社会资源:他们有良好的成长和教育条件,可以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可以就读于教学质量、硬件资源都优越的公立或私立学校。然而在已有研究中也已呈现出城市留守儿童潜在发展的各种困境,如更高的抑郁、焦虑水平①文湘兰:《株洲地区留守儿童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现代医生》2012年第11期,第14-18页。,个性敏感、偏执②雷海玲:《网络环境下城市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4年第11期,第5-6页。③范方:《留守儿童焦虑/抑郁情绪的心理社会因素及心理弹性发展方案的初步研究》,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家庭亲密感更低、情感表达少、家庭矛盾多④雷海玲:《网络环境下城市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4年第11期,第5-6页。⑤范方:《留守儿童焦虑/抑郁情绪的心理社会因素及心理弹性发展方案的初步研究》,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亲子沟通缺乏⑥卫利珍:《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今日南国》2010年第1期,第218-220页。,孤独感是他们最多的负性情绪体验⑦刘霞、武岳、申继亮等:《小学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的特点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4期,第325-327页。。
缘何这些儿童拥有如此优越的外部资源却仍发展出上述诸多问题?“留守”便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说农村留守儿童的形成源于三农问题的宏观背景和户籍制度本身的资源区隔⑧江立华:《留守儿童问题构建与研究反思》,《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第178-183页。,那么对于城市留守儿童来说,可能更在于社会文化的变迁。为了职场或事业的发展,子女养育的重任对年轻的父母来讲,无疑是一种压力。所以孩子的出生为老年人的价值再现提供了重要而合理的机会,也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城市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城市儿童留守的原因众多,如父母一方进修、父母工作异地等。当然也有许多父母与子女同在一个城市,却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不能亲自照顾子女,而交由祖辈或其他人帮助养育的情况⑨程秀丹:《城市留守儿童的教育诉求——一项关于寄宿班生活的质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有学者将城市留守儿童界定为儿童户籍所在地为城市,但由于种种原因父母无法亲自照顾而交付农村的祖辈来代养的儿童⑩张垠:《城市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研究——J市K社区儿童个案工作过程探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也有研究将在城市调查对象中处于留守状态的儿童视为城市留守儿童⑪杜玲利:《城市留守儿童攻击行为与孤独感的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12期,第1864-1866页。。两种对象界定虽都称为城市留守儿童,但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前者是对农村中留守儿童根据户籍地进一步细分的结果,而后者是城市生活区域中的留守状态,并未经过户籍关系的考量。本研究将城市留守儿童界定为户籍所在地为城市或者城镇,父母一方或双方不能陪伴在其身边共同生活的儿童。
段成荣⑫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第29-36页。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中计算出我国城市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量的13.5%,并认为这一数据会继续增加。按照目前文献中对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的估算,留守儿童总量应为7052万人,城市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在952万人。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城市留守儿童的发展状况对于小到个体、家庭的幸福,大到社会国家的稳定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儿童抗逆力的研究自一开始就备受关注,学者们致力于找寻弱势儿童生态系统中的保护性因素与风险因素的互动机制,以便为更多生活于困境中的儿童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近20年来,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的问题研究已经备受瞩目,但城市留守儿童即便存有更长的历史,依然没能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如今“留守儿童”这一术语也几乎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代名词。那么城市留守儿童面对怎样的困境?他们适应结果如何?这是我们想要关注的问题。
为了回答上述的问题,我们从抗逆力的理论视角,尝试对城市留守儿童抗逆过程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抗逆力概念的提出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Werner等人的纵向研究,他们发现同样身处逆境中的儿童(如贫困、暴力、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等),有些(大约1/3)并没有发展出人们预期的适应不良或心理障碍,相反他们发展良好,甚至更优秀。学者们在原因探索中发现,基于个体水平的认知、情绪情感及与生态系统中的支持性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均可作为其逆境中的保护性资源,在个体抗逆过程中起到补偿和调节作用。如个体层面的乐观、幽默、自信、自我价值感,环境中的同伴、家长、老师、学校、社区等提供的有效、可及的保护性支持①田国秀、邱文静、张妮:《当代西方五种抗逆力模型比较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9-19页。。然而这些内、外部因素究竟如何作用于个体的抗逆过程?Richardson在其身心灵抗逆平衡模型中指出,个体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或挫折事件时,原本的身心灵平衡状态被打破,个体为了维持平衡,就会调动诸多内部保护性因素与压力挫折进行对抗②G.E.Richardson.The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2,Vol.58(3):312.。如果压力过大抵抗无效时,平衡就会被瓦解,此时个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认知系统,进行有意无意的重新整合,这个过程就是抗逆力重组。个体可能经过抗逆达到更高的平衡状态,也即获得成长;也可能恢复到初始的平衡状态,或者个体不得不放弃原有动机或希望而消极应付;最差的适应结果为功能失调性重组,个体可能产生行为问题、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应对压力,此时需要借助心理治疗得到恢复。城市留守儿童的发展困境如何?这些困境如何作用于留守儿童?外部资源究竟在留守儿童的成长中能够产生多大的效力?他们的抗逆重组结果如何?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的基线调查数据,尝试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并从抗逆力重组的视角为城市甚至农村留守儿童的成功适应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数据来源
文章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基线调查数据结果。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采用多阶段概率成比例抽样方法,以学校为单位,包括全国31省、28个(区)县级单位、112所初中学校、438个班级,共计2万名学生的调查样本(表1)。由于我们想要关心的是城市留守儿童状况,因此根据儿童是否与父母同住、是否在户籍所在地及户口类型三个指标,将样本分为8类,去除其中流动儿童的数据,对剩余的留守与非留守儿童进行分类比较研究。我们对数据中认知成绩使用调查结果中的认知标准分数,学习成绩采用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均值。根据问卷条目内容选择与儿童心理、监护及互动相关的62个条目进行因子分析,检测KMO值为0.846,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在项目可靠性检验中,Cronbach’s Alpha系数在0.724到0.867之间,显示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因子分析共抽取出儿童心理状况、父母监护状况、学习态度、亲子互动、学校生活体验、同伴关系9个因子,形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心理状况指负性情绪出现的频率,父母监护指父母对儿童学习生活的管理状况。心理状况、消极学校体验、问题同伴三个因子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环境适应越差,其余因子得分越高则表明家庭功能或学校适应越好。
三、结果
(一)留守风险效应显著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19487)

表2 城乡儿童留守模式及交互方差分析结果
本文对留守与否的界定根据儿童自我报告中与父母同住状况进行划分,将与父母同住儿童视为非留守,而只与父亲、母亲一方同住或父母都不在家的儿童视为留守儿童①根据目前留守儿童的界定,概念操作中还需要一个时间维度,但由于数据本身无法获得,因此在此处进行了模糊处理,因为若没有这种误差的结果应该会使两组之间的差异更大。。目前虽说有部分学者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是被建构的、夸大的,但绝大多数文献仍然认为留守儿童本身就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对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分城乡区域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各个因子上均差异显著。这样的结果与现有的研究基本一致。也就是说,留守儿童相比非留守儿童,认知成绩更低,学习成绩更差,父母的日常监管行为更少,焦虑、沮丧等情绪问题更多,学习行为中表现更为被动,对自我学习能力的认知更为消极,与父母之间的互动交流频率更低,对学校生活体验更为消极,交往同伴中的不良行为问题也更多。
我们的结果与前期文献有一个不一致之处在于学业成绩的差异。前期很多对留守儿童问题“正名”的文献中就指出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表现更优于非留守儿童,因为这些孩子有更好的自理能力,并且因为父母外出务工也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同时由于父母接受了更多城市文化,对子女的期待也更高,更关注这些孩子学业上的发展,等等。但是这种不同在我们的结果中并不存在,并且上述用来解释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更好的原因在城市留守儿童中几乎都不成立,那么他们的留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后面继续讨论。
(二)城乡差异遭遇留守趋于缩小
如果说现有研究中留守儿童问题更多的是城乡差异的结果,那么不论在留守组还是非留守组,这个差异应该是基本固定的。但是在我们对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都进行的城乡差异比较中(表2)发现,城乡差异在非留守儿童中除了学校生活中的积极体验之外,其余因子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然而在留守儿童组,城乡差异却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果,并且城乡差异显著缩小。
因为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学校生活积极体验这一项目中均不存在城乡差异,因此我们暂且将这一因子去除。在留守儿童组,城市儿童认知成绩、学习态度、母子互动三个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儿童,而学业成绩、心理状况、父子互动三个因子显著低于农村儿童,父母监护、学校生活消极体验、交往同伴中不良行为与赞许行为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留守模式的交互作用
现有研究认为儿童的留守模式是影响儿童发展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研究结果存在分歧,一部分研究认为父母都不在家的留守模式对儿童的发展最为不利,然而另外有研究证明,与母亲单独留守比与父亲单独留守对儿童的发展影响要好很多。最差的留守模式不是儿童单独留守,而是与父亲一起的留守模式,因为这种留守往往与家庭经济的困难高相关。

图1 留守模式对儿童认知及学业成绩的影响
我们研究发现,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其影响效果如图1所示。图1(左)是留守模式与儿童认知成绩的交互作用,其交互模式在父母都在家的时候成绩最好,与母亲留守次之,再次是与父亲单独留守,而最差的结果是父母都不在家的情况①因为数据集中仅有父母是否在家的情况,但是无法得出儿童与父母单独留守或者父母都不在家时是否与祖辈同住。,在儿童心理状况、学校生活积极体验及同伴中不良行为问题中,与留守模式的交互作用与此相似。图1(右)是留守模式与儿童学业成绩的交互作用,此类交互中最差的留守状况并非父母都不在家,而是单独与父亲在家的情况,与此相似的交互模式还有父母监护、学习态度、消极学校生活体验及同伴中赞许行为四个因子。
(四)城市留守儿童适应结果的回归分析
在抗逆力适应结果的文献研究中,对于发展良好的适应结果往往被操作化为学业成绩、认知水平、心理状况等,我们也将这三个因子作为因变量,探讨城市留守儿童来自个体、家庭和学校、同伴的保护性因素如何影响了这些适应结果,同时将非留守儿童结果作为对照以探讨两组差异。其中认知成绩和学业成绩分数越高,表明其发展状况越好,而心理状况分数越高则表明心理适应结果越差。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表3 城市留守与非留守儿童适应结果的回归分析对比t(B标)
从表3的总体分析结果来看,来自个体、家庭、学校和同伴中的保护性因素对其适应结果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而这种影响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心理状况的影响。在对城市留守儿童认知成绩的回归分析中,通过检验的因素为母子互动、积极学校生活体验、消极学校生活体验、朋友中的赞许行为和问题行为5个因子,可决系数为0.092。以学业成绩为因变量的回归中,性别、个体未来信念、消极学校生活体验、朋友中的赞许行为影响效应显著,可决系数为0.103。而对心理状况的影响效应中,性别、未来信念、父子互动、学校生活体验、朋友中的问题行为等影响显著,可决系数为0.176。而在对非留守儿童的回归方程中则有更多的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其可决系数除认知成绩低于留守儿童组,学业成绩和心理状况的可决系数都较留守儿童组更高。
儿童抗逆力的研究提出,父母监护与亲子互动是儿童适应结果和成功抗逆的重要家庭影响因素,但是从上述结果看,父母监护影响不显著,亲子互动影响也比较有限。为此我们在与非留守儿童的进一步对比中发现,这些因素对留守儿童的适应结果影响力几乎都小于非留守儿童组,并且这种影响力的削弱不仅存在于亲子互动和父母监护方面,儿童自我的未来信念、学校生活体验和同伴影响都有弱化。
四、讨论与结论
(一)留守塑造了城市儿童弱势群体
城市社区所蕴含的福利资源远远高于农村社区,然而城市留守儿童在抗逆重组水平上却没有显示出户籍制度带来的福利优势。正如本研究所示,非留守儿童中城乡差异显著,但是在留守儿童中城乡差异却趋于缩小。
已有研究中,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在许多领域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如王思斌所言:“长期以来,我国不但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而且在政治权利、教育权利、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实行城乡差别的政策,这种由户籍制固化的差别将农民群体(准确地说是农村居民)变成了弱势群体。”①王思斌:《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83-91页。然而这种弱势在城市留守儿童身上一样凸显。虽说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讲,他们之所以遭遇留守的主要原因就是户籍壁垒造成的城乡二元福利分化,与城市儿童相比,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并不能够同等享受城市儿童相同的福利待遇,他们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面临着来自城市的排斥,因而处于劣势地位。但对于城市留守儿童来讲,他们虽从小就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较多的认知发展资源、较好的教育环境,他们的父母生活的社区也拥有许多有利于儿童健康发展的资源,但留守带来的亲子分离使得这些优势几近荡然无存,使得他们成为城市发展中的又一类弱势群体。
(二)亲子分离是儿童适应发展中的重要风险
在本文研究结果中,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留守这一主效应显著,并且独立于其他外部社会资源的多寡。正如其他研究中指出的,父母亲情的缺失是留守儿童情绪情感、行为问题及心理状况的首要原因。留守的本质是亲子分离,唐有才②唐有才、符平:《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人口学刊》2011年第5期,第41-49页。对亲子分离的时间、空间、频率等维度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虽说不同模式的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结果不同,但结果也再一次证明亲子分离作为一个儿童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切实存在。
John Bowlby提出,儿童生来就有与母亲接近的倾向,儿童与照顾者建立的亲密关系是早期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并且随着儿童的成长及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扩展,父亲、兄弟姐妹都可能成为儿童可选择的依恋对象,但其早期建立依恋关系的性质(安全或不安全),构成了之后社会关系的基础。Ainsworth发现尽管依恋是人的生物性的欲望,但个体建立依恋关系的强度和质量极为不同。因此她在实验基础上将依恋关系分为五种类型:安全型、不安全-回避型、不安全-矛盾型、不安全-混乱型及无依恋。个体的依恋模式作为一种心理经验,在特定社会背景下铸就了儿童独特的发展路径。如果儿童的社会关系质量不佳、失常或者混乱,必然为其后期的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损害儿童组织社会经验的能力、发展自我概念的能力、应对焦虑的能力、理解他人及社会关系的能力,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将出现累积效应,不利于儿童的成功适应和健康发展③David Howe:《依恋理论与社会工作实践》,章淼榕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32页。。
亲子分离直接影响着儿童依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而依恋关系现在几乎被公认与儿童抗逆力发展相关,它作为影响抗逆力发展的双歧因子①指在抗逆过程中,并非单纯作为风险因素或保护性因素作用于抗逆过程,而是在一定情境下起风险作用,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则起到保护作用的因子。如依恋类型若为安全型,则更多起到保护性作用,但是依恋类型为不安全型时,则可能更多表现为适应风险。与儿童环境中的其他因素进行博弈。根据Bowlby的依恋理论,幼儿期建立的安全型依恋关系有助于后期人际关系的发展,并因此更有机会获得支持性资源。所以说,在儿童依恋关系建立的发展关键期,父母能否给予足够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上讲,在儿童发展关键期的非留守状态,有助于儿童的健康发展。然而留守儿童状况与此恰恰相反,尤其在城市中,年轻父母的职业发展往往促使他们在其子女成长中缺席。儿童良好的依恋关系建立由谁做主,祖辈抑或他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三)母子互动为抗逆力重组提供有限补偿
在与留守模式的交互作用分析中发现,不论认知适应、心理状况还是学业发展结果,与母亲的单独留守相较非留守稍差,但明显优于儿童与父亲的单独留守结果。在学习态度、消极学校生活体验及交往同伴中的社会赞许行为中,与母亲单独留守的情况要相对好于其余的留守模式。可见母亲在家照顾子女的留守状况对于亲子分离带来的留守风险具有明显的补偿功能。
家庭不仅是多个个体共享的特定物理或心理空间,更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系统。家庭成员各有角色,分工交流,以内隐或外显的方式完成着家庭中的各项功能。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功能良好的家庭鼓励其成员个体潜能的实现,能够成功平衡家庭系统的需要与成员个人利益的关系。随着留守儿童与父母或其中一方的分离,他们所处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系统的内部平衡遭到破坏,家庭功能也便随之发生失调。这种功能失调的结果往往导致留守儿童社会化适应不良,甚至在自身认同感与归属感无法得到满足时,从家庭外部找寻这种需求的满足,或以不被社会赞许的方式适应家庭结构不良带来的压力,如加入问题少年的群体之中,田国秀②田国秀、赵军:《高危青少年问题行为分析及介入策略——基于隐性抗逆力视角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21-126页。将之称为“隐性抗逆力”。然而,母子互动形成的家庭子系统在我国家庭结构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这可能与传统文化中赋予女性的角色期待有关。因此,虽然有时亲子分离不可避免,但若能在母子互动中为儿童提供更多的信任与支持③田国秀:《力量与信任:抗逆力运作的两个支点及其应用建议》,《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1期,第78-83页。,对于儿童抗逆力的发展也不失为一种补偿性应对策略。当然这种补偿功能仍有其局限性,因为无论母子互动如何补偿,留守与非留守之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可见这种补偿并不能完全弥补父亲缺失所带来的风险。
(四)内、外部保护因素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传统抗逆力概念被描述为个体经历风险逆境但仍能适应良好,但就适应良好这一结果描述,不同学者观点各异。当将城市留守儿童认知发展、学业成绩及心理状况分别作为抗逆适应结果进行线性回归,儿童未来信念、亲子互动监管、学校体验及同伴类型则显示出不同的效应模型。
有研究表明未来信念对儿童的抗逆结果有积极贡献,放松而自信的孩子会乐于寻求新经验,儿童得到的刺激和体验越多,建立的抗逆模型就越具有灵活性,越有用,抗逆重组水平也越高。在本研究中儿童对未来的积极信念对其学业成绩和心理状况均因为有显著的影响而进入了回归方程,但这种影响效应对儿童认知成绩没有类似的显著性结果。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其一,城市留守儿童虽说经历亲子分离,但其照顾者往往具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对儿童的认知能力训练也往往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其二,认知结果更多依赖于发展,而学业成绩和心理状况则更有赖于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个体未来信念的保护效应只有在个体与其所处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够得以体现。
我们的数据表现出父母监护功能影响效应不显著的结果。虽说亲子互动对儿童心理、认知及学业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在留守儿童身上却非常有限。究其原因,对于留守儿童来讲,无论亲子互动还是父母监护功能都是弱化或失效的。我们知道,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的信念系统、组织模式及沟通功能是影响家庭及其成员成功抗逆的关键因素。信念系统是家庭功能的核心,个体会通过内化家庭信念而为自己的经验建构意义,以应对风险或逆境;有效的家庭组织模式能够缓冲压力带来的挑战,并根据情境重新组织家庭资源,应对逆境;良好的家庭沟通则影响成员的互动质量,有助于专注目标,主动应对,合作地解决问题。留守儿童与父母不定期的亲子分离导致其情感诉求得不到满足,不利于家庭信念系统的建立,影响留守儿童对自身经验意义的积极建构;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时空上的隔离不利于家庭规范的形成或维持,影响了家庭组织的功能实现;这种时空隔离也为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带来不便,不利于良好沟通模式的形成和有效合作的产生。如此种种,都造成留守儿童家庭中保护性资源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影响其面对困境的应对功能和抗逆重组的结果。因此,在留守儿童家庭养育中,与儿童建立良好的联结感,使其虽现实留守,却依然能够获得良好的亲子沟通质量、良好的父母监管效果,形成明确的家庭规则、明晰的家庭期待、稳定的家庭安全感与归属感,最终促使他们顺利获得自我掌控感,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留守儿童的抗逆重组质量和水平。
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体验和同伴效应对适应结果影响显著。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或许学校生活中的保护性、支持性因素才是真正有效或可及的资源,尽管其影响效应低于非留守儿童。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友好互助都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依恋,有助于儿童安全感和归属感得到适当满足,而这些正好是留守家庭提供不足或不能提供的。但这种影响也存在两面性,积极学校体验的正性影响与消极体验的负性影响同等重要,甚至我们很难说出何为因何为果,但是无论其中哪个部分的改变,都能够带来其他部分相应的变化。
本研究的发现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从抗逆力理论发展的视角,对抗逆力“发展良好”这一结果的评价应该更为多元,因为文中数据可以证明,认知发展良好并不意味着心理健康的结果或者学业的发展良好,当这些结果不一致时,如何评价个体是否发展良好,抗逆力重组水平到底如何也难以定论,因此提示我们在抗逆力评估或研究中应从多角度对抗逆结果进行评估。另外在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中除了外部资源的提供之外,更应从亲子互动、同伴支持及心理关爱的角度进行服务,才能真正有助于留守儿童的成功适应和发展。
五、研究局限及展望
虽说本研究得到了一些发现,但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之处:现有研究中已经有人从留守时间的长度来探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但是在儿童不同生命周期之中,亲子分离的影响效应应该不同。如在婴儿期与抚养者安全的依恋关系建立对儿童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人际互动模式都有影响,此阶段的亲子分离从理论上讲,对儿童的适应结果应该会产生负效应,但是在青春期对儿童的独立性的训练却为其良好的社会适应有重要的支持作用。也就是说在儿童发展的不同关键期,分离效应对儿童影响应该有差异。因此后续研究中仍需从儿童生命历程的角度探索不同时期的留守对其发展结果的影响并展开细致探究。
对亲子分离与隔代养育的影响差异没有细分。亲子分离与隔代养育本是两个概念,但在本研究中没有将二者进行区分。亲子分离并不必然意味着隔代养育,亲子分离的影响与隔代养育的影响应该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因此希望在后续研究中能够基于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将留守的影响进一步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