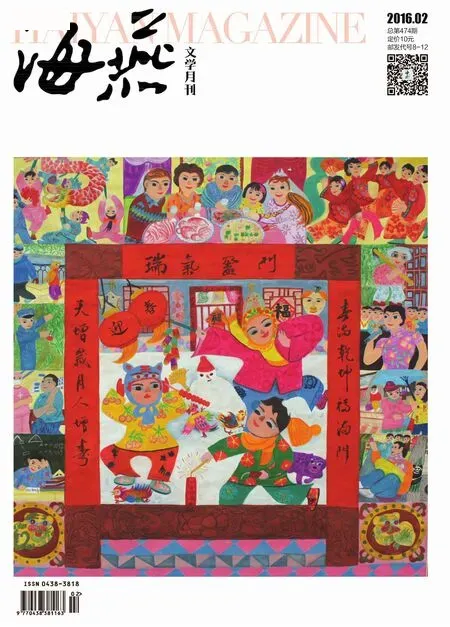麻杆儿打狼
2016-05-16祝全华
□祝全华
麻杆儿打狼
□祝全华
一
岳母给我找了个麻烦让我挺烦,可是我的性格又决定了我不可能那么麻利地把这个麻烦推掉。这个麻烦对于我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麻烦,我没有一口回绝,自己都知道是瘦驴拉硬屎。这么说吧,假如我真把这个麻烦给解决了,也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我原在国企搞政工,越干越没劲就主动离职到一些媒体打工去了,有一天没一天的。这个麻烦找上我时,我正跟一个暗访组到中原大地上的一个城市暗访,为即将到来的“3、15”“备料”。岳母打来电话,说她最好最好的一个妹妹遇到了一个天大的冤屈,让我无论如何也得帮忙。我问什么冤屈,岳母说是车祸死人没赔偿什么的,她岁数大了,说话又是那个味,我没大听明白。后来岳母说让你郭姨亲自跟你说吧,你等她电话啊。一会就来了一个陌生电话,自称“我是你郭姨”,这是一个近六十岁的女人的声音,好响亮的,底气很足的样子,说,你看咱有当记者的姑爷怎么没早用呢,早知道有你这个记者姑爷郭姨还愁啥呢,还是北京首都的大记者呢,这回我可有指望了。
记者的高帽给我一戴,我内心里立马羞愧难当。我只是做过记者,却是没有什么记者证的,只有个报社发的采访证,严格说是没有正式记者资格的。特别是眼下,我连个采访证也没有的,就是跟着别人跑跑写写罢了。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就是个纯粹的临时工。现在郭姨一口一个记者记者的,我心里自然就虚虚的了。
为什么虚呢?因为我这人特别诚实,不愿意说一句假话,我觉得说假话太累,说了一句假话。后面得用无数的假话来维护第一句假话,心累,伤身体,还是实话实说心胸坦荡。所以我坦言相告,我就是打个工,在这做点事,不是什么记者。
我本来还要解释点别的什么,郭姨却生气了,说,我跟你岳母老好老好了,这个忙你可不能不帮呀。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现在就给你下跪了,我给你磕头了啊。
我赶紧说,郭姨你别,你别这样。那边却一直在说。
你郭姨现在就给你磕了啊,我也豁上这张老脸了,现在就磕了呀,你听着噢。
在我连声喊“郭姨”的时候,电话里回应的却是几声闷响。听着确是磕头的声音,力量好大呢,没磕破吧?那么大个岁数了,这是何必呢!我心里那个难受哇!羞愧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了,我都想在电话里往回磕头了,只是没有给我恰当的机会。接下来就是郭姨的哭诉。
原来,郭姨的老伴被车撞了,医疗费花了九万多,经法院判决,费用由肇事方承担,但肇事方只给了三万就再也不理不睬了。更让郭姨难过的是,治疗两个月院后,老伴死了!郭姨本想先要了治疗费,再要死亡赔偿的,可是折腾了大半年一分钱也没得到。法院说找不到人,可是肇事方郭姨总能见到,是想见就能见到的那种情况,这就证明法院是放任不管的态度。
郭姨说,我礼也送了,送了两条中华两瓶茅台还有两千块钱呢,多了咱也送不起!可是,人家东西是收了,可就是不办事啊!
我说,那是因为对方送的比你多。
郭姨说,是呀,肇事的说了,就是把钱花给法院,我也别想得到,你说气人不?可气死我了!郭姨叹了一声,又说,我现在也累了,死亡赔偿我也不要了,我只要回我花的,这也是经过法院判了的医药费,这个钱要是要不回来,那真就要把我逼死了,所以大侄儿呀,你一定要帮帮我呀,你不能眼看着让郭姨就这么倒啦!
我这一会就成了人家大侄儿了,我安慰道,郭姨别上火呀,你放心,我会尽力想办法,只要有一点希望我就会尽力的。这是我当时的真心话,并没考虑我能不能帮忙,怎么能帮上忙。
郭姨说,我能不上火,现在知道有你我就好多了,我知道大侄儿一定能帮我,到时候我去北京看你噢,好好报答报答我大侄子。
我说你不用客气,你也不用抱太大希望,我试着办吧。
郭姨说,我是没有一点办法了,我全指望你了,你就是天啊,这回是天助我了!一会我让你妹妹把院长的姓名和电话号给你发个信儿。
看,都把我捧天上去了,又出来个妹妹,这可如何是好呢?我脑袋经过急速的转动,模模糊糊觉得,办这个事多说只有1%的希望,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是办不了这个事的,当时只是考虑到郭姨的情绪,我不好立马回绝,我怕她已经对我抱了太大的希望,我一口回绝她精神上受不了。
现在电话断了,我就反复想这个事,想到郭姨的冤屈和无助,真是感觉既同情又无能为力,既气愤又无可奈何。
郑策划问,什么事唠半天?
我说,一个老太太遇到了苦大仇深的事,让我帮忙还帮不上。
郑策划说,帮不上就不帮呗,何必苦恼自己。
另一个同事说,不是实在亲戚吧?天下的冤屈多了去了,你能管得过来?这事我也经常遇到,以为是记者就多大本事呢,咱还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我说,也是。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一直嘀咕这个事,本来已经够冤屈了的人,却还得送礼,而送礼也不是要偏得什么,只是想得到一个公平的结果——不,郭姨连接近公平的结果都没想要,她只想得到花掉的钱,死掉的人她都没心思要什么赔偿了!
这他妈的算什么事呀!还有没有天理了还?这时,那个叫善良的东西开始起劲地纵容我了,气愤也不断地给我打气,于是我就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愿意帮这个可怜的人。可是,这1%的希望在哪儿呢?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愿意帮这个可怜的人。可是,这1%的希望在哪儿呢?
苦思冥想之后,我想到了经常给我发稿的一位编辑,姓罗,在一家中字头的“时报”编副刊,一联系,这哥们倒好说话,说能报就报一下。他还强调,我们能做的只是客观地报一下,结果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谢过之后,就满心欢喜地等待了。
二
那天我们从济南飞到东北沈阳,从机场往市内去时跟出租车司机说起二人转,向司机打听刘老根大舞台在哪,票多少钱一张,司机说得二三百块钱一张票吧。我们不舍得花这钱,同来的大个儿说认识谁谁谁的,就往台里打了一通电话,找了半天人,人家还真给面子,可以免票进去了,我们到了地方一看宣传海报,最低票价只是28块钱一张,大伙就乐了,说这么便宜还到处找人,得领人家多大情啊。
演出多是瞎扯淡,搞得你既恶心又不得不笑。突然电话响了,一接是郭姨打来的,问事情办怎么样了,我说跟报社说了,现在怎么个情况我还不知道,我一会问一下告诉您。
我来到大厅侧面的走廊里,和罗编辑通上电话,他说真不好意思,报上去了,但这个选题太平常,这个忙帮不上了。我说,那你就帮帮忙,以报社名义往那边给院长打个电话吧,那边一听是北京报社的,说不定会当个事起些作用。罗编辑说,一来吧,我打电话那可就是个人行为了,这是违反纪律的。二来呢,这事不是我们部门管的事,我只是编副刊,这你是知道的。我要是个人打这个电话,说不定会捅出什么娄子呢。再说吧,单位又要分房子了,这批我可能差不多了,有了房子我也就算在北京站住脚了,我不能有一点节外生枝的事。理解吧?
听罗编辑这样一说,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这就如同我不能用台里的电话解决这个事一样,只要电话一打出,说不上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比如人家查查这个号码是什么部门的,或什么时候回打过来,说找你们领导某某某,假如正赶上我不在,接电话的人会怎么说,会怎么想,一传开,自己成了什么人?再说了,事也是不可能拿到台面上的私事,这就有假冒或招摇撞骗的嫌疑了。所以我知道,罗编辑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不能再难为人家了。赶紧谢了人家。
放下电话,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袭上心来。仅有的1%希望落空了,得怎么跟郭姨说呢?她一定对我抱着百分之百的希望呢。这个事对报社来说确实算不上稀奇事,可对一个摊上事的普通百姓来说,却是个天大的事呀,郭姨怎么能受得了呢?我的善良劲儿来了,想象着郭姨的样子,又将人心比自心,我替郭姨难过起来。我没心思再进去看二人转,就在走廊里百无聊赖地晃。
走廊里有橱窗,里面展放着赵本山及其弟子们各种姿态的照片,我扫了几眼,一个个拿五作六的,也没心思看这帮人了。
不过,有一张照片却印在我脑海中了,在我抽烟冥想的时候,这张照片时不时的在我眼前浮现出来。这张照片中,赵本山戴墨镜坐在中间,一帮弟子恭敬地围在周边,个个表情严肃,而且都穿着黑衣服,这就成功地营造出黑帮的意思了——看来他们也是故意要这效果的。我就想,我要是黑帮老大,下面哪个敢不听话?忽然间,我感觉这张照片好像给了我一丝启发或灵感,虽然一时间这灵感还细如蚕丝且飘忽不定,但我认定从中能捕捉到一点有用的东西了。我反反复复梳理着,筛选着,分辨着,最后我终于捕捉到了这灵感的魂——我完全可以用“北京”这两个字搞点名堂的。北京是首都,机构林立,高官云集,随便到哪个楼里喊一嗓子部长、主任啥的,都可能有人回应。我就以个人的名义,用手机给院长打个电话,实话实说,却不把话说透,也就是让他感觉到实中有虚,深不可测,看他怎么应对。反正成不在此一举吧,顶多也就浪费点电话费。
我知道,这个电话怎么打非常关键,第一次怎么组织语言说更是关键的关键。于是我就仔细分析院长这个人,做到知己知彼。现在有利的条件是,院长在明处,我属于在暗处,这个“仗”怎么打,主动权在我。院长40多岁,刚由区法院升到市法院当了院长,这说明他上面是有人的。而他敢收钱收物,来者不拒,甚至当事人双方的好处都敢收,谁给的好处多为谁办事,给少的可以忽略不计,说明他贪心十足又狼心狗肺。哪怕他没我想的那样不是东西,但最起码他是收了可怜的郭姨的好处的,又是钱又是物的,虽然不多,但毕竟是收了,收了就嘴短,就怕人知道,而收了却不给郭姨办事,就更不是东西,就这一点,我就在心里战胜了他。可以说,他这个院长的心态我是把握准了的——我完全可以让他把惊弓之鸟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落下一点诈骗之类的口实,实就实到家,虚就让对方雾里看花摸不着头脑。就是说,我实就实话实说,掷地有声,虚就模棱两可,真假难辨。总之是做到不落下任何把柄,日后无论怎样,自己在理上在法上都不亏,一个原则——犯法的事不做。
三
我选择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给院长打了电话。这时我们刚吃过早餐,同事正在鼓捣摄像录音设备,给电磁充电什么的,而我知道此时的院长在时间上应该不是太紧迫,精力上也应该是一天当中最充沛的时候,而且情绪上,一般也应该是不错的时候。不是有种说法吗,要找领导签字报销,得趁领导情绪最好的时候,而领导情绪最好的时候,就是上午十点左右。
电话通了,我故意压住嗓子,使声音变得缓慢而深沉,我说,你是江院长吧?我故意没用“您”,又把“你”说得很清晰,我的意思就是让他知道,我并没把他当盘什么大菜,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院长说,我是,您是——?他倒是用了“您”这个尊称,我就知道他是谨慎的,这效果就出来了。
我说,噢,我姓祝,有个事,我想知道差在哪。有个案子我一说你就知道,就是姓郭的那个老太太的案子,车祸治疗两个月后人死了的那个,听说你还帮她忙了,希望你帮忙帮到底吧,这个老太太太可怜了。
我是东北口音,我不知道有几个姓祝的在北京做大官,但我知道有一个姓祝的从东北某地调进北京没几年,官不大也不小,而且正是公检法系统的。我希望他能想到祝某某。我抱定一点:你可以以为我是什么大人物,但我决不自己声称是什么人物。并且,实实在在的假话也绝不说一句。
院长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实话实说,我和老太太以前不认识,他们托人找到我了,我是受不了老太太那一跪,所以我想打个电话问一下案子的情况。
院长说,您能把名字告诉我?
我心里出现一丝紧张,但我很快就稳定下来,说,我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太太实在是太委屈了,这你也是知道的,这个案子也拖了好久了吧,如果你感觉了结这个案子有什么难度,我可以让记者过去帮你助助威。
院长说,那倒不用,这样吧,这个案子时间是长了一点,我再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
我说,好,那就麻烦你多费点心。
我知道院长会先摸摸我的底细,然后才会考虑案子的事情,我就给郭姨打电话,让她张扬说,通过关系在北京找到硬人儿了,人家那才是大好人呢,礼都不要还给办事。我再三叮嘱,绝对不要说你和我岳母认识,更不要说我是谁谁谁,并且,以后到法院也不要再低三下四,理直气壮地要求法院尽快执行判决,甚至你都可以在法院吵吵嚷嚷,就是让他们感觉你背后有人的样子。
郭姨说,能行?
我说,就这样。
四
这天是周末,我休息。闲来没事,我到玉泉山那边去转转。
我经常往那边去的,特别是夏天,一是住的近,就在西四环那边的“舍茶棚”,距离玉泉山只有一两千米,离香山也只有几站地,抬眼可见的;二是感觉玉泉山有点神秘,总想看得明白些。
玉泉山下有一口机井,说是朱德当年打的。这里的水那才好呢,流量还大,从管子里出来流到水槽中,再顺着水槽流向那一大片稻田。当地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皇粮,专门给干部吃的。这水好到什么程度呢?在夏天里把手伸进水中,清澈透明又凉爽,捧起来喝一口,那可真是一种享受哇。所以在夏天里我总提着塑料桶到这里打水。
由于讲究养生和怕污染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里打水有时得排队,有好多人开着轿车来打水呢。遇上人多,我就先在附近转一转。
这里四周绿化极好,远远望去,除了草就是树的。玉泉山是围着高墙的,里面住的人当然是了不得的人物。你想想看,过去那是皇家人游玩居住的地方,现在没权没啥的你想进去看一眼都痴心妄想。也许是墙里面太拥挤了吧,墙外正建着大片的房屋。从那房屋的样式看,肯定不是商品房了,看上去很传统很厚重的那种。
往回走的时候,遇见一伙披麻戴孝的人站在玉泉山西门外,白衣服上写着一些字,才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好象是拆迁死了人,有一肚子苦水要找地方倒一倒,把门的军人正很耐心地劝他们离开。
我心想,上访还上这儿来了,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呢?有“高人”指点吧?据我所知,这里住的都是退下来的“老同志”。
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军警示意我走开,我便走了。这时电话响了,我一接是郭姨来的,她急急地说,这是怎么了,你没和这边说话之前还好,起码我到法院他们还客客气气的,昨天我一到法院,他们都不给我好态度了。还说我,你不是能找人吗?不是能找记者吗?能耐大了,还找北京去了,他们能办你让他们办吧,别再找我们了。
我一听就乐了,心想事成一半了。我说,郭姨,你应该这么理解,以前他们跟你客气,是知道你有理,不想惹你太生气,事却拖着不办,现在他们觉得不办有压力了,所以不高兴了,这说明起作用了。你就等待吧,隔三五天一周的,你可以到法院问问情况,腰板一定要直,别低声下气的。
郭姨还是担忧,问,这样好吗?
我说,只有这样才会有希望。一定要硬啊!一定!一定!
大约过了十来天吧,郭姨又来电话,问,法院没给你啥信啊?我昨天去了,这回都没人理我了,给我气得也不管那个了,骂了他们一通,骂也没人理,这都是怎么了?
我说郭姨先别急,我今天给院长打个电话问问,看他怎么说吧。
郭姨说好,我等你信。
我拨通江院长的电话。
江院长先说你是谁都不告诉我我怎么办,又强调这个案子是区里办的,你找区里,我不管这事。
我一听,他是想推一推,拖一拖,能不办就不办,就是办也得先跟我过几招,试试水的深浅,弄明白了我是谁再说。
我说,这个案子是你办,不是我办,我办时你还有机会办吗?我也知道案子是区里办的,是你在区里时办的吧?是不是因为你在区里案子办得好,工作出色,所以现在就升到市里了,恭喜了。
紧接着我话锋一转说,当个官不容易,当顺了,能进步了,更不容易,有机会能为老百姓做点什么就做吧,做点让人说个好的事心里踏实,你说是不是?
我打足官腔,又话里有话,努力让他感觉到上面的人得罪不起,一句话就可能断送他的政治生命。
对方说,那是那是,前一阵子事情太多,我再督促一下,会尽快有个结果。听得出,对方多多少少有些仕途不保的担忧和恐惧。
五
一晃又半个月过去了,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消息,我知道郭姨比我更焦急,但是只要郭姨不来电话追我,我就能拖就拖,这也就是人的惰性吧。说心里话,一直以来我心里总会闪出这样的念头:这事不管成不成,都要快点过去好,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同时我还必须得承认,我内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提心吊胆的隐忧的。对手毕竟是法院的,还是个院长,侦查或反侦查能力应该不低,真要搞清楚我是谁,真难说他会如何出手,起码要回钱肯定没戏了。
那天我正在写东西,电话响了,我没看就想到了郭姨。说实在的,从摊上这个麻烦事之后,电话一响我就想到郭姨,我拿起电话一看号码,果然是郭姨。这一阵子来来回回的,她的号码我已经熟悉了。
郭姨说,你说差不多了,这咋还没动静呢?急死我了。
我说,那我再追江院长一回吧。不知怎么的,这时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胜券在握了。
没想到,江院长接我电话态度比较生硬,说,最好你能过来见个面,不能过来你也应该告诉我你是谁吧,你告诉我我就办。
我知道他心里憋气,又不便发作,我能想得到他的心思:办吧,是不得不办,又没和我搞上“交情”,就是连个情也没人领;不办吧,又真怕得罪了“北京的我”,有个好歹犯不上。而他最闹心最疑惑又最憋气的是,他搞不清楚“北京的我”到底是谁,是干什么的。
我摆出有些生气的样子,急急地说,真有必要我过去吗?你真想知道我是谁吗?看来你办这个案子难度还真不小呢。好,我明天就先让记者他们过去,好好帮你助助威,我就不信我不过去这个案子就办不了了!如果记者过去还不行,那你我就一定能见个面了,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
我说话时的语气相当肯定。
江院长说,搞那么大动静干啥,好了,我尽量办吧。院长的语气明显发软,话说得又有点不甘心。我知道快有结果了。
那天中午在梅地亚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是一个自称在北京混了十多年的内蒙人请一个同事,说他们是老乡,我们都是跟着借光。八九个人只开了一瓶红酒,请客的人话比菜多,说请一年了今天才给这个机会。他这么说,应该热情张罗才对,可实际上场面清清淡淡,酒下得比打点滴还慢。这就是文明的喝法?一个个放不开的样子,看着都难受。喝酒讲究个尽兴,但是,请客的不张罗倒酒,总不能自己动手吧?人家不喝完你也不能把酒杯喝光了,就得一点一点的用嘴抿啊抿,把我难受死了,连个酒味都感觉不到,都不如吃个盒饭舒坦。我心想,还内蒙人呢,哪有这么喝酒的呀,就是白酒也没这么喝的吧,是不是纯种内蒙人都两说着。更有意思的是,喝到最后酒瓶里还剩三分之一的酒呢。
往台里走的时候,郑策划跟我说没吃好吧?我笑着说能吃好吗,就听他臭白话了。郑策划说,就是忽悠,装,撑,瘦驴拉硬屎呗,是他让多喊几个去的,咱几个真去了,他又打怵花钱了。
听郑策划这样说,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句句说我吗?自从摊上郭姨的事,我不就一直跟那个未曾谋面的院长忽悠吗?为了能让郭姨心里存留些希望,少一些委屈,我装,我撑,我瘦驴拉硬屎,心里有苦说不出,面上却装得架势好大。多亏了我跟院长不是面对面,要是跟院长面对面,我装得起来吗?人家内蒙人好歹还从容谈吐淡定喝酒呢。
恰在这时,郭姨来电话了,说钱给了!
郭姨说钱是法院出的。我说为什么是法院出钱?郭姨说,法院说找不到当事人,就法院出了,还说这也是为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不过他们给钱时让我少要点,我没干。
这帮逼人,什么东西!这话我是在心里说的,因为这样的表达面对同事或哥们啥的还行,和郭姨那么大岁数的老妇人这样说话是不妥的。我跟郭姨说,也太不要脸了,这只是你花掉的医药费,死亡赔偿都没要,这已经够忍让了,现在还要再扣除些,什么东西!
郭姨说,可不是。
我说,你应该再要要死亡赔偿。
郭姨说,累了,和他们扯不起了,这给了就行了,有你这姑爷我可省老了心了,谢谢你了大记者,抽空到北京去看你。
我说别客气,可别到北京来呀,我总出门。我压根儿不想让郭姨谢我什么,一是她没权没势,比我还底层,再一个我也没太费什么劲儿,让人家谢什么谢。
说心里话,化解了这个麻烦我内心中有极大的满足感,一时间感到非常轻松和兴奋,可是当我和别人“显摆”时,就是没人相信,说,市法院的院长,就让一个打工的搞定了?谁信呀!甚至有的同事说,说白了咱就是个打工的吧?就让你三个电话搞定了?吹吧你就。
我说,咱都知道有的骗子冒充中纪委的到处骗吧,一骗一个准儿,这怎么解释?
责任编辑 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