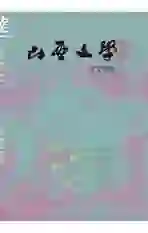吴小虫的诗
2016-05-14吴小虫
在洛阳博物馆或此时代,做一个怎样的诗人
即使时代的车轮碾我四分五裂
白的脑浆红的血肉
在漂白的变幻形式的容貌中
我——一颗心
火中有莲,水中倒映月亮
在万物中显影——
一个诗人,有忘记和隔膜
园中培土、播种、浇水
于惊蛰的虫声中
一个诗人,无法逃避的
香烛过半、月晕渐清
万物中显影,记录迟缓的光
这瞬间有我们反复的生死
难忘的事,流泪、高兴
但不要忘记为我合上眸子
我遗失在路上的鞋
在展示台前,寂静的回音
触过的光阴变成黄金
这一路的过错
大抵,还是喜欢要求别人
即使此刻的牡丹
初见还会簇叶而闭吧
我的过错在于
对方说干了,我一饮而尽
我说干了,他举杯示意
一生有许多过错
像许多朋友站在一起
阳光草坪,一截黑暗
投射到背后的水泥路面
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却没有意识到那正是伤害
前面还有路
得时时用针扎着
春日登古剑山写句
我的人生也大致已定,稍微需要修改的
就是要像个笨公鸡缓缓落地
诗人,天地之间,更要在一小块冰中
就比如登古剑山,陡峭的石阶
需要良好的体力和对山顶的眺望
你哼哧哼哧,在半路停下来脱掉外衣
这说明久蛰深冬,虚胖的人生
“春风送我上山来”,更应留意道旁风景
而非一股脑穿过古寨门,还苍蝇一样搓着手
没意义啊没意义。因为缺乏凝视
和想用体温来告诉绝望的人
所以在舍生崖边,对着锁链上的情锁
转复依靠白云,才觉神仙逍遥
爱啊,剑胆琴心
在翠翠鸭汤喝酒
暮色牵引我进入昏黄
小雪垂直落到地面消融
神的面容已经稀薄
祖先的后代风云四散
那日我坐在一群土家族中间
自酿的酒刚进口就燃烧起来
那日我和自己对着歌
鸡杂啊青菜牛肉,我醉了
座中我记住了老莽汉孙亚西
年轻时视写作为神圣
如今他只频频举杯
绝口不提那些腌臜玩意儿
座中我记住了癫哥和麻爷
少年风流中年倜傥
我听到江水拍击岩石
还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
一名叫祖国的兄长
出现在第二天夜晚的食堂
我们没有谈政治
不时将手伸向脚下的火盆
但我确实醉了,我说过什么
之后我从他们脸上寻找痕迹
癫哥说一起去看雪吧
雪,带着圣洁的律令
看天
熟悉一个地方,像熟悉一个人
从石油路轻轨站出来
就可见断臂的维纳斯
她守望着这个城市的爱与美
守望一个诗人,像一盏台灯
发出微弱的光
一个诗人也可以是一个胖子
走在人群里,穿过小巷
穿过路边的烧烤、花店
但现在我情愿在核桃壳中将自己
雕刻
过马路去龙湖时代天街享用夜晚
在陈眼镜火锅店谈论旧事
那地中海风情所给予我的
我将以剩余的生命
我将在早晨乘车去工作的地方
将不断走同一条路线
我也许会变,也许不变,但终究
不变——
一个核桃仁的奇迹
吴小虫,1984年生,山西人。曾在《诗刊》《星星》《北京文学》《诗歌月刊》《延河》《诗选刊》《都市》《山西文学》《黄河》《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组诗与随笔。
【小对话】
唐晋:为什么会有这一组诗?
吴小虫: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组诗,我也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很多事物的存在和来龙去脉。或许跟某个阶段的心境有关,我想说点什么。
唐晋:《在洛阳博物馆或此时代,做一个怎样的诗人》,这个标题很有意思。显然,诗作与参观洛博有关联,或许是某件某类型藏品打动了你。从诗中“莲”“月亮”“香烛”“光”“生死”“寂静”这些词语分析,很可能是佛像。洛博著名的藏品之一便是北魏以来至盛唐的佛造像,高古气息浓郁,纯净意蕴浩荡,对人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借助这首诗,我想你在对自身做了一番反思。
吴小虫:这首诗代表了我的一种生活状态。人,要怎么活才对得起这一生?很早我就有了宿命感,因此成为诗人是必然的道路。那年去洛阳博物馆参观,看到那些藏品,触动很大,它们似乎就是一种昭示。
唐晋:自从到了重庆华岩寺,你对自我、对身际、对一切事物的体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抄经无疑是一种功德,但我觉得你的态度似乎超越了自我的功德心、奉献心,渐渐显示出其原本如此的安定心。你自然而然将自身视于这个位置,那么,继续你的这一首诗,诗心和禅心似乎不应有如是的分别,你是如何在诗中找到禅,又在禅中圆融诗的?
吴小虫:进入寺院工作的经历消解了我很多的心念,我现在变得单调和日常,不再把自己固定在诗人这个角色上,也不再觉得诗的作用有多大。但我知道自己的心性没变,这个需要提出来。关于禅,开始我略懂,后来就不懂了,现在完全不懂。
唐晋:去年有幸在重庆与你相见。城市之大,的确令人产生许多的不适。九龙坡偏离市区,你的大部分光阴就在寺中度过。你并非自我封闭的人,在当地也有许多朋友往来。寺院中的时间与寺院外的时间不是一个概念,你将此视作修行,就我所见,你也确实过得简朴纯粹,但你肯定也怀有内心的冲突,包括对自我行为规范近乎苛求的追责。《触过的光阴变成黄金》有这样的意味,我认为它可能是较早时期的创作。你方便谈一谈吗?
吴小虫:是的,前两年写的,我太容易激动,总喜欢以自己的认识去看别人。现在明白,人是有局限的。
唐晋:除了寺中的静,你也有着动如脱兔的日子。你并且担负着搜集整理整个巴蜀地区历朝历代佛教碑碣文字的工作,时常翻山越岭,深入人迹罕至之地。《春日登古剑山写句》也许正是此种工作之余的感受所得。记得我们在寺院中有过交流。关于这些堆积如山的古文字,你又是目前极少数的解读者之一,你对人生、“舍生”乃至“春风”“爱”如今有什么“究竟”?
吴小虫:整理古碑确实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和视野,在寺里这三年同时也读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书。这个过程经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曲线变化,到最后会生出一种幻灭的感觉。生而无趣,除非一直痴在梦中。《春日登古剑山写句》是种回归吧,虽然那未必对。
唐晋:“之后我从他们脸上寻找痕迹”,我觉得这一句颇具意趣。“但我确实醉了,我说过什么”,前面这句看作由来。你比从前变得审慎,虽然依旧不变你在太原时候的酒兴与激情。你既容易被酒忘情,又不忘警惕自身的口意、口业。华严寺依山而起,绿色如染,既染既净。每天行走在寺中山道,人渐欲忘言。不言也是一种修炼,目的是不妄言。“雪,带着圣洁的律令”,是提醒人“畏心”吧?
吴小虫:老子说,惟患有身。有时被业力牵引,自己管不住自己,常常事后后悔。心存敬畏是必要的,尤其在这个虚无弥漫的当下时代。
唐晋:《看天》,冥想之作。也是总结之作。这首诗将你的生活状态展示得淋漓尽致,尽管它是“外在”的。“我也许会变,也许不变,但终究/不变——/一个核桃仁的奇迹”,这一句带着禅味。你方便解释一下吗?
吴小虫:“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生活相对。诗,作为一种对内心世界探索的介质,那么现在,我走到了我的反面。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作为一种积累和沉淀,对生命是有益的。“我也许会变/也许不变/但终究不变”,这是《金刚经》的句式,我是说,即便是外在的,宿命依然存在。
唐晋:我也经常看天。很难做到单纯地看,总是走神,想起不少人事,包括回忆自己已逝的年月。或许有刹那,我们都在看天,时空也就不以为意了。读你的诗,想起你的容颜。遥握!
吴小虫:谢谢唐晋老师。去年你们来重庆,对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深感你学识的渊博和为人的厚重。在你身上,我看到的也是博物馆藏品的品质和精神,那是立足大地又朝向天空,时空相隔交错,那是接近永恒的姿势。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