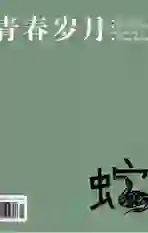艰难时期下的人性书写
2016-05-14陈佩瑶
陈佩瑶
【摘要】本文以茹志鹃1958年创作的《百合花》为主体,通过和孙犁1949年的《山地回忆》进行对比阅读,从而体会在政治语境下的文学性回归,探索特定时期下的人性书写。本文立足于文本,主要的评论方法涉及结构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
【关键词】《百合花》;《山地回忆》结构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
茹志鹃的《百合花》自诞生以来,饱受批评。这篇短篇小说带有很明显的十七年文学的烙印。与之故事相似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是孙犁《山地回忆》。二者均以表现战争时期的军民关系为主题,以男战士和女村民的关系冲突和融合来展开全文,但文章本身不涉及到爱情。
一、《百合花》背景探究
《百合花》和《山地回忆》以重大战争环境下军民关系为题材,但二者都避开了直接描写宏达的战争题材。由此我们来展开分析二者的背景。孙犁《山地回忆》中的背景中没有直接展开描写宏大战争的场面,但是作者通过了许多细节的侧面描写表现战争的残酷性。例如塑造了“我”大冬天在河水里砸破冰洗脸,“毛巾也都冻挺了”;生活习惯的改变,“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物资缺乏,“非到10月底不发袜子”;环境塑造,“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等等。究其原因,恐怕和文章本身的布置没有太大关系。孙犁在谈《荷花淀》的创作也说过,“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这种回避反而直接将人物关系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并且不时穿插的侧面描写很好烘托了气氛。
《百合花》则不然。根据1946年的中秋这一时间,“天目山人”,作者茹志鹃的籍贯(江蘇)可以基本确定这场战役是苏中战役。然而根据《江苏省志》记载,1946年9月,苏中地区基本全部沦陷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由此可以确定,茹志鹃的创作和历史不相符。再看1980年茹志鹃在《青春》上发表的《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文,我们可以判断茹志鹃所要表现的是以战争时期人性的美好,反衬斗争时期人性的丑恶。可以将其理解成“有目的”的写作,文章中的有些历史裂缝就不必斤斤计较。恐怕定在9月10日的这一天是用中秋节的团圆之意来与战争时期的生离死别形成反差,更加突出战争的残酷性。
并且,再看回《百合花》的写法,“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这一句出现在文章开头,在基调上起到了一个很明显的用意,就是弱化战争的残酷。这句话表现出的诙谐感是和战争环境乖违的。再看她对景色的描绘,也用了彩色笔调,突出了生命力,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文章还有一处直接描写战争的地方,“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同样的,在描写战争时,也极尽诗意美感的笔调削弱了战争的暴力感。在这里所表现的处处都与真实有所抵牾,但是茹志鹃是真实的参加过苏中战役的。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在军区话剧团当演员,后调到军区文工团创作组。种种的迹象表明,茹志鹃的《百合花》是为了凸显人性之美而创作的作品,收到了当时时代的制约,而一味的虚化和削弱历史背景,目的是为了更加突出人物关系。
两篇小说在规避战争环境的情况下相同,但是原因恐怕是大不一样的。
二、《百合花》的人物关系探究
在展现人物关系的方式上,《百合花》是“我”的视角间接展开的。
《百合花》中的“我”,是一个旁观者,见证的是通讯员和新媳妇为代表的军民关系。我”作为旁观者,通过我的见闻来展现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可信度较高,显得真实。在写作难度上也较大,因为“我”的存在,使得主要展示的新媳妇和通讯员的关系要突出则有所困难,弄不好就会偏离了主旨。茹志鹃在这一点上的处理是很见功力的,在故事的前半部分,通过“我”与通讯员的短暂接触,初步塑造了人物形象,提升了读者的心理预期。最后再展开了新媳妇对通讯员借被子的态度,到最后通讯员牺牲时的场面,很好的隐去了“我”的主体性,仅仅是把我当成了过渡作用。
而山地回忆是直接通过“我”来表现的。“我”是主人公,通过“我”所做所为,来展现我和姑娘的关系,直接且自然。在叙述方式上,《百合花》展现两人关系主要是顺序的方式,通过两人关系的大起大落转折,构成了文章的张力与戏剧冲突。人物关系的冲突是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冲突,因为通讯员借被子碰壁,但是这种冲突一直处于未触发的状态,是很含蓄的。要说这个冲突,仅仅算作情绪上的,之所以出现,一来被子是新娘子的嫁妆,珍贵,二来,通讯员年纪小,不太会说话。但是从故事细节处可以窥见,茹志鹃对新媳妇的情绪处理很到位,首先在“我”借被子的时候,新媳妇“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说明情绪不是抵触的。其次,“她好像故意气通讯员”反映了新媳妇的调皮,仍保有少女式的天真。加之,塑造出通讯员可爱的形象,例如“我”问他对象时,“他飞红了脸,忸怩起来”。这样,之后的大落大起不会突兀。当伤员里有已经伤得很重的通讯员时,这时的故事达到低潮,茹志鹃继续塑造着形象,通讯员是为了保护战友,自己扑在手榴弹上。随之而来的是故事的高潮,一向给人感觉爱笑的新媳妇“忸怩羞涩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擦拭着身子。最后那句气势汹汹的“是我的!”,强烈要求把自己的嫁妆——百合花图案的被子给通讯员盖好,和前面忸怩、害羞、不愿意借被子形成最强的反差。那句“是我的”自信来源绝不仅仅是所有权的自信,嫁妆的珍贵,而是感情的强烈性让读者感动也不觉得突兀。文章的余味也在于于高潮处停止,人物关系则留给我们慢慢地回味。值得玩味的是这里的新媳妇和通讯员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超一元的。在简单的军民关系下,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情愫。这里,作者所言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是不是迫于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运动还尚存疑。整个故事中,新媳妇人物的形象塑造不能得到完整合理的解释,既然是“新”,那新婚后的丈夫在哪里?文章中对此毫无交代。读者的疑惑得不到解决,尤其是茹志鹃塑造“新媳妇”是表现这个人物即有少女的调皮,又有少妇的顾全大局。然而正是少女的调皮,如“她好像故意气通讯员”,显得有些暧昧。但是作者的态度表现的很明显,既然已经是“新媳妇”,在特定语境下,则是抹杀爱情可能性的身份设置。作者为了直接斩断读者对爱情的幻想,偏向于用人物身份进行暗示。
而《山地回忆》运用的是倒叙的方式。与《百合花》不同的是,孙犁故事里的人物关系冲突是被触发,且有些尖锐的。比如女村民一开始的冲突无理,并且颇有些“辣”的语言描写,而军人也是满肚子窝火,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心平气和了下来。”其实,当村民看到军人的艰辛,军人看到了村民居住的被烧毁了几次的房屋,二者逐渐开始互相体谅,军人从一开始就是妥协的状态,在国家危难之际,小我的意气有所削弱。也正因为一开始军人处于的被动地位,使得人物的冲突性得到较好的控制。然而,虽然这篇文章也提到了没有爱情的存在。但是仍然有暧昧的分子。例如刚开始看到我洗脸的抱怨,到愿意请我去她家洗脸,到为我缝补袜子,再到陪我背枣的路上做了好的食物,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是很有力度的佐证。但是,和《百合花》异曲同工之妙之处是,《山地回忆》同样很明显的摆出立场,爱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把袜子不仅仅理解成军民关系的信物而是定情信物的话。“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的意思是女孩子愿意等到“我”打败日本人后归来。但是后来“我”打胜仗归来后,在洗澡时袜子不小心被黄河水卷走。“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直接说明了袜子作为中介的消失,也是感情的消逝。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曾经的一点点情愫只变成了可供怀恋的记忆。
三、女性主义视角
《百合花》中,茹志鹃的女性主义视角主要是从两个维度进构建的。一个是茹志鹃本人的视角,一个是新媳妇人物的塑造。茹志鹃本人,即作家视角,在选定线索上,用了图案是“百合花”的被子。对比孙犁选的“山地蓝”的布,这一线索诗意化程度更高,象征性更强,更加体现了女性审美的维度。而且,“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还有把百合花被子盖在了通讯员的身上,这些细节符合了一个女性作家某些完美主义强迫性的特点。第二层则是在塑造新媳妇的形象上,因为新媳妇既含有了少妇的顾全大局,又有少女的天真赌气的描写,体现了女性的身份特点。还有对新媳妇的外貌描写,体现了传统东方女性的外貌形象。而“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
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这几处则体现了中国传统妇女的羞涩与含蓄的性格特点。《山地回忆》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与《百合花》则有很大不同。首先,《山地回忆》中不涉及妇女的外貌描写,尽量淡化以男性看女性的眼光,着重凸显性格特征。其次,孙犁所描写的这个女村民,实际上是很多个农村女孩集合式展现,她们中既有泼辣的,也有关心的。最后,值得玩味的是女村民的态度,尽管在往逐步谅解,关心军人的方向发展,但自始至终女子的关心、关切都在是装作漠不关心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仍然是任性式的泼辣的语言。这种心理体现在女子本身的性别和性格豪爽的冲突,也在于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很多女子越想掩饰的关心,拐弯抹角的技巧都拙劣的不合逻辑,但却正是小女孩式的心理。这一点上的表现,足见孙犁揣摩人物心思的功底。
《百合花》和《山地回忆》直到今天,也是当代文学中的经典短篇小说,尽管遭受过猛烈的批评,我们也应看到哪些问题是作者或作品受到了时代的制约,在特定政治语境下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哪些是自身的问题。在逐步探究的过程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两篇短篇小说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还尝试着艰难的人性书写,并且书写较为到位,此可鉴之。
【参考文献】
[1] 茹志鹃: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M]. 《青春》,1980年11月号.
[2] 茹志鹃. 百合花[J]. 人民文学, 1958,6.
[3] 孙 犁. 白洋淀纪事[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4] 茅 盾.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M]. 作家出版社, 1958(6).
[5] 苏泽民. 江苏省志[M].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6] 孙绍振. 以进攻中的姿态表现军民之间的深厚感情——读《山地回忆》[J]. 语文建设, 2007(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