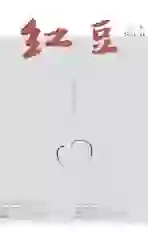或者因为是白天,或者因为是夜晚
2016-05-14许含章
许含章,毕业于安徽建筑工程大学设计专业,曾为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现为《清明》杂志社编辑。
从我家阳台往楼下看,通往大路的小巷里有十二盏灯,加上两盏不亮的,一共是十四盏。
如果你抬起头来看天,一颗星星也没有。
我记起我去过的一个地方叫陈村。
那里有条河,河的上游建了水库,陈村是水库的名字。
河从村子中间直穿而过,两岸住着人家。一岸是平地,住的人多些;一岸是山地,只有星点的几户。村里的人出行大都靠船,因为无论去哪里,第一站总是河下游的县城。去县城步行需要一个小时,划船可以节省一半时间。
我在几年前的这个时间里,坐过一个陌生人的船。
我们在岸边沿河而行,他从河上顺流而下,我于是就在岸边喊:“让我们搭你的船吧,付钱给你!”
他慢慢地把船靠岸。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笑着说:“行啊——行。”
“给你多少钱好呢?”
“看着给呗。”
小小的船,像是古画上的一叶扁舟,只可以坐四个人。坐进去就不敢动了,因为一动,河水就好像要漫进来。
于是我们拘谨地坐着这诗意的小船,去往下游的县城。舟子似乎也并不划船,由水流而下,顺势便可到达。
船行河中,陈村就从身边流过。一岸是磊磊怪石,上有峰峦;一岸是掩映在林中的人家,绵延不断。
间或能闻到桂花的暗香。
此情此景,如果我是站在岸边的人,会觉得那村民该唱首渔歌才好。但他并没有唱歌的意思,只是始终在船尾,撑着一根竹竿。
他一直很憨厚地笑。
“要是往回走,就累一点……每天要划船接送女儿。”
“女儿多大啦?”
“小呢,在县里上幼儿园。”
我们坐着他的船去县城,而后又去他的家里吃饭。吃到了真正的农家菜,刚从河里捞上的小鱼,加点姜丝酱油蒸一蒸,除了鲜味,没有别的味道。一开始是有点吃不惯的,总感觉有点少油没盐。男主人还特意去卤菜店买了板鸭,炒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清炒萝卜丝,爽,鲜。
后来给了多少钱也忘记了,只记得我和妈妈去小卖部,给他上幼儿园的女儿,买了一箱牛奶。
这个人姓什么也不知道,当时应该是问过的吧,过后也就不记得了。
不过他既然是陈村人,那么多半该姓陈。他家的厨房很干净,给钱的时候,他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这是一个好人。
后来我们又到河的上游去看水库。水库像是水泥砌成的变形金刚,巨大而冰冷,实在没什么好看。
水库下面也不好看,岸旁没有人家,没有桂花树,只有一片河滩,上面长着蓬蓬的芦苇。那芦苇非常高,颜色又非常白。起风的时候,它们银白的穗齐齐向一边倒去,因为风大,我担心它们会被折断。
这就是诗经里说的“蒹葭”。
其实与我想象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蒹葭完全不同,它们看起来像是没有生命,那苍苍茫茫的灰色,枯草一样遍布暗黄的河滩。
可是我知道,它们是有生命的。
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些凄凉。
陈村的夜,重的不只是颜色。
宾馆前面唯一的一条道路,是夜的分界线。你跨过路旁的两排路灯,黑暗就齐刷刷地把世界切成了两半。浓黑压下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打开手电,一道圆形的光柱穿透黑夜,亮与暗之间,也被齐刷刷地分割开来。
没有微亮,没有余光。手电筒的光,好像手术刀一样,锋利又冰冷地把夜划开一道口子,仿佛能听到“唰”的一声响。
于是我把手电关了,让夜依旧完好如初。
依旧完好的夜,会流血吗?
夜不流血,但不代表夜不活着。沉重、压抑、无尽的黑色,好像要拨开眼前的浓黑,才能够往前走一步。伸手出去,你看不见自己的手指,却能听到夜的呼吸。
这夜色令人窒息。
还好,对岸山上,有人家亮着灯火。
然而我并不打算涉过河去,去陌生的人家寻找光亮。
那光亮与我无涉。
这里的白天和黑夜,就这样齐刷刷被切开了。
它们是夜晚,还是白天?
或者是,或者不是;或者因为是白天,或者因为是夜晚。
而现在,现在是早晨六点,我家楼下的小巷里,十四盏灯全部熄灭了。
天上依旧看不见星星。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刚刚过去的夜晚,想起了几年前的陈村,在看惯了的万家灯火里,突然想起那晚的黑暗。
触目的黑夜没有生命,所以并不让人觉得恐惧;所以遍地灯火,也不让人感觉温暖。绝望之为虚妄,就如希望,我只怀念那位陈姓或者并非姓陈的朋友,和我搭过的那艘小船。
责任编辑 宁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