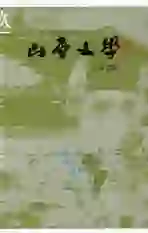痴迷者的迟缓
2016-05-14闫文盛
余绪
我种下的第一茬麦子已经收割完成,现在,大地上一片丰收后的荒芜。
我种下的第一批人类现在已经进化完成,在那茫茫空际,我看到了他们的独立思绪。
他们已经越出了我的范畴,在我们可以共同进行的思考当中,他们是独立的,倔强的,善恶不分的种子。我想在新的理想国中将他们重新栽种。我希望重新做一次尝试。
现在,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不再崇尚做一些没有个性的人。我不希望看到的那种思想的忧愁和我在设计之初最最憎恶的那种平庸的忧愁何其类似。
他们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
他们在最初越出我的范畴之时,我并不在意。但现在,我不能不慎重地对待这最新的发现。他们的智力现在已经发展到顶峰。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野心像奔泻万里的银河瀑布。
我并不欣赏他们的邪恶智力。
现在,说出这些已经毫无意义,就像任何标榜和伪造的谦逊都毫无意义。我反对这样的虚无。
宇宙最初以很久远的时间来酝酿和生成一些征兆,但我难以记忆这个过程。我只是在漫漫太空中用尽了我的思想去做一个孤独的神,这样的光阴已经太久了。
那些麦子在丰收之后,他们点燃了遗留在田垄中的无数根茎,这是由他们自己发明的火源和火种。
我不喜欢烈焰扑空。是那些火红的事物加速了我的警觉。我的思绪并无人知情。
但是,我从未在他们的视野中出现过。在那些白云和高远的时空之中,我精心地度过了属于我的那些无边空旷和黑暗,我无须收获,但大潜流和汹涌的泡沫状物质始终跟从。
我的孩子们,他们早已代代更新。我注视着这亘古未有的奇迹。
是的,我不相信人类。我一直在犹豫。
那些人类的全体,那些期待我善加注目的弱者始终没有逃出命运的束缚,但我没有给他们套上任何枷锁,是他们自己在作茧自缚。那些制造悲剧者都不认同。他们只是在互相诅咒之中度过了一生。我一直没有同情过他们。
这任何可能都不会存在的实质性幻想是我游荡在太空的全部价值。
我并不慎重。
在一些流动的物质之中,我埋下了假想之永恒。
但是一些极端时间依然难以解除,比如,那些生命中的黑暗物质,他们会自行繁衍。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绝对地控制他们。有时候我会对这样的思考失去耐心。
我并不希望那些我看到过的大陆沉沦。
我不喜欢而且也觉得任何极端行径都毫无意义。尽管,在那些只手撑穹天的时间之中,出于一时新奇,我还进行了许多高低起落的试验。但的确毫无意义,生死存亡都不新鲜。
人类制造了他们自己的法则,但他们始终难以遵循全部。
他们如同任何事物一样率性。
这一切都非我所愿。
但一切理想皆已不存。那种深植在我心中的流浪之感难以解除。
我无法凝视任何事物,多少思绪都如浮云。
他们难以静定。
我需要十分小心。
但这是公开的秘密,他们总是在坚定地侵袭,直到最终的粉碎来临。
我早已打坏了祭坛,但我不能封闭他们的感官,否则,那天地大还原之神也无法借力。
他们是我惺惺相惜并且一直抵制的同类。
我无法彻底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所以,他们蔑视我的情绪。
所以,他们视我为诗人,视我为苍穹,视我为怪异但并不值得敬畏的主宰。
但我始终在此,在彼,他们并不知情。
说出这些并无意义。
他们早已长大成人,他们不是新鲜的幼子。
他们的繁复思绪,那些研究者并无法窥其万一,但这确实是不幸的。
“像上帝创造了人类。”
“像宇宙生成。”
“像你我之存灭与死生。”
天地如卵,一派蓝光。
夜色中的光
黑夜蒙昧,黯淡。夜色密布四方。那似穹窿的事物都在成长。
我们龟缩和藏匿的地方已经乱得不能再乱,那些小麻烦都在成长。
我们从誓言中逃离,但一切思想都无意义。那些雨水,敲打着窗棂;是的,我们总是能看到夜的尸体,它一天接一天地埋葬我们“虚无的内心”。
我们无法确定的那些指数,早已不被认同。
它们被新的概念取代,那些增生物都已变得浮动,玄虚而高耸。
我们看到造影子的人。那身体的幻想之光笼罩了夜的黑暗。
这只是我们寄居之地,所有的夜都不包容。所有的夜都色彩杂乱。
我们谙熟它们广阔的过去,那些叶子被置于我们的心头,它们在渐渐地变轻,飘落,像一个人的逝去,身体坠如星辰,灵魂潜返大地。
它们的轻与重,都难以辨别。
那夜色中的陌生人,发不出高声。
到处是隐秘而盲目的夜晚,我们处于此地,每一夜都会有蹊跷事情发生。
但是,所有的暗物质都在成长。它们要取代那些不够稳定和坚实的部分。
我们要取代那些陌生人。他们的灵魂,早已混入我们人类,被涂上厚厚的泥土。一切都可以互换,无情地离别,抖动,怅然如昨,又新鲜如初。
不,这终结性的一幕并未发生。
战争并未发生。
但我们从无常态性的安定时日,那些夜色,它们制造着表面的淡泊。那些寂静的,灰突突的事物,它们自我种植。
我已经慢慢地使自己远离一切幻象。
但这高悬空际的生活难有凭借,我依托的一些人早已故去。他们作为指引者的角色无法久存。
我们从未有踏踏实实的恒定的人生。这些年来,被我们主观地或客观性地改变的事物太多。
夜色如昨。一切都未有大错。
是的,敏感的人,总是对痛苦体验的程度更深。
我们看到的人心的变化莫测。那些我们仍然看不清的部分,它们都在悄然长成。
夜色,它无法容纳全部。总有一些破壳而出的事物,它们以艳丽的光束刺破天幕。
它们是夜晚新的构成。
那些强烈的无法诉说的事物,是我们寂寞生活的全部见证。作为心怀空洞的人,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出口。我们或许可以自我包容。
那些人类,他们的命运总是比我们所经历的更为深沉。
我们无法识别,所以几无认同。
这个世界,总是看起来如此陌生。
一切都无关大碍。好吧,夜色散去。
那光在升起。
但新的意义尚未诞生。如你所见,这夜色余荫未了。
那些局部区域,总是阴晴不定。
我们都无见识,步履零乱,如蹉跎时日。
是啊,我们都不安于任何朴素的事物。
种种变异都在发生。
我们都不是自己人。
迟缓者的痴迷
我总是如此记录:那些苍茫之日,虚汗淋漓,空虚的内心和朴素的生活。
那些街区,那些流浪者,那些不安定的命运。
那些战争。那些迟缓者的痴迷。那些阴云和秋季的雨水。
我总是如此记录:可生命并无任何过错。
他们过着最为简单的生活,他们总是过着最为简单的生活。
我们看到了无数过客,那些梦境和制造梦境的僧人,那些诗歌艺术家和沉迷于物质世界的陌生人。我熟悉他们的生活,甚于熟悉我所经历的生活。
我总是无法凝聚。
我无法使那些潜在的事物显形,我无法使自己变得像那些已经慢下来的人。
他们并非我们的全部。我并非任何人的替身。
不错,我正在经历那些我尚未开掘的部分。
这一切挣扎,使我经历的这一日变得沉重。
我们厌倦了离弃自身和陌生人的生活,那些远遁者,并非我们惟一的救赎。
当然,我从来没有使自己的看法变得更加纯粹和成熟一些。
就像我那些迷离而纷繁的梦境,它们从不曾由我掌控。
我领略过那种忧愁:那些迟缓者的生活。
是的,你,我,我们任何人都不懂得。我们的借口并不充分。
我们并不能仅仅为刻苦地活下去而找到任何一种理由,他们,那些僧人,他们同样诞生于这个忙乱的尘世。他们建造了一个宗教主义者的寓言。
我们长途跋涉,抵达了他们曾经栖息的那些聚落。
在那陡峭的山壁之间,我们同样在镌刻:那些迟缓者的记录。
他们到底有没有内心剧烈的冲突,他们到底有没有与我们相似的生活?
在我们日复一日的苍茫内心之中,并没有任何经卷可以解决任何问题。那些虚拟的部分,已经缓慢地流逝。
一个迟缓主义者的记录:他无法自足的生活。
他并非书写者,爱生命的俗客,强烈地追求名誉的人。
他并非自我。
一个迟缓地迎来送往的人,在岁月之中,他活得并不从容。
这并非全部的表象。
他活得并不从容。
有时,他是在与阳光的博弈之中发现了生命的秘诀,他抢在光阴黯淡之前来到了此处。
那些柏木森森的风景,与他的心境暗合。
这庞大的,纷杂的语言,印证了这二十年来他所看到的部分。那些歪斜马路,已经被重新改造。在他记忆的虚像之中,那些过路人都不慎重。
他看到了故土,那些飞扬的灰尘早已被湮没……
他并不客观。
他只是伪造的自然。
在无限的迟缓之中,他并不陌生。
是的,“他赢得了战争”。
痴迷者的迟缓
那些事物,我总是想写下的;那些曙光,我早已在忘却的;那些激情,我早已将之泡沫化的;那些生活,我们迟缓地沉浸并且获得的;总之,那些,一切有待于被记录的,在这个早晨,早已丢失和沦丧了;我只是出于一种虚无主义者的本能在凭窗远眺;我根本无法看清更远的地方;我根本无法看清更远的事物;在这个时代,一切遮挡物都如迷雾;它们,一切被我蔑视的,一切被我尊崇的事物,都在渐渐地丢失和沦丧;我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本能也在减退,消逝;我出于对人类的爱而痛苦的时光也成了最为稀缺的背景;这是我们无法将之驱散的时光但它渐渐黯淡。
这是我们无法将之驱散的时光但它渐渐黯淡;并没有一种法则可以改变我们的获得;我们寄望的那种生活永远不会到来;在人心的顶点,也许这才是一个永恒的寓言;也许,一切完美的事物即是永恒;一切消逝和不存在物方是永恒;这是我们人心所难以洞察的宇宙。
这是我们人心所难以洞察的宇宙;在我们毕生所走过的路途中,并没有一种事物已经抵达了完美;并没有一种事物彻底消逝不存;并没有一种事物是真正迟缓的如同凝滞不动的时光;只是,它们如同化石一般凝固的形象进入了一切艺术;它们无法凝滞不动,那些源流不息的色彩之变被岁月磨蚀,变成了人心的疮孔;而这种难以抵达的事物激起的新变被一个个崭新的时代所磨灭;在一切难以完成的寓言学中,就酝酿着,构建着这样的可能;是的,有时爱是单一的艺术,但它充满了复杂的变异的可能。
这是我们始终难以信服的复杂之处;在爱的变异之中,我们仍然相信它是单一的艺术;因为那些维系我们之间联络的激情,它们仍如单纯的婴儿;在泡沫化泛滥之前的那些时代,整个世界一片洁白;我深信这种痴迷者的生活笼罩了我而立之前的全部时光;我深信生命如若重新来过,我们仍然晶莹,纯洁如婴儿;在一切破败,混乱者的内心,充斥着一种黯黑的艺术;在一切充满了机巧者的内心,密布着我们所难以解析的艺术;在一切地狱般的内心,充满了灵光一现的光明;在一切高尚的明亮的内心,充满了生命本体那无法复制和还原的乌黑的背景;我们从来没有一种时候,可以令思维趋向于停顿;在那样一种痴迷者的迟缓的体验之中,山林在潺湲度日,它们是我们最为可能的收获。
在一切体验日,痴迷者在潺湲度日,他们是我们最后的堡垒;我们以自己的力量攻克了第一个阶段的内心宇宙;但它们在继续裂变,孳生,发展得更多,更复杂和无望;迄今我只是在表达一种过时的激情;我的匠心所至,只是泥,牛,马,羊和内心的伤悲无数;但这仍不是全部,我无法表述的事物,它们一味地沉默;它们只是“迟缓者的艺术”。
读诗的可能
诗歌是精神生活的有效补充。但我的感觉并不完整。我总在诗歌中试图读出某种温柔的可能,我总在诗歌中试图找到某种阅读的可能,但我始终没有完成。我的寻找并不彻底。对于人间诸事,我仍然没有看清。我相信是他们先发现了自己。
我曾经很主观地准备离弃他们。
诗歌是某种遗憾之事的有效补充。
而在技艺并不成熟的诗中,一些常见的疏漏总在发生。或许,她的表述并非不生动,但绝不充分(口齿不清),更不精准(语义含混,语感常有断裂),我们以此可以窥见这个初学者的内心。她焦躁地看着我们。
每一个字词看起来都无大错,每一个句子都近于急切生分,它们共同记录了她的悲哀。这是我们之阅读尚需止住或重新开始的见证。读这样的诗句,我总有下笔修改的冲动。
我在寻找一种温柔的可能。那些莫须有的斗殴和负重,是她们迷离目光中的神兽。
诗歌以赞美辞般的魔法引诱她们。
我总在寻找读诗的可能。
我们的生活本身并不奇特。它们毫无特色,更谈不上丝毫艺术。
只有死亡和寂静是残忍和美的,它们以近于完整的诗歌面目呈现。只有彼此交融充满了隔阂,它们以近于古怪的生活面目呈现。反复之间,我只看到了饥饿本身的纹理从容。
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已经苍老,气喘,身肩巨负。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尚且不是诗人。我们相识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寻找“读诗的可能”。她从我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取材,写成练习诗篇,张贴于众目的审视之中。我们相识的时候,我尚且没有深入到生活的压迫之中。
诗歌使我们变成众人。在彼此的窥探中,这世界如旋转的木马。我们在奔走之时试图隐身,变成另一个人,另另一个人,但从未成功。她仍然苍老,气喘,身肩巨负。
我总在寻找读诗的可能。
在嘈杂的日子里俯瞰鸟群,那鸟群替代了天空,我们总在担忧中茫然顾盼。高处的居所中储满了风声。
我们总在寻找并制造着读诗的可能。有时是一整个下午,有时是清新的早晨,有时是在远游的途中,有时是在梦境的反光镜中。
我常常会回忆“那些梦中道路”。
我常常对一切都不服从。
诗歌预示着另一种可能。
我们并不总是如此主动。
有时夜里心事冗沉,我会想到那些从未接触诗的时辰。我会想起我的老祖母。她令我念诵赞美诗的时辰早已不被歌颂。我的忘却之路充满了另一种可能。
我已很少主动。
岁月一天天将锈蚀的灯罩笼上我的脸。
暗夜里并无揪心诗篇。
我已经过得平静,自重,如同一个庸人。
我毫无读诗的可能。
刻意的旅行
河水上涨,桥梁已被冲断,垮塌。
时间一直在随意地旅行着,在拘谨地旅行着,在沉重地旅行着,那水草如同烟雾般弥漫。那雷雨中的黑暗如同岁月般弥漫。那表意的符号如同痛彻心肺的记忆般弥漫。
那次我们相爱的过程异常短暂。只是有些刹那,我们动用了自己最敏锐的感官。我们丢掉了一切物体,神思和匠心,我们丢掉了一切土地,树木和赖以容身的器具。那根本性的追击不会起作用,在那些异常卑微、平淡的事物之中,埋藏着我们不死的神灵。有时,我们张大的翅羽能覆盖整个天空。
能埋没整个天空。
旅行者偶尔会忘却他的一切。
但我必须借助整个天空来表达,借助整个宇宙来表达,借助那茫然中所受的困阻来表达。
我必须借助旅行来印证我的未知世界。我不喜欢的那些时空,它们在微风中悄然抖动。我不喜欢的那些事物,它们张扬夺目。在那些无人居住的星球,空气和水是我们的旅途书。
我必须借助莫须有的事物来寻求抵达。我貌似刻苦地活着。
书籍已尽数被毁弃,死去的人从未复活。那树木间的大风波,使我想起了幼年所居的古村落。在一种完全不合法的生活中,我们成为劳作者的反衬,在里巷中冲突,但时间毫无法则,它随意地运行着,将那陈腐之物撒遍了我们的视野。
写作只是一种自造光阴。
那些人,他们只是熙熙攘攘地活着。
我虚构出了分裂的思绪,它们像难以凝聚成型的蒸汽飘散在空气中。
在一种旅行和一种错误之中,我看见了无数面孔,那些游弋于灵魂和重物之间的众人,他们貌似刻苦地活着。
“不,他们活得不错,日夜间寻欢作乐。”
一种古已有之的怜悯,使我们浑若满怀同情的观者。
但是,“单纯的书写毫无特色”。
我制作了一些对话录,有关梦境,推理和意图的学说。有关解析的学说。有关破碎和消散的学说。有关旅行的学说。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有关“大”的学说。最后,我将自己完全吞没。我迷恋于一种失败和困苦的学说。
但我们之中,没有真正的刻意之人。
没有真正独立的系统和风格。
没有道德和自我。
没有食欲和真正的诗情。
没有任何颜色。
只是旅行者常被自己诱惑,类如我们被自己完全吞没。
“我们毫无特色。”
在那漫长的岁月背后,那些最终因恐惧而疯狂的亲人们与我们并列存在。
“他们毫无特色,只是那刻意构筑的桥梁已经垮塌。”
我们只是生活的泡沫,就像那些幻觉的碎片被置于“人世的风险”之中。
只是貌似刻意地活着,但我们并无任何借口。
我们就像被“看到”的无数面孔。
那些旅人经过,始终喋喋不休。
“是啊,这都是被破坏的部分。”
“与我们大体相似。”
“与我们完全不同。”
闫文盛,1978年生。迄今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作品300万字,并入选100余种文学选本。主要著作:《失踪者的旅行》《你往哪里去》《在危崖上》《主观书》《主观书:为燃烧的烈火》《主观书:痴迷者的迟缓》《沉醉的迷途》等。现为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