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郡主,猛于虎(七)
2016-05-12君素
君素
上期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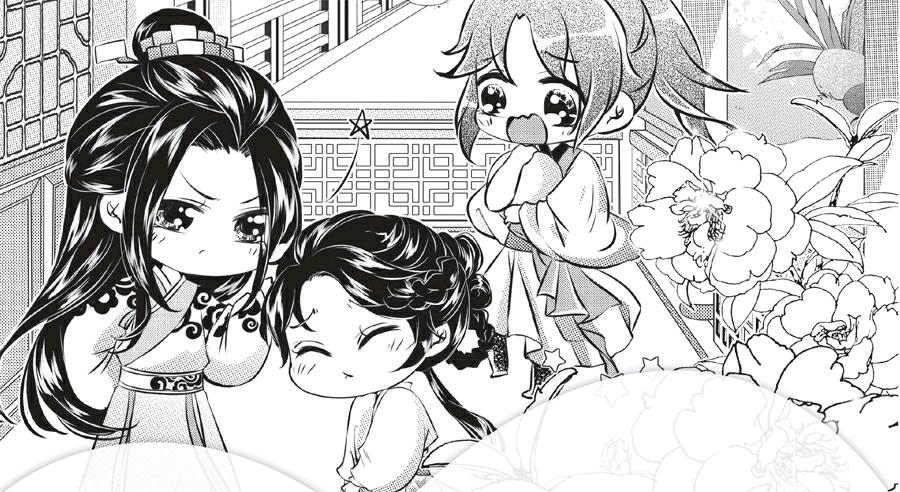
如此过了两个年关,我与辛沭一同到了漠北。
此处是北曌与大燕交界之地,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通常要隔上七八十里路,才会有一处村头。
日暮时分,我趴在一方小沙丘下。前方三十丈开外,一名白衣女子手里拿着生肉,正喂着一群野狼。
我盯着她,双目放光,嗑着瓜子:“不知为何,刚才看见她的那一瞬,我总觉得膝盖一软,很想跪下喊娘。”
“……”
“我相信,这一定是上天注定的缘分。茫茫大漠里,竟让我遇见了她。”
辛沭面无表情的觑着远处,拆台道:“上个村头你看见那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人时,说的也是这两句。”
我无语,扭头剜了他一眼:“兔崽子,敢和为师顶嘴!”
他保持着淡定,继续道:“这个女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
我摸摸下巴:“这才说明她内涵过人!不像我这样靠脸吃饭。”
辛沭表情略纠结,看我一眼,嗤之以鼻。
我哼唧道:“等会儿依计行事,为师去下聘,你留在这里画她的画像。”
辛沭默了默,认真问:“前辈,你的小叔是不是有什么隐疾,让你一路走来已经下了三百多家的聘,连这种类型的都不放过?”
我也认真思考了一下,答曰:“我小叔的确有隐疾,病症就叫看见我不按三餐抽就手痒。”
“……”
“我这一走好几年,难保哪天回去被他逮个正着还有没有命。我一直怀疑我小叔脾气那么暴躁就是因为没有娶妻无法泻火,再加上更年期已至。所以,这回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他娶一房,让他为我苏家延续香火,毕竟这事我已经无能为力,只能靠他了!”
片刻后,辛沭啐道:“怕被打死就直说,当个媒婆还那么多借口。”
我心窝子狠狠中了一箭,泪流满面,我反思当初为何要救下这个大逆不道的兔崽子。
深吸几口气,我调整好心绪,将纸笔交给了他,再整整胸前衣襟,把缠着封条的重剑往背上一抡,昂首阔步地走下了沙丘。
放目四望,大漠落日圆,一线残红如血。远处一座孤零零的房屋顶上,冒出袅袅炊烟。女人的左侧,还有一方以无数砖块砌成的乱石堆,不知是什么含义。
我走至盆地中央,本在用食的狼群嗅到生人气味,赫然扭头,张开血盆大口朝我低鸣。我停下步伐,见女人很有些心如止水的高人风范,心头更有了三分欣赏。
我取下重剑,往地面一杵,霎时尘沙飞扬,威势骇人。狼群见状,悄然往女人身后退了退,不稍须臾,便由头狼领着,一溜烟得撤退了。
我捋捋额前呆毛,这才不急不缓地问:“姑娘如何称呼?”
女人不答话,只是从散乱的发丝间隙,露出了一缕凌厉的目色。
我站直身子任她看,又问:“姑娘可曾婚嫁?”
她收回视线,默默回身。
我跟上去,一只手拖着剑,一只手往她跟前晃晃:“是这样的,我家有一叔叔,正当壮年,长相是风华绝代、天下无双。他脾气好,能动手绝不吵吵;人品好,说打断你两根肋骨绝不对第三根下手;武功也好,几乎没人干得过他;名声更好,话本子里几乎天天更新他的故事,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隔几天就要回天庭陪玉帝吃饭。”
女人背影僵了僵。
我锲而不舍地比画:“所以,若是姑娘未婚嫁,我家小叔正需要您这样一位不修边幅、超脱世俗、内涵丰富,还极具爱心的女子为妻,不知你是否愿意考虑?”
十八分之一炷香后。
女人袖口一晃,然后扔了手里的肉。观其臂力,应是不小。这么随随便便一丢,肉就越过了两个山头……
旋即,她又拍拍手,往乱石堆走去。
我咽了口口水,本着做媒做到底的决心,一路跟着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刚想搬出我家镇国府的名声来威震她,忽然,我觑见乱石堆的另一面,竟是一块无名墓碑。
我愣了愣,摸着鼻子道:“难怪不说话,原来是个寡妇啊。”
周遭莫名其妙的劲风一拂,有点儿寒意。
我又道:“唉,这么年轻就死了丈夫,估计你是克夫命,着实不妙。”
耳畔,一声骨关节脆响。
我做了一辑,顺便留下一锭金子:“拿去修葺修葺这座孤坟吧,夫人,打扰了。告辞。”
话刚说完,我冲着沙丘上挥手,一句“别画了,这厮是个寡妇,我小叔肯定不喜欢二手的”说辞将将脱口,我突觉背上一阵剧痛,还来不及反应,就壮烈地摔了个脸朝地。
……
待我回过神来,重剑解封,大有横扫千军之势。
此战起得突然,我和女人都各自有所留手,意在先探对方能为。她起初还是赤拳与我过了数十招,然后目光愈发讶异,一柄软体长刀自腰间一抽,明晃晃地现于绯霞之下,青光凛冽,刀锋饮血。
我一惊,不敢大意,流萤逐月三式上手。然则,她的刀法却是快得不及眨眼,刀影成花,难以破解。我不过与她对了四十式有余,便立刻落了下风。
她沉声问:“你之剑法,师承何处!”
我打了个哈哈:“洒家的剑法百家相传,不知夫人问的是哪一门?”此话绝对良心。毕竟启我入武道之人是慕渊。他的方法便是让我多看各种武学,集百家所长。后来小叔亲身教导我,我又融会贯通了一些小叔的独特招式。这会儿她问起来,我也不知该回哪个人的名号。
还在专心应对之际,女人凶狠一刀劈下,我硬接不住,虎口顿裂,鲜血长流,一时剑尖杵地,半跪了下去。辛沭见状,拔剑欲加入战局,被我厉声阻止。
女人又问:“苏衍青与你是何关系?!”
我一恍神。
哦,原来她是小叔的旧相好。我敛下武息,特别真诚地笑道:“苏衍青就是我小叔,也就是刚刚我与夫人要说媒的那位。夫人可是认识我小叔?关系好不好?有没有一腿?你家死去的相公知道吗……哎哟!”
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
七、死鬼,你的性向还正常吗?
我从昏迷中悠悠醒转的时候,辛沭正端了一碗汤从门外走进来。我茫然地四下望了望,但见身处的屋内陈设简朴,无非一床一桌椅,再看天花板,是黄土颜色,连丝毫的装饰都无。
辛沭吹凉浓汤,往我跟前递进半分,道:“喝了。”
我发呆。
他又道:“起来喝汤。”
我继续发呆。
小兔崽子皱了眉:“是不是被打傻了?”
我瞪他一眼,重新看回天花板,疑惑不解:“好端端的,她和我小叔也是旧相识,怎么一上来就动手?难道我小叔曾经负过她?”
“不像。”辛沭面无表情地接话,“真那样,应该趁你晕,要你命,不会把你像拖死狗一样拖回来。”
我哽了一哽:“那,此事说不通啊。毕竟洒家长得这么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老少通杀,没道理会有例外。”
“……”
辛沭冷静地放下碗,准备起身,被我单手一摁,才不情不愿地坐回原处。
“是你嘴太贱,自己找抽。”
我捂住胸口,酸涩凄然道:“有徒如此,不如去死。”
小兔崽子也不安慰我,仍然执拗地把汤碗递到我手里,再次重复:“喝了。”
我闻了闻,问:“什么汤?”
“滋补壮阳治肾亏的,你敢不敢……”
他话还没说完,我仰头一口灌了下去。
“……”
末了我舔舔嘴,双眼放光,道:“还有没有?给为师盛个十碗八碗,放在边上凉着,等会儿回来好漱口。”
话音未落,我跳下床操起重剑。辛沭跟着我站起来,冷冷道:“这么快又去找死?”
我:“难得有高手过招,不打个天昏地暗,骨头缝里都发痒。爱徒,你就在屋里等为师凯旋,与你好生庆祝。”我豪迈地甩了甩头发,摆出一个帅裂苍穹的姿势来。
辛沭不忍看,只道:“你确定不是让我给你收尸?”
“我去!你这个逆子!”
我踏出房门,正值大漠里风沙骤起,茫茫之势遮天蔽地。红似火烧的日头悬在半空,周围乌云涌动。女人手执着扫帚,正在打扫孤坟。尘埃去而复来,根本扫之不尽。
许是听到身后脚步声渐近,她道:“苏衍青就这等本事,将你教得如此?”
我感觉被嘲讽了一脸,很不幸福。
涉及武学源宗,师承之意,我不愿多言。重剑立地,风沙卷起长衣飒飒,碎石四溅间,我扬手起招,认真道:“无须多言。智慧与美貌并存,狭义与大胸的化身,苏愉悦,在此请招!”
“……”
女人不知是用什么样复杂的表情面对了我半晌,继而缓缓横起扫帚,冷颜以待。
我:“别开玩笑了,洒家习武近十年,自问拥有以一敌百,拯救凡间的能力,剑式一流,步法风骚,你要用一根扫帚都能赢我,我立刻喊你亲娘!”
于是,五炷香的时间后,我跪在地上,表情十分哀戚地喊……
“娘……”
夜里辛沭给我上药,这兔崽子一直眯着眼,浑身乱抖,最后我的淫威没能震得住他,他愣是扶着墙笑了大半个时辰,让我十分伤心。
而这日过后,女人打我像打上了瘾,每天都按三顿抽,和小叔的凶残程度简直有得一拼。常常天还未亮,我还在梦里和慕渊长相厮守,就被她一扫帚从床上打到地下,慌乱间连剑都来不及拿,就被她追着四处狂奔。
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能在她手底下过个数百招的,有攻有守,偶尔还能占占上风。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三个月,我逐渐感到自己的内力不可同日而语,剑法亦是愈趋精妙,将先前的破绽都逐一弥补了起来。恶鸡婆的眼里有时会流露出赞许和欣慰,待我想细看,却又一闪而逝,取而代之的还是那副冰山模样。
她和我小叔真是特别配。
辛沭闲暇之际,也会去几十里外的城镇买些新鲜肉食回来。恶鸡婆的厨艺不错,一般揍完我之后,都会生火做饭,好好给我补下身体。
我知晓了她叫傅瑾,孤身在这荒漠守着一座坟,已经守了二十三年。问她墓中之人可是她丈夫,她却如何也不肯回答了。
她让我唤她瑾姨,我面上乖乖答应,一转过背就和辛沭讨论这恶鸡婆的种种。事实上,她是比较凶悍嘛。当然了,我也因此被抓包好几回,从而被她打了个生活不能自理。
时日一晃匆匆。冬去夏来,仿若白驹过隙。
我时常在夜里,对着浩瀚沙海,饮一壶灼喉的烈酒,想着那人如今会在何地,是否已经转世,若再遇上,还能不能相认。
生当复归来,死当……长相思。
我已有七年,不曾提及那个名字。
有一阵,我听的某个话本子里讲,每个人的心底都会埋一段故事,藏一个人。那是念在嘴里怕疯魔的人和事,只能任由其沉淀入血肉最深处,慢慢将自己折磨,等待救赎。
我有一个这样的故人。我想,傅瑾也有。因为我常常见她在无名墓前,一站就是一整夜。
临近七月底的时候,边关出了状况。北曌十万大军倾巢而出,看样子是打算对大燕进兵。附近几个村头的百姓都急往内陆逃命。我和辛沭路过去帮忙收拾残局时,听见了一个名字。
慕容谦。
据说他是日月楼的楼主,不世奇才。半年前,在凌霄山以弈棋开局,广邀天下名士参加,最后一百零九人,包括当朝辅相,都折在了他精妙奇思的棋风之下。王上得知此事,让辅相以优渥条件请他入朝为官,他却洒脱婉拒,直言了自己的闲云野鹤之意。而近来,更是助大燕的边境守将,用奇门阵法暂时困住了北曌大军,使得对方迟迟难以过境。一时间,此人名声大噪,几乎无人不晓。
我听见这些,不明为何,总觉得眼皮子一跳,对他似有几分熟悉之意。
回到居处,我将村民的话转述给傅瑾听。她本无甚反应,直到踏出房门逮着一只信鸽,她便匆匆回房收拾好了包袱。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简单迅速地回:“离开。”
“……去哪儿?”
“日月楼。”
我吃了一惊,还不及细问,她又把我和辛沭的包裹扔过来,继续道:“一同上路。”
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在商量的意思,我怀疑我要是不答应,肯定会被她当街打死。总归我也想去见见那个劳什子慕容谦,便默许了下来。
一同出了门,傅瑾开始挖掘无名孤坟。我瞧着她那稳准狠的劲儿,吞了口口水,还是决定劝劝:“瑾姨,虽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你这样是对前人不敬的……”
她的手一顿,片刻,她抬起眼来看了看我,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你知晓自己的身世吗?”
“啊?”我张张嘴,愣愣地回答,“小叔甚少提起我爹,更没提过我娘。”心窝子猛地一跳,我激动地握住了傅瑾的手,“莫非,你当真是我亲娘?”
看这和我小叔几乎同出一家的暴力倾向,完全有可能啊!
傅瑾的嘴角微微一抽,然后继续刨坟:“不知也罢。今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苏衍青。”
“为何?”
我以为,接下来会听见一个开篇狗血,中途曲折,最后虐心的爱情大戏,然而,傅瑾还是用她那不冷不淡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似在警告我不要胡思乱想。我不怕死地想追问下去,她动作麻利地将所有尸骨收敛进一个蓝色布包,旋即拎到我跟前,道:“跪下。”
“啊?”我又迷糊了。
她神色肃然:“给你两个选择,一,跪下磕三个响头;二,被我打死在这里。”
我咬了咬手指:“有没有第三个选择?”
“无!”
然后,我就在她要动手前,果断跪了。末了,我心如止水地问:“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这人是不是曾经和我爹或者我娘有一腿,最后被我爹娘男女混双打死了?”
傅瑾:“……”
日月楼地处含谷镇,是大燕与北曌交界三百里内最繁华的镇子。两国通商的唯一要道须得路经此地,是以这个地方商贸异常兴旺,再加之天然的地理优势,更是鱼米丰饶,风调雨顺。边关逃难的百姓也大多是涌往此处。
我们赶了两个昼夜的路程,终是在第三天黎明时,进了含谷镇。饶是外面战火将燃,此地的百姓也似未受影响,仍高兴过活。问及理由,大多都是同一句话:“日月楼楼主都在这罩着,我们怕个毛。”
这民风,简直甚合我意!
稍是一打听,日月楼的诸多消息就进了我们耳里。譬如,楼主慕容谦是个风雅之人,极少现面,能见他的人都是不俗之士;再譬如,日月楼说白了,就是处风尘地方,虽只接待有名气的文人墨客,楼里姑娘也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且卖艺不卖身,但说到底,都是陪人快活的。
我看着路人流口水的暧昧模样,鄙视他一通后,心里迅速打起了小九九。好不容易有个正当理由让我去风流之地溜达,我一定要来个女扮男装、左拥右抱!叫十个姑娘来给我念小黄书,一人一段不准重复!
这厢我正幻想着酒醉金迷的美好画面,刚想启齿说一句“瑾姨,那地方不适合你这种冷清的气质,不如由我代劳”,话还没说,傅瑾开口:“妄想!”
我:“……”喂,我还没说话啊,你要不要这么未卜先知!
我顿时很受伤。
辛沭同情地看了看我,安慰道:“前辈,下次记得收起你的一脸猥琐,那表情早已深深地出卖了你。”
“……兔崽子!吃我一掌!”
从长街尽头转入一条小巷,再走十来丈远,出了巷尾,便到了传说中的日月楼。其地处青山绿水环抱之间,风格与普通青楼大为不同。古朴雕花的一方小门内,两名女子正在候客。腰间配短剑,长发盘起,神情肃杀,不像要陪人吟诗作对,更像是一捞袖子就要扑上来干个你死我活的打手。再抬头,七层的高塔矗立眼前,塔尖直耸入矮云之中。二三楼里不时走过衣着艳丽的女子与手执骨扇的文人。再高的地方,便是一片寂然,不知有何玄机。
我打量了须臾,扶着门框,跟候客的女子搭话道:“听说你家楼主是个男人,开什么烟花之地啊,不如将此处让给我,我保证三年之内,集齐全大燕最有名的花魁,让这里成为名扬大燕的销金窝,怎么样?”
女子十分轻蔑地翻了我一记白眼。
我“啧”了一声,刚欲开口,让她见识一遭本人的人格魅力,傅瑾一把将我挥至身后,寒声开口道:“在下傅瑾,今日依约来见日月楼楼主。”
原来如此,她和此地主人有约。想来,那信鸽约莫就是那什么慕容谦遣来的。
候客女子仔细打量了傅瑾一会儿,探手引路道:“楼主料到姑娘今日会到,早已备好茶水等候,请随我来。”
言尽,她领着我们阔步前行。
比起从外看到的日月楼,这内中格局更是大得超乎人想象。蜿蜒至塔前的小径两旁,左侧有数间厢房,排列与一般府邸不同,似掺杂着乾坤阵法在其中。而右侧,朱漆拱门之内,像是一方花园。我不经意望过去,便看见碧波假山,水榭长廊,徒剩枝丫的梅树亭亭而立。像是……
旧年王府的湖心小筑。
我不禁恍然,眼前又不可遏制地晃过许多铭刻于心的画面。
到了塔楼入处,傅瑾当先而进,我紧随其后。一脚刚要迈过去,引路女子伸手拦下我,问:“姑娘可是姓苏名愉悦?”
“你认识我?”我稍有愕然。
她又道:“你可是镇国将军府的郡主?”
“正是。”我捋捋呆毛,深沉地笑道,“你家楼主可是认得我?也对,毕竟洒家名声在外,你叫你家楼主不用太客气,茶叶什么的随便喝喝就好,我向来是个随和的人,只喝三百金一钱的洞庭碧螺春而已。”
“……”
话音落地,女子从草丛里拿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牌匾,“哐”的一声立在地下。我定睛一看——苏愉悦与禽兽,不得入内。
……
我大怒:“你叫你家楼主出来,说苏霸天要和他谈谈人生,不然我一挥手,马上拆了你这座破楼!”
女子明显表示不信我的话,转头,面无表情地对傅瑾道:“姑娘请自行上楼,主人在七楼等候姑娘。”
我准备拔剑。傅瑾面色一冷,阻道:“愉悦,不得无礼!”
我一滞。
她甫缓和了些许语气:“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很快出来。”
我竟无言以对。
而最令人不忿的是,这厮最后居然把辛沭也放进去了,逆子临走前一句宽慰我的话都没有,特别嘚瑟地就跟着傅瑾上了楼,把我隔绝在一堵形同虚设的小木门外。鉴于傅瑾的淫威,我还不敢踹了这扇门。
那一霎,我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叫养徒不如养头猪。
……
天际云潮翻涌,惨白的天光几经变换。我守在塔下十分不耐,想着用轻功飞上七楼去看看,每当要起跳,守门的女子就用一种警惕的眼神看着我,随时准备抽剑厮杀。老实讲,我倒不怕和她大动干戈,就怕把她打残了,坏了傅瑾的事。
挠了半个时辰的门,又贴在门上听了大半个时辰的动静,始终没能听出内中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声响。我腹诽着那个劳什子楼主住这么高干什么,也不怕一失足摔死他。乍回头,恰巧对上了女子极其厌恶的目光。
我干咳两嗓子,就地坐在台阶上,一只手闲散地撑着头看她。
她见我目不转睛,索性哼了一声,扭头去看另一个方向。
我道:“你们这日月楼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
她不回答,我便自言自语。
“寻常的风流地都是叫正当壮年的汉子来镇场,而你们却反其道行之,全是清一色的姑娘。我听别人讲,你家楼主又是个不世奇才,这样的人,开这样的日月楼干什么?”
她仍傲气地不肯出声。
我摸摸下巴:“莫非你家楼主有什么隐疾?肾亏?还是不举?是不是需要众多姑娘环绕来慰藉他脆弱的心灵?”
“你!”女子横眉怒目,看架势恨不得把我抽筋扒皮。我不知道她碍于什么理由,迟迟没有行动。反正她不动,我也懒得动,于是继续撑着头问她:“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啊?”
她立刻表现出迫切的肯定。
我哼声:“你现在讨厌我,主要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
“……”
“你要是了解我了,一定会想打我的。”
“……”
百无聊赖地蹲在草丛边上看了半天蚂蚁搬家,暮阳消尽,万家灯火通明时,傅瑾与辛沭才缓缓从楼上下来。我全身心都是怨念,翻白眼翻得眼睛都快抽筋了。傅瑾看着我哭笑不得,只好派辛沭为代表,来和我进行交涉。
“前辈。”
“哼。”我一点儿都不想理你们。
“前辈……”
“哼!”叫个毛线!
辛沭扶住额,冷静了一下,耐着性子道:“让你久等了,前辈。”
“哼哼哼!”我没好气地用鼻子连喷出三声,甫拍拍手,站起来,一脸“洒家大度,不和你等凡人计较”的表情,“知道就好!”我咳了一嗓子,又道,“怎么样,那什么劳什子楼主是不是长得奇丑无比,脚底生疮,脑门流脓,看一眼都恶心得半年不能吃饭?”
女打手:“……”
傅瑾:“……”
辛沭:“前辈,你想多了。”
我望着天,哼哼唧唧。
他描述道:“此地的主人的确是个风雅之人,一曲琴音堪绕梁三日而不绝,儒雅斯文,用风华无双来形容他,也并不为过。”
这么一说,我脑海里闪过一个人影,鬼使神差地屏着呼吸问:“穿着一身蓝衣?”
辛沭讶然,但很快道:“是。”
“脸上写满了‘我的智商你别猜,猜来猜去也只能跪拜的此类嘲讽?”
“……楼主确实算是多智之人。”
“那么,”我十分紧张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他长相是不是搁谁谁高潮,姑娘见了统统合不拢腿的那种,简称帅得逆天?”
辛沭捂住了脸:“我现在说不认识你,还来不来得及?”
我抓住他的肩胛,半丝玩笑意味都无:“快告诉我是不是?”
他默了半晌,估计正在内心扮演着正常女子见到那人的景象,而后满脸纠结道:“是。”
我表情复杂地放开他,沉思着摸了一会儿下巴,道:“爱徒,你的性向是不是还不大明确?需不需要为师帮你想想办法,治上一治?”
作为一个男人,你怎么能对另一个男人想入非非呢!
辛沭顿时表现出想弑师的举动,还未付诸实践,塔里忽然奔出来一名黄衫女子。她跑到辛沭跟前,上气不接下气,胸前波涛起伏,特别壮观。
她道:“辛公子请留步。”
我:“这不是还没走嘛。”
黄衫女看我一眼,好奇道:“这位是……”
“我……前辈。”兔崽子很是别扭。
黄衫女闻言,冲着我甜甜一笑,霎时如同三月桃花齐齐绽放。她再福福身子,恭敬道:“前辈好,我叫黄莺。”
我忍不住小退了半步。我才放我徒弟出去浪了几个时辰而已,这什么情况?
辛沭似乎也甚为不解,问:“黄姑娘追出来所为何事?”
“哦,是这样的,”她道,“一来是向公子道谢白天之事;二来,主人说了,三位若是在含谷镇暂无居所,不如先在日月楼住下,可好?”黄莺眼中闪出期许的光芒,一眨不眨地锁定着辛沭。
辛沭抖了抖,往我身侧挨近,转头问傅瑾:“傅前辈以为如何?”
傅瑾眼神一凛,刚要脱口一个“不”字,我抢话道:“既是如此,我看日月楼厢房也多,环境亦是不差,便依贵楼主之言吧。”
“真的?”黄莺跳起来,“那再好不过了!”一个猝不及防,她挽住辛沭的手,再道,“我旁边便有一间空房,辛公子,你就与我比邻而居好吗?”
辛沭:“我还是习惯和前……”
“好!”作为一个常年说媒的人,我必然有些媒婆的觉悟,所以隔岸观火道,“爱徒,你怎能拂了黄姑娘的好意?!”
咱们师门私生子遍天下,这个伟大志向就靠你发扬光大了好吗!
辛沭狠狠瞪我一眼。
黄莺却是喜上眉梢,问我:“你是辛公子的师父?”
我深沉而低调点头。
她当即便用另一只空闲的手挽住我,极力套近乎:“我一定好好招呼前辈,前辈请先随我去厢房吧。”
我淡淡一笑:“好说,好说。”路上,趁着黄莺纠缠辛沭之际,我对傅瑾道,“瑾姨,且先住下吧,我有一事,想搞清楚。”
“关于此地主人?”
“嗯。”
傅瑾沉默须臾,一言不发,算是默许了。
我仰头,望望一旁的高阁灯影,恍然又想起七年前前往风华谷途中的事,那名与慕渊有着七八分相似的人,当真只是巧合吗?那么,那座与王府相似的花园呢?
夜深时分,万籁俱寂。
一只夜鸦自头顶飞过。天幕上点缀着七零八落的星子,光斑闪耀,与城中还未熄灭的烛火相互辉映,似在无声倾诉不欲人知的情思。
我保持着谨慎的姿势趴在瓦片上,严肃地审问身旁面瘫的少年人。
“你说说,今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去人家楼里逛了一圈,你就给我带了个徒弟媳妇儿出来,这事虽然干得漂亮,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为师至今未出阁的复杂心情?”
辛沭端正坐着,斜眼瞄我:“不要污蔑人家姑娘的名声。”
“呵,现在就知道护短了,分明是有一腿,还想摆出正人君子的模样来迷惑为师?”
小兔崽子不禁蹙了眉:“你就非得拽着我半夜三更在别人房顶上,讨论这种不雅的问题?”
“什么叫不雅,我又没和你探讨采花应该使用哪几种姿势更容易欲仙欲死,我是在跟你说正事好吗!”我义正词严。
他翻了个白眼,很是不耐地道:“白日上楼时我正好遇见她,她端着茶,不小心脚底打滑,险些摔倒,我扶了她一把,仅此而已。”
我想了想,基本想出了当时的情形。这故事开头委实有点儿俗套,好在结果我还比较喜闻乐见。
我拍拍辛沭的肩膀,叮嘱他在这方面一定不能丢了师门的脸。他蔑视我一通,转移话题道:“傅前辈与此地主人应是早有约定。”
“怎么说?”我抬起头。
他道:“从他二人的谈话里,只能得出少许信息。大致是傅前辈有一仇决意要报,一直在等机会。而此地主人告诉过她,若有一日,北曌大军压境,她的机会便来了。”
我整个人一激灵。
北曌大军压境,才有机会报仇。这傅瑾的仇人是谁?若是江湖门派或是普通贵族,大可不必等到两国即将交战时,除非……
我白了脸色。
辛沭问:“你可是想到了什么?”
我理了理思绪,正要答话。蓦地,身下瓦片一松动,我听着这声响,额前呆毛不自觉的一立,直感不妙。我连忙说:“我觉得要出大事儿了,等会儿万一我……啊!”
话音未落,我趴的地方就破了一个大洞。我惊呼一声,毫无准备地坠了下去。辛沭伸手想来拉,却是为时已晚,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摔进房里。
即将落地时,亏得我身轻如燕,轻功不错,游刃有余地转了个圈,放荡不羁地站稳了脚跟。彼时白细的尘灰还未尽散,我目光一定,看见一缕紫色轻纱后,一名男子正在桶中沐浴。他背对着我,三千长发披散,无限春光旖旎,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搭在浴桶边,带着透明而撩人的水色。
我喉头一烧,尚未想出说辞,那人便道:“原来苏姑娘喜欢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我一怔。
这个声音,熟悉得如雷贯耳。
我记得无数个昼夜里,都有一个人在我耳边低唤:“阿悦,阿悦。”致我肝肠寸断。
我不知所措,杵在原地久未出声。那人许是心生不耐,只手一扬,动作快得迅如鬼魅。一眨眼的工夫,他便已取下了不远处挂着的白色亵衣,随手一裹,转过头来眯眼睨我。
我只觉平地一声惊雷炸开,双眼一红,讷讷地喊了句:“王爷先生。”
他的表情微有动容,不过刹那,又换上了一副从容的轻笑:“在下慕容谦,一介平民罢了。苏姑娘的称谓让在下受惊了。”
受……呃……
我哽了哽:“你的性向还正常吗?”
慕容谦先是没有反应过来,等想通了,脸色顿时一青,呵呵了两声,拉着尚未系好的衣衫朝我走过来。我坦然瞅着他胸前大片光洁的肌肤,眼睛都不舍得眨。
他在我耳畔呵口热气,淡淡地说:“苏姑娘,你想让我把你扔下楼去吗?”
我正气凛然地退开一步,生怕慢了会把持不住。眼珠子左右转了一圈,我还是决意埋头看地板,问:“你是不是王爷先生?”
慕容谦默了一阵,答:“不是。在下慕容谦。”
我想起早年初见慕渊,也曾这样问过他:“你是不是我孩子他爹?”他也如此斩钉截铁地回:“不是。”
我再抬头,细细打量了一番面前人。
慕容谦与慕渊的容颜还是有些出入,他的棱角比慕渊冷峻三分,鼻端也比慕渊稍显挺拔。
但他看我的眼色,却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大致是被我盯得不甚自在,慕容谦别过头,悠悠道:“七年不见,小郡主已经如此亭亭玉立了。”
“真是你,”我回过神来,遂情不自禁地摸了一把他的屁股,“当年那个大当家还找过你吗?”
慕容谦神情复杂。
“放心,此事我从未说出去过。但有一事我不解。”
“……”
“你我初遇时,你的武功已是令人惊叹,怎么会……”我斟酌了一下词句,慕容谦的脸色不大好看,甚至已经凝出了剑指。
我识时务地抱住柱子,大无畏地道:“你怎会后庭失守的?”
“……”
接下来的事,已经超出了我的估计。慕容谦二话没说,就和我打了起来。他的剑境登峰造极,十尺之内,都笼罩出冰寒摧毁之意。而我重剑解封,大巧不工的招式混着傅瑾刀法的迅捷,一方面严防死守,一方面伺机而攻。
招来式往,满屋木屑纷飞,瓦片塌落。
慕容谦道:“重剑无锋,如何伤人性命?”
我一剑刺出,险险划过他颈侧,断了一缕黑发。
“便是如此。”
他面上带笑:“与当年稚子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自然。先生亦与当年有所变化。”
听出我的话里的弦外之音,他两指扫过,在屋内圆柱上留下一指深的痕迹。
“我并非姑娘故人。”
“或许。是我心中执着,无法放下罢了。”
“一念放下,便是万般自在。”
我平淡一笑:“若能换他一世长宁,被困一生又有何妨。你能如我所愿吗?”
剑指与重锋猛地一撞,气劲横扫八方,屋内诸物皆裂成碎片。我和他各退半步,顷刻,又战至一处。
“你今夜来此,便是为了此事?”
我手上一顿,望了眼屋顶,诚恳道:“也不全是。要是我说我爱徒怀上你楼里姑娘的孩子了,你看你是不是能负一下责,安顿我师徒俩的下半辈子?”
“……”
然后,我就被慕容谦直直扔下了楼,在花圃里砸出了一个大坑。
半炷香过去,辛沭才从屋顶跳下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嫌弃道:“你每个月那几天是不是提前来了?”
“……逆……”
第二个字尚未出口,我就晕了过去。
慕容谦,真是特别狠。
下期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