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屯考古手记:那些散落的遗珍
2016-05-03李飞
李飞
1600年,海龙屯被攻陷。
早在破屯之前,平播大军主帅李化龙便已想到,诸军将士必定会蜂拥而入抢夺屯中财物,这已成了历朝历代战后的惯例。李化龙敏感地想到,若这是杨应龙设下的陷阱,自己岂非有反胜为败的风险?于是三令五申,破屯之后将屯内府库封闭,待造册清点后,再行奖赏,期间严禁抢掠。可明军的人数实在太多了,破城之日抢掠财务,相互杀戮无法避免。不过杨应龙也未向明军设下陷阱,万金俱灰之下,他举火烧屋,最后自缢而死。
彼时火势如何,我们难以想象,如今只能从《献俘疏》中那一句“须臾,火烧楼房一空”窥探一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阿房宫如是,海龙屯亦如是。经历了灭顶浩劫,海龙屯是否如眼前所见只剩下漫山残瓦和半围围墙?

瓷语无声:土司钟爱的景德青花
《平播全书》作为研究平播之役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口吻记述了海龙屯末代土司杨应龙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无奈,“酋惊知我兵已入城中,急呼亲信苗头,而诸苗亦各奔散,无应者。酋自度不免,因抚膺顿足谓田氏曰:‘我今焚死,断不落乱兵手。田氏牵衣号哭,酋摔去,入我房将房门钉闭,举火烧房,同爱妾周氏何氏缢死。”一代权倾播州的土司,就此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而杨氏一族在播州长达700余年的统治也随风飘散。
明军入城后,新王宫内财物被抢掠一空,而瓷器却似乎并不在劫掠之列。这些精美的青花瓷并非出自本地昕产,而是来自千里之外鼎鼎大名的制瓷重镇江西景德。
杨氏似乎是对名动天下的景德青花情有独钟,我们根据出土瓷器器底年款发现,新王宫内昕出青花最早产于宣德年间,最晚则产于万历年间,也就是海龙屯被攻破的时间,此外还有成化、嘉靖、隆庆时期的器物。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皿听过两岸的猿声啼鸣,看过轻舟疾驰如风,在跨越千山万水之后,终于抵达了这座西南深山,并在历代土司的手中代代相传。
在目前被发现的瓷片中,绝大部分为民窑器物,其中不乏精美质优者。另有部分官窑瓷片,以嘉靖年间昕产的居多,万历年间的则极少。可以推测,至少在嘉靖年间,播州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还是算比较和睦的,这些官窑瓷器,应是由中央政权或皇帝昕赏赐。
我想,既然杨氏如此珍爱这些精美青花,那位传说中美丽的杨二小姐的纤纤玉指也一定曾滑过这些精美如玉的瓷器。或许,此时正躺在某处早已支离破碎的某只凤杯上,还印有她的唇间脂红,彼时它也曾温润精美。虽然,早在400年前大火便已熄灭,抢掠便已结束,可是看着这满目疮痍的一片片碎瓷,顿觉喊杀之声四起,不绝于耳。
在发现这些碎瓷后,我们考古队开始了一场万里挑一的“拼图游戏”。厨房里的上万片碎瓷被一一拾起,洗净晾干后密密麻麻地摆放在桌子上,再按照纹饰分作若干类,最后将它们一片一片地缀合。这样的“游戏”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我曾花三天时间来细细拼合一只绘有凤凰图案的高足杯,硬币大小的数十片瓷片,每一片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须将之严丝合缝地拼整。诚然,这绝对是一项繁琐至极的工作,但每当我们又发现一片碎瓷时,当图案渐渐完整时,大家还是会觉得由衷的快乐。这世上有许多工作看上去很难让人理解,但我想,对于从事那些工作的人而言,或许其中的快乐亦是难以言说而旁人更难以理解的。
旧食记:土司餐桌上的美味珍馐
海龙屯的考古工作工程浩大,需要我们长时间待在屯上,维持生活就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从海龙屯到最近的市集,最陕也需要2小时,于是我们在抵屯后便种下了一些粮食果蔬。来时,尚是万物复苏的初春,而今不知不觉间,树梢的叶子都已被霜打泛红。我们餐桌上的菜肴,也从野生的春笋、柴胡、蕨菜变成了八月笋和菌子,这些虽不见得都是我们昕种,却都是屯上的产物,来自大地之母的慷慨馈赠。
偶尔,我们还会下河去捉些鱼虾,或从附近猎人手中购买一些野味来改善伙食。有时我会想,今时今日海龙屯的食物与400年前有何不同?当时这屯上的主人,又都吃些什么?
从理论层面讲,考古学可以对此作出解答,而我们也一直尝试着去做。有幸的是,在清理新王宫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三处厨房的遗迹。由砖砌而成的灶台虽已破败不堪,可周围四散的灶灰、炭屑,和破碎的器皿、精致的石盆还是向我们透露了这里曾经的功用。在一房间内,除了上述物品我们还发现了形制与今时带把的锅儿相同的的铁锅碎片,以及惊人的数千瓷器碎片。瓷片大概分为青花瓷与土瓷两种,按器类分青花瓷有杯、盘、碗、盏、钵等,而土瓷的器形普遍不大,多半是储存油盐和香料的器皿;部分带流,或为酒器;部分有盖,像极了我们如今的泡菜坛子。
此处的厨房紧邻的可能是土司寝宫的“三台星”,其中器物多是雅致精美,应当只有主人才可以使用。有龙纹修饰的高足杯、带流的执壶,这些显然是为了土司的美酒佳酿所准备。泡菜坛子则表明,在遥远的400年前,腌制食品亦是杨氏餐桌上的常客。不过,更多的美味或许并未留下肉眼可以观察的遗证,想了解400年前的土司餐桌,我们只能借助器皿上的残余物和溅落地面的植物种子来识别,方能知晓。
很多时候,人们会理昕当然地认为现代生活里的许多事物是古已有之,向来如此,包括我们餐桌上的食物。可事实上,数百年来,我们的习俗、语言和饮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触手可及的,往往是最容易被人昕忽略的。
如今贵州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辣椒原产于南美,1493年随哥伦布传人西班牙,大约十六世纪才传人中国。与许多外来品种一样,它被冠以“番”出现在各种古籍当中。还有现如今在贵州广泛种植的玉米、土豆和番茄,均是外来物种。虽然各种作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目前仍有争论,我们无法断定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是否吃过辣椒、玉米和土豆,但其明代以前的先祖是断无此口福的。
从明朝何乔新与清代巨儒郑珍昕留下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稻、麦、麻、黍、豆、茶、蜜、鱼鲜、野味及各种蔬菜、野果和野味都是土司餐桌上的美味。除了明确的外来物种,更多的是当地昕固有的。许多古法烹饪,甚至延续至今。“半朝天子”的饮食引人遐想,或许,彼时的他,生活比之今人更加有品质。巨石语:海龙屯的血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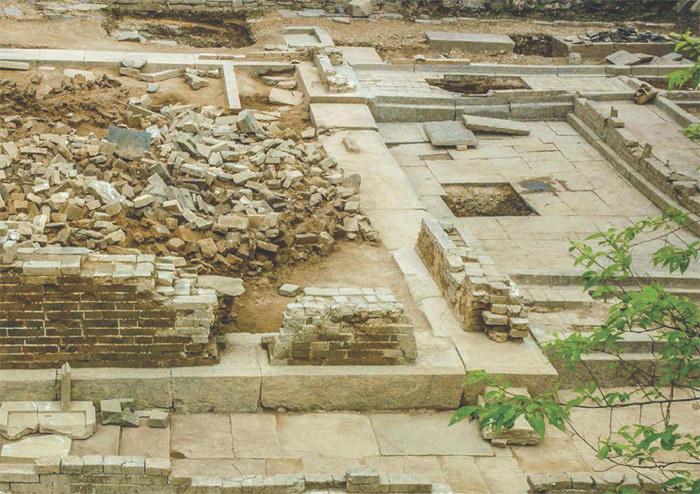
海龙屯由石、砖、瓦、木等建筑材料修筑,其中又以石材应用最为广泛,关隘、城垣、屋基、台阶、柱础、窗户,几乎无昕不用。为了测量屯巅用石的方数,我们特别邀请了地质专家,在他告诉我们最为常见的泥灰岩比重后,只要准确测量了石头的体积,便可计算其重量。经过反复验证,我们确定了屯上石材的比重是2.8吨每立方。在海潮寺前踏道上有一方长达2.55米的巨型条石,经测算,其重量达2.5吨,而逾吨的石材在新王宫内更是比比皆是,如此多的巨石采自何处?又是如何运抵此地的呢?
传说,杨应龙有一条神鞭,能驱石赶山。在鸡犬不鸣不吠的深夜,只要他挥动鞭子,便石如猪奔,城堡如此筑就。这则故事版本诸多,流传甚广,虽不过是笑谈,可海龙屯工程之浩瀚也可从中窥探一二了。
据飞龙关、朝天关匾额上的修建时间,再结合“平播之役”的史实,我们不难推算出杨应龙在重新修建海龙屯上昕花费的时间不少于7年,可见海龙屯虽非杨应龙用“赶山鞭”以一人之力重建,却也是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后才有的结果。
在另一个版本的民间传说里,杨应龙的形象暴虐异常,他下令筑屯者每日须穿坏3双草鞋,否则便将其视为偷奸耍滑,扔下臭名昭著的杀人沟。在我看来,这个传说或许更加接近真相。筑屯时,匠作人役的使用一定不少,以海龙屯昕用石材之巨,死伤者也该不在少数。
从挖掘情况看,石材是被运至建筑工地才进行深加工的,从铺地的砖、石下可以发现厚厚一层从整石上凿下的碎石屑。那么,如此多的石料又究竟是从何而来?
在老王宫后有有一石山,地势高敞,石上隐有凿痕,其西南方向有大片凹地,俗称“窝坑”,在10多年前,被先期调查者认定为“采石场”。这一说法较好地解释了海龙屯上的石材来源,即就近取材。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请来了地质专家。这些历经百年岁月的巨石,在地质者面前仿怫焕发了生命,开始讲述自己的历程。经检测,山上主要岩石以粘土岩为主,夹杂部分泥灰岩,与海龙屯上的大部分建筑石料种类相吻合。不久之后,我们对“采石场”又进行了一次局部清理,更是发现开采石料昕遗留的各类楔眼,其形状、大小,与新王宫部分石料上昕留完全对应。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此处确为一处采石场,且新王宫内至少相当部分的石料是取自此处。
而从位置上看,老王宫距离此处更加接近。彼时播州告急,吕、杨二人仓促之间欲“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时,在短时间内建成坚固的防御工事也只能考虑就近取材。昕以,采石场的时间可能早至宋代,而其中一组近方形的楔眼就有可能是早期采石昕遗留。
不过相对于开采而言,运输的难度要大许多,一种由高处向低处借助特殊工具,并辅以冷水泼地加以润滑等方式进行拖拽的运输策略被认为是最合理可行的,只是,关于这一点,已难以找到过往痕迹。
许多人问过我,在海龙屯上这些日日夜夜,没有麻将、没有电视剧,生活陷入巨大的空虚和迷茫,你是怎么度过的?每次听到这样的询问,我都会想到自己漫步在屯上的日子,夜幕星空下,空旷的山谷总是能给予我足够多的感怀,虽然不能亲历此处有人以来的每寸光阴,但生而有幸,可以让我在废墟中追寻文明的碎片。这些碎片埋藏在黄土下,埋藏在废墟里,它们让我可以去重新发现、诠释与建构历史光影中的海龙屯。
缀合着一枚枚散落的遗珍,我很庆幸能够与它们相逢。透过它们,我仿怫看见勤劳石工如雨的汗水渐渐风干,听见山林里的劳动号子渐渐飘远,一座石头城堡雄伟屹立在我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