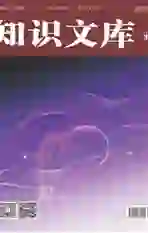试论先秦两汉魏晋人伦观的演变
2016-04-29黄沁茗
在传统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君臣、父子、夫妻是最基本的三组人伦社会关系,它不仅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走向,而且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和谐,影响着家庭的基本结构。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儒家的“三纲无常”一直是维系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皇权统治的基本伦理大义。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用以保障实行“三纲”。然而,这种个体被消解、“他者”被漠视的绝对化的人伦观并非原始儒家所有,它更多的是两汉以来主张儒学官方化的哲学家对其进行法家化的改造的结果,而到魏晋时期,随着玄学兴起,儒道会通,它又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松动态势。
一、先秦儒家人伦观
先秦儒家和法家都主张人伦有序,长幼有别,如孔子已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韩非以“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但它们的人伦观在基本价值取向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和差异的。
先秦儒家的人伦观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包含着古典素朴的生态情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就是每个人心中要有他人,友爱他人、尊重他人,同情他人。爱人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者合起来,孔子称为“忠恕之道”。从这种基本的“仁道”出发,先秦儒家强调“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情“,而不是后世宣扬的那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对待的、对等的,而不是单方面的。《论语》云: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在位期间,鲁国公室微弱,大夫多失礼于君。定公很忧虑,想知道怎样摆正君臣关系。问孔子,试图有所补救。孔子因此对定公说了上述那样一番话,其重点在要求鲁定公“君使臣以礼”。“礼”指“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皇疏》:“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君使臣不仅要以“礼”,君待臣还要以“义”。子曰:“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义”谓“各得其宜”,各当其称,使贵贱长幼皆有所节。有了“礼”、“义”的保障,人们才能各尽其责,社会才能良性运行。又如: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说,如果为君者能遵行为君之道,为官者能恪守为官之德,父亲尽到父亲的职责,儿子尽到儿子的本分,则国家又何愁不能长治久安、家庭何愁不能和睦兴旺呢?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人伦思想。《孟子》云: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很显然,在孟子看来,君有礼,臣尽忠;君有过,臣则谏;民为贵,君为轻,这些才是君臣大义;而无条件的效忠,并不是君臣大义。君臣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但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等级地位来衡量的。孟子的君臣之“义”中包含着人格平等的意义,即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其他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也是如此。总之,“角色是父子、君臣等关系中的人,而德性则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人伦理念: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荀子的这段话影响深远,“从道不从君”,更是激励过后代无数志士仁人。荀子认为,士臣应该依从正确的原则和道义,而不是盲目的依从君王。推而广之,“从义不从父”,顺从道义而不顺从父亲,这亦是做人的最高准则。总之,道义高于君父,高于忠孝,其中蕴含着朴素的民本、民主思想元素,与孔孟的主张一脉相承。
二、两汉对儒家人伦观的法家化改造
先秦的儒家的人伦观,强调相对温和的君主统治和相对平等的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辩证性。但这种相对民主的人伦观并不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的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中皇帝是核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这一政治系统稳定的关键就是要保证皇帝的权威。“尊君卑臣”是维系以皇帝为核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而这种绝对的君臣观是由先秦法家首先提出的。
法家从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出发,主张“尊君卑臣”,以严刑峻法治民。如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重“术”,主张“尊君卑臣”,君王“示天下无为”,把“术”藏于胸中,以驾驭臣下。只能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统治,不容许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政而专其令”。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认为,一切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均出于“自为心”和“计算之心”,他们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基于此,他认为帝王应运用“法、术、势”,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他指出:
“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明君无为于上,人臣悚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可见,韩非强调的是一种单方面的、不对等的人伦关系,认为君臣之间应该分清等级,严格界限,臣对君绝对忠诚,而君主则不必事必躬亲,只需运用政治权术,驾驭人臣,使人臣自动听命于自己,绝对顺从于自己,为己所用,从而实现“无为”而治。
显然,先秦法家的人伦观更适应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事实上,先秦时期诸侯各国推行封建化的改革以及秦朝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都是以法家人伦观为主要理论依据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是明证。因此,儒学在封建国家要取得合法地位,必须吸取法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法家化的改造。
孙叔通是汉代第一位将儒学法家化的儒生。汉初礼制不备,“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请求由他到鲁地去征召儒生及弟子“共起朝仪”将“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后其所制定的朝仪被采用,首次朝仪后刘邦大喜道“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也”。但朝仪的实质如何呢?朱子谓:“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其实质就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礼节。叔孙通把“尊君卑臣”变成儒家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迈出了儒学法家化的第一步。叔孙通之后,公孙弘又把“尊君卑臣”的原则进一步推广到君臣的生活方式之中。《史记·平津侯列传》载,公孙弘“每朝会议,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意”。他的“不肯面折廷争”和“以顺上意”无疑是对儒家“诤谏”和“议政”的传统的一种阉割。总之,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损伤君主的尊严。经过叔孙通和公孙弘等人“曲学以阿世”,源于法家,而原为儒家所反对的“尊君卑臣”的观念渐为汉儒所接受。但真正将“尊君卑臣”神圣化、绝对化并将其输入儒学系统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以韩非的“三事”为中心,并杂以阴阳五行说,提出“王道之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定“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以“阳贵阴贱,天之制”来论证臣、子、妻只能依附君、父、夫来行动。董仲舒的“三纲”说直接建立在其“天人感应说”的基础上。他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谴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他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认为阴阳尊卑之道是永恒不变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论证了即“王道之三纲”的神圣性和绝对性。至此,儒学人伦观已经彻底法家化,从而使儒学在政治伦理思想上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为其实现被定于“一尊”的理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魏晋对儒家人伦观的道家化改造
汉武帝看到了董仲舒的新儒学对于封建统治巨大的维护作用,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上升为官方思想,并对道家及其他学说进行排斥打击。随着东汉末年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演化,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魏晋玄学乘势而起,以自然和名教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核心,试图调和儒家和道家的伦理思想。
王弼从“以无为本”的宇宙本体论出发,以“体用不二”的哲学论证方式,冲破了汉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思想禁锢,大胆地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王弼认为,“自然”即“道”也即“无”,“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道者,无之称也。”“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万物即有名有形的具体存在物,包括自然万物、政治人伦、纲常名教在内,都不能离开“无”这个“体”而发挥作用。王弼认为名教是末、是子,自然是本、是母,主张“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试图以此调和自然和名教的矛盾,挽名教于既倒。汉儒把名教说成是天意,借天的权威,强制人们恪守名教规范,结果导致奉名教者不以名教立身只以名教格人的普遍虚伪,使名教出现信仰的危机。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的提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名教”的信仰危机,而且以玄学伦理学替代了两汉的神学伦理学,开启了魏晋时代伦理思想发展的总方向(“自然”与“名教”之辩)。
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伦理观。嵇康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反对世俗纲常名教,认为“名教”违背“自然”,非“自然”之所出,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对立,主张摆脱名教的束缚,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从欲则得自然”。进而抨击名教统治的虚伪,指出名教“造立仁义”,广开“荣利之涂”,使人“凭尊恃势,不友不师”,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达生任性。认为这样便可“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使人性达到一种不扰、不逼,“默默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的自然素朴的本然状态。
玄学后期代表人物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郭象以物各“自生”、“自化”的“独化”说为基础,说明“自然”是不施人为力量而天然如此,“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又说:“自然者,故曰性。”认为“仁义者,人之性也”,包括仁义道德在内的名教,都是“自己而然”,“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在郭象看来,“天地万物皆为一独立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特殊的逻辑,不相统率,不可取代,若按此独化的轨道运行,则入于玄冥之境。人类社会亦复如是,‘人人自别’,‘人自为种’,每个独立的个体都以自我的性分为轴心而自为,子足于己,无待于外,互不相与,互不相为,但就在此卓尔独化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自为而相因’的作用,把人类社会凝聚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自王弼到郭象,魏晋玄学家通过“自然”与“名教”的讨论,完成了儒道会通的理论建构,肯定和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值,为人的发现或曰人的觉醒奠定了思想基础。由此,我们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到,魏晋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君臣之间(包括上下级)、男女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相互激赏、平等对话成为一种时代风气。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