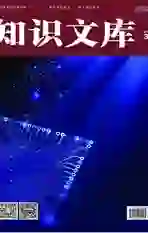高职文化素质课程的教学困境和授课策略浅析
2016-04-29王福铭
文化素质教育要增加学生智慧,丰富情感,使学生养成相互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深入思考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并形成推动这种价值与尊严的人文观(樊旭敏沈利斌 2011)。而在高职,文化课程的开设及学生文化素质的养成是短板,如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我们最重要的场所是课堂,最重要的载体是课程。
以《世界历史与文化》这样的文化素质课程为例,开设的目的有二:首先,培养学生的历史感,使他们具备世界情怀,此为价值观培养部分;其次,掌握历史的描述方法,使他们知晓如何讲述历史,此为训练学生思维能力部分。就所有层次的教育而言,价值观的培养从没有中断过,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任何一门人文社会课程都应该具备这种功能,而思维能力的培养则千差万别,比方说数学培养的是精密思维,而语文培养的是语言逻辑和语言思维。可以说任何一门人文社会学科,都兼有价值观念培养与思维能力培养两个方面,这两种能力孰重孰轻?高职高专的学生,在专业课程里,最有特色的是实践性课程,需要手脑结合,强调学中做,做中学。而空中乘务专业,其未来工作环境有典型的社会、人文取向,十分注重交际与沟通,而且空中乘务员越往高端服务发展,愈加重视个人的广阔视野。虽然,我们可以将价值观念作为一种隐性的能力来培养,而思维方法作为一种显性的能力培养,但是,从长计议,要想突破人才培养的玻璃屋顶,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这种隐性能力的多寡与高下,学生离开学校后,在未来岗位上所达到的高度,往往也取决于这种隐性能力。
一、学生喜欢听什么
在讲授《世界历史与文化》课程时,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中外历史的对比,古今历史的对比,往往受到学生的喜爱,而作为历史学特有的理论方法,哪怕是最为简单的历史线条和历史发展逻辑却一直受到排斥,也就是理论如何以一种更多样的形式,充满魅力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似乎只有大师才可以迎刃而解。作为历史学内核的历史发展逻辑丢失了,我面对空中乘务专业学生抛弃了学科最为核心的知识,而留下的历史感和世界情怀在一学期内的增长是微乎其微的,余下的只有是讲述历史的思维方法了。至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时间是几时几分,站在因材施教的角度,纠结它们是完全不合适的。一名专业老师在不断地与空中乘务专业学生融合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里最能吸引他们的是精彩的故事。对于老师来说是悲还是喜呢?对学生的需求了解愈多,对学生的了解愈甚,我们会发现这场博弈,教师唯有不断地倒退,不断地迎合,只要最后剩下的故事还可以吸引他们,为他们原本单薄的知识储备增添一份能量,就是奉献。当然故事可以讲得很精彩,也可以讲得很清楚,也可以说的不清不楚。于是,我们将故事的方法放在了课程能力培养的核心位置,故事本身被安置在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当然,这种能力的培养永远基于源源不断地去发掘历史故事的基础上。
作为教育者而言,讲故事是手段,讲授历史的叙述方法是目的,而相反,作为学生而言,他们更在乎有吸引力的故事,而不是掌握所谓的讲述方法。为了避免将方法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学生面前,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教师必须明白手段是永远可以显性地正面暴露在同学们面前的,而目的必须永远隐藏在手段的后面,虽然我们的教学目的同时也是我们讲故事的指导原则。若没有长期的教学经验,我往往会把这种真实的存在当做教学的一种悖论。但是,高职高专空中乘务专业的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像教师一样,将手段与方法高度融合在一起?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在一个班的学生当中,我们会发掘出少许善于融会贯通的长才。对于这些逐步意识到思维方法重要性的同学而言,我们可以在批改他们作业的过程中,给出中肯的建议,而不是在课堂上对所有同学言明这些不是很好理解的理论方法。对大多数同学而言,若反复听还不解其意,就会产生挫败感,对于课堂而言这是灭顶之灾。而相反,鼓励是最好的教学手段,可以无限的重复使用,但是对他们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任何伤害,就触摸了教育的底线。
二、老师面临的困境
在《世界历史与文化》这类文化素质课程中,假如你照本宣科,那么极有可能出现台上老师自己讲自己的,台下学生自己玩自己的,毫无疑问这就是一次失败课堂的标准写照。当然,现在的教材良莠不齐,老师在接受一门新课的授课任务时,可能因为时间不足,也可能因为对课程钻研不深,只有借助别人东拼西凑的教材来传道授业解惑。但是,情况也不一定如此,或者一个严谨的学者,考据充分,论证严密,可还是不能在课堂上将学生拉回来,他们仍然各行其是。
新老师如此,老教师在带新课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何在课堂上让学生产生共鸣,教学内容怎样,教学手段如何呈现?对学生而言,一门新课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知识领域,面对不同接受层次的学生,在新课程的知识内容上应当有不同的剪裁,所以教材的选择很重要,假如我们是站在大学课堂的讲台上,当然自己写讲义,往往可以做到在内容上更加契合学生的需求。即便如此,问题依然存在,在上课的伊始,你如何判断学生的知识功底,文化语言素养?只有经过长期的磨合,我们才有可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学生。
问题在于,我们上的很多文化素质课程只开设一个学期。等你和学生磨合得比较好时,很有可能已经是期末,而相应的教学评价在期中或者更早已经展开。就教学评价而言,学校并没有站在教师的角度,更多地采集的是学生的意见和反馈。我们先不论这种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是否合理,至少造成的结果是给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固然承认,评判一堂课好与不好的最终尺度是学生的接受与理解程度,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把教师放在一边?
毫无疑问,在每一堂课里,在每一门课程里,学生是教师全盘教学计划与教学实施的最终受益者,我们若简单的只在乎学生的评价,那么显然是只在乎结果,不在乎过程。一门课程的授课计划具体包括:授课内容、授课进度安排及课时量。教师,特别是带新课的教师在确定课程内容时,会参考所谓的课程标准,翻看以前订阅的教材,但这两项对课程而言并没有问题,只是课程服务对象的需求产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什么,在教师没有走上讲台时,永远无法知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整体地把握教学对象,所依赖的有同事对学生的评价,甚至学生入学的录取分值也可以作为重要的标准。通过这些收集到的信息教师可以在侧面了解到班级学生的文化和专业素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班级或者这几个班级当时的学风和班风如何?掌握这些基本的信息以后,我们可以再着手整理教学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本科院校和科研性的院所,在高职院校里,特别是提前批招录的专业里,我们的公共文化课在内容选择上,理论总结和归纳永远在精彩的内容之后。将简单的内容精彩地呈现在学生面前是在高职授课的一个趋势。可是,理论也可以很精彩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吗?当然可以,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在高职教授学生学习理论,需要大师级水平的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将平常的内容讲得深刻,将深刻的内容讲得平实。一个教师自己对理论掌握得不精熟,讲起来往往让一般的学生觉得艰深难懂。所以,作为一个在高职院校教授文化基础课的老师,我们了解学情是一方面,自我的剖析与评价也相当重要。应才施教,也应该包括教师根据自身的才学和实际情况来实施教学。
三、解决方法
我们在充分尊重学生的同时,也努力地认识学生,了解他们的实际能力,真实情况。必须承认,文化基础课在初高中阶段是高职空中乘务专业学生的短板,如今在大学阶段,我们再一次设计文化课程,实施文化课程的教学,得更多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思考。你若想知道学生学习不擅长课程的感受,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比如你不擅长舞蹈,觉得舞蹈课很痛苦,现在要学舞蹈,你希望老师怎样教你,这样换位思考你就能明白学生的感受(Neil Postman 1996)。若顺着这个思路,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学生并非擅长文化课程学习,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将庞杂的知识简单处理,简单的知识则需要讲得更加简单明了。但是,何为简单明了?就《世界历史与文化》这门课程而言,应该去了解和关注学生通过网络及电视得到历史讯息的任何点滴,实际上我们所传授的任何世界历史与文化知识,在他们脑海里,会和他们的已知产生关联,即便这种关联是在不自觉情况下发生的。
既然这种不自觉的关联会发生,那么当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自觉地运用这种关联。比如,在讲到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莫拉比时,不妨问问同学们通过看影视剧,觉得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显然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教学设计,因为汉莫拉比和晚于他几千年的雍正都属于凡事都亲力亲为的帝王,为人苛严,好峻法。如此,同学们在学习西方的历史文化时,找到了对应的参照物。
正是这种比较方法,使得我们在讲授新知识时,可以有意识的选择参照对象,方便教学的展开。但是,教师光使用这种比较教学方法是不够的,因为所有的教学最终评价都依赖于学生的掌握程度,而在一般条件下,我们唯有通过他们的期末测验成绩才能判断他们平时的学习效果。可是像这类一学期就结束的文化课程,我们假如在期末才可以全面真实地掌握他们的学习效果,会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所以,从调整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的角度,我应该更多地进行随堂测试。简单有效的测试方法,可以是要求我们的学生随堂复述教师讲述的内容,这一环节可以放在每堂课的开始,也可以放在每一堂课的结尾。放在上课伊始,则是温故而知新,衔接新课程,置于课堂的尾声,则可以视为我们在归纳总结当日的课程内容。问题在于,高职学生鲜有下课复习功课的,课前预习功课的习惯,所以,毫无疑问在一堂课结束以前,由学生作复述和总结学习效果最佳。
我们讲授课程的一个方法是比较法,使新知识与已经储存在学生脑海里的固有知识发生关联,而检验学习效果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方法是让学生在下课前作总结复述。即便这么做,我们还有欠缺,因为作为一个老师是受过历史训练的,在讲述的时候已经将框架、层次和要点完全融合在了一起。而没有经过学科训练的学生,在练习时体现不出学习效果,如此,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是无差别的。我们必须将自己已经熟练掌握,而且加以无意识运用的思维方法明晰地展现给我们的学生。它们包括:首先,选择合适的思维模式——演绎或者归纳,演绎意味着我们先对历史文化事件下结论,再将事实铺展开来,而归纳则意味着先描述事实,再最后下定论;其次,选择展开知识的方法是并列还是递进,在这里我们需要做的是理清所描述事件或者人物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比如形容人物的爱情婚姻、事业、性格可以看做并列关系的,而成长、挫折、成熟则明显属于递进关系。这些思维方法的反复练习其实才是同学们学习的核心。
(作者单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