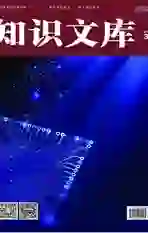窦娥“冤”的客观说法
2016-04-29张敏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品,窦娥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本文试从客观角度分析造成窦娥悲剧的原因,分别从桃杌其为人,案件的审理过程等方面进行阐释。
悲剧最初是源于西方的戏曲门类,20世纪初王国维首次将这一观念引入中国。从悲剧的角度出发,他对《窦娥冤》给予了高度认可。他的《宋元戏曲史》中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窦娥冤》是一部代表性悲剧,在内容和艺术上都非常成熟。
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是一个坚持斗争的女性形象,虽然结局悲怆,但其斗争精神贯穿始终,具有“主人翁之意志”,这也是窦娥形象具有悲剧意蕴的原因。本文试从客观角度分析窦娥冤的悲剧性。
楚州太守桃杌是窦娥悲剧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他在第二折出场,上场时便自述:“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后有情节——“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些都属于戏曲中的插科打诨,增加舞台效果,让观众获得愉悦的心情。从桃杌的陈述,可以断定他不是一个清官,更不是一个好官,但不能因此断定他就是一个贪官。细读文本发现,他并未接受贿赂,或者说他至少未有意去索要钱财。
分析文本知,窦娥方的经济条件远胜张驴儿,在楔子中蔡婆婆自叙:“老身蔡婆婆是也,……只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家中颇有些钱财。”而原告张驴儿父子本是无业游民、社会无赖,他们没有钱。相比之下,蔡婆婆家是“颇有些钱财”的,文中多处细节涉及蔡婆婆的家庭条件:“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从窦天章的口中得知“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物……”同时,窦娥成为蔡婆婆儿媳时,蔡婆婆不仅没有向窦天章索要本金,还额外送了他十两银子做盘缠,应科举之费。这些细节都证明蔡婆婆家财殷富。经过两方经济实力对比,显而易见窦娥一方更有资本去收买桃杌。但是,从戏曲文本中可知,楚州太守并未有意袒护窦娥一方,更未主动索要钱财,反而轻易听信张驴儿的谎言。
排除楚州太守个人因素,下面分析整个案件的审判程序:一开始,原告与被告双方在桃杌面前各陈其词;张驴儿恶人先告状,窦娥因不认罪而受到严刑拷打,后为不让婆婆遭罪,窦娥承担了所有罪行。故而案件本身是否合理呢,桃杌便成了决定性人物。暂不考虑他是不是一个贪官,作为官员来讲他会觉得,被害人张驴儿的父亲中毒而亡,属人为因素;从亲疏程度判断,窦娥就是首要怀疑对象。张驴儿又在公堂上对桃杌说:“他自姓蔡,我自姓张,她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作甚”?因此,桃杌也会觉得要先审理窦娥。随后,在窦娥不招认的情况下,才采取了必要刑法。“刑讯逼供在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种刑罚,而是作为获得证据的一种手段,尽管今天看来不合理,却符合当时的法定程序,甚至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认可。”对于刑讯逼供,窦娥挺住了“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来”。这时桃杌说“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可见,桃杌已要把窦娥排除在外,顺承怀疑蔡婆婆。窦娥担心婆婆年纪大,承受不了棍棒的拷打,主动认罪。这使原有程序未得正常进行,成为案件的转折点。故而,窦娥主动认罪成为导致悲剧最最直接的原因。而桃杌其人,虽不是贪官,但他随便相信小人的谗言,没能做到明察秋毫,是一个想法简单、判案能力不高的昏官,成为窦娥悲剧的最主要推动力。而窦娥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的不完善,官员没有能力为百姓服务,却能随便决定平民的生死。
除上述情况外,蔡婆婆在案件审理过程及后期都没有反驳上诉,而只是哀叹“兀的不痛杀我也”,这也使人困惑。笔者认为,这是由于蔡婆婆的软弱,更是因为她无法确定张驴儿的老爹究竟是不是窦娥毒杀。一开始蔡婆婆便惊慌的问:“孩儿,这事怎了也?”窦娥解释说“我有什么药在那里?都是他要盐醋时。自家倾在汤儿里的。”可见蔡婆婆起初也是怀疑窦娥的,她深知窦娥坚决不同意和张驴儿结为夫妻,故有毒死张驴儿老子的动机。况且,张驴儿父亲喝的羊汤确实是窦娥煮的,她有下毒的机会,且没有证据证明毒药不是她下的。最最重要的是窦娥最后认罪了,蔡婆婆虽痛心但也无能为力。
文本中可知,案件是在窦娥死后三年才被窦天章发现的,而且若非窦娥托梦,案子难以昭雪。一方面是官员无作为,但更多的是案件原有逻辑很难被推翻。人们宁愿相信是儿媳害死了公公,也不认为是儿子药死了老子,事实上张驴儿本意也并非如此,这更易让人误解。
窦娥确是被冤枉,但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无人可扭转这种局面,这是乱世中人的悲哀。这一罪责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是多方面社会因素造成,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满了无力感,只能安于命运的摆布,这是乱世中人的悲剧。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