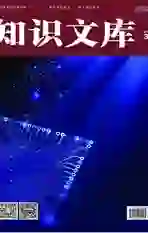简析囚虏时代古犹太教演进的特点
2016-04-29胡德富燕国华
囚虏时代是古犹太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期,对犹太宗教和犹太历史的演进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意义。这一时期古犹太教在外力冲击下偏离原有的发展轨迹,在神权政治形态、独一神观念、上帝形象与宗教功能、宗教平民化发展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使犹太教脱离了西亚同期其它宗教信仰的发展阶段,真正走向成熟。
有关犹太教特征的讨论自国内上世纪七十年代犹太学兴起之后就从未停止过,切入的角度亦各有不同,有文化、历史、宗教、文学等等,不能一一具足。然而从发展变化的角度以比较的眼光探讨某一阶段犹太教的特征还有待深入。一般认为,犹太教是一脉相承的宗教,但对于古犹太教来说并不如此。囚虏时代是古犹太教一个很重要的分期是确定无疑的,不仅在于以色列人自此开始丧失完全的独立主权,开始了寄居的历史,而且在于犹太教在囚虏之后的纯化和成熟。本文试图简要分析囚虏时代古犹太教演变的特点。
一、囚虏时代古犹太教演进的特点
囚虏时代的古犹太教在外力冲击下偏离原有的发展轨迹,在神权政治形态、独一神观念、上帝观念、宗教功能和宗教平民化发展上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神权政治形态上,宗教对犹太社团的渗透由高层贵族发展至社会底层,实现了整个犹太社团对上帝的完全信仰。这一特征对外表现为周边强敌环伺的民族生存环境和持续的外力冲击不断压迫着犹太教偏离原有的发展轨迹;对内表现为神权与政权的不断紧密。前囚虏时代古犹太教呈现出“创痛式”的发展轨迹,这一特征在囚虏时代表现的最为显著。凯伦·阿姆斯朗在表述这一类似看法时这样写道,“由以色列的神转化成代表超越力量的象征,并非是平静祥和的过程,而是夹杂着痛苦与挣扎。”整个前囚虏时代,宗教信仰呈现出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时刻总是与异族压迫和外敌入侵相伴随的,如之前的摩西出埃及,如之后的巴比伦之囚时期。现实的政治环境并没有使犹太人脱离对上帝的信仰,反而使之更加依赖。除此之外,以色列的社会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囚虏时代之前的犹太社会是一个披着神性外衣的奴隶制家长制社会。犹太家庭以家长或族长为中心,社会地位由高到低依次向外是妻妾、已婚未婚子女、奴婢。“说它是一个政治单位,是因为族长或家长威权极重,除战时外,国家亦有所不逮”。家长权力几乎毫无限制,土地、房产、子女均由其支配,子女的婚配也由其做主。囚虏时代,氏族社会被消灭。“在政治独立丧失的新背景下,旧时以色列族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犹太人开始以宗教重新界定自身。”犹太社会的结构逐渐变得相对单纯,宗教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和底层化,社会结构大致呈现“社团宗教领袖——犹太人——外邦人”三级形式。
其次,异神崇拜冲击与独一神观念斗争呈螺旋状形态共同推进犹特太教演变,在囚虏时期这种斗争由众先知领导,回归后则由犹太社团领袖领导。布朗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雅各布·纽斯纳认为,犹太人总是从其他民族中频繁地借入一些品质或现象,并使之变成犹太教或者犹太人的品质。螺旋状形态意味着二者之间的斗争是相互交织,此起彼伏的。在前囚虏时代,异神崇拜对犹太教的影响大致呈现出三种类型:部落或祖先崇拜遗留、西亚其他宗教冲击和巫术的影响等。在囚虏时代,主要表现为西亚其他宗教对犹太教的冲击,特别是巴比伦宗教信仰和撒玛利亚人多神崇拜的影响。巴比伦之囚时期,犹太人虽然保持了较高的社团独立性,但由于自身环境的完全改变,无可避免的受到巴比伦信仰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天使”的出现和“七眼星辰”上。有关天使的形象是这样的,“…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她们翅膀上有风,飞的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七眼星辰”则是天使为约书亚传神谕时所立的一块石头,目的是为了“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同时,耶和华还这样告诫以色列人,“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在被人记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则反映了巫术和假先知在当时也对犹太社会有一定的影响。而在回归之后,这种斗争主要反映在对撒玛利亚人的斗争上。撒玛利亚人是由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与亚兰众多城邦的移民与撒玛利亚城原本的以色列人混居而形成的,分国时代受北国祭司的引导而崇拜雅赫维。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根据《圣经》记载,撒玛利亚人崇拜的西亚其他神灵多达七八种。为此,回归的犹太社团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宗教改革,即以斯拉宣读圣书和尼西米改革。重新树立了对上帝的信仰,禁止与异族的婚姻,纯化了犹太民族的信仰,排除了对异神的崇拜。
第三,囚虏时代犹太教上帝观念进一步丰满。上帝形象由部落祖先形象,到带有巫术色彩的战神形象,再到丰产与律法之神,在囚虏时代最终由先知改造成充满仁爱、怜悯和公平形象的全能神。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上帝职能的不断全面,以及犹太教的社会功能的逐渐完善。囚虏之前,雅赫维无论是作为部落神还是战争神,他的社会功能都极为有限。而至士师与王国时期,无论是士师还是之后在王国时期出现的先知,无疑都更为接近下层民众的生活。囚虏之后,上帝关心的对象由亚伯拉罕的后代扩大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在众先知的口中,上帝对自我的称谓不再是“我是亚伯拉罕、雅各的神”或者“我是摩西的神”,而是说“以色列人哪,你们应当听耶和华的话”,对犹太人的诫喻从“你…”或“你要…”变成“你们…”或“人子啊…”。其次,上帝形象的丰满和职能的扩大还从雅赫维称呼的变化上直观的反映出来。族长时代称上帝为“主”、“我主”,摩西时代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到士师时代成为“万军之主耶和华”,王国时代更进一步称“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到囚虏时代及之后又称为“律法与万军之耶和华”。与之前相较,囚虏时代宗教对人的关怀在王国时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怜悯更多,上帝更容易宽恕人的过错。不同的先知在各自的时期对社会的观察和上帝的认识都是不同的。“皇室出身的以赛亚曾把耶和华当成是国王,阿摩司则把他对穷人的同情体验归因于耶和华,何西阿把耶和华看成是被遗弃,但对妻子仍念念不忘的丈夫。”。在先知的注意和发展之下,上帝除了开始关注公义、仁爱等品德,亦开始注重伦理的塑造与维护。
最后,宗教演进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表现为宗教领袖的平民化和祈祷形式的平民化。从祈祷形式上看,在巴比伦之囚以前,神与人之间的互动与沟通都是间接地。无论是族长还是士师,国王亦或先知,神都是与个别人接触,由单个人表达神的旨意来指导人事。因此,会堂形式产生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了神人之间间接的沟通方式,神与人的交流和人对神的体悟变得更为直接。神直接面对群体,人人都有机会通过祈祷领会神意。韦伯认为正是由于寄居异地,圣殿献祭的宗教义务被迫中断并就此不复存在,与之对应的是犹太国家中原有的祭司阶层消亡。“身为异地的客族,既然不必负担建造自己的神殿的义务,自然使他们获得了无比的移动自由。”从宗教领袖的社会地位上看,族长时代至士师时代的宗教领袖由部落族长或军事部落联盟的领袖担任,从摩西时代开始,宗教领袖只从利未落落中选拔,“你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在为各支派分封营地时,“有利未营在诸营之中”,说明当时并没有为该部落划定地域,而是将其置于圣所所在的地方,显示出祭司部落独特的地位。至士师与王国时代,祭司阶层完全成为城市贵族。巴比伦之囚之后,祭司消亡,先知作用凸显。众先知出身不一,社会地位也参差不齐。出身贵族的有以赛亚、耶利米等人,而出身微末的典型代表则是何西阿。反映出祭司阶层的崩溃,宗教领袖由利未人垄断继承变为道德和学识优异、关心底层社会状况的人担任,先知的来源开始多元化。
二、结语
以横向比较的视野审视囚虏时代犹太教的变化,会产生一种犹太教比较早熟的感觉。与西亚同时代其他宗教或信仰相比,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神宗教,犹太教的特点和差异性在囚虏时代完全凸显出来。紧密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宗教控制、权威的独一神崇拜体系、丰满的上帝形象和完善的宗教社会功能,以及犹太教平民化的发展趋势,都使得它排除了西亚中东地区那种混乱的、驳杂的信仰状态,真正走向了成熟。囚虏之后,犹太人开始了罗马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先知犹太教被拉比犹太教逐渐代替,犹太教的基本信条已然稳定并直至今天。
(作者单位:安顺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