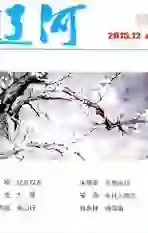辽东以东
2016-04-20芦刚
芦刚
1
其实妈妈本可以不去通远火车站抡板锹,可那段日子她总是对爸爸说自己有富余的力气。爸爸说,那也好,只是得管好这两个儿子。
妈妈答应好好的。等干起男人的活儿,妈妈哪顾得上我和哥哥。我这样叙述,目的在于替妈妈开脱。事实是,无论我怎样辩白,我双胞胎的哥哥最终还是丢了。
当初妈妈嫁给爸爸时,姥爷不给陪嫁。妈妈想找份活儿,不但能让紧巴的生活松口气,还可以在爸爸那里争个体面。
车站的人管装卸工叫“抡板锹”,清一色的男人。爸爸去求站长,站长不要,说装卸队只要带把儿的。等爸爸把乳房高高的妈妈往站长跟前推了推,站长高兴地答应收下妈妈后还跟了句,可以晚来早走。
我家离火车站三里路。我和哥哥每天用捉迷藏的游戏来伏击时间。哥哥好动,手脚不能闲着。哥哥每顿都要比我多吃,他饿得早。
那些天总有一个摇拨浪鼓卖糖豆的人反复从我家门前过,每次都会扔进两个糖豆。哥哥飞快捡到手,把其中一个咬成两半,递给我一半,之后他又飞快地把剩下的一半连同另一个糖豆一并扔进嘴里……
有一天拨浪鼓刚刚响起,哥哥就让我数一二三,他说他要藏起来。
我家大门每天都是妈妈上火车站前从外面反锁的,妈妈不让我们出大门,可那天的哥哥,鸟一样飞过了院墙。
拨浪鼓戛然而止。
就在那天,哥哥把自己藏丢了。
2
当天晚上,爸爸疯了一般,狠狠地打妈妈。看我哭,爸爸又开始打我。
爸爸不去火车站抡板锹了,他发誓说他一定得找到大双儿(哥哥)。他把炕头腾出来,铺上哥哥的被子。
爸爸走遍火车站附近的所有人家后,他开始跟妈妈要钱。起初妈妈挣了钱大部分给了爸爸,爸爸很快就把钱花光。再跟妈妈要钱,妈妈不给,爸爸就打妈妈。
爸爸知道妈妈藏钱,他回家一次便把柜子抽屉炕席底下连同墙缝像翻猪大肠一样统统倒腾个里朝外。不管妈妈怎样哀求,爸爸都要撕烂妈妈可怜的几件衣服,每次幸免的只有妈妈缝制的几双鞋垫。
这样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等我上了学,哭叫声依然在我家弥漫。有一天爸爸实在没什么东西可撕,眼睛只好盯在几双鞋垫上。
爸爸开始撕鞋垫,并且很快有了收获:他从鞋垫里撕出了妈妈私藏的钱。
爸爸自然又打起了妈妈。妈妈这次没哭。
妈妈开始允许站长摸她的手,妈妈求站长先替自己保管她抡板锹挣得钱。
后来的一次,爸爸薅下妈妈一缕头发。爸爸举着头发看了好久,觉得妈妈会把钱藏在发丝里。
等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爸爸整天呆在家里,不说话,像扣紧盖子的油瓶。
我每次放学都发现爸爸把耳朵紧贴在墙上。
墙上贴了我好多奖状,爸爸会把奖状抠出个小眼儿,他说小眼儿里还应该有哥哥的奖状。后来我再回家时,爸爸开始说他从小眼儿里看见了哥哥。我记不清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多久,我只记得,爸爸每天都把耳朵贴在奖状上,静静地听着什么。
爸爸目光空洞,但随便有什么声音响起,他的眼睛忽然闪动光亮,立刻循着声音奔去。到后来爸爸耳朵每天都提醒他到处跑到处翻,回到家,他会把手伸进炕头的被子里摸摸说,刚才明明看见大双儿在那里哭。
转过年的夏天,不知道为什么,雨水特别多,雷声频频。我很惶恐,因为雷声一响,爸爸就会把耳朵贴在墙上,他说他又听到了哥哥的哭声。
就在那个夏天,下最大一场雨的夜晚,爸爸被雷声惊起。他说他听到哭声了。
爸爸把手伸进炕头的被子,爸爸说被子是热乎的。他夹起被子,整个人就挤进了雨中。
3
再见到爸爸时,爸爸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一块苫布覆盖了爸爸。我躲在妈妈身后,看那块苫布。苫布下是爸爸被火车碾过的骨肉,像一堆打包的剩菜。
火车站的扳道工说,爸爸那晚搂着被子上了火车道,嘴里还不断重复着一个人的名字。一列火车鸣笛的那一刻,爸爸迎着火车跑去,火车的笛声瞬间拆卸了爸爸的身体。
打点了爸爸的后事,妈妈张罗搬家。轧死爸爸的火车是向东开的,妈妈想把家往西搬。我开始盘算着搬家的日子,我对方向充满了期待。
装卸队长大秦向妈妈透露一个秘密。
大秦说站长曾私下找他让他刻一枚印章,还让他去站上代领了800元钱。那800元钱最终又交给了站长。大秦说告诉妈妈,爸爸的死,火车站也摊责任,800元钱就是丧葬费。
妈妈想到了自己还有980元工钱也在站长那儿,两笔钱加起来就是1780元。天大地大的事,妈妈赶紧去找站长要。
站长含含糊糊,他让妈妈坐在站长室那张床上,他捧着印有红色火车头标志的茶缸嘘嘘地吹热水,茶缸堵了他的脸,两个眼珠像动漫一样在茶缸沿儿上转圈跑。站长说,只要你肯把家搬到火车站,钱的事好说。
妈妈说,我丢了儿子死了丈夫,不信钱还能长翅膀飞了。
妈妈决定搬家,一路向东。
爸爸死后,妈妈喜欢听到风的声音。妈妈说,风里有人在哭。
一个没月亮的晚上,站长带着拖拉机来为我们搬家。拖拉机的车斗很有特点。所说的车斗其实是一个拆掉了四面挡板的平台。平台四周有铁钩,铁钩上永远是一堆绳索,主要用于车站装卸大的物件。
开拖拉机的是大秦。
站长告诉妈妈,说大秦住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准。但大秦这个人特别会鼓捣让人心里舒服的事儿。站长让他临时代理装卸队长,准备找机会把他转为正式的工人。
里里外外能装的东西妈妈都让大秦往拖拉机上塞,站长说火车站那边的铁皮房子空间小,人去了,其他物件全没用。
大秦也劝,坛坛罐罐,带着绊脚,走起来碍事。
妈妈摸摸炕再摸摸墙,眼圈红起来。站长说,有你好日子过。
说着话,站长的手奔向妈妈的腰。
4
铁皮房子在车站后院,离票房子二十几步,是工人的宿舍。妈妈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站长说,先预留个地方放张大床。站长说到大床时眼神儿不停地抚摸着妈妈。
大秦殷勤地帮妈妈摆放物件。大秦愿意把几样东西往高处叠放,结果很小的铁皮房还是腾出了很大空间。
妈妈说,都是空儿,看着就有种没挨没靠的感觉。
大秦说,日后总会派上用场。
搬到火车站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睡得不踏实。我总听到站长在敲门。今天说擦把手,明天借块香皂。
大秦说,你那张床老给人留念想。
妈妈想把床搬走。
有一天站长老婆到我家喝口水,妈妈说非要把床送给她。
站长老婆说,你家这张床硬实,非得俺这大屁股的女人躺上去才接得住男人。
但站长老婆停顿了一下后忽然问妈妈,那你的孩子住哪儿?
去你家呀。
其实妈妈当时心里有底。
隔着我家一条街,有个八卦预测馆。妈妈经常悄悄溜进去听人预测今生和来世。去的次数多了,妈妈深陷其中,把自己的际遇讲给算命的。算命的瞎子刚握住妈妈的手就满口嗟叹。
他说只要跟你搭上手的男人,这辈子吃尽苦头。
妈妈追问,当官的也灵验吗?
瞎子说灵验。
屋里的女人们都向妈妈投去怜悯的目光。
妈妈却突然笑起来。
妈妈拉着床去站长家那天,妈妈硬是把我也带了去。
妈妈说,你给我儿子当干爸吧。
站长一脸茫然。
站长第四个女儿刚过百天。
站长老婆说,不用睡觉就白捡个儿子,认!
站长老婆强行把我留在她家,叮嘱我说,遇到人你就说,你爸是站长。
站长老婆说妈妈,听说你有一手看家的缝纫活儿,你找个人弄台缝纫机,上哪服装厂整些碎布头扎成鞋垫扎成垫肩,就当是劳动保护,我叫全站的人都得上你这儿买。你能扎多少我叫他们买多少,大不了有了赚,给俺那带官帽的甩几个酒钱。
那段日子,妈妈常常叹息。
大秦不停地追问妈妈,妈妈就把站长老婆的建议告诉了大秦。
当天半夜大秦就用拖拉机给妈妈拉来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
妈妈眼圈都红了。
站长老婆随后就把一包碎布头送到铁皮房。
妈妈卖出了好多鞋垫和垫肩,站长老婆每次给妈妈送碎布头的时候总是满脸汗水。碎布头是省城一家织布厂给乡下一家鞋帮厂发的货,站长老婆每次都从货场顺出一包大的扛到妈妈家。
接下来的事却有了变故。
工人反映鞋垫还有垫肩不好用,碎布头毕竟是碎布头,接头多,鞋垫还有垫肩上面棱多,咯脚,咯肩。
站长担心把事情捅大,任凭妈妈多给酒钱,决不再接受妈妈做的鞋垫和垫肩,除非妈妈改用宽幅的布料。
大秦说自己可以从站外进便宜的布料。
大秦果然给妈妈送来了一包乳白色的帆布。
妈妈只好把藏在裤袋里的钱不停地掏给了大秦。
铁皮房所有空间,都被大包的帆布塞得严严实实。
这回妈妈不但可以做鞋垫和垫肩,而且可以做套袖、围裙。
夜深人静,站长也在值班或空闲的时候,不停地来铁皮房擦手借香皂。妈妈想跟站长要回钱,一直犹豫自己迟早会顺了站长。
看着站长老婆实心实意为自己跑腿受累的样子,妈妈心里陡然添了愁事。妈妈想起算命瞎子说的话,终于心有不忍。
妈妈盘算着想离开火车站。搬家,继续向东。
站长室必须得去,妈妈暗下决心。
5
在站长室,站长并没有急不可耐地消费妈妈。
妈妈想起自己命硬的事,就诡秘地看着站长,妈妈觉得自己的身子变成来一剂毒药。
瞬间,妈妈变成剥了皮的香蕉。
淡黄的灯光下,站长忽然拍手鼓掌。
他绕着妈妈转,之后,他的目光停留在靠墙的保险柜上。站长拿起一个坐垫放到保险柜上,然后把妈妈放到保险柜上,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保险柜对面,自己慢悠悠坐上去。
妈妈站在保险柜上。
淡黄的灯光照在妈妈还很旺盛的身子。妈妈似乎被站长这种奇怪的嗜好冲击得神魂颠倒,妈妈有了异样的感受。
凝固的时间让妈妈难以忍受。
妈妈的目光并没有投向站长,而是投向窗外。
那天在站长室,假如妈妈的目光不是投向窗外,我也许会在车站健康成长。但妈妈毕竟还是向窗外望了一眼,是想告别一段生活,还是渴望得到拯救,一切都成往事。
必须肯定的是,妈妈目光投向窗外的瞬间。妈妈惊悚地看到路灯下的拖拉机平板车斗上站着一个人,正在向站长室张望。
是大秦。
妈妈从保险柜上跳下来,并野兽般撞开了站长。
站长悻悻地说,又不是新鲜玩意儿,怎么到你这还立上牌坊了。我是孩儿的干爸,我自己给自己戴顶绿帽子行不行。
敲门声在站长的叹息声中响起。
进来的是大秦。
大秦往站长手里递过一张表格。
站长问大秦,啥?
大秦说,转正表。
站长说,操。来的真是火候。站长去接表格,忽然觉得表格厚重,里面明显夹了什么东西,站长有了笑容。
大秦转身出门时,一列火车呜呜叫。
蜷缩在保险柜后的妈妈对站长说,把钱给我吧……我想出门找大双儿。站台上天天都有人迎来送往,我死不了一颗心。
站长坐回到椅子后,顺势把手扣到妈妈腿上说,不就是想坐火车吗,我负责变通。
6
站长认识火车上的人,他每次都能把妈妈送上南来北往的火车。站长指着火车,想坐哪趟就坐哪趟,不用买票,就当是你家的自行车。
妈妈开始在箱子里藏了一块黑布。
妈妈每找完一个地方,就拿出一片碎布头写上那个地方的站名,再在站名下用红笔工工整整写上火车的票价,并把票价描粗,然后用浆糊小心翼翼把碎布头粘在黑布上。横竖对齐,片片相接,而且行行相连。
由于站长的庇护,我的书读得很顺利,我那时刚上小学二年级,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
进入暑假,我说我也要找哥哥。怕我也会丢,妈妈翻出一根尼龙绳,一头系在她的手腕上,另一头系着我的手腕,我成了妈妈的风筝。
妈妈每次回家,不管有多累,都要找出剪刀、笔和浆糊,先剪碎布头,再写站名。但用红笔写票价时妈妈会在站名的上方和下方同时添上两个票价。做完这一切,妈妈开始在小楷本缝隙中(我用过的小楷本反正面都写满了字)往一起加火车票的总额。
妈妈告诉我,这些走后门儿省下的车票就算是你干爹在偿还他黑我们的钱。
我问妈妈干爹究竟黑了我们多少钱。
妈妈说,这些年我们坐火车省下的车票是1762元,你干爹还欠我们18元。不管找到还是找不到你哥,咱娘俩只能去一个18元的地方。
行程不能取消。
18元也是仇恨的价格。
就在那个暑假,站长频频来到铁板房,不断跟妈妈强化,假如妈妈愿意,他会立马赶走他老婆和四个孩子。每次临出门,站长总是在铁皮房里摸摸这,碰碰那,似乎在寻找什么。
有一天,妈妈去倒垃圾,忽然看见垃圾里有耀眼的白纸屑,妈妈蹲下去看,脸也瞬间耀眼的白……那是撕碎了的职工转正申请表。
我和妈妈到底也没能去成一个18元的地方。
我是在凌晨3:00点离开通远火车站的。
那个凌晨,站长家忽然乱成一锅粥。站长老婆和孩子被闹闹哄哄的一群人用车匆匆接走。车子响马达时,站长老婆和孩子的哭声难分彼此。
谁也不叫上我,谁也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因为急促,甚至来不及关上房门。那一刻,整个屋子死亡般沉寂。我不敢大声呼吸,我想稳稳神儿,悄悄听一听沉寂背后的声音。
以我当时的年龄,无论如何我也没有能力抵抗黑暗。我把别人的枕头强加到我的头上,我想让自己快速晕眩,或者快速睡去,设法让自己成为黑的部分,或者成为沉寂的部分。
最终,我没能睡去。我被一个人从被窝里揪出来,像鸟窝里刚掏出的雏鸟。
后来听到风声。
我被人扛在肩头,厚厚的肩膀抵住我的肚子,我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穿过小道,拐过几个街角,我在漆黑的夜里最后砰一声被扔到拖拉机上。
扛我的是大秦。
大秦快速抓起摇把,然后用摇把指着我说,搂住你妈,松手就摔死你!
大秦急速发动了拖拉机。
我本能地搂住妈妈的腿,日子瞬间起起落落。
天开始放亮。
拖拉机那个平板车斗上,左右各放着两个帆布口袋,我碰上去硬硬的,好像铝线和铜线。妈妈平躺在两个口袋中间,手被细绳捆绑着,妈妈看到我,身子剧烈扭动,我看见妈妈嘴里塞了一团碎布头。
拖拉机颠簸得很厉害,我想靠近妈妈的头为妈妈掏出碎布头,我不停撞到两面的帆布口袋,有两次险些摔倒口袋上。妈妈开始可能希望我为她掏出口中的碎布头,后来看我险些一次次被甩出车外,妈妈又痛苦地仰躺下去,不再睁开眼睛。
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盼望妈妈快点把真相说给我。
可妈妈不说。
妈妈嘴里那团碎布头堵住了所有的话。
很多年后,我凭着几页发黄纸张上断断续续的文字拼凑成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辅助几个退休铁路工人的回忆和推断,勉强理清了那天晚上发生在通远火车站那起盗窃伤人案的相关脉络。
因为车站连续发生失窃,大量铜线和铝线被盗,站长决定蹲守。
就在那天夜晚,埋伏在夜色里的站长与肩扛铜线的大秦不期而遇。
大秦根本没有给站长喊叫的机会,迅速挥动一把板锹,利落地劈倒了站长。
意犹未尽的大秦并没有急于逃跑,而是从容地蹲在站长身旁,一字一句告诉躺在黑暗中的站长,我马上去铁皮房,顺便偷走你的女人。
在铁皮房,妈妈是挣扎过的,但妈妈躲不开大秦的力气。
妈妈问大秦你要把我带到哪里?
大秦说,东面。
妈妈问大秦要走多远?
大秦说,向东,一直向东。拖拉机油箱里的油在哪耗光,咱就在哪安顿。
8
我是在一个乡道的拐弯处失去妈妈的,或则说是妈妈失去了我。
我记得大秦把拖拉机开得飞快。一路狂奔,硬是将黑夜开出了亮色,我搂住妈妈的腿,我的双臂渐渐失去感觉。其间我从没有放弃去掏出妈妈口中那团碎布条的念头,我在努力,但我不敢松开搂住妈妈腿上的手。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是,东方一片白的时候,我发现妈妈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小,甚至不再挣扎。
大秦开始回头看着平板车斗,看着帆布口袋以及夹在帆布口袋中间的妈妈和我。大秦开始吹口哨,后来干脆唱起了现代样板戏《沙家浜》的一段:
新四军久在沙家浜
这棵大树有荫凉
大秦的腔调一浪高过一浪,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拖拉机的排气管那一刻也卖力地配合大秦,喷着烟,并且一刻不停地在喊“到到到到到”,可大秦的目的地始终不到。
拖拉机进入一个很大的缓坡时,我忽然感到妈妈的腿在扭动,并且想挣脱我的双臂。见我不松开手臂,妈妈开始利用小腿左右挣脱,这样一番用力的摆动,我感觉我的手臂恢复了知觉,我明显感到双臂发麻而且乏力。我开始没有力气搂住妈妈的小腿肚子,随着拖拉机的晃动,我的手臂渐渐滑落到妈妈的脚踝处。
偶尔有车与我们交汇。
妈妈一直闭着眼睛。风掠过妈妈身体,妈妈身子微微抖动。两侧的树和田地与我们忽远忽近,来时的路,蛇一样蜿蜒摆动。这些越来越陌生的树木、青草和花朵变得梦一样迷离。
一路向东。鸡冠山、凤凰山、五龙山与我们擦肩而过。这是我后来从《旅游手册》看到的名字。我重走了这条路,当年我和妈妈经过的地方如今都已成为旅游景点。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年前,大秦竟然带着妈妈和我,一路向东,仓皇逃窜在一条美丽的风景线上。
拖拉机的速度明显开始减缓。我看了一下路,前面即将驶向一个大岭,在靠近大岭附近是一个急弯,急弯处绿草茂密,期间点缀着红红的马蹄莲。
一辆拉着木头的车经过我们的拖拉机,尖锐的刹车声撕裂了时间。
因为路窄,车身经过我们拖拉机的瞬间,带来尘土和急促的风。尘土在那一刹那对妈妈来讲,肯定不会有任何意义,但风则不同。我确信那阵忽然卷起的风一定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给妈妈带去了神谕。妈妈扭动双脚摆脱了我环绕在妈妈脚踝上的手臂,我身体挣扎着往妈妈脚前扑。
就在此刻,妈妈急促地往回缩了腿,旋即猛地用力蹬向我。就在拖拉机拐弯减速那一刻,我看见妈妈冲着我诡异地一笑,我被妈妈瞬间蹬出了拖拉机的平板车斗……
就从那个夜晚开始,我丧失了故乡。
多年以后,我如期长大。重回通远火车站,我仔细翻动记忆中的隐痛。站长已经故去,因为当初大秦的那一锹,站长虽然没有送掉性命,但丧失了大部分记忆,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癫痫病,他是在听到一个消息之后,因兴奋引起癫痫病发作而离世。
这个消息与大秦有关。
一天夜里,车站停着一列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凌晨一点,大秦窜上了火车。妈妈本来趴在火车下负责望风,平常这个时段根本没有火车过,偏偏相邻的火车站有辆火车头出现故障,结果,一辆负责维修的火车头在夜色中驶过通远火车站。
火车头就从妈妈身旁经过,巨大的碾压声让妈妈变得异常兴奋,妈妈从藏身的地方冲出来,全力追逐疾驰而过的火车头,妈妈不断摇动着双臂,连续不断在喊叫着一连串的名字,尖锐的喊声刀一样划向夜空。
大秦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妈妈的啸叫,他正专注于火车里复杂多样的物资。大秦后来准备跳下火车时,铁路公安已经将他逼住。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这些人谁也没有扑上去抓捕大秦,而是在大秦缓过神儿抓起随身携带的一把板锹的刹那间,警察从容开枪,将大秦击毙在火车上。
我是在妈妈发黄的笔录中读到与妈妈相关的人和事的。
在我不断追问妈妈下落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车站派出所当晚抓住了妈妈。妈妈开始还能说出很多事,但后来,妈妈开始狂躁。妈妈说她是顺路寻找,她说她要找的人就藏在18元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妈妈开始砸东西,她甚至脱光了衣服跳到桌子上惊恐地向外张望。
有一天,警察开开门,拎着茶缸出去找热水。
警察回来后,妈妈不见了。
跟哥哥当年捉迷藏如出一辙,妈妈也把自己藏丢了。
多年来我形成一个习惯,每年都到通远火车站,每次都逗留一些时间。最近我还去过那里。火车站刚刚经过改造,往日的痕迹越来越少。站长是新到任的一位女性,据说是当初那位站长最小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