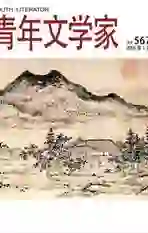从精神分析角度论父亲与卡夫卡的成长和创作
2016-04-19赵倩
摘 要:本文着力以精神分析的角度从父亲对卡夫卡所产生的影响去观照卡夫卡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和父子冲突主题;透过卡夫卡的成长去找寻其作品背后的现实生活根源,以求更加全面真切的认识卡夫卡、理解卡夫卡,同时通过对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梳理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利论证。
关键词:卡夫卡;父子冲突;精神分析理论
作者简介:赵倩(1982.3-),女,籍贯:河南郑州,硕士研究生,高校讲师,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写作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校主要从事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3
卡夫卡与弗洛伊德同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焦虑的时代。一个是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的精神与困惑,有“现代文学之父”声誉的伟大作家,一个是“以害俗惊世的文论和博大精深、大胆新颖的思想,使一个时代的观念、生活和想象发生了一场革命”[1]的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强调研究艺术家的人格,探究艺术家的深层意识与作品的关系,他认为艺术创作的动力来自原始的性欲望,来自幼年形成的俄底浦斯情结,因而艺术创作活动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作家的创作冲动来自心理底层的无意识领域。在他看来,在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中,以俄底浦斯情结为核心的幼儿心理经历具有普遍而深刻的意义。在文学巨匠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中,对于父亲的优越地位的态度不是在“日常的思考”中形成的,他将“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亲身经历到的”一直留在心里。卡夫卡在三十六岁的时候,鼓足勇气写出了《致父亲》,并借着这封信,将自己三十多年来所受的父亲的压抑和盘托出。父亲这样一个角色究竟在卡夫卡的成长和生活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在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中烙下了什么样的烙痕,有着怎样的体现?寻着这些问题,本文着力以精神分析的角度从父亲对卡夫卡所产生的影响去观照卡夫卡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和父子冲突主题;透过卡夫卡的成长去找寻其作品背后的现实生活根源,以求更加全面真切的认识卡夫卡、理解卡夫卡,同时通过对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梳理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利论证。
一、卡夫卡的成长于父亲
卡夫卡几乎一生于父亲不合,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在《致父亲》这封长信中,依然细数从幼年开始他一生无法挣脱的父亲的阴霾。“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您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仿佛只有在您覆盖不着的地方,或者在您达不到的地方,我才又考虑自己生存的余地。根据我的想象中您哪庞大的身躯,这样的地方并不多,仅有的那些地方也并不令人感到多少欣慰。”[2]卡夫卡的一生是不间断得与父亲斗争的一生。在幼年卡夫卡的眼中,父亲强壮、高大、肩宽,而自己却削瘦、弱小、肩窄。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父亲卡夫卡充满了崇拜和敬爱,他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强大的父亲而倍感骄傲,但同时又为自己的成长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父亲强大的身躯内包裹着强悍的性格,性情粗鲁霸道、专横暴虐。对卡夫卡来说“父亲的教育就是百般的责骂,诽谤、污辱……”[3]。父亲的强悍使弱小的卡夫卡觉得自己宛如草芥,卑微可怜。在这人生第一场与父亲的斗争中,还没开战,卡夫卡就觉得“我们之间无所谓真正的争斗;我总是很快便败下阵去,剩下我便只有逃避、愤懑、内心冲突的份儿。”[4]便败下阵来。
卡夫卡没能走出于父亲的斗争,却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云的笼罩,敏感的卡夫卡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与不安中,一生苦于困惑,无法与自己的父亲沟通。这个被父亲彻底击溃的小男孩背负着父亲的阴影,走入了他一生的困苦。卡夫卡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则是一种无限的内疚。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无法突然改变我的这种心理状态,反而对他们怀着更深的内疚。正如我说过的,我得弥补您在业务方面对他们犯下的罪责,酿成那些罪责,我也有责任。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哪怕匍匐在他们脚下舔他们的脚,也永远抵消不了您这个老爷从上面对他们劈头盖脸的一阵乱砍滥杀。”[3](P47)卡夫卡不仅要逃避父亲,对于家庭,甚至对于自己的母亲,卡夫卡也充满了歉疚而不得不去逃避。虽然卡夫卡也感激与母亲对自己的爱和保护,但他更苦恼与母亲“她为事业、为家庭辛勤操劳,家里一人得病,她受双重的痛苦,而这一苦痛中之最甚者,莫过于她夹在我们和您中间两头受罪了。她对您一向很温存,体贴入微,在这一点上您跟我们完全一样,可是您很不体恤她。我们肆无忌惮地烦扰她,您是从您那一边,我们则从我们这一边。……她为您的缘故受了我们多少罪,而为了我们的缘故受了您多少罪呀!”[4]P49)
弗洛伊德认为:“在青春期,有一种很强烈的情感的流露以反应俄狄浦斯情结;但是因为意识已经知道严于防御,所以这些情感的大部分不得不逗留于意识之外。一个人从青春期起就必须致力于摆脱父母的束缚,只有当这种摆脱有所成就之后,他才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成文社会当中的一员了。”[5](p268)卡夫卡备受着来自父亲,家庭,母亲,朋友各方面所产生的罪责和内疚。弗洛伊德说,在受到一种旨在压抑某种矛盾冲突之后,“自我”受到震惊而退缩回去,从而阻止该冲动跑到意识界,并不让它的动力宣泄出去。结果该冲动所带来的“力量”还是原封不动,这就使发泄不掉的“潜能”受到压抑。这种被压抑的潜能构成潜意识。卡夫卡在成长之初便郁积了其难以负荷的罪责和内疚,弗洛伊德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从对于童年生活经历的发掘发现人类潜意识的基本成分髂前就是幼年生活的凝缩物。
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可能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父亲庞大的身影将卡夫卡渺小的身躯、微弱的自尊和生活的理想一同踩在了自己那硕大无比的皮靴下面,卡夫卡“并不是面临婚姻问题我才检验自己,而是在每个小问题面前都在检验;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过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向我证实我的无能,正如我尝试着棉鞋的那样。每件小事中正确无误并证明你有道理的”[1](p115)。长此以来卡夫卡成了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单为他而发明的。他为了获得生活抛弃了生活而无法畅所欲言。以致卡夫卡在所有人面前都失去了语言表达的能力,结结巴巴知道不能说话。对父亲的畏惧使得父子之间出现距离,父亲的权威阻碍了交流,从而使父子之间产生隔膜,而这种隔膜在卡夫卡的生活中蔓延,从而构成了卡夫卡与生活的隔膜。卡夫卡的一生充满了悖谬:内省与冲动,懦弱与顽强,绝望与救赎。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他有一个强大不可撼动的父亲。
二、卡夫卡的创作与父亲
“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面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2](P72)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不过是艺术家在原欲支配下制造的幻想,是原欲的补偿。“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是因为人们必须放弃现实生活中某种本能的需求而痛苦地从享乐主义转到现实主义这一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神经质病的人一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她自己想象力造成的世界中。”[3](P69)所以卡夫卡选择了写作,卡夫卡将他的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由此建筑了他自己想象的王国的避难所。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并不只是静静地躺在心理结构底层的、暂时被忘却的东西,它更多的是被压制的动机和情感的聚集。它们来自于过去的生活事件,其中主要是儿童期性发育过程中的创伤性经验。所有这些被压抑的心理都有十分强烈的要求出路的愿望,企图得到发泄和表现。于是乎,艺术家的创作活动都成了这种发泄和表现。
在卡夫卡的创作中,父子矛盾一直是卡夫卡的重要主题。正如他在《致父亲》当中强烈的控诉一样,在他的创作中,卡夫卡把自己描写成他父亲的牺牲品——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压根儿就不写其他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所经历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刻画了赫尔曼似的父亲的形象。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母沙一天早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完全不能动弹了。祸从天降到这个终日疲于奔命的小职员的身上,然而即使变成了虫,格里高尔还想拼命起来赶火车上班,还想着拼命工作去养家糊口,但家人对于他的突变的反应却令人错愕:秘书逃跑,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恐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母亲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但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视他为沉重的累赘,因此悲痛欲绝。即使是最亲近的妹妹在一段时间之后千方百计想要摆脱他。格里高尔 最终“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中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萨姆沙一家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
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写了一个人变甲虫的看似荒谬的故事,在《致父亲》中,卡夫卡讲了这样一件事情,父亲将他并不认识而卡夫卡喜欢的德国犹太人演员洛伊比做甲虫。卡夫卡对于这样一件事情一直记忆深刻:“我得父亲这样评论我的朋友(此人他根本不认识),只不过因为它是我的朋友罢了。”[1](P19)弗洛伊德说“一个强烈的现实事件在诗人心中唤起了对一个更早的、多半属于儿童时代的事件的回忆,正是从这一儿童期的事件中萌生出愿望,这愿望又在如今的作品中得到满足。”[2](P108)卡夫卡所谓的于父亲之间的相互斗争存在着两种斗争形式。“一种是骑士式的斗争,与自立的对手较量,各归各,胜败自负。还有一种是虫豸式的斗争,虫豸不仅蜇人,而且为了生存还要吸血。这是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的你缺乏生活的能力,可是又要过得舒服、无忧无虑、不需要自责,于是你便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一切生活能力并将之揣入口袋。”[3](P19)这就是卡夫卡“虫豸篇”的根源之所在。
弗洛伊德把艺术家与精神病人等类同视,认为他们都是用幻想来补偿自己的原欲对象的丧失,只不过精神病人是用肉体的方法来摆脱兴奋状态,不能以精神方法来处理,艺术家却能将艺术用来缓解自己的兴奋状态。精神病人一旦沉溺幻想就不能自拔,艺术家不过比精神病人懂得如何再度把握现实。如果拿《变形记》和卡夫卡的性格个经历相对照,也会发现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卡夫卡以他独特的创作,继续着他与父亲的斗争,完成这他挣脱父亲的夙愿。
《判决》是一部感情如狂风骤雨的短篇。生病的父亲对儿子百般挑剔责难,不管儿子有多善良、顺从,父亲却视他如魔鬼,并在儿子与其朋友之间的交往中扮演了一个挑唆者的角色,在激烈的对决摊牌之后,父亲对亲子做出了溺刑的判决、要他永远消失,最后更从病床跃起像要攻击他,导致惊恐的儿子夺门而出,走上了孤独的大桥上纵身一跃而下。直到最终儿子还轻声呼喊:“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然后纵身跳下落水致死。小说十分突出的表现了作者对父母尤其是对父亲的那种爱恨交加的情感。年轻的儿子因为父亲的判决投河自尽,这恰恰是卡夫卡心理的自传。正如弗洛伊德的作家与作品中人物的同一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场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结底是“自我”。正常的人都会对外来压力进行抗争,不屈服于他者的虐待,而卡夫卡长久以来潜意识中的负罪感和内疚感让他甘心承受无味的惩罚,在他人眼中被剥夺了作为人的生存资格,成为附属品。所以我们看到,人或者走向“异化”变成一只可怜的甲壳虫,或者走向死亡。《美国》是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16岁的少年卡尔·罗斯曼受到中年女仆的引诱后,被父亲放逐到美国的生活经历。这部小说中父亲的形象虽然没有出现,但父亲的权威和力量却依然不可忽视。
结语:
卡夫卡说他要在地球上爬着找到一块清洁的地方,有时,阳光会照耀到那块地方,便可以得到一丝温暖,写作成全了他的理想。卡夫卡把他的作品作为从父亲身边逃脱出来的一种企图。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抑制的经验的回忆。回忆恢复了过去被潜抑的经验的动力,从而产生了要求补偿实现它的愿望,对受创经验的回忆是创作的契机。通过对卡夫卡成长的梳理,我们更加真切地理解了卡夫卡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和父子冲突问题,以及卡夫卡作品背后的根源和潜在的隐喻。卡夫卡在《致父亲》对父亲坦言:“我的作品写的都是您,在这些作品里我只是倾吐了我不能向您的胸怀倾吐的悲伤。这是一次有意持续很久的告别,除了它,尽管确实是您强加给我的,但去向却是我决定的。”(p123)尽管父亲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努力似乎有些不屑一顾,总是用“把它放在床头柜上!”打发,送书过去的卡夫卡,但卡夫卡依旧能从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短暂的满足。他用这样一种方式在有限的空间里证明着自己的存在。
注释:
[1]沃雷姆.弗洛伊德.前言[M].黄欣等译.昆仑出版社,1991.
[2]卡夫卡.致父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卡夫卡.致父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卡夫卡.致父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