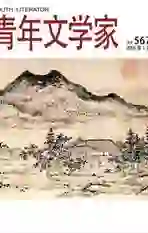余华小说主题研究综述
2016-04-19杨明辉
摘 要:论文总结了余华80年代以来发表的小说的创作主题,将其归纳为“暴力主题”、“生死主题”、“苦难主题”和“善恶主题”四种,分别将近年来的研究者对这四类主题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进行研究整理并做出综述。
关键词:余华;主题;暴力;苦难
作者简介:杨明辉,女,硕士研究生,山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2
余华发表的小说数量并不多,然而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价值,论文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四大主题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综述,并以此作为对余华小说主题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暴力主题
暴力主题尤其在余华八十年代的小说中频繁出现。在《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等小说中均有对暴力场面的露骨描写,内容包括手足间的虐杀、吃人的残忍画面以及残酷的刑罚场面等等。近年来对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主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切入:余华小说中暴力主题的呈现特色、暴力主题在余华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原因、对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主题的评价。
余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后的暴力主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中,余华更加青睐暴力主题。对于余华对暴力主题的呈现方式,研究者多结合具体作品给予描述性的评价。通常认为,暴力主题在余华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已经初露端倪:独自出门远行的年轻主人公试图主持正义的英勇行为被村民的暴力行为粗暴阻止,从此开始接触到了真实人生的荒诞面目。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余华表现出了对暴力主题的痴迷,此类作品的情感基调是冷峻的黑色,对暴力的呈现是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零度书写”,对暴力行为的细节刻画细致入微,甚至被研究者普遍认定有一种对于暴力的痴迷。九十年代后余华的创作更多着眼于苦难命运对人的折磨,对直接的血淋淋的暴力行为着墨较少,蒋蓉将余华八十年代创作中的暴力主题归纳为“个人的暴力”,而九十年代的暴力主题则是“命运的暴力”[1]。
对余华小说中频频出现暴力主题,及其呈现出的独特特色的原因,研究者通常从如下几个方向进行解释:一方面是童年经历的影响,余华来自一个外科医生家庭,童年时期与外科手术室、太平间等场所的零距离接触,导致灾难和血腥在他记忆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也造成了他从小就对血腥和暴力有着天然的更大的接纳度;另一方面是工作经历的影响,余华曾当过五年的牙科医生,对人的生理结构非常熟悉,也就对痛苦和暴力表现得更为冷漠;另外,出生在60年代初的余华承认文革对他个人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文革成为他最初经历的社会事件,为他的童年镀上了灰色和血腥的色彩;最后,余华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周建华认为“川端康成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述,卡夫卡思想的跳跃深深地影响了余华关于小说的认识”[2],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余华对暴力主题的异常敏感以及独特的呈现方式。
对于余华80年代的小说中集中出现的暴力主题,正面的评价认为其以零度视角冷静客观地刻画暴力行为的独特方式,将暴力归结为人性中的一个方面,有对历史和人性独特挖掘的独特作用,然而也有不少负面的评价,认为余华80年代的此类小说只是暴力行为的简单堆砌,仅仅只是一种发泄和寻求刺激,是文明的倒退。
二、生死主题
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余华的小说鲜有不涉及死亡的,研究内容多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研究生死主题的叙述特点及其转变。余华前期和后期对死亡主题的不同处理方式成为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惠静的《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分别探讨了余华前期和后期的死亡叙事的表现方法和特点,认为前期侧重于对死亡表象的描写,善于运用荒诞和戏剧的方式来展现死亡,乐于刻画个人化死亡体验的想象,后期的作品中,“死亡变成了一种生存状态的假设,他不再事无巨细地关注死亡的过程,更多地关注死亡背后的形而上的东西”[3],表现出悲天悯人的生存关怀,然而对这种转变的原因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从整体上讨论两者的内在关系;常智娟的《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论余华小说中死亡主题的嬗变》从死亡表象、死亡思考和死亡承受三个由表及里的方面探讨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主题,从前期到后期其实是余华对死亡的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前期的小说主要是刻画死亡的表象,后期的小说开始对死亡产生思考以及思考承受死亡的方式;周述波的《死,而后生——余华小说与存在还原》将生死问题拆分成A、B面,认为余华80年代的创作直面生死的B面:死亡,90年代的创作直面生死的A面:生存,并探讨了生死的转化还原关系;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者对这种转化的原因做了讨论,认为这种转化不光与余华个人经历和风格的变化有关,还与时代风气的转化直接相关。
研究生死主题中表现出的生命意识。对生命意识的探讨常常与对死亡的叙述方式的探讨联系在一起。从生死书写方式的变化可以考察出生命意识的变化。研究者对余华前后期生命意识的变化轨迹的认识是大致趋于一致的,认为前期的作品对死亡的展现常常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将死亡看作是暴力的结果和暴力的最高形式,而展现暴力和死亡的人物往往只是作为一个符号,成为一种动物性的生命存在;后期的死亡,如《活着》中有庆的死、凤霞的死、《许三观卖血记》中阿方和阿龙的死,往往与更大的时代悲剧结合在一起,包含一种宿命感,死亡成为生存的一个环节和最终的结局,开始关注人物面对死亡的态度,因此人物不再仅仅进行着动物性的生命活动,而是进化成为了有着独特生存哲学的生活活动。这种独特的生存哲学被有些研究者归纳为一种“宿命观”,甚至被认为与道家有关,刘颖的《余华小说中的道家人生哲学》认为余华的这种宿命观与道家“安命无为”的哲学思想有着相似之处。
比较余华和其他作者对死亡主题的呈现。这一类研究将余华小说中的生死主题同其他作家的生死主题进行比较,这一类的作品有郭运恒的《向死而生——也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蕴》、张润的《死亡与痛苦的大胆展现——海明威与余华创作主题之比较》、王亮的《死亡之美——川端康成和余华死亡创作主题之比较》、潘超的《三岛由纪夫与余华作品中的死亡意识比较》等。从死亡主题产生的根源、死亡主题呈现的方式、不同的生死观等各个方面,对余华和其他作家的死亡主题进行比较,进而在历史和国际的坐标中标定出余华死亡主题呈现的独特定位。
三、苦难主题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总是生活在一种由个人生活悲剧和时代悲剧编织而成的无法逃脱的苦难境遇中。对于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主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研究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主题前期和后期的不同内容及苦难的根源。大部分的研究者认为余华前期小说中的苦难直接与暴力和死亡相关,其根源是一种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之后的人性恶,是基于动物性的一种人类的宿命;而后期展现的苦难与其说是死亡带来的,不如说是一种对生存的承受,余华展现出了活着即为承受苦难的主题,因此反而对苦难产生出一种理解之后的超然,甚至在苦难承受中体现出一种温情的倾向。因此余华前后期的苦难主题的表现呈现出了不同的情感色彩,前期是黑色血腥的,后期则是温存厚重的,这与余华前后期对苦难根源的理解不同有关。
更具意义的研究是锁定余华对苦难的特殊的叙述学的处理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使得研究者得以统摄余华前后期看似不同的苦难主题内容的背后一脉相承的更深层次的苦难观。一种独具意义的看法是余华对苦难有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呈现:论文《苦难的衍生与超越》认为《活着》里“我爹”蹲在茅坑上死去的情节,《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向许玉兰求婚的情节、每次卖血之后心心念念的“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等情节都在展现巨大苦难的同时带来了一抹可笑荒诞的色彩,用一种与悲苦相反的色彩来反映悲苦。《命运·苦难·反启蒙——论余华小说创作的民间故事》认为余华运用了一种“说唱”、“童话”和“传奇”的民间文学叙述方式叙述苦难,余华讲述的是民间的故事,也采用了一些传统的民间叙述方式,小说《活着》的叙述者是一个民歌采集者,他与福贵的交谈中加载了很多民歌,民歌的古老悠远极大地冲淡了福贵叙述的故事的悲剧性;《在细雨中呼喊》采用童年主人公的视角叙述故事,忧郁敏感的童年心情取代了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兄弟》中强烈的悲剧冲突可以被看作孩子间的游戏;将小人物的人生经历书写成具有戏剧冲突的传奇故事,也在用剧情稀释着苦难的浓度。论文认为余华“借助于民间传统的表达方式和技巧完成了对民间苦难的寄托和消解。”[4]如果说余华前期的作品直面暴力,那么后期的作品则是用叙述技巧巧妙地软化和淡化了苦难的悲剧性,让读者在直面苦难的前提下关注更深层的生存哲学。
郜元宝认为,无论是余华前期对暴力的赤裸裸的书写,还是后期对苦难的平静回忆,看似是一种对苦难的无动于衷,实际上都是避免了传统文化习俗中对苦难的习惯性回避,“目的就是要在小说中把这些欺骗蒙障之物统统揭除,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正视苦难。”[5]这正是余华独特的苦难主题的叙述方式的意义所在。
四、善恶主题
善恶主题的展现体现了余华独特的人性观。对余华小说中善恶主题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有如下几种:
其一是研究余华前后期不同的人性观。研究者多认为余华80年代的作品在对暴力的持续关注中贯彻了“人性恶”的观念,塑造了一个个由无法抗拒的人性的暴力冲动而造成的生活悲剧;而后期的作品更倾向于一种温情的叙述走向,或者说开始信仰“人性善”,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余华此时的人性观仍然是灰暗的,但对人性的思考更趋近现实,更加复杂化。
其次是研究人性恶的类型。这一类研究通常将余华笔下的恶分做不同的层次,最常见的一种将恶分为了“人性之恶”和“人世之恶”。人性之恶一方面源于人的动物性的残酷天性,有《现实一种》中的四岁的皮皮对弟弟的源于一种生理冲动的残忍虐杀,另一方面源于成人的欲望,如《兄弟》中的“选美大赛”;人世之恶则是特殊的时代背景造成的人群的恶意,这种恶意看似不如人性之恶来得赤裸裸,但它对人的戕害却更为恐怖,如《在细雨中呼喊》中逼死王立强的人们的恶,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批斗许玉兰的人们的恶,这种恶可能来源于作者对“文革”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记忆。
对于人性善恶开掘的深度,《人性恶的证明——余华小说论》认为与其他表现人性恶的大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余华虽能够直面丑恶,但缺乏将丑恶上升为到人性分析的高度。
综上所述,余华小说的暴力、生死、苦难、善恶主题虽有不同的侧重,但内在精神是相通的,且对每一个主题的呈现都因其小说创作的前后分期而呈现不同的特色。然而认真思考,便可看出在不同主题和分期的背后,是余华一以贯之的对人性和生存的冷静深入的思索。
注释:
[1]蒋蓉《暴力与温情——试论余华的先锋小说》,载《合肥学院学报》2012.
[2]周建华《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页.
[3]惠静《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载《延安大学学报》2011.
[4]宋晓培《命运·苦难·反启蒙——论余华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5]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载《文学评论》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