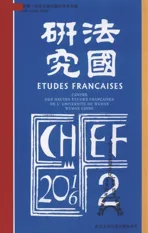论德里达解构主义于哲学与文学间的延异
2016-04-17于艳玲杨卿
于艳玲 杨卿
论德里达解构主义于哲学与文学间的延异
于艳玲 杨卿
【摘要】本研究从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哲学渊源入手,界定解构的概念及其实质并详细阐释文学本质、文学与哲学关系,同时,通过对其文学理论文本焦点的关注探讨了结构主义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延异。
【关键词】解构 延异 散播 哲学 文学
[Résumé]Nous nous proposons d’interroger les origines théoriques de la déconstruction derridienne avant d’êtres fixés sur l’essence exacte de la notion.Tout cela se fait dans le but de cerne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littérature et la philosophie.
【项目】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项目:2015VI037
雅克·德里达(1930-2004),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自柏拉图以来,许多哲学家都认为存在着某种终极的、客观的和外在的绝对参照物。而这种绝对参照物也就是一种中心结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持“逻各斯中心论”和“声音中心论”,而他也被称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之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以法国为中心,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普洛普、热奈特等学者将这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以及文本叙事方式等文学研究的领域,形成结构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文学符号学等文学理论。而几乎是与此同时,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确切的说是1966年10月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的报告《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直接对结构主义之父的列维·斯特劳斯发难。对结构主义的质疑首先集中在对结构的经典性概念提出质疑,对中心论的绝对性和神圣性质疑。他认为结构的结构性总是被赋予一个中心,某种固定的源点,无组织的结构是不可想象的。他指出,这种中心关闭了那种由它开启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游戏。解构就是结构内在的自行解构。这种预设的中心、整体、逻辑都是人为的,都有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因此,都会自行解构。同时德里达也尖锐的指出结构主义这种对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的依附。此后,在继承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的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的基础上,以《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三本解构力作建立起了解构主义哲学观,解除了以“在场”作为理论的思维起点,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权势之下释放了出来,奠定了其文学观的哲学理论基础。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一文中,以隐喻为突破口,消解了哲学和文学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哲学文本中的封闭性的意义,被视为与文学一样,不过是遣词造句的一种效果。
一、解构主义文学观形而上学之基础
(一) 解构性
解构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他提出了“解构”或“消解”这个概念,并由此形成他的“消解主义”。它是一种反结构主义的姿态,结构要被破坏、分解和排除沉淀物(各种类型的结构:语言的,“逻各斯中心论”和“声音中心论”)。德里达又指出:“解构不是一种否定性活动,与其说它是一种破坏,不如说它是为了理解一个‘整体’如何被构成以及如何重新构造整体。消解或解构并不同于分析或批判,拆散结构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批判。”①D.Wood , R.Bernasconi, Derrida and Difference.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其次,他还对结构主义者关于结构具有整体性的观点提出批判。他认为整体性意味着结构中的某一方终是处于主导地位,而语言这个邻域本身就与整体性相排斥,语言这个邻域实际上是一个无限游戏。一切都是在不断延缓的差异中形成。
因此,德里达提出“游戏论”来对抗“结构中心论”,用“意义链”概念来取代“结构”概念。“游戏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运动和自由活动的存在,强调无法确定的东西的存在,反对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意义链既无起源,也无终结,既无中心,也无整体性,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②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 32页。
(二) 符号、意义观和“异延”理论
德里达解构主义符号学意义观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重复性使符号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进入一个可以任符号自由游戏的开放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谓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符号之间可以无限替代,意义可以无限游离、散播(dissemination)。然而散播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意义未完成状态,意义在不断溢出的同时也在损耗自身,像播散的种子一样“无度的分散于外部”③Jacques Derrida, “Linguistics and Grammatology.” Critical Theory Since1965.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他否定语言的同一性、一元性及确定性,认为语言与所指物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存在纯粹的所指,没有任何连续性的指称,意义具有流变性、不稳定性和多元性。
“补充”是德里达解构理论的重要概念。“补充”一词来自于卢梭关于“教育是对天性的补充”观点。因此,在卢梭那里,“语言被制作出来是用来讲话的”,书写仅仅是“言语的补充”。然而,作为补充的东西也就成为被补充之物的本质性条件,这样补充和被补充之间的绝对界限消失了,言语和书写之间的界线被消除了。将书写视作言语的补充而将之弃置一旁是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的杰作,这同时也在消解形而上学自身。原来有内在结构的文本在德里达那里成了无限开放的东西,文本里的东西不断的涌现出来,文本外的东西不断涌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文本的“意指链”。因此,德里达说,收信人“死了”,理解的权威“死了”,文本成了四处飘零、无家可归的孤儿。就这样,整个支撑结构主义文学观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厦彻底瓦解了。在德里达看来,所有话语都因历史而变化,我们的概念和意义都受到我们所处的历史的影响。意义自身不能在言语或写出的文章中呈现于我们面前,由于时间关系,意义产生的种种观念和种种差异被推迟了。正是在对语言概念的历史性的讨论中,德里达提出了他符号意义观的又一重要理论——“延异”理论。在德里达看来,语言不是可以被自由支配的工具,语言所表达的是文字本身或者语言本身,而不是某种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先在的意义。语言本身是一个意义开放的系统,而且其结构本身也是不稳定、不明确的。每个语言符号的意义都没有明确的边界,所以说“意义不是来自语言之外的所指,而是来自与其他能指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德里达又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记,它的意义总是在语言符号漫无目的的自由嬉戏当中,以延异的形式存在。而且,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延迟和差异,符号的意义无尽地“散播”(dissemination)开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没有任何的中心,没有任何的明确意义,最终消解在无穷无尽的符号当中。在这里,德里达正是借différence 与differance的不同来说明他哲学中主张的“差异”具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差异”的含义,即“产生差异的差异”,是一种差异化的运动。①杨卿:“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渊源简论”,《理论月刊》,2009,第8期,第47页。
总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观就是在其解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传统形而上学本质观的系统反思。德里达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客观本质的意义,语言和文本也不是恒定不变的,真理只不过是人对外在世界的阐释,文本离不开各种文化和社会的符号,文本的意义难以限定,而言说主体传达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会被不断的阐释,产生不同的意义,阐释没有尽头,意义的变化也就没有终点。
二、德里达对文学本质、文学与哲学关系的阐释
对文学的本质追问一向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德里达一方面试图把文学和非文学区分开来,站在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对人们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就文学本质问题做出的思考进行解构;另一方面,又从“文学是什么”这个关于本质、真理和同一性命题出发,认为对此类问题作哲学思考没有价值可言。因为人们可以阅读大量的文学文本,提出若干假设,但作品的产生永不停息,对文学预设的回答只能是徒劳的。他要求不要穷尽文本或确定文本的意义。文学的本质主要体现为文学性,这种文学性不是内在于文本中,而是被阅读召唤和复活的文学特征。德里达认为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颠覆和生成的过程中,其意义才得以产生。
(一)消解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19 世纪初,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艺术是理念的表现,“哲学是理念的高级理性的充分的表现形式,美和文学艺术是它的低级感性的不充分的表现形式,文学艺术终将被宗教、哲学所代替的思想。”从古希腊哲学家把柏拉图将哲学家尊为理想国中第一等人而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到 20 世纪瑞恰兹把诗视为一种不同于经验实证的哲学语言的“情感”语言,这种重哲学而轻文学的观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②高原:《文学行动--德里达结构主义文学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第22页。而在德里达看来,哲学和文学都是借助于语言(文字)符号来传达的话语文本,都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们本身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由于符号本身的修辞性,哲学和文学一样,都处于隐喻之中,其差别仅仅在于“文学坦率承认它植根于隐喻和修辞,愿意并且能够反思为它所用的各种文体”,而哲学虽然说到底同样也是隐喻和修辞的产物,同样要考虑风格和效果,却总是自以为超越了文本的隐喻结构。所以,哲学本身就是文学性隐喻和象征的产物,必须借助于文学性的这种隐喻的作用,哲学的概念和判断才能得到说明,反之如果将这些东西全部抽空,哲学本身也会是一无所有。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一文中,引用了法郎士的小说《伊壁鸠鲁的花园》波利斐若对阿利斯托的一段话:“那些一心想摆脱意向世界的形而上学家们到头来仅是让乖张的命运永远束缚在譬喻之中,那些古代寓言不屑一顾的可悲的诗人们,自己不过就是寓言的搜集者而已。他们在制造白色的神话。” 他还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人在洞穴中看到被照的东西,内中有一个光源,并逐渐从黑暗走向光明,哲学即是起原始作用的那个太阳,它是隐喻。③高原:《文学行动--德里达结构主义文学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第24页。
所以用独特性、同一性来界定文学的本质都是徒劳,用语言的隐喻性、修辞性模糊了哲学和文学严格划定的界限,认为文学和哲学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关系,哲学和文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文化形式,没有等级差别和优劣之分,诗歌和哲学,文学和哲学都基于同一种经验即普通的语言经验之上,是人类的两种不同的话语形式,是平等的。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文学理论中,无论是以探求文本结构、意义为目标的文本中心论,还是强调文本的动态多样性,主张充分发挥读者阅读积极性的读者中心论,他们各执一端的片面性却在德里达对文学和哲学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补充,德里达认为,“一方面,人类所有的话语文本都是行为,都是叙述,都是修辞性的、文学性的,压根就没有本源,没有中心,自然也没有统一的结构和本义。一种话语文本永远与别的话语交织在一起,是个开放的系统,极富多元化。这样,传统文本本体论对文本本义的追求注定不会有结果,这种追根溯源式的解读法根本上是一种误入歧途的文本阅读方式。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任何一种话语,任何一种文本在叙述过程中无不围绕着某一个话题、某一个中心,也就是说作者在行文运思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文本一种结构,一种意义。”①肖锦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127 页。所以,对一文本的阅读则不能不以文本本身的结构为出发点,但那种主张完全抛弃文本结构和文本现实,而借助文本的语言能指进行漫天的自由发挥的现代读者本体论脱离了文本的实际状况,也无法成立。
(二)真理与文学的关系
关于文学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文学和哲学关系的问题,而德里达关于文学本质的论述与他对文学和哲学关系问题的论述密切相关。在西方传统观念中,文学和哲学关系是对立的。哲学是关于判断和陈述的学科,它借助语言来传达世界的本质和主体存在的真理,是一门关于理性的学问。而文学则注重虚构、隐喻和想象,经常描述些荒诞离奇、虚无飘渺的东西,人们无法辨别它们的真伪,因此文学借助语言传达的东西与真理无缘。关于文学和哲学两者关系的表述,最早见之于柏拉图的“模仿说”,在柏拉图的名篇《斐里布斯》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片段:我们的心灵就像一本书,它记载了我们的记忆、感觉以及感情,如果它记载的东西是真实的,我们得到的意见和见解就是真实的,否则便是虚假的;画家随手写者之后描绘我们的意见和见解的灵魂之图像。德里达谈论文学离不开哲学,离不开文本以及文本阅读,这在形而上学概念体系看来是混乱的、难以理解的。然而,这与德里达的解构逻辑是一致的,他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了补充,文学、哲学、文本、世界、读者、作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无物不是文本,而“异延”、“踪迹”、“补充”作为语言存在的根本,不仅使文本与文本间相互依存,而且是文本与其派生的无数他者相区别,相联系,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容纳矛盾、容纳差异的一个多元的世界。②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26 页。
三、德里达的文本观
“文本”不仅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核心范畴,而且也是他文学观所关注的焦点。
(一)文本性
传统的形而上学文本观认为,文本是一个有着终极目的的封闭单元,是写作主体的绝对在场,读者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一在场,在作者、读者、文本三者的关系中,作者无疑成了权威,他无所不能。而读者只有去追寻文本背后的作者的意图,毫无能动性可言。但事实上,作者其实也没有能动性,因为一旦写出便是绝对在场,所以作者意图总能实现,甚至连作者意图也不必要有,因为这些意图中的许多构思、体验等本来都是为了实现“在场”而准备的。这样一来,作者、读者、文本之间的关系完全成了一种机械的生产——吸收的模式,这显然与文学生产的现实相脱节,也不利于文化的发展。而德里达的文本概念,就是对这种传统文本观的彻底变革。
德里达的文本概念,常被概括为一句格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只有文本性,即文字书写与生俱来的各种长短利弊,诸如再现与遮蔽,延异与撒播。用德里达艰涩的文字解释:“如果说没有文本之外,那是因为一般化的书写痕迹总是已经开始。”①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Paris: Minuit, 1972; trans.佘碧平,《多重立场》, 北京:三联书社,2004,364页。它的意思是文本既不关涉现实,也不关涉作者的意向,但文本可以指涉其他文本,形成文本织体,编织出文本的锦帛;文本敞开又叠合,如阴阳和谐,道法自然,不断地开裂,生成新的文本,这种文本所具有的特性,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文本的“互文性”。在德里达看来,文字不是外在实物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符号的差异的运动。文本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现,与之相反,客观世界都已被文本化了,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纳入一个文本。阅读和写作不断地渗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世界,而我们的世界除了解释别无他者,但阐释者无法超越解释,因为他被囚禁于语言牢笼之中,必须面对修辞和差异构成的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所以他的解释也是永无止境的。一篇作品既不属于某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时代,带有不同作家的文本痕迹。所以,针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和阅读也是千差万别的,任何一个新的文本,都与以前的文本互为文本,而过去文本的痕迹,则会通过作者的扬弃而渗入他的作品,就像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会悄无声息地潜入语言体系中一样的道理。②高原:《文学行动--德里达结构主义文学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第30页。
德里达认为正是文学文本所具有的这种开放性特征,才能使其自身能够向所有的话语开放,“如果不是对所有的话语开放、如果不是对这些话语的任何一种开放,它也就不会成为文学。没有对于意义与指示的中止关系就没有文学。中止的表示悬而未决,但也表示依赖、条件、条件性。在其中止的条件下,文学只能超越其自身。毫无疑问,所有的语言都表示与本身不同的东西,或者说表示作为别的东西的语言”。③德里达:《文学行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14 页。文学处于一切的边缘,几乎超越一切,包括其自身。德里达在对语言意义思考上,他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中心主义,认为对任何本质主义、中心主义的意义的追问,都会导致文学意义的真正丢失,文学永远处在确定性的边缘。作者对作品的支配性地位已经瓦解,作品的意义只能无止境地在文本间的关系中去寻找。而对于文本的阐释,只能是一层层不断地展开能指成分和所指成分,而每一层又需要转化成一个新的能指,如此替换,以至无穷。这就像剥洋葱一样,有许多层构成,但没有内核,惟有无尽的包膜,其中包含着的只是它本身诸多“表层”的链锁。
(二)意义的撒播
所指的终极意义也不会存在,而所谓的本源、中心实际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之中。德里达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对传统文本观的解构,也是对读者与文本传统关系的解构,因为他把权利交给了具有无限阐释权利的读者。批评家的任务不是从文本中得出意义,而是分解文本,考察印迹,把整个作品看作隐匿的“结构”,揭示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德里达对文学文本的这种开放性思维使我们对文学的思考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对文学的定义,主要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是极易多变的,它意味着某些人在特定语境中依据特定的标准和按照一定的目的而赋予价值的任何事物,“人们可能会把一部作品在一个世纪中看作哲学,而在下个世纪看作文学,或者相反;人们对于它们认为有价值的那些作品的想法当然也同样会发生变化,甚至人们对于自己用以进行判断的依据的想法也会变化。”①[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 页。的确,一切文学作品都会被阅读它们的社会中的人们所“改写”,就算仅仅是无意识的改写,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人改写过的历史。期望对一部作品权威的、流行的评价在解构主义看来都是不可能的,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如何看待或从哪个角度来看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被当作文学的事物是一个没有终点,无限“异延”的原因。正像德里达曾在 1972年《撒播》(La Dissémination)中所描述的:“与延异一样,散播是反还原的。同隐喻一样,散播开辟语义漫游的可能。散播并非一词多义,它指示意义的散漫增生。”②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Paris: Minuit, 1972; trans.佘碧平,《多重立场》, 北京:三联书社,2004,第61页。基于《撒播》中一篇长文《柏拉图的药》,他又证实,Pharmakon(药)并非模凌两可,因为还有魔术师及替罪羊等歧义,在杂乱语境下,任何读者都无法做出单一选择。因此,他总结到:“Pharmakon即差异运动、差异场所、差异的生产游戏……”③Jacques Derrida, la Dissemination, Paris: Seuil, 1972; trans.Babara Johnson, ChicagoUniversity Press, 1981,第287页。“散播”的确无止无息。
结语
德里达对文学文本的这种开放性思维使我们对文学的思考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他的解构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把一种以哲学为旨趣的理论应用到文学研究的直接通道是可行的。到此为止,德里达的解构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具有莫大反讽意味的哲学图画:哲学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几千年来它极力排斥和贬低的东西:文学,只不过是看不见的白色的文学而已,一旦我们在它上面撒上一些显示剂,它隐的真相就会显现出来。正是这个向世界播撒显示剂的杰出思想家德里达,带着哲学难题,言犹未尽地走了。
哲学乎?文学乎?德里达的结构,确实是一场哲学向文学的延异运动。或者,因为,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解魅。而文学批评的繁荣,诗与艺术的再度附魅,则彰显了当下的一大鲜明特征:即放弃最高价值,开放学术试验,多方探索真理与瓦解的各式条件。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罗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