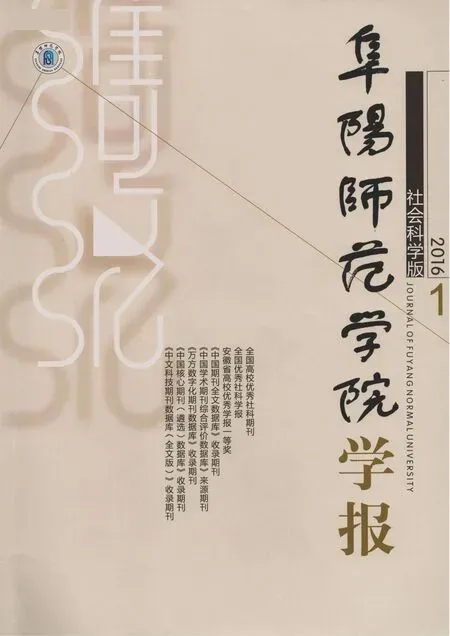临演社会、微托邦与共存——论博瑞奥德关系美学
2016-04-16叶蔚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叶蔚春(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临演社会、微托邦与共存——论博瑞奥德关系美学
叶蔚春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摘 要:关系美学是法国策展家博瑞奥德于1998年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关系美学是依据艺术品所表征、生产与推动的人际关系来评判其美学理论。当下的社会限制了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人际关系在分离的社会中变得模糊,关系艺术通过建构开放自由的系统,重建某种共同体的感觉,来修复人际关系中的崩塌。博瑞奥德提出的临时演员社会不同于景观社会,在其中的多数人由观看者变成了表演者。“间隙”(interstice)一词形容关系美学所发生的空间,它可以嵌入整体系统内,提出另一种可能性。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微型乌托邦,它在效果上类似于福柯所说的异托邦,在实施策略上,又与情境主义者所提倡的“构境”相似。关系美学的核心恰与朗西埃提出的歧感相反,由此引发了二者的论争。
关键词:关系美学;临演社会;微托邦;歧感
关系美学是法国策展家尼古拉斯·博瑞奥德于1998年在同名著作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关系美学是“依据艺术品所表征、生产与推动的人际关系来评判其美学理论”[1]112。根据博瑞奥德的界定,关系美学只对那些能够体现人际关系的作品起作用,而最能体现人际关系的是90年代的艺术品,因此他认为艺术史在90年代发生了新的转向,“继人性与神性的关系领域之后,接着的是人性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艺术实践至此专注在人际关系的世界里”[2]27。为了呈现这种转向,博瑞奥德于1996年和2002年分别在法国波尔多、美国圣弗朗西斯科艺术学院举办了“交通”(traffic)展,“接触”(touch)展,后者在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艺术时,强调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联系,更加注重社会性的交流。
一、临时演员社会
博瑞奥德认为艺术不仅要提出社会问题,而且要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认为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是:“任何无法被市场化的东西都将不可避免地消失。不久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在贸易领域之外将不复存在……被普遍的物化影响得最为严重的是当前的关系空间。世界被劳动分工、过度专业化、机械化与营利原则统治着……这种巨大的‘分离’影响着人际关系的走向,表明了当前社会正处在居伊·德波所描述的‘景观社会’的最后阶段。人际关系不再是‘直接经验’的产物,而是在‘景观化’的表征中变得模糊。”[1]9分离与物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核心之一,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方面会出现分离的特征,如技术的发展、劳动分工的精细化等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际关系逐渐变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则在《启蒙辩证法》里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顺着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思路,卢卡奇将韦伯所说的合理性中的分离指定为物化,这种物化可视为两种分离,即人自身内部的分离与人际之间的分离。德波在这些基础上,提出了景观的概念,他并未否认生产对人的物化但他的重心在于景观社会的到来。“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3]3景观的物化作用不仅在于生产与消费领域,它还体现在支配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人们在闲暇时间里成为虚假的消费者,普遍的物化却让人们欣然接受消费的快感。
顺着德波的路径,博瑞奥德提出了“临时演员社会”(the society of extras)。新技术比如互联网与多媒体系统的出现,都指向创造“共活”领域和有关文化对象的新型交流形式的集体欲望,临演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被删节的交流渠道中找到互动民主的幻象[1]26。从历史上来看,前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通往帝国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了阻碍,它完全掌控了社会场域,因此它可以煽动个体在其所监视的开放空间内自由嬉戏,因此在消费社会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临演社会的开始,个体在其中发展为自由的兼职替身,公共空间的签署者与盖章者[1]113。在临演社会中,临时演员与景观社会中的消费者一样,是被时间与空间控制的主体,博瑞奥德将其理论的适用时间限定为90年代之后,并且用新技术的发展来推进德波与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
博瑞奥德认为临演社会是在景观社会出现之后的社会形态,这似乎不如将其视为与景观社会、消费社会的共在更为合理。景观在生产条件下不断堆积并展现为社会的一部分,成为错觉与伪意识的领地,在这之中虚假的需求不断被产生,人们在丰裕的物中成为了消费者,而在消费社会里消费者扮演的是临时演员的角色,个体作为接受者处于被动的位置,每一个细微的活动都受制于市场。与德波所说的“当景观有三天停止谈论某事时,好像这事就已不存在了”[3]116相对应的是,在临演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中间人被电视节目、街头或时事的问卷调查传唤,因此成名15分钟”[1]113。景观混淆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误导人们将其与真实事件等同起来,而人们在成为消费者后也变成了景观的配角。临演社会与景观社会的不同在于,在景观社会里多数人是在观看掌控着资本的少数人的表演,而在临演社会里多数人自己变成了表演者,甚至能在“15分钟”内成为社会的主角。科技的发展,加速了摄影摄像工具的普及化、便携化,如果说在景观社会里大多数人的观看是被动的,那么在临演社会里的多数人则积极参与到了被景观化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变成了主动的拍摄者,而且乐于成为被观看者,甚至想方设法地取得更多的关注,争当社会的主角,如社交软件facebook、微博、微信里大量的个人照片、信息的自我暴露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当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表演者,人际关系将变得更为模糊不清,而这样的扮演最终又促进了景观的堆积。
二、参与、间隙与微托邦
单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关系美学,容易将人与人的关系全部划入关系美学,而博瑞奥德定义的关系并不是通常所指的人际间的社会关系,他认为关系艺术是“把整个人类关系及其社会语境作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出发点,而不是独立的、私人的空间内的一套艺术实践”[1]113。博瑞奥德所指的关系是:“一种排除主体概念后的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和相遇……这些接触远远超出这些现成的社会关系的局限,从而呈现出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之外所存的巨大的关系构建可能性。”[4]113
参与性和传递性是关系美学的重要内容,成功的艺术品往往同时具备这两种特性。没有传递性的作品如同死物将在沉思中粉碎,而成功的作品能够暂时凝聚起情感,并将这种情感传递给观看者,观看者对情感的二次体验同时给艺术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能够促进这种情感的发展。戈达尔认为一个肖像需要两个人来完成,观看者是完成作品的因素之一,类似于杜尚所说的“画作是由观看者完成的”。艺术家在创造之前必须事先假定他者的存在,艺术品可被视为包含无数通信者与接受者之间对话的关系物。博瑞奥德认为艺术家可以通过艺术场域外的关系来描述其特殊性并完成作品,因此作品可以呈现出个体与团体、艺术家与世界以及通过传递性形成的观看者与世界的关系。关系美学特别重视观众与艺术的关系。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与陌生人共处同一空间的机会增多,艺术家愈加倾向使用表演性、互动性强的技术,艺术品也更加依赖于观众的反应,而关系艺术本身就意欲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更多的人发生关系。在博瑞奥德策划的一些项目中,他极其强调团体内的合作与互相影响,重视策展家与艺术家的共同决策,“艺术批评家的任务不再是阐释艺术家的意图,而是寻找另外的角度,展示它从未被人注意到的那一面”[5]165。
90年代以后的艺术越来越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艺术创作明确将重心倾向于如何在人群或社交模式中创作人际关系。博瑞奥德用“间隙”(interstice)一词来形容关系美学所发生的空间:“间隙一词来自卡尔·马克思,用于描述一种可以规避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的贸易共同体,它可以消除利润法则:以物易物、办展销会、自给自足等。间隙是存在于人类关系中的空间,它几乎和谐而开放地嵌入整个系统内,提出了不同于现行系统的另一种交易可能。”[1]16当代艺术展在间隙中创造出了自由的空间与超越了日常生活维度的时间,与之前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交流不同,它鼓励的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交流。当下的社会限制了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不断进步的科技减少了人与人交流的机会,关系空间被日益精细的机械化逐渐限制。博瑞奥德举了清洁工具、叫醒服务、自动柜台机等一系列例子来证明技术不仅没有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反而使人们越来越孤立,变得冷漠。因此他认为科技是一种意识形态,艺术家应该正视科技的影响,而非沉默地接受。
与间隙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微型乌托邦(micro-utopia),博瑞奥德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乌托邦与革命让位于日常生活的微型乌托邦和模仿策略,任何建基于当下无法实现的边缘幻象的立场之上的对社会的直接批判都是无效的,甚至是后退的。”[1]31当代艺术的乌托邦在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如果将前卫艺术视为正面介入政治的形式,那么当代艺术则是微观上的介入。微型乌托邦在效果上类似于福柯所说的异托邦,它是将不同空间与场所并置于同一地方的既反映又对抗着社会的真实场所,是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在实施策略上,微型乌托邦与情境主义者所提倡的“构境”相似,它通过漂移、异轨等形式企图在同样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来重构生命过程。博瑞奥德认为情境主义者的情境建构核心在于替代,它试图“用日常生活中实验性的实现来替代艺术再现。如果说德波关于景观生产过程的诊断给我们带来无情的打击,那么情境主义理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如果景观首要对付的是人际关系(也就是那句话‘影像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中介’),那么它只有通过生产出人们之间新的关系模式才会被反思与打击”[1]84-85。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博瑞奥德的使用中发现微型乌托邦与间隙的含义基本相同,几乎可以相互替换,比如在提到前卫艺术与现代性时,他说:“如果他们不再天真地或者是愤世嫉俗地认为激进的、普世的乌托邦在当下是可实现的,我们也许可以用微型乌托邦和社会中敞开的间隙来讨论问题。”[1]70
关系美学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力度到底有多大值得我们思考,正如朗西埃在谈及关系艺术时所说:“(关系)艺术不再试图去回应商品与符号的过渡,而是回应(社会)纽带的缺失。正如这个学派的主要理论家所说,‘通过提供微不足道的服务,艺术家们填补了社会纽带中的裂缝’。”[6]57关系美学的提出仍旧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虽然博瑞奥德意识到媒体技术、景观社会、消费社会对人际关系具有强大塑造力,但他的关系美学论实际上只是在重复交流的必要性,他并未对为何要建立人际关系、又为何将人际关系视为其艺术理论的起点作出明确的回答。博瑞奥德企图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他既倾向于本雅明的前卫美学,又表现出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式的自律——把艺术看作独立于社会其他体制的社会间隙。”[7]272当他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规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体时,他的出发点正是要完成资本的生产、重组与贸易,而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三、歧感与共存——博朗之争
关系艺术拒绝对抗、替代与异议,而是希望建构一个能够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开放自由的系统。关系艺术的作品共同点在于突破时空束缚,与更多的人发生关系,意在通过重建某种共同体的感觉来修复人际关系中的崩塌。因此它认为艺术的作用在于营造情境,创造出社会连接的新形式,最终缝合破碎的关系。关系艺术是一种共识艺术,而关系美学的核心在于协商(negotiation)与共存(co-existence),这与朗西埃提出的歧感(dissensus)正好相反。朗西埃所说的歧感并“不是指个体在利益或者意见上的争执,而是通过不被接受者,即政治主体来与现有的感觉结构和思想对峙并采取行动来抵制司法裁断,在可感知秩序中制造分歧的政治过程”[8]88-89。朗西埃希望建立的是“歧感共同体”(dissensual community),因此他对强调协商、契约、共存的关系美学不以为然。
在《美学及其不满》里,朗西埃提到,关系艺术不仅力图转换展览空间,而且还将多种多样的形式介入日常的城市生活空间中,如改变公交站的作用、互换本地人与外国人的关系、把闲置的亭子变为郊区居民的社交场所等,“关系艺术由此不再创造物品,而是创造情境与遭遇”[6]56。博瑞奥德把重心放在了对社会纽带的重建上,无视当下社会中商品与符号的泛滥。而对于重建人际关系,博瑞奥德也没有提出有效的策略。“关系艺术声称已经克服了博物馆与外界、艺术表演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分离,将不再去生产物品、形象或信息的复制品,而是去生产真正的行动或者物品,进而产生新型社会关系与环境……关系艺术的前提是拥有在博物馆与画廊中创造新型关系、改造城市环境的意愿,并希望因此能在感知方式上带来一些改变。”[9]146根据朗西埃以上的论述,关系艺术似乎陷入了重重疑团中,关系艺术的重心在于纽带的重建,那么它生产出的真正的物品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恢复崩塌的社会关系呢?为何在实践行动上,关系艺术却没有创造出物品,而是创造出了情境与遭遇呢?博瑞奥德是否已经将重构社会关系简单化为艺术生产?真实物品与情境遭遇无法等同,那么关系艺术要如何在二者间找到平衡点呢?
面对朗西埃的质疑,博瑞奥德在2009年发表了《未稳定的建构:关于艺术与政治的问题回应雅克·朗西埃》进行回应。他首先对朗西埃关于“艺术的政治实效不在传递信息,而是对身体的处置”的看法表示同意,然后认为他把艺术处理视为社会关系是一种误读。关系艺术通过艺术形式来呈现社会关系,艺术家通过形式来参与对话,“每一件特殊的艺术品都存于一个共享的世界里,每位艺术家的创作都与世界有着许多的关系,并且会无止境地引发其他关系”[1]22。博瑞奥德认为:“一种未稳定的美学体制正在速度、间歇性和脆弱胜之上建基并发展。”[10]78当代艺术的本质在于将世界保持在未稳定状态。在这之中,政治框架是固定而明确的,变换的只有表象而已,而艺术充当的角色不过是一台计算机,它可以将日常生活当作素材来处理,对形式进行调整、重组与操控。而艺术的真实正是在于它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表现为转码、闪烁与模糊三种模式。现实是以蒙太奇、场面调度等组成的世界,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嵌入其中。
从1996年首次提出关系艺术,到2009年的这篇回应,博瑞奥德的前后思想似乎不太衔接。固然后者有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但我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是矛盾。在《关系美学》里我们看到他不断强调用艺术来填补社会关系的断裂,不断强调微型乌托邦和模仿策略的重要性,但在这篇《未稳定的建构》里,博瑞奥德却重点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性,意在强调艺术是偶然的、不确定的,甚至认为艺术作为政治纲要的本质意义仅仅在于对不稳定社会的认识。在这里,博瑞奥德似乎不再在意关系美学的社会效用,也不在乎人际关系的崩塌应该如何解决,而是重视起了感知——“艺术的功能就是分析和重述这个世界,以影像或者其他方式改写这个世界。”[11]63他在文章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案,其实可以看做是博瑞奥德向朗西埃的靠近。“打开那些为传媒所‘阻塞’的言语渠道,发明社交性的另类模式,创建或者重新构建相距遥远的符码之间的联系,通过具体的独异性(singularities)来表征抽象的全球资本主义……开辟了真正的政治艺术的道路。”[11]63
参考文献:
[1]Nicolas·Bourriaud,Relational Aesthetics[M].Les Presses du réel,2002.
[2]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M].黄建宏,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3]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孔锐才.关系美学:关系的狂欢或美学的保守[J].东方艺术,2014(11):112-115.
[5]邵亦杨.后现代之后:后前卫视觉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Jacques·Rancière,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trans[M].Steven Corcoran,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9.
[7]王志亮.关系美学与前卫理论谱系[C]//朱其.当代艺术理论前沿4.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8]Jacques·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trans[M].Gabriel Rockhill,Bloomsbury Academic,2013.
[9]Jacques Ranciere,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trans[M].Steven Corcora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0.
[10]尼古拉斯布瑞欧.未稳定的建构:关于艺术与政治的问题回应雅克·朗西埃[J].黄建宏,译.新美术,2013(2),75-82.
[11]蒋洪生.关系艺术,还是歧感美学:雅克?朗西埃 VS尼古拉·布里欧[J].艺术时代,2013(3):56-63.
Society of Extras,Micro-utopia and Co-existence—— A study on Bourriaud’s Relational Aesthetics
YE Wei-ch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Relational aesthetics is named by Bourriaud in1998.Aesthetic theory consists in judging artworks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human relations which they represent,produce or prompt.The present society limits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relations,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re becoming blurred in society.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which is free and open,relational art builds the feeling of community to repair the collapse in human relations .The Society of extras is different from society of spectacle; most of the people in it are turned into performer.The interstice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space in which the relational aesthetic happens,it can be embedded in the whole system,and provide another possibility.Micro-Utopia is similar to heterotopias in effect and similar to the constructed situation which is advocated by the situationist in strategy.The core of relational aesthetics is contrary to dissensus which is proposed by Ranciere,so they hold a heated debate .
Key words:Relational aesthetics; society of extras; Micro-utopia; Dissensus
作者简介:叶蔚春(1989-),女,汉族,福建寿宁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
收稿日期:2015-12-03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1.017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1-008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