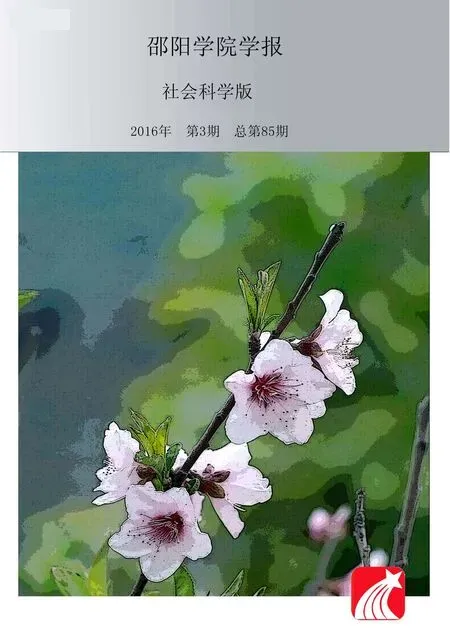阿赫玛托娃走向永恒的死亡意识
2016-04-13董爱兰
董爱兰
(大同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阿赫玛托娃走向永恒的死亡意识
董爱兰
(大同大学文学院, 山西大同037009)
摘要:“死亡意象”贯穿于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创作的不同时期,是其诗歌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现象。阿赫玛托娃的死亡抒写蕴藏着超越死亡而走向永恒的死亡理念:有限的自我因死亡而回归到永恒的大自然,短暂的自我因诗歌的记忆而超越死亡,必死的自我因汇入历史大河而永恒。从自然走向历史,从朋友走向民族,随着个人情怀的提升,阿赫玛托娃对死亡的体悟在不断发展,但无论如何她那超越死亡的意识给世人以光明和温暖。
关键词:阿赫玛托娃; 死亡; 永恒; 自然; 历史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重要的女诗人,她的“思想和情绪即使不是永远,也是经常地朝向死亡,她很乐意‘埋葬’爱人和她自己:‘风啊,埋葬吧,请把我埋葬……’,‘灰眼睛的国王昨天死了……’,‘在我临死前的昏睡中’……”[1](P59)。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有服毒自杀的情人、死在路边草丛里的未婚夫、葬于橡树下的母亲、横尸流放地的作家、战死的士兵。从早期个人情感引发的死亡想象到后期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生发出的死亡体验,死亡思绪始终伴随着阿赫玛托娃,即使在沐浴着“清晨迷醉于春日的阳光”、通向远方的路边“短木桩/在绿宝石般的草皮上清晰地呈现白色”的如诗如画的想象中,结尾却也会突兀地奏出不和谐之音:“而林荫路的深处是墓地的拱门”。目前国内对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手法和爱情诗的探讨上,关于其死亡意识的研究文献很少。《献给逝者的花环——安娜·阿赫玛托娃与萧红的死亡主题》一文将大部分内容用来总结两位女作家在死亡意象和个人生活经历上的异与同,对阿赫玛托娃的死亡意识缺乏充分的剖析;《阿赫玛托娃诗歌艺术创作的变化与发展》只粗略谈到和死亡有关的颜色意象。
尽管死亡意象和对死亡的想象萦绕诗人创作的各个时期,但其诗歌并未因死亡意识的伴随而笼罩上悲观色彩,因为阿赫玛托娃抒写死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走向永恒的超越与力量。在《我们俩不会道别》一诗中阿赫玛托娃不停地追寻永恒:我们“肩并肩走个没完,我们俩走进教堂,看见/祈祷、洗礼、婚娶,/我们俩互不相望,走了出来……”直到最后“我们俩来到坟地,/坐在雪地上轻轻叹息,/你用木棍画着宫殿,/将来我们俩永远住在那里”[2](P113)。在墓地的宫殿方是“永远”:永远的不道别,永远的静止。“面对现实中的死亡,阿赫玛托娃以一种乐死的超越姿态借助于笔下的死亡意象承受并消解了死亡”,有人认为她超越死亡的态度源于基督教思想:“当死神几次降临其头上时,以基督徒的平和之心,她愉悦地迎接死亡,并由此获得超越死亡的某种高峰体验。”[3](P184)正如叔本华所说:“动物并不真正知道死亡这回事,所以个体动物直接享受到了这种种族不灭的特质。……人的反省理智思维为人们带来了对死亡的认识,不过,这反省思维也同时帮助人们获得了形而上的观点,从而使人们在死亡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安慰。”[4](P204)阿赫玛托娃在诗歌中总是将死亡的恐怖、绝望与毁灭放置于艺术、历史、宗教及有温度的自然等人类用想象力虚设出的空间中,死亡借助这些“形而上的观点”被超越,并成为抵达永恒的必由之路。
一、死亡——在自然中永恒
阿赫玛托娃和其他诗人一样喜欢借用神话思维消解科学建构起的自我与自然间的主客体界线。维科认为原始人的神话思维习惯于把无生命当作有生命,将自己的生命渗入到自然对象上,把生命性推演到一切对象。于是,在阿赫玛托娃的笔下大自然成为阴性的“她”,包容、博大、安宁,通向永恒;作为从大自然泥土中而来的人,有限、个体、短暂,而死亡是对生命起点的回溯,是对生命家园的归返,“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亡使人回归永恒的自然。
(一)死亡:回归泥土后的永恒
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泥土以及由泥土衍生出来的‘大地’、‘草坪’、‘旷野’、‘小路’等一系列意象,构成了阿赫玛托娃抒发情感的载体”[5]她在自己的诗歌《故乡的土》中否定了基督教高高在上的天国,认为脚下的尘土才是人的精神家园,无意识中呼应了“人从土中来”的人类起源母题。人都是尘土,不论是“套鞋上的灰尘”、“我们齿间咯吱的沙粒”,还是“我们磨蚀它、搅拌它,碾成粉末,/那无法与其他东西混和的尘土。/可是,直到我们躺入其中,与它融为一体,/我们才可以从容地宣称:我们的尘土”[6](P246)。人只有再次回到自然的泥土中才真正回归到自己的家园,获得灵魂的安宁与永恒。阿赫玛托娃的另一首诗也描写到:缪斯“也曾像种子一般在地里腐烂,/为的是以后能像灰烬中的凤凰”。诗人借《圣经》中的格言“一粒种子仅仅是一颗种子,一粒种子腐烂了才可以长出无数的种子”,再次昭示出只有复归泥土的死亡才可以超越有限,走向无限的思想。
(二)死亡:物我合一后的超越
“天与地无穷,人死则有时”,时间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决定了死亡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人类可以在幻想中达到羽化成蝶、主客体浑然一体,如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个体自我与生命力充盈的自然交融为一,生命被转移,时间得到延续,从有限走向永恒。
阿赫马托娃来自一个热爱大自然的文学传统大国。俄罗斯广袤的疆土滋养着历代作家,暴风雪、高山、悬崖、森林、草原、大海、白桦树在俄罗斯作家笔下有着生命的灵性,仿佛分有了上帝的神圣。同时,阿赫玛托娃所属的阿克梅派“相对统一的为数不多的几条线索之一”便是“在物质上打上人的印记,它们从外部投射出人,同时保护人免受‘虚无’空间的寒冷。这一思想被曼德尔施塔姆扩展为家务性原则组织世界经济,成为‘宇宙家园’”[7](P66)。
阿赫玛托娃给予了大自然以温度与永恒,从而使大自然成为人的生命家园。在《风啊,埋葬吧,请把我埋葬……》一诗中,埋葬于自然的诗人,夜成了她的裹尸布,蓝色的大雾为她朗诵赞美诗,喧响的苔草为她歌唱春天,在这首诗中有限的自我因死亡与超越时空的大自然融为一体,走向永恒与无限。《今天是斯摩棱斯卡亚的命名日》是阿赫玛托娃写给诗人勃洛克下葬时的悼词,勃洛克的死亡原本是一种“痛苦的陨落”,但阿赫玛托娃将他埋葬在“蓝色的香雾在青草上弥漫”的墓地,那里“夜莺的丛林,在明媚的阳光中宁静”。在草坪、歌喉婉转的夜莺、明媚的阳光、没有纷扰的宁静的环绕中,死者如“纯洁的白天鹅”,沐浴着圣母的神圣之光,充满了神性,逝去的诗人与上帝同在。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阿赫玛托娃使诗歌中的死亡成了生命回归自然的媒介,使得生命复归神性,得以在宇宙万物中永生。
二、死亡——因诗的记忆而永存
“对阿克梅派作家来讲,文化本身就是目的。与此相关联,他们对记忆这个范畴持有特殊的态度。……在他们的作品中记忆是最重要的伦理成分”[8](P98)。阿赫玛托娃1913年给好友苏杰伊金娜写了一首《记忆的召唤》,通过该诗诗人隽永地暗示出记忆对生命的重要意义:当现实只剩下“一面墙,上面是天空熄灭的火焰的反光”,记忆为世界构建出丰富而感人的意义:海鸥飞掠过蔚蓝平静的水面的美感、皇村巨大的公园的昔日温暖、曾经生与死的波澜起伏都因记忆与人相伴永远,而诗歌艺术则可使个人的记忆化为永恒。
阿赫玛托娃写到死亡的诗歌中,很多是献给已自然或非自然死亡的历史文人,如普希金、但丁、索洛古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勃洛克、鲍里斯·皮里尼亚克等,这些文学家和他们的灵魂因他们谱写的篇章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阿赫玛托娃又用自己的诗将他们的灵魂和篇章承载,使其历代传承。“一切艺术基本上是对死亡这一现实的否定。事实证明,最伟大的艺术恰恰是那些对‘死’之现实说出一个否定性的‘不’字的艺术。埃及国王的墓穴中的种种家具和陈设,西安秦始皇陵墓坑里的兵马俑都是这类伟大艺术的实例”[9](P222)。
《致索洛古勃》一诗写道:“你的木笛在寂静的世界上吹响,/死神的声音也秘密相随,/而意志柔弱的我,因你甜蜜的残忍/慵倦不堪,怡然心醉。”[10](P217)索洛古勃(1863—1927)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最具艺术成就的现代派作家之一,死亡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索洛古勃认为永恒与无限受到粗鄙的现实世界的羁绊,而死亡是摆脱束缚的最佳手段,因为死亡是对无限精神及永恒的向往与渴望。阿赫玛托娃用“木笛”的吹响比喻索洛古勃的艺术创作,“死神的声音紧密相随”概括出索洛古勃的死亡意识。索洛古勃虽已逝去,但他的这些“甜蜜而残忍”的精神遗产却使后人“依然心醉”。阿赫玛托娃用《献给亡人的花环》悼念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阿赫玛托娃赞美他“只有你一个人能猜透这一切……”。皮利尼亚克1938年被苏联政府处以死刑,其人其作却被阿赫玛托娃牢牢地留在记忆里:“当不眠的黑暗在四周宣泄,/那阳光灿烂的铃兰花盛开的瞬间,/就象尖楔刺入腊月的黑夜。/我向你走去,沿着小路,/你笑得无忧无虑。”[11](P143)阿赫玛托娃用诗歌的记忆“否定”了文学家们现实中的死亡,在艺术的殿堂文学家们的灵魂化为永远的记忆,超越死亡,走向永恒。
三、死亡——在历史石碑上永恒
到了创作的后期,阿赫玛托娃描写死亡的笔墨更加浓重,这一点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体现得尤为典型。该诗第一部《一九一三年》(《彼得堡故事》)主要写知识分子的悲剧——孤独与死亡。这一部分描写了一战前夕1913年的彼得堡被死亡与孤独笼罩的面貌:死刑枪声般的嘭嘭击鼓声似乎预感到了明日的动荡、战乱、死亡,并通过龙骑兵少尉克尼雅泽夫的自杀指明彼得堡如同一座殡葬之城,死亡与孤独是其唯一主题,每个人都渴望逃离;第二部“硬币的背面”则通过社会的苦难进而表现死亡,社会的高压彻底控制了人,甚至时时刻刻在毁灭人:“判处公民死刑的盛典,/我已饱览得不愿再览,——/请相信,我夜夜都梦见这些。”而我们只能“在磨灭记忆的恐怖中”想方设法“存活下来”, 并且把子女抚养成人,这一切也不过是“为断头台,为刑讯室,为监狱”;第三部“尾声”,进一步上升到整个人类的高度,人类的苦难与死亡。*这一部分文字,参考了曾思艺:《二十世纪的苦难:诗的见证——也谈〈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未刊稿。
可贵的是,在经历了二战和苏联的大清洗的洗礼后,“阿赫玛托娃冲出了个人情感的小圈子,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12](P78),黑色的死亡因自我与历史融为一体而被超越。在献给茨维塔耶娃的诗《迟到的回答》中,阿赫玛托娃这样写道:“我同你今天,玛丽娜,/在午夜的首都漫步,/身后同样的人又何止千万,/却走得无声无息,/周围是丧葬的钟鸣,/加上莫斯科风雪的嘶叫,/雪遮盖了我们的足迹。”[13](P304)在这首诗中诗人的个别与身后千千万万、悄无声息的人民相融合,一起走进俄罗斯的历史风雪。
阿赫玛托娃后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安魂曲》,取材于叶若夫年代阿赫玛托娃的儿子被捕事件,期间诗人“有十七个月是在排队探监中度过”。在序言中作家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天,探监排队时有人把她认出,那是一个排在诗人身后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她“在我耳边低声问道:‘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能’,我说。”序言表明整首诗“我”的抒情叙事起点已是置身于人民洪流之中的“我”,所以“我不是只为我一个人祈祷,而是为了所有的那些人们,他们同我一起站在耀眼的红墙下,无论是冬日的严寒/还是七月的酷暑”[14](P407)。弱小、无助的自我因站在人民的队伍中获得无限的力量与勇气,以此为出发点,阿赫玛托娃设想了自己的死亡:“如果有朝一日在这个国家里,/有人想为我把纪念碑竖立,/但只有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我同意以此来纪念胜利——/不要立在我出生的海边,……/不要立在皇村花园朝思暮想的树桩旁,……/把它立在我站过三百小时的地方,/在那里门栓从来不曾为我开启。/因为在获得解脱的死亡之中,/我害怕会把黑色囚车的嘶鸣忘记。/我害怕忘却那令人可憎的牢门关闭声,/和那老妇人如负伤野兽般的哀泣。”[15](P13)在这里,个体的死亡因构建了历史,而成为历史上永恒的石碑,使后来的俄罗斯人民,甚至整个人类铭记这段“黑色囚车”、“可憎的牢门”、哀泣的老妇人的历史。
总之,不论是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诗》还是在《安魂曲》中,诗人从现实走入历史,从个人走向人类,将死亡放置在历史、民族、人类的高度,从而使死亡具有了反思历史的意义和功能,构筑了历史的个体的死亡不再是结束而是历史永久的铭记。
正因为阿赫玛托娃赋予自然以温度,赋予诗歌以灵魂,赋予历史以坚韧,所以个体才能在生与死、有限与无限、人与物中自由穿行,超越死亡的毁灭与绝望,因此,涅道布拉沃称赞阿赫玛托娃“勇敢地照亮了人”,她的抒情诗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性质。”
参考文献:
[1][7]俄罗斯高尔基世界研究所编.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二)[M].谷羽,王亚明等,译.兰州:敦煌艺术出版社,2006.
[2][6][10][11][13][14][15]晴朗李寒.午夜的缪斯:阿赫玛托娃诗选[M].珠海:银河出版社,2011.
[3]刘艳萍.献给逝者的花环——安娜阿赫玛托娃与萧红的死亡主题[J].山东社会科学,2012,(7):181-184.
[4]叔本华.叔本华美学随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阿赫玛托娃的泥土情节[EBOL].http://www.gmw.cn/01ds/2008-03/19/content_750762.htm.
[8]曾思艺.试论俄国抒情诗的发展历程[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4-104.
[9]纽曼什.怀疑论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12]邱静娟.阿赫玛托娃和她的诗歌创作[J].俄语学习,2003,(1):48-53.
Akhmatova’s Consciousness of Eternal Death
DONG Ai-lan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037009,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death running through Akhmatova’s cre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is important for her poems. The consciousness of death written by Akhmatova has implied the idea beyond death and into eternity. Through death, the short life can return to the eternal nature, and being remembered in poems; the physical body can surpass the nature death; and with going into the history, every individual will become perpetual. Akhmatova’s consciousness of eternal death varied with her perspective broadening from the nature to the history and from friends to people whenever she has warmed and lightened human by surpassing death.
Key words:Akhmatova; death; eternal; nature; history
收稿日期:2016-03-18
作者简介:董爱兰(1980—),女,山西天镇人,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6)03—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