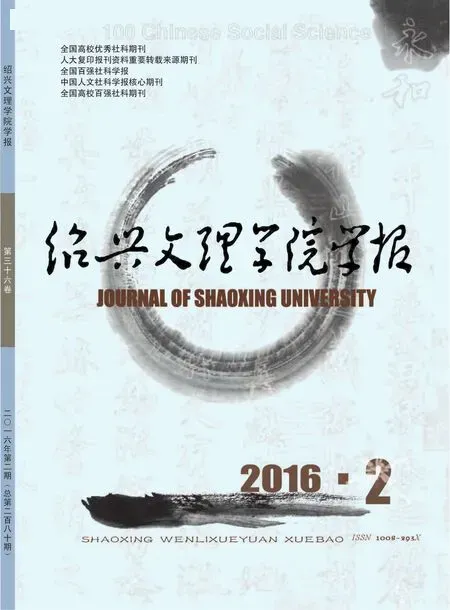外国文学的翻译传播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2016-04-13陆建德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北京100732)
外国文学的翻译传播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100732)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及自己早年插队时的阅读经历,他所喜欢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外国小说。清末民初以来,域外文学的译介对新文化运动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冰心、曹禺等往往也是翻译家。特别是鲁迅先生通过翻译和创作,不断地把“为人生的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回顾这一历史并予以积极的评价,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外国文学;翻译;传播;鲁迅;新文化运动
最近,在某些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特别强调小孩子要穿汉服、要行弟子礼、要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就个人而言,我并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一百年来,新文化运动这条路能走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好些年之前,我曾对新文化运动中有些激进的方面作过一些批评。比如说当时有人要废除汉字,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这些国民党元老在巴黎办了一个杂志叫《新世纪》,当时他们就有这样的说法。到了《新青年》创办以后,又慢慢地形成了一种风气,那就是大家提倡说“万国新语”,“万国新语”就是世界语,叫“Esperanto”,认为汉字应该慢慢地走出历史舞台。这种说法是非常极端的,我在不同的地方都批评过。但是总的来说,新文化运动还是有大量的贡献在今天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们的现代文学、我们的整个新文化运动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分不开的。
大家去关注一下鲁迅,《鲁迅全集》里是不含鲁迅的翻译作品的。就目前而言,《鲁迅全集》最好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一共18本,大家都很熟。大家去看一下鲁迅所翻译的外国小说,不管长篇、短篇还是儿童故事,加在一起远远超过鲁迅自己的文学创作。鲁迅为什么这么积极地从事翻译?鲁迅对于翻译的迷恋,或者说他感到翻译对中国文化界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业的这种想法,是他同时代的很多人所共有的。翻译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以后,就像是燎原烈火一样熊熊燃烧,在整个中国不可遏制。我们可以看出,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的新式文人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他们对世界不是排拒的,他们有一个很宽广的胸怀,是拥抱世界的。我觉得这种姿态一直到现在还是很重要。我并不是说,“拥抱了世界”就要忘记自己的文学传统。因为,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拥抱世界,反而会使你的文化传统变得不断与时俱进,使其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校正力。
2015年是《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我们想一下当时胡适、陈独秀他们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陈独秀当时为什么要拉出一个“大口径的大炮”对传统文学进行猛轰?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学在某些方面不够接地气,习近平总书记也经常讲文学创作要接地气。比如陈独秀当时批评的是那些无病呻吟的贵族文学及山林文学,这些都是他攻击的目标,他们希望“为人生的文学”。所以,鲁迅先生通过他自己的翻译和创作,不断地把“为人生的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
刚才我说到,翻译在19世纪末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当时的人们觉得一定要去了解外国,知道外国文学是怎么样的、外国人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他们跟我们的价值有什么是共通的,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哪一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哪一些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林琴南(林纾)对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特别多的。他最开始是翻译《茶花女》,后来他翻译《黑奴吁天录》,《黑奴吁天录》就是他在杭州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翻译出版以后,鲁迅刚去日本,他的朋友还把这本书寄给他。鲁迅在《黑奴吁天录》这样的著作里面看到了中国的缩影。这本书里讲到了两种黑奴:一种黑奴是逆来顺受的,像Uncle Tom,他是虔诚的教徒,他不反抗;但是在《黑奴吁天录》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混血黑人,他坚决地反抗,离开了美国逃到了加拿大去。林琴南他在翻译时有意地要形成一种对照,说明还有一种反抗的黑奴,他希望这种反抗的黑奴形象能够激励中国人,希望大家能关心自己的民族、国家,不甘愿成为奴隶。鲁迅先生在日本读到这本书后,对他的启示是非常具体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振作。那个时候的翻译一方面是文学的翻译,但与此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文化视野的开拓,它是要唤醒国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如果继续这样浑浑噩噩地下去,何时才能不做奴隶?
早期的翻译有特别多的政治内涵。林琴南就把他翻译《黑奴吁天录》的目的交代得清清楚楚。《黑奴吁天录》前面写前言,后面还写跋,都有着它的政治目的。《黑奴吁天录》原书里面有很多基督教的说教,林琴南基本上都把它去掉了,他觉得跟中国的现实不太合,作用不大。所以他更强调《黑奴吁天录》里那位年轻的黑人的英武气概,这种英武气概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特别重要。
我们发现,自1900年以后的几年,浙江到日本留学的人特别多。比如在绍兴,秋瑾就是其中之一。对秋瑾他们来说,当时留学日本非常想学的是“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就是强调“尚武”。他们觉得中国的文学太“文弱”,读书人又耻于当兵,这是不合理的。中国传统的戏剧里面,有这么一个模式,那就是女孩子喜欢的大都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发愤读书并考取状元后荣归故里,大家都要抛绣球给他,我们要看的是读书的成就;对于武艺高强的武士,可能女士不一定喜欢。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里面,很多英雄都是单身。秋瑾那个时代的人突然意识到,如果过分崇尚文学的造诣,我们的民族就会变得比较文弱,所以他们要提倡“军国民主义”。当然,如果“军国民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变成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这是非常不好的。但这对当时的国民来说,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剂猛药,使大家清醒。林琴南翻译的一些作品里面,有一些也讲到了战争,他甚至也翻译了日本人的小说,其中就讲到日本人在日俄战争期间,要把俄军打败,必须抢占旅顺一带的军事基地。林琴南就认为,日军打仗不惧死亡,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在打仗,一百个人哪怕是九十九个都阵亡了,只要有最后一个人存留下来,并战胜了,就是日本胜。林琴南翻译这些作品是为了唤醒、激励当时的国民。因为晚清时候的中国人国家观念是比较淡薄的。所以,当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民工甚至要去讨一个活干干,侵略军要在中国找民工是特别容易的。
到了鲁迅的那个年代又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知道,鲁迅一到日本后,就马上开始练习翻译。他早期的一些作品,翻译、编写和创作是混杂在一起的。
鲁迅到日本不久后就开始写作,有一部作品叫《斯巴达之魂》。《斯巴达之魂》其实和秋瑾他们所仰慕的“军国民主义”是差不多的,讲的是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比较重视文教,在它边上还有一个城邦叫斯巴达。斯巴达人的生活比较艰苦朴素,但是他们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传统,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共同体的观念。说到共同体这个观念我还要特别强调,就是中国传统文学里面共同体的观念是不强的。我们有家的观念,有国的观念,但是家和国之间应该有一个连接,这个连接的东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社会。如果要叫英文的话,除了“society”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可能平时我们不是很强调的,叫“community”。“community”我们称它为共同体,叫社区,它是超越家庭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共同体内的任何人都友好。但这种精神我们现在是缺失的,是做得不够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对陌生人不够友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强调家的观念不能过分,强调家的观念过分了以后就会导致只对自己的宗亲好,但对陌生人、对异姓就不好。像现在的产品造假问题,其实都是这样,因为那些人不觉得生活在大的社区里的陌生人也是他们的同胞,他们也要为同胞的利益负起相应的责任,这种观念可能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淡。鲁迅先生创作的《斯巴达之魂》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讲斯巴达这个小城邦遭遇了八十万波斯军队的入侵,斯巴达这个小城邦就汇集起三百勇士,到一个重要的关隘去防守波斯军队并最终全部牺牲的故事。鲁迅他也要用这样一个故事来激励普通中国人的爱国心。在那个故事里面有几个场景还是非常感人的,就是在斯巴达三百勇士里面,有一位眼睛瞎了,得以活下来了。他回到家以后,他夫人觉得非常耻辱,因为她觉得她丈夫是活着回来,而其他人都牺牲了!她为此非常难过,她自杀了。这个故事有点极端,我丝毫没有劝大家去学习的意思。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他们对于共同体是如此忠诚,一个幸存者的家人觉得其同胞都战死了而参战的家人没有牺牲,很难为情。所以鲁迅在1903年到日本去了之后不久,就根据日文的材料编写翻译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然,鲁迅后来也有所改变,过了几年他又写了《摩罗诗力说》,这本书介绍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像拜伦、雪莱,还介绍了东欧几个比较小的国家的诗人如何反抗殖民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源头性的著作,鲁迅用了大量的外国的例子来鼓励一种反抗社会的精神,是要“猛进而不退转”的,他希望用这样的一种精神来激励大众。
我们再回顾一下晚清,当时有一首诗是非常有名的,叫《哀希腊》。《哀希腊》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长诗《唐璜》里的其中一章。因为在文艺复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希腊及南欧的有些地方是被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是在亚洲的最西端,隔了一个海峡到对面就是南欧,南欧很多地方也是被它所控制的。所以不光是希腊,包括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都是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我们看拜伦的图像,他是英国的贵族,作为一名诗人他三十几岁就病逝了,他到巴尔干半岛去组织军队抵抗殖民统治,因为当地有伊斯兰教的信仰,所以他图像上是包着头巾的。拜伦在他的诗里面哀悼19世纪初期希腊的命运,这首诗就是《The Isles of Greece》,这个英文诗特别有名。好几位都翻译过这首诗,最有名的可能是马君武译本。他们翻译这首诗的真正意思其实是要激励中国人不要做奴隶,我们要争取自己民族的独立。在晚清,当时的文人们除了用希腊这个例子外,还经常讨论到印度,因为印度是英国殖民地;同时还经常说到波兰,因为波兰是俄国的殖民地,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当时整个背景下大的政治话语是分不开来的。
到了鲁迅先生的时代,翻译就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因为在晚清的时候,像林琴南、梁启超、严复等,他们特别强调“群”的观念,就是“group”或“community”。但鲁迅先生他们开始翻译的时候,他从《摩罗诗力说》之后开始比较突出“个人”,喜欢尼采式的“超人”,而这个“个人”可能和当时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他是敢于顶天立地反抗整个社会。五四青年的翻译作品里面比较突出个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发现了个人。我们现在研究时也会说,鲁迅他们认为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特别杰出的个人。但我的观点可能会和他们有些不一样。
中国传统的文人,传统的诗文,从《楚辞》开始就是有一个传统,总是有一个孤零零的文人对抗着整个黑暗的世界,从屈原开始就不断有这样模式出现,后来的一代代诗人也在重复着这样的神话。比如这个诗人是特别优秀的,却没有被当时的政权所认可,他觉得他的才能要被浪费。他看到他自己应该是一棵参天大树,是一棵松树,应该到朝廷里去做宰相,但他觉得自己在涧底没有人关注。最终是高坡上的小草,长势很不好的植物,凭借比较高地势占得了优势,他们不断享受着阳光的照拂,享受着君王的宠爱。这在中国的文学中是特别多,就是有一个失意的个人对抗整个社会。所以,五四时期这种孤零零的个人形象就出得特别多。但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孤零零的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学上那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模式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它有一点尼采式的超人思想,好比我有一个巨大的意志,使我敢于藐视庸众。就好像他们当时翻译的易卜生的一个剧本叫《国民公敌》,如题所示,里面有一个角色是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但所有人并不一定是对的,有可能真理就掌握在这样少数人的手里。所以五四时期对这样的大人物特别崇敬,而这种崇敬背后其实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鲁迅称其为“个人的无治主义”。鲁迅先生当时受到了一位叫斯蒂娜的影响,她和19世纪末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就是说这样的个人是和社会坚决不合作的。中国的传统失意文人是把自己看得独一无二,是参天大树,要到朝廷去做大官;但五四时期的这些雄伟的个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和社会不合作。所以鲁迅先生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还翻译过俄国当时一位非常极端的作家叫阿尔志跋绥夫的一部作品叫《工人绥惠略夫》。这部作品讲一个死刑犯绥惠略夫反抗沙皇政府,他在警察的追捕下躲进剧院,并在里面向观众开枪,最终被警察逮住。他看起来有点像一匹“独狼”,是一个孤零零的恐怖分子。鲁迅在有一段时期是很为这种个人的无治主义所吸引的。所以我说到1907年的时候就有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鼓吹这种主义,在日本东京鼓吹的是刘师培和他的太太何震。鲁迅先生在留日时期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是很浓的。所以有一阵我觉得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有发现个人的因素,有积极因素但也稍微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成分。这些庞大的个人常反抗社会,为着反抗而反抗。但鲁迅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转变,这也为他在1930年正式加入左联做了铺垫。因为鲁迅先生在早期的大量信笺、随感录里面,他都是看不起“庸众”的,他把他们叫作“mob”,英文里就是“群氓”的意思。但到了20年代中期以后,他慢慢地对民众有了更多的同情。所以到了30年代左右,他在跟一些所谓的莎士比亚专家辩论时就不再简单地站在所谓“庸众”的对立面,他能用更积极的眼光来看待群众,也正是这一积极的改变促使他后来走向了左翼。所以鲁迅当时还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理论,尤倾心于苏联成立前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学思潮,于是他后来就写下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祝中俄文字之交》和他前期所翻译的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也是有关系的。像刚才我所讲到《工人绥惠略夫》时,我们也能看出当时俄国民众的生活是极端困苦,但是鲁迅能从俄罗斯人面对痛苦的情况下看到他们的伟大,鲁迅一般很少表扬人,却会说“伟大的俄罗斯民众”,他的思想开始一点点变化,对普通民众有了好感。所以鲁迅也开始翻译十月革命以后的新文学,他所翻译《死魂灵》这种革命文学又成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活水源头。因此,我们会看到,外国文学的译介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多方面的互动,自1907年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当然,鲁迅还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本及日本的一些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籍。我觉得我们对这些文学批评所作的研究是不够的,因为有文学批评里牵涉到大量的欧洲文学理论和文学家,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进。鲁迅先生翻译的面很广,他还翻译过不少荷兰的文学作品,对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极大。
除了鲁迅之外,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现代文学有哪些奠基人与翻译结缘。林琴南主要是用古文创作,是一位翻译家,他对中国白话文学的贡献是有限的。当然,他在1898年写过一个特别重要的诗集,叫《闽中新乐府》。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想一想,中国新文学史的奠基人有哪几位?茅盾、郭沫若、巴金、冰心、曹禺,哪一位不是翻译家?每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都是翻译家,这个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极少见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还有幸看到一些前辈学者,比如我在外国文学所时见过冯至先生,他是研究德国文学的,他翻译了大量的德国文学作品,鲁迅先生又说他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冯至先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去世,他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外国文学研究所还有其他诗人,比如卞之琳,他翻译的作品是特别多的,他把莎士比亚的四个悲剧作品都翻译出来了,他还翻译了大量法国小说和英国诗歌,他自己是诗人。当时外文所还有一位叫李健吾先生,李健吾先生的笔名叫刘西渭,他写了大量的剧本,但他是研究法国文学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来。现在健在的杨绛先生,她已104岁了,杨绛先生也是翻译家。而且后来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像卞之琳先生、冯至先生他们的翻译不一定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或者政治信仰,借此进行传播。比如冯至先生翻译时主要看重一部作品的文学地位,而且他还引进了十四行诗这种诗体并加以创作,特别优秀,最终又被德国人翻回成德文,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然后像卞之琳先生他们就受英国现代派影响比较大,像艾略特、奥登等。因为像卞之琳这批中国诗人他们在三四十年代写作时特别强调“非个人性”,用英文说比较好理解叫“impersonality”,对中国诗人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的传统诗人他们喜欢伤春,喜欢悲秋,喜欢登高,喜欢抛洒眼泪,有很多诗歌是属于无病呻吟的。但我们看中国现代像卞之琳一派的诗,他们对感情是非常节制的,是不外露感情的。梁实秋受此影响也很大,他到美国去留学,他在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强调“文学的纪律”,这是一个古典主义的概念,就是不放纵自己的感情,有太多的个人成分。这种理想也反映在学衡派身上。学衡派相比较而言对翻译的贡献少一些,但他们都是美国留学生,这些文人一方面有一个宏大的西学背景,一方面又想用西学来维护中国的传统,但他们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旧派的中国文人,他们是在对西方文学格局了解的立场上来维护中国文学的传统。实际上吴宓是外文系的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他讲文学与人生,其实他基本上讲的是外国文学作品,小说和诗歌都有。所以我感到很奇怪,在民国的时候,外文系的学生是文学创作的先锋。在北京大学,胡适实际上是在教英国文学,国文系的一些老师像马裕藻是做小学的,就是训诂、音韵,他们跟文学创作的关系不大,与文学创作大的反而是外文系的学生。比如胡适在北大既教英国文学又教哲学,因为辜鸿铭以前是教英国诗歌的,后来外文系有一个学生做了清华大学的校长,就是罗家伦。然后有人就反映说辜鸿铭的英国文学上得不好,他一下说这个诗就是中国文学的《大雅》,一下说这个诗就是中国文学的《小雅》,在学生抱怨下辜鸿铭就离开了北大,他的英国诗歌课就由胡适来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林语堂,实际上他是英文老师,徐志摩也是教英文的,其他像陈源等都是这样。但鲁迅先生不是,鲁迅先生兼课一直是讲中国小说史,但他在外国文学方面,不管是翻译实践还是文学理论,他是站在特别前沿的,有一个比较眼光,所以做得特别出色。
清末特别是民初,出现了大量的杂志,翻译和创作两个是齐头并进的。比如茅盾,我们大多认为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杰出的作者之一,但他在编《小说月报》的时候,刊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茅盾的英文也相当不错,他能判断林琴南翻译的作品和原文是不是相近。巴金服膺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他和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向来有深厚的渊源,所以他特别热衷于法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所有的这些我都感到很奇怪,他们一边从事小说的创作,一边进行翻译。老舍翻译的东西就杂一些。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和外国人也有一些交往。有一位英国现代派作家叫康拉德,擅长写海洋题材的小说。老舍特别喜欢康拉德,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康拉德的海洋小说里面总是讲一批海员,他们在水手长、二副、大副、船长等的带领下面对很多艰难险阻,小小的群体战胜了很多自然界的灾害,使他们的大船平稳地行驶在辽阔的海洋上。老舍对这一方面很感兴趣,他的英文是很好的。新中国成立后,老舍还翻译过萧伯纳的戏剧《苹果车》。冰心也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英文水平很好。郭沫若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翻译方面的才能我就不说了,而且就他早期写的白话诗而言,我觉得他也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外国文学。
中国早期的现代文学奠基人,他们都是把翻译、阅读外国作品跟自己的文学作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当时钱玄同看鲁迅先生在搜集碑帖,有充裕的时间,就让他给《新青年》写东西,所以他写了《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完全是从俄罗斯文学里脱胎出来的,因为果戈理写过一篇同样题目的短篇小说。果戈理的小说中,这个狂人的精神病是一点点走向深化,最终一步步走到无可救药;鲁迅小说中的这个狂人最开始时就确定了,最后他将这整个作品变成是讨伐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檄文,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社会是几千年来的吃人的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的信息。鲁迅先生还有很多作品,一直和翻译有一个互动,现在学界对这方面的发掘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之间其实有一个互文性。
中国现代文学自来到世上开始,就明显地带着世界文学的烙印。鲁迅先生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想办一个杂志,就叫《译文》。这个《译文》就是专门用来登载翻译的文学作品,但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一直到了40年代,研究法国文学的傅雷先生想在上海办一个杂志叫《世界文学》,结果仍是不了了之。到了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局势稍稍安宁,外国文学的研究又重新踏上正轨,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杂志叫《译文》。《译文》杂志到了50年代后期的时候改名为《世界文学》。《译文》的第一任主编就是茅盾先生。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从林琴南那个时候开始,还是从《新青年》创刊时算起,最终它都是把世界文学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但并不是说有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就脱离了本土的背景,其中这其实有一个积极的消化理由,就是将其变成我们自己文学创作的基地。说到文学,我们很大程度上想到的就是小说创作,小说创作在中国传统文学里面不是这么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学是重视诗文的。中国传统的小说有很多连作者是谁大家都不是很在意,小说要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也正是通过翻译以后,小说成了一个很崇高的文学类型,最有才的人他们才会去创作,原来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的。所以小说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地位,而且它的地位绝对不低于诗文。这是郑振铎先生在林琴南逝世以后,他在写纪念林琴南先生的文章中指出的。
和翻译一并兴起的还有胡适和郭沫若等所提倡的白话诗。白话诗我们一直使用延续到了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会说,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要写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一种新的声音,那就是怎么样来关注新文化运动以后旧体诗词的写作?这是一种新趋向。所以,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发掘一些很好的旧体诗人和旧体词人。但是这并不能撼动新诗所形成的新的传统。
再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戏剧。曹禺先生创作了不少戏剧,他的这些戏剧有不少美国戏剧的影子。尤其是美国二三十年代一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家,叫尤金·奥尼尔,他对曹禺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当然,曹禺后来作品不多,但后续作品的模式基本上还是这样,和中国传统叙事不一样,像老舍这些作家也是一样。老舍先生翻译萧伯纳的作品,也是有意义地进行一个创造性的借用,然后来从事他的戏剧创作,但是他的戏剧创作又很富有“京味”。
我刚才说到的是小说、诗歌、戏剧,另外一个门类就是散文。我们现在说的散文和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文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英文和法文说的“essay”。鲁迅先生通过大量翻译日文著作,其实也是在不断地讨论“essay”这个门类。所以,散文写作后来也成了中国文学一个庞大的分支。我们现在四个主要的文学类型,就是在现代文学发展的时候奠定了基础。我们现在还生活在那个传统之下。但是我要说,这样的传统,我们不应去否认它,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说最好这一百年不存在,然后能和这之前的文人有一个无缝对接,以为对接之后我们就能确认自己不受污染的文化身份了。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可能不仅是偏颇的,而且可能还是危险的。鲁迅先生要是发现这种情况,一定会极其极其失望。鲁迅先生有一个焦虑,我自己和有几位同事交流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共识。鲁迅先生中文的书实在是读得太多了,古文太好了,他对于我们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太透彻了。他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曾经说过一些过于激愤的话,包括“不读中国书”,实际上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代课、在教育部任职所赚来的钱都用到了哪里?他主要是用来买书,他买大量的外文书,也买大量的中国典籍。我们如果到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去看看就会发现,其实他不仅很懂中国的古籍,而且买的也是特别多。但是他希望青年有一个向前看的眼光,不要太多地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拖累了。但我觉得这一点上他可能不一定对,因为我们的传统它有一个继承翻新的过程。比如说在当今的中国我们现在已经在科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物质基础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在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重新温习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可遏制的亲切感,和1915年陈独秀他们写《文学革命论》的时候有一种不同的心境。我们处于一种更安全的处境,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来发掘中国古代文学里面很多积极的因素,使它和我们现当代的其他元素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传统。但是这种新的传统如果真要顺利形成的话,它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要非常善于比较。我觉得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原来我们看中国文人,他们和国外的学术传统相比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的文化就是中心,我没必要学外文,这和唐代时去取经已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面,只有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国人到中国来学习汉字、购买汉籍,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传播汉字文化。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太去关注其他人怎么样。最近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有一个新的倾向,比如清华大学的葛兆光先生、南京大学的张伯伟先生开始关注海外的汉籍,比如在越南、朝鲜、日本用汉字写的书籍,尤其是关注这些书籍里面记载的这些国家的人到中国来看到了什么?他们是怎么评价中国的?原来我们的士大夫对这些不感兴趣,现在中国底气足了,也更开放了,所以他们对于这方面感兴趣。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处于一个比较的眼光,我们不仅要比较汉字文化圈里面其他旁支文化的人是怎么看我们的,而且我们更要注意自己要懂得外文,我们还要看外文的人和我们形成了什么样的差别,然后对其进行比较。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在这方面是有点吃亏的,因为我们这种比较的意识发展得比日本晚。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已经会用非常敏锐的眼光进行比较了,而且日本在比较中并不是将自己作为固定的一极。而在中国一直是“中外”比较,好像外国都是一样的,其实它们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中西”,好像中国是简单的一极,西方是铁板一块。其实我对西方的了解是特别不够的,所以当谈到西方的时候我觉得它们的差别非常之大,很难一概而论。这个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观察不细腻,我们比较的工夫不够,日本在这方面是做得比中国厉害的。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有这种非常敏锐的比较的眼光。这种比较眼光是怎么得来的呢?它是通过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一起参照起来读,这样的收获会很大。
现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现在有一种趋向,就是跟海外汉学界的互动更多了。千万不要小看海外汉学界,我对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永远要强调这句话。首先海外汉学界有一个学术特点是我们不具备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地方所有懂中文的汉学家他们的日文是非常好的。他们觉得你不懂日文你研究的汉学是不好的,因为日本汉学的研究是特别好的。我们如果去看日本对中国的很多具体的研究,比如说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冈村繁全集》,王元化先生为他写的前言,像这些学者对中国史料的熟悉程度是让人敬佩的。所以,海外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任何东西,他们不仅要懂中文也要懂日文,但我们在这方面不一定。有一些海外的研究者,对我们经典的翻译实际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我们经典研究的高度。翻译是一种解说,要想成功地翻译一部作品,必须要有大量的版本学工夫和扎实的考证。我们平时阅读我们熟悉的作品,读过去就是了,但翻译就不是。比如英国有一个翻译家叫David Hawkes,他翻译《红楼梦》特别著名。正是他的翻译使《红楼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在世界上有相当影响。他另外还翻译中国的《楚辞》,实际上他对《楚辞》的研究是做得非常深透的。现在美国又有人在做这项工作,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跟普林斯顿大学的Martin Kern又在翻译新的《楚辞》版本。他们翻译新的《楚辞》版本其实背后有大量是对文字的解释。因为对《楚辞》文本字词的解释在国内有时候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比如说汉学家宇文所安又翻译完了杜甫的诗集,这是很了不起的。我希望这些东西最终都能促成进我们的交流。如果我们说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懂,其他人不懂,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提。文化之间最终是没有壁垒的,但实际上有大量的文学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是人类所共享的。所以意识到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千万不要说到国外的东西就产生一种抵拒的心情。我们还是要像我们习总书记那样,就是不管对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还是外国文学,都保持一种新鲜、活泼的兴趣。让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都能让这种兴趣像一堆火一样,不断地在燃烧,然后这种燃烧就会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永远都有一种幸福感。
所以,我再次希望大家不管自己是中文系的还是外文系的,都一定要有一种决心,既要熟悉一种文学,也要多多地像鲁迅先生那样,去关注其他的文学,而且把其他的文学同样地作为自己创作和学习的资源,最终利用自己的勤奋和才能将这种资源使用到极致。
(根据《风则江大讲堂》同题讲座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林东明)
The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China
Lu Jiand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In his talk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Xi Jinping looked back on his early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mentioned many masterpieces in world literature as well as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inseparably tied up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a, and the pioneers or founding father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re all translators. Lu Xun and his brother Zhou Zuoren, Mao Dun, Ba Jin, Bing Xin, none of them is exception. Lu Xun’s effort to translate “literature for life” into Chinese has decisively transformed the literary sensibility of his countrymen. A positive appraisal of the translational enterprise in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flower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ng; spread; Lu Xun; New Culture Movement
中图分类号:I046:K 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2-0001-07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2.001
收稿日期:2016-01-06
作者简介:陆建德(1954-),男,浙江杭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