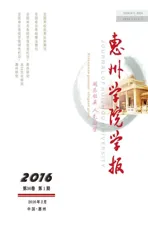“祇”和“祗”的源流及分别
2016-04-13朱学斌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战国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006
朱学斌(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战国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祇”和“祗”的源流及分别
朱学斌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战国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对于同一个隶定字“”,字形表及其检索表作“祇”字,释文却作“祗”字。前者是错误的,是未分清“祗”与“祇”的做法。经过考证,“祇”、“祗”有各自的字义、字形、字音,在战国出土文献中,“祇”字尚未从“祗”分化出来独立成字。所以应该分清“祇”和“祗”,把“”字释为“祗”。后世对古文字的隶定,要尊重字本身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战国文字;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祇”;“祗”
一、问题的提出: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谈起
但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的《芮良夫毖》篇二十二简释文却为“所(祗)畏[1]146”。连接上一简全句通读为“此惟天所建,惟四方所祗畏。”“祗畏”出现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的《芮良夫毖》篇,全句作:“邦亓(其)康(宁),不奉(逢)庶戁(难),年㝅(榖)焚(纷)成,风雨寺(时)至,此隹(惟)天所建,隹(惟)四方所(祗)畏。”释文“此惟天所建,惟四方所祗畏”当中的“祗畏”,意为“敬畏”。
“四方所祗畏”一句,传世文献《尚书·金縢》“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可与之相对照。按《说文解字》:“祗,敬也。”后世传世文献亦作“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但纵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字形表、笔画检索表、拼音检索表,当中不见“祗”字,唯见“祇”字。而“检索凡例”标明“三、本表字形略依大徐本《说文解字》部首序列分排[1]173。
根据《说文解字》部首序列分排,“祇”字见于《说文解字》【卷一】【示部】:“,地祇,提出万物者也。从示氏声。巨支切。”而“祗”字见于《说文解字》【卷一】【示部】:“,敬也。从示氐声。旨移切。”《说文解字》的“祇”、“祗”小篆字体差异可见,明显不是同一个字。因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字形表和检索表把‘’定作‘祇’,看来是混淆了“祗”、“祇”两字。
二、传世文献中的“祇”和“祗”
按《说文解字》“祇,地祇也”、《尸子》“天神曰灵,地神曰祇”,“祇”字的本义为“地神”,此用例又见传世文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修礼地祇,谒款天神”、《论语·述而》“祷尔于上下神祇”。
根据《汉语大字典》[2]2557,“祇”字从示,氏声,发音为qí,多用作名词。“祇”字本义是地神,引申出神祇(天神和地神)的意思。“祇”字其他义项“此兹”、“安心”、“病患”、“很大”、“盛大”等更与“所(祗)畏”当中“祗”字的“恭敬”义相去甚远。
值得注意的是,“祇”字作“病患”意思的时候通“疧”字,发音为chí。语例如《诗·小雅·何人斯》:“壹者之来,俾我祇也。”可翻译为:“前次你从我家过,使我生气病一场。”
根据《汉语大字典》,“祗”字从示,氐声,发音为zhǐ。本义是恭敬,多用作动词。传世文献当中的“祗”字,如《尚书·皋陶谟》“日尹祗敬六德”、《诗经·商颂·长发》“上帝是祗”、《周礼·大司乐》“中和祗庸孝友”、《广雅》“祗,祗敬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都表示“恭敬”的意思。“祗”字组词也取“恭敬”的意思[2]2562,如祗候人(在官府执役的小官吏);祗候(恭敬侍候);祗请(恭敬邀请);祗若(恭敬顺从)等。
“祇”和“祗”两字的相通[2]3282,见于《汉语大字典》“祗”字义项⑥:“用同“祇(qí)”。引《正字通.示部》:“祗,与祇通。”用例为唐代韩愈[2]2563的《与孟尚书书》:“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而“祗”、“祇”两字在传世经典当中出现的混淆,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字音上,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从“凡假借必取诸同部”出发,在“祇”字注当中认为“如周易无祇悔……通志堂刻作无祗悔、则误”。同时更在“祗”字注下明确地说明了“古音凡氐声字在第十五部。凡氏声字在第十六部。此广韵祇入五支、祗入六脂所由分也。”“祗”从氐声,上古音属于章母脂韵,上古属十五部,与氏声字不同[3]3。
传世文献中的“祇”和“祗”是两个不同的字,各有自己的音和义。两者有时可相互通假,“祇”可通“祗”,“祗”可通“祇”。依据传世文献,“祇”可通“疧”、“祈”、“祗”、“禔”、“坻”等字;“祗”可通“圻”、“祇”、“低”、“砥”、“振”等字。可见从“氐”、“氏”、“斤”声旁之字可以通假,所以“祇”和“祗”有时可以相通假。
至于“祇”、“祗”在中古时期在使用上产生了混淆[4]42-43,是因为“在‘音支,义适’的情况下,‘祇’、‘祗’两个字经常混用。”在《经典释文》的著者陆德明所处的隋唐时代,支、之、脂已经合流了[5]24-26。《正字通》更是得出合为一字的结论:“与祇通。郝敬曰:祗从氏下一,韵书别出,其实同。”
在传世文献中,“祇”和“祗”用楷书书写,两个字的区别是明显的。表地祇用“祇”字,表恭敬用“祗”字,只是在“音支,义适”的情况下可以偶尔相互通假,“祇”和“祗”仍是不同的字。
在战国出土文献的复音词当中出现时,“祗”的意思仍为恭敬:
一是“祗祗(祗祗翼翼)”,充当形容词,意为恭敬的样子。如战国中期的中山王壶《殷周金文集成释文9735:中山王方壶》:“(祗祗)翼卲(昭)告(后)(嗣)”[11]37-56。
二是“祗敬”,充当动词,“祗”、“敬”为同义语素,联合式用法仍表敬慎之义。《诗经·商颂·长发》:“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左传·僖公十三年》:“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此词传世文献亦见。《楚辞·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在战国出土文献中见于燕侯载簋铭文《殷周金文集成释文10583:郾侯簋、燕侯器》:“(祗)敬祀。”
三是“祗畏”,充当动词,意为“敬畏”,上文已经提及。
在出土文献中,“祇”字一般如本义作“神祇”义,但是都是其他字的通假,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三德》:“毋訽(诟)政卿于神(祇),毋亯(享)(逸)焉(安)。”另外,“祇”字在战国出土文献当中见于异体字“缇”字头下作、[12]195等形。
从出土文献来看,“祗”词产生得早,当在西周时代;表“祗”词义“恭敬”的是“”字。到战国时代亦然,只是多出这种字形。
四、结论
综上所述,“祇”的本义是地祇,而“祗”的本义是恭敬;另外,在出土文献中,“祇”可通为“缇”,“祗”可通为“希”;“祗”字有“祗”有异体字“”,而“祇”字无。在传世文献当中,“祇”字另有“正、恰、只”之意,如《诗经·小雅·何人斯》:“胡逝我梁,祇搅我心”。传世文献当中“祗是”的“祗”可以通写作“只”、“祇”、“秪”[14]2-3,但是在战国出土文献当中“祗”字并无“正、恰、只”的意思,释文、隶定时不可混淆。
所以战国出土文献当中的“祇”、“祗”二字理应区分开来,而不可混为一谈。“畏”的“”字字义并非“适”,战国出土文献当中的“祗”字不可替换为“祇”字,“畏”亦作“祗畏”,不可作“祇畏”。战国出土文献的“祇”仍写作“祗”字形,二字尚未分化,尚无“祇”的本字。但是,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当中,同一个隶定字“”,字形表及其检索表作“祇”字,释文却作“祗”字。前者是错误的,应该分清“祇”和“祗”,把“”都释为“祗”。既然《清华简(三)》要用楷书隶定,就应该分清“祗”和“祇”,表地祇用“祇”字,表恭敬用“祗”字。
参考文献:
[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M].上海:中西书局,2012.
[2]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
[4]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6:42 - 43.
[5]李福言.祇、祗、禔音义混用原因试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1):24 - 26.
[6]董莲池.新金文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7]孙刚.齐文字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4.
[8]汤志彪.三晋文字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3.
[9]王美盛.石鼓文解读[M].济南:齐鲁书社,2006:67.
[10]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23.
[11]王颖.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37 - 56.
[12]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95.
[13]臧克和.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M].广州: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999 - 1003.
[14]乔玉雪.“祗”、“止”、“只”的历史替换及相关问题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04:2 - 3.
【责任编辑:赵佳丽】
Origi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Zhi”and“Qi”
ZHU Xue-b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Abstract:In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Tsinghua University(III),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is brought forward as“Qi(祇)”in the glyph table and the retrieval table,but as“Zhi(祗)”in the word interpretation. The former is wrong as it does not distinguish“Qi(祇)”and“Zh(i祗)”. Textual research shows“Qi(祇)”and“Zhi(祗)”have their own different meanings,forms,and sounds,and in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Qi(祇)”has not been separated from“Zhi(祗)”. So read⁃ers should distinguish“Qi(祇)”from“Zhi(祗)”and interpret“”as“Zhi(祗)”.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of the early archaic Chinese language should respect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the word itself.
Key words:characte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excavated document;classical document;“Qi(祇)”;“Zhi(祗)”
中图分类号:H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5934(2016)01 - 0070 - 03
作者简介:朱学斌(1993 -),男,广东广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YY106);华南师范大学2015年度“挑战杯”金种子项目(C1090402)
收稿日期:2015 - 12 -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