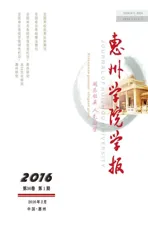南洋金英教符咒的护身、医疗与社会功能
2016-04-13王琛发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马来西亚吉隆坡
王琛发(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马来西亚 吉隆坡)
南洋金英教符咒的护身、医疗与社会功能
王琛发
(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马来西亚吉隆坡)
摘要:金英教以罗浮山客家人地方教派流传至南洋地区,至今自认教法传承源自“佛、道、仙”三教三位神话祖师结义开教,并基于儒家价值教导教众遵守“五敬”与“五戒”为人处世。教派过去能在南洋华人社会持续发展,主要由于它使用家乡方言举行仪式和念诵咒语,入会仪式暗喻民族大义,极易唤起民众的乡梓记忆与文化感情,其开教神话亦有利在信仰氛围浓厚的先民之间烘托教派神圣可靠。另外,过去的乡野地区,现代和传统医药都不普及,金英教以教法和符咒协助民众治疗不论来自身心的疾病,还是炮击刀伤,用材与理路都暗合传统中医药,不失为符合平民百姓经济负担的简单实用选择。发展至今,原本客家教派的教众与信徒早已多元民族化,教派对医疗观念与本身的社会定位显然也有调整,但其真正人事历史的研究还待学界更多努力。
关键词:创教神话;前传口教;林显江;金英子;符咒
自清代以来,金英教由广东惠州罗浮山传播南洋,早期主要以来源地区的客家方言传播,教派到了南洋,主要也是传播至华南先民聚居的开拓区,尤其是客家方言群较集中的地区。到今日,金英教教众散布各地城镇乡野,已经由于城乡人口变迁,发展来自其他祖籍的华人,甚至拥有外族的教众与信众。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越南,许多迄今盛行客家方言的地区,依然可见地方上的金英教众使用客家话念诵咒语。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有些教坛采用其他闽粤方言,包括以普通话为媒介语,举办内部以声称依靠“前传口教”一脉相承的入教仪式。
探讨源自中国客家地区的教派为何与如何在南洋地区传播,或可以金英教为例,回到教派存在目的讨论。除了重视当地早有客家群体,以及南洋各地方散布华人聚落,语言与文化相近,有利教派方便传教,更重要的原因,还要看教派南传能否发挥有益当地社会的功能,支撑或满足地方群众在文化认同、社会安全、生活方式等领域的需要。
一、创教神话背后的道德与价值认同
据金英教的说法,它创教于约三百年前,其始祖林显江可能是原属全真道的广东罗浮山白鹤观道士,他被教中尊为“五岳五观林太祖师”,金英教迄今也追认中国罗浮山白鹤观为祖庙。它与清末惠州、增城一带各宗道士的合流,以及两地当初借助宗教神道号召的农民起义,有极深的渊源。按教众相传先辈回忆,自起义队伍撤散后,其成员南下南洋各地,除了传教与济世活动,在各地亦拥有抗英反殖的记录。[1]65以新马两地信众记忆为例,便有传说,自金英教众散播当地,至清朝消亡以前,其教众入教仪式,尚流行由传教师持伞站在由三张桌子叠成的高台,主持仪式[1]66。这是借助公开仪式暗寓“不见青(清)天,不踩阴(英)地”的骨气,教人感叹民族气节礼失求诸野,暗藏教派中[2]29。虽说如此仪式随着清朝灭亡也逐渐式微,可当年金英教众不忘教导民族气节,以神明鉴证大是大非,实有利神道设教的努力,将民族意识既强化又内化为教众信仰生活的俗世立场。
关于金英教的缘起,至今充满神话。“五岳五观林太祖师”的称号,也许是指林显江身兼中国五岳的道观传承,但是有位金英教开坛主持告诉笔者,这是指林太祖师教传五岳五观,但此说令人怀疑。第一,一般道脉,如果教法只能是分布五观,没啥值得大书特书;第二,“五岳”若是一般人认识的“五岳”,范围未免太大,而且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五岳道观有金英教的传播。实则,如果按南洋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南部一带金英教众广泛传抄的《罗浮山白鹤寺金英教序》逐字翻看其中描述“教史”的渊源,金英教祖庭据称是“白鹤寺”,而不是“白鹤观”,居然难以从地方文献对照。可是,笔者001年春由数位暨南大学同仁陪同到罗浮山,依照教众辗转相传的地理位置寻访“白鹤寺”,发现白鹤洞原址只有“白鹤观”,考虑到金英教内部的口述历史明说,部分教众曾经挥别白鹤一路转战南下,以后又在南洋经历零星起义,笔者过去也曾怀疑,初期教众是否有心掩护祖庭,刻意称“观”为“寺”[2]29。后来发现,当地也有人习惯把“寺”与“观”混称,当一群热心人介绍“白鹤寺”时,就将笔者等人带去地方志记载的“白鹤观”。但至少白鹤洞一带的父老还记得过去当地常有白鹤栖居嬉戏,吻合教众集合祖庭分散起事的传说[1]79。只惜原址多年来被改造为军事重地,无缘入内参访[2]29。再后来发现,南洋客家民间教派,本有将“观”与“寺”混称的例证,特别是某些教派,受着白莲教等信仰系统强调三教合修”的影响,既建道观又供奉佛像,为求突出提倡“三教”有别于一般道观,也会延续称“观”为“寺”的习惯①。
依据《罗浮山白鹤寺金英传序》考据林显江传下法脉,这整套“创教神话”显然深受民间流传《西游记》影响,是接续着唐三藏取经的神话故事,编造出烘托教派非凡来历说法。金英教在民间宣称其教派三教合一,所以其开教神话就除了说教派主要祖师是七岁修行的赤膊金英子,又说这位祖师后来得到宿世道友唐三藏鼓励,再巧遇茅山仙师及潮源洞师(七姑仙女),三者结拜,往西域取经,所以金英教奉称他们为三教祖师。而他们共传的本领,以后由林显江发扬光大[3]69。
在各金英教分脉辗转相传的《传序》,其中提及:昔日金英祖师在西天极乐世界成佛,曾与金禅老祖结义金兰。后因金禅老祖在天庭打破玉盏玻璃,导致佛祖大怒,罚他下凡转世受苦,金禅领旨转世为唐三藏。其时金英正在把守东河桥。多年后,三藏成就正果,回返西天极乐世界,由佛祖告知三藏,其前世是金禅老祖,曾与金英结义金兰,触发唐三藏往东河访问金英祖师的因缘。金英祖师听完唐僧叙述前往西域雷音寺取经功成事迹,感慨喜悦,也要前往取经。途中,他在“波罗沙甲地”先遇到茅山三仙师之中的末师,结伴同行,半路又遇上七姑仙女最末一位,即在潮源洞修行的潮源洞师,三仙一见如故,结伴前往取经。这三位祖师,也即是金英教崇尚的奉三教祖师。祖师偈言:“大破天门正出世,把守东河正世身,通是西天佛法教,何怕风吹摇动人,结义茅山潮源洞,各为三教老祖师,太上仙师同帮助,传于世间弟子知,完全此语诗十首,正是天上为金英。”另外,也有较详细说法,提及赤膊金英子七岁在玄山修行、九岁得道,得度西天学佛法,奉御旨把守河东,总结其神仙事迹可以用八句诗文:“玄山成道果,玄门第一仙;亲身朝王阙,东河守苦居。号令如山岳,众神不敢欺;赤膊金英子,日月化仙虚。”[3]69
但是,据马来西亚甲洞南华宫有缘收藏的手抄道派法本,其中有马来西亚甲洞地区流传的封面混称《茅山道术》的手抄法本符书,内称是“五学五观林太祖师称(亲)口传教陈飞龙,亲口传教陈法辉四郎”的系统,其说法提到了金英教三师的前世因缘,抄本上记录了许多看似以普通话读念客家词汇造成的谐音讹字,先说金英和金禅在盘古开天地时和西天如来曾结为兄弟,一同往天门破阵,金英是破了天门阵通了大海,得到把守天河的“正出身”,而金蝉是破了白鹤金岗(刚)黄河阵后,往西天斋堂学法,不慎打破香炉,犯了“文罪”,下凡为三藏。而其诗证后部也与上述不同是说:“大破天门正出世,把守东河正世身,我世(是)西天佛法教,何怕风吹摇动人,先有金言带吐出,我世上头为金英,请师归转死园内,法界上头是虽(谁)人?”接下去又有说茅山仙师把守南天门不能“破了”(开悟了生死),兄弟“带来身之地,走在波罗头安宿,异日出世,安名茅山仙师,居波罗吵(沙)呷哋”;而这七仙女也被指是破金岗(刚)黄河阵时,重伤(散)六人,应凡一位,为了西天求法,才在波罗吵(沙)呷哋遇到金英祖师和茅山仙师。
金英教既然传播这样一套开教神话,后人若要追溯教派在林显江以后的发展,固然可以有人物有地点可考,可以追溯师承与分脉系谱;但是要解读林显江前期的创教神话,若硬要从历史文献与年代考证上下功夫,就绝难欣赏其中意义了。然而,如果要追溯类似说法的渊源,早在明正德年间,就有无为教宝卷的先例,金英教其实尚在后期。无为教《叹世无为卷》自称“有心待把法不传,背了唐僧发愿心”,并唱念:“三藏师,取真经,不是虚言。老唐僧,去取经……”,这是以唐僧自况,说明教派所传都是难得真经,也说出修行成道很辛苦。而嘉靖年间黄天道开教,更自认全真道正统传承,其《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等经典,便是以取经比喻修道,出现“修真须要采先天,意马牢拴撞三关……龙去情来火焰生,汞虎身内白似金……古佛化,现唐僧,六年苦行,自转真经”[4]158-159等等说法,以《西游记》比喻由“修道”到“成佛”的经历过程。参详金英教一整套创教神话的深层意识,金英教开教神话中,赤膊金英子正如许多道派修行人物以“某某子”身份称号,又说“玄山成道果,玄门第一仙”,足以证明他原来拥有玄门羽士本相;而开教神话强调祖师学习唐僧西天取经,还是反映着民间教派企图糅合释道两教“性命双修”的风气,借用“再演”《西游记》比喻其教法主张“修道”到“西天佛法”;既要从修仙入手,学法求长生、求趋吉避凶,又想要明心见性,超三界成佛。
所以,神话后头的道理未尝不是教义真相。金英为了要学金禅求法而路过“波罗沙甲地”、茅山仙师要从“波罗头”转世到往西天的“波罗沙甲地”,潮源洞师也在此地与他们相遇,正说明金英教自认继承的多种传承来源,原来都有类似的修行最终指向。由此或可推测,所谓祖师死过再生、重新出世(做人),以及从“波罗头”到通往西天的“波罗沙甲地”的说法,其来源可能相关道教修行的归根复命功夫,也相关佛教词汇“波罗”与“揭谛”,即“觉悟智慧”与“登彼岸”。神话与通俗传教的结果,是把向往的修道境界,从象征意义说得像其他空间真的存在“波罗沙甲地”。
只不过,金英教的“三教”强调以金英子为主,教派另奉茅山三师之中“末师”和“潮源洞师”的传承,而不是抬举儒释道三教教主,就表明它所指的“三教”有两层意味,除了意味着思想上继承“儒释道”三教,也意味着其传承历史结合了民间金英、茅山、潮源洞三个教派的教法。教众子弟也有因此将“三教”传授的三师教法解释为“佛、道、仙”,将“道”与“仙”分开者,从中或可推测其“仙法”即指内外丹法。这亦反映,金英教的最早传承可能经历过对外融合,先后接续与纳入“茅山”与“潮源洞”道人传授的功夫,所以要求后世弟子合祀“三教祖师”,以示崇德报功,慎终追远。这或许能解释金英教众为何要自称“道教”,或自称“西天佛祖教”,却又偏偏不将自己归纳“佛教”。
直到现在,金英教用符,确实包括茅山道派流传俗家法教演变出的那系列符箓,除了“过教”使用的符章用上“茅山祖师”等三教祖师名号,或如“急医术符咒”等符法还会用上“赫赫阴阳,茅山法主降凡阳”等名义。但至于所谓“潮源洞师”,是否关系到青莲教其中在南洋传教的张东初分脉自1860年代回返罗浮山朝元洞设坛的渊源,难以查悉。只是,朝元洞自认“儒门修道”,确有修炼内外丹法,其坤道专修女丹仙道,表面以“小姑娘”、“老姑娘”、“大姑”、“姑太”相称修道位阶,尤其修行到一定阶段,诵经上表都必须由修炼女丹及斩赤龙有成者主持,自称“男儿”。[5]56从金英教创教神话总称“潮源洞师”参与为“兄弟”而非“兄妹”结义,以及部分金英教用符,包括符上加强法力“花字”,会采用青莲教不用的“青莲教主”名称,也许足以反映金英教其中确有部分源自朝元洞系统的影响。
然总结金英教教规,其教义表现在重视弟子日常为人处世,建议将天命人道归结在儒家价值观去体现。其入教弟子遵守的“五敬”内容包括“一敬天恩浩荡,风调雨顺;二敬地育万物,五谷丰登;三敬君临威德,頼及万方;四敬亲顺亲心,父慈子孝;五敬师重道义,同骨肉情”[3]69。基本上还是归服儒家伦理,是将一套对待“天地君亲师”的态度作通俗的延伸解释。而金英教的“五戒”,则可能由于山区民间狩猎生活,以及应对社会斗争的形态,教派戒律也就不似佛道教原来五戒会针对“妄语”、“喝酒”与“杀生”,而是针对着人们常见的“奸淫邪色道”,要求教众“一戒奸娼败名,不知廉耻;二戒淫逸骄奢,任情妄行;三戒邪恶罪行,邪歪气性(盛);四戒色迷意乱,想入非非;五戒盗窃劣根,毋败家声”[3]69。笔者注意到,金英教反对“妄行”、“邪恶”、“邪歪气性”,较之笼统解说“妄语”、“喝酒”与“杀生”,更能概括社会上各种具体人性错误。
按照金英教自家人评语,教派最基本目标在导人向善。“五敬”旨在教诲弟子世人向善,建立亲情、国泰民安完美社会,“五戒”旨在重整社会道德信仰、以修身培德、弃邪归正、扬善救人,这是要结合在儒教的仁义、佛教的慈悲、道教的修身养性,普度众生。[3]69然而还得考虑,具体道德标准到了不同群体,受重视的轻重程度,毕竟会受着历史与文化背景左右。“天地君亲师”这套理念,易于在华人之间传播,正是由于它源于大家共同接受的社会文化主流观念,所以金英教将之延深解说,转为神圣教谕的教众社会规范,也容易被大家信受奉行。深一层看,金英教创教神话、“五敬”与“五戒”,它礼敬神灵和三教祖师的活动,还有它的过教仪式所隐喻的民族意识,并不是可以分开独立呈现的概念,而是要互相结合成为整体同在,展现在各个面向,才能形塑参与者对待特定教派的信仰观。
“五敬”与“五戒”被当作人类与鬼神互相感应、得到鬼神回应的神圣教谕。正由于一切构成整体教派印象的元素,都是源自同样土壤的儒释道三教价值观,或其相应的文化风俗表现,表达为这些元素的互相重组或再重组。教众加入金英教举行“过教”仪式,就不仅在脑海建立自身对金英教的认同,也是通过参与金英教的具体印象,内化对于以儒释道为根基的传统民族文化之归属感。所以,金英教作为教法传承的“三教”是“佛、道、仙”,作为神圣皈依的“三教”是“儒、释、道”。
金英教是俗家法教组织,即使祖师源自道教,资深教众自称道人,教内一般教众也不是蓄发、素食、独身的全真道士。教派正是要依靠创教神话,才足以解释其内部为何延续同奉儒释道三教的全真道色彩。由是,金英教创教神话作为神秘化且兼神圣化具体事实的符号,虽会导致神话叙述代替历史过程,但如此色彩的传教说法又是以永恒不死的神佛世界代替短暂多变的俗世历史,开启信仰的根据,连带将教派文化内容以及价值观念贯穿其中,丰富其内在的民族元素,一并形构为整体神圣印象。哪怕当事人本是文盲,对三教各自严密复杂的思想内涵不见得真有知识。这是从信仰忠诚启发共同文化价值,更有效感染信仰者思维态度。其入教仪式不仅注重提醒与重塑个人道德观,而且有利维持教派集体文化与价值认同倾向。
金英教到了南洋,以家乡方言举行仪式和念诵咒语,很容易吸引原来从华南各地离乡别井到南洋垦荒的先民,通过信仰聚会凝聚大众心灵中另类的乡梓认同,缩短心理上的家乡距离。大众信仰金英教系列活动,其实也是通过集体参与,在异地重建客家/华夏文化与价值体系。金英教延续着民间原来流传的《西游记》传说,从华人民间本有的信仰模式衍生出大众易于吸收的创教神话,在人们鬼神观念浓厚的年代,是更方便解释教派源流,也更有利烘托教法的高深,引导大众入教;尤其是它融入客家地区各教派成员形成自立体系,更有必要从神话的内涵说明教门传承的合理。
二、符咒演练注重保身与医疗功效
符咒是金英教各种法门的主要表达形式。金英教修炼,每到相关阶段都有相应的过教仪式。新弟子参加最基本的过教仪式,入教都得吞服符箓,师父表示弟子入教受到保护,也得用朱砂替弟子身上重要部位画符“封身”。还有所谓“寄石”或“寄木”,则是将新进弟子的生辰八字藏入小罐,到深山找石头或大树下埋藏寄放;另外所谓“寄水”,做法是将八字刻在铜板投入大海。新弟子过教,也会让新弟子见证以利刀猛砍腹部、以咽喉打筷子、以香火扫身过法等神功妙术。其中,过教过程有“叫阳师吐法”仪式,由师父口含茭杯吐法给新学弟子,是要学法弟子手握按唐尺计算三尺六寸长的红布,等待师父站在香炉压着红布的一端抛茭杯,教众必须得到茭杯,而且失手不得超过三次,才能通过入门。其中有所谓过“五行教”,是师父站台上,一脚踏在俗称“金炉”的铜炉上给弟子传授教法的。姑不论农工教众对“五行”观念理解多少,至少仪式摆现的威势巩固了概念的认同。如此亦证明教众入教是种殊荣,有机会“过教”不单靠人间缘分,不是师徒私相授受,而是天命允应,辛蒙祖师神圣遴选,通过完整的天人感应仪式,才能学好本领。且过教弟子之间,除了过教师父是“阳师”,还有“阴师”之说,即某些先辈已经成仙,犹能通过托梦或附体,传授法术。总之,教派各个过教传法步骤,目的在于去疑启信,强调“法”的存在,确认祖师与神明长期承诺佑护学法弟子,也换取得弟子长久忠诚遵守教规。
金英教弟子之所以过教,其中精彩者,也就反映在其入教的祝表和符咒往往反映着人身安全的愿望。
以甲洞地区传本为例,教中《表闻师公》从祈请诸天神灵一直到“前传口教历代祖师”,祝愿的原因是“扶持弟子头如铁身如铁木,手如钢条刀,口如软化铁如棉,力如猛虎……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入律令”,而《请神》一路请到“本宗师傅,下罗浮山白鹤寺五学五观林太祖师称(亲)口传教陈飞龙,亲口传教陈法辉四郎”,也是总结在“刀来刀顶、棍来棍顶,炮码打来远走他方……不怕猪羊狗血,不怕五色军器、不怕刀枪利器”。此外,教众入教接受所谓藏魂寄石的保护,《藏魂表神咒》是为了避免受到邪术伤害,或担心刀兵灾害,导致魂魄散乱丢失,所以设想到古代水底镇江河的大铁牛,念出“十八罗汉扶持弟子化为铜皮铁骨……藏身铁牛肚内好”,《寄石咒语》则说“斩那(哪)里,寄赖(那)里……打一百,寄在深山大石格;打一千,寄在深山大石边,打一千万,寄在西天佛祖边栏(客家话:旁边)手撑在内”。
到了马来西亚槟城州,根据当地登家楼路附近玄武宫有缘收藏的金英教法本(内中未有文字提及传承系统),在《敬香请神咒》之后唱念的《喼寄打符食咒》或《喼驱邪符咒》,也是直接说明教众祈愿入教学得刀枪不入:如《喼寄打符食咒》的开首几句即说:“扶持弟子某某某,不怕横人枪刀利器,枪来抢顶,棍来棍顶,任斩不入身,任锯无痕,炮来炮隔,全身寄在深山大石隔”;而《喼驱邪符咒》末句则唱念“凶神恶煞邪魔鬼怪妖精化为尘”。
配合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有“顶打符”、“人身肚中符”、“炮码符”、“左手符”“右手符”、“左足符”、“右脚符”,还有“初一、十五食符”,其中用语有“百打百胜”、“刀斧劈来当坭(泥)尘”、“玉皇大帝扶持弟子炮伙打来风吹过”。
或者,必须考虑到金英教创教的时期背景——从华南到南洋,长期历经各种纷争战乱,才可能明白金英教为何过教会提倡教众修习燃香扫身、刀锯手臂、斧头劈腹、咽喉顶筷子之类的神功。客家语称弹药为“炮码”,像上述甲洞抄本《表闻师公》的祝愿包括“炮码铁器化为尘”、《请神》祝愿作“炮码打来远走他方”,还有《急符请师公》和《写大符》的咒语都有说“炮码利器打来化为尘”,都足以反映这些文字的出现年代不会太久远。18世纪中叶,马来亚华人社会发生严重内战,已经大量使用毛瑟枪等先进火器[6]123-133。此后,平民百姓身在殖民地,也经常会遇上非法土匪流氓或合法军人警察的枪炮威胁。金英教这些表文和符咒上的用词,恰似回应旧时代的写照。只有回归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社会环境,才更可能理解,那时的平民百姓,经常会陷入面对各类“横人”的情境。金英教教导大家如何“全身寄在深山大石隔”,又提倡凡夫之躯有办法一再幸获神人与成仙先辈附身教练武艺,确实很能直接满足老百姓保全个人平安的理想。
金英教众固然要遵守“五敬”与“五戒”,才能保障学习符法有效。可是,在有神论优势的社会,上述数套符咒,可谓切中大众在凡俗生活盼望的两大奇迹。教众要学习戒律道德,可以听儒释道三教讲述为人处世。但金英教的过教,却是承诺随时神迹保身,带给大家反击“横人”以至灵界侵扰的信心。同样的,当时医药不发达,再加上民众无从预测和掌控不确定的外来因素,事情不管是否真的相关灵界,民众无计可施往往宁可联系上妖魔鬼怪,看看能否凭着教法对付灵界寻得转机。金英教的驱邪符咒,是一口气把民间传说中各种灵界的负面力量,包括“凶神、恶煞、邪、魔、鬼、怪、妖、精”,都压制了,也真有神人一致大显威灵的豪气。
但是,不能否认,金英教的符咒除了以强调和保障刀枪不入作为吸引民众的重要特征,若以符咒种类的数量而言,它大部分的符咒都是为了应付治病救人的需要。以上述甲洞抄本为例,其中咒语便有“发冷咒语”、“急安胎下胎咒语”、“封咽喉咒语”、“急化骨咒语”、“博(驳)骨咒语”、“止血咒语”、“急化骨符咒”、“拔毒消肿咒”、“牙咒”,而符式则有“小肠气痛”、“发洋吊(癫痫)”、“手脚松软”、“脚肿”、“风软”、“刀伤”、“铁(跌)打”、“中炮码”、“保胎”、“下胎”、“安胎”、“马上风救急”、“发冷”、“吐血”、“肚痛”、“心气痛”、“化骨”、“伤寒”、“消肿”、“牙病”,以上各类疾病的符式几乎都是多达二式以上,按不同情况配合咒语使用。
如果比较上述槟城抄本与甲洞抄本,槟城抄本的符咒采用客家方言“喼”字,并且常以“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终结,而甲洞抄本在“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以外,也祈请一般神灵,常有以客家话押韵的“如到来”代替“如律令”,可以清楚金英教本源是客家地区道教影响。可是,根据金英教的练法座符的要求,以金英教“驱邪、寄打符”以及“安胎”、“发冷”、“肚痛”等医疗符共享的符架为例,看其符架笔顺结合哪类咒语催动符架作用,其义理思考显然与主流道教有差别,也有别于其他很多教派。其“驱邪、寄打符”咒语,是依照符架的笔顺念咒:“左转天地动,右转日月明,法杖华山一下鬼神惊,天令,地令,帝令,雷令,各位老师公命令,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在咒文中,“帝令”的“帝”所指何神,是否原指传民间传说力劈“华山”的华光大帝,尚待参考;但咒文“各位老师公令”,也意味金英教系列采用这种符架的催符咒语,在请神以外,也都祈请历代师承冥冥中帮扶。
上述“寄打”和“驱邪”咒,都提及:“师公签过灵符,如有符头咒语花字不够,师公加够;符头咒语花字写错,师公改正;符头咒语花字写多,师公收起”,其《急符请师公》和《写大符咒》亦是说“弟子请唔(不)到,师公来得到;弟子请唔(不)明,师公来得明”,这些都印着教派其他祝文/咒语常会出现的“前传口教”四字,证明金英教很强调历代亲传,也强调一切符咒要师徒面对面亲授,以至历代祖师都要对其传承负责,才能发挥符法力量。但是,这样一来,历代“师公”在教派的地位无疑成为历代弟子请神念咒画符依赖的保人。金英教咒语会搬出广府话/客家话称“师公”的“祖师爷”助阵,冥冥中又倚赖“阴师”,以至画错符也要请求“师公”在灵界佑护错有错着、有效有力,除了说是非常注重慎终追远,并借重死去仙辈“显灵”鼓吹民众继续用功修炼,何尝不是反映出教众的文墨水平参差不齐,以致必须依赖如此咒语内容补充画符者缺乏的自信。
参考教派出版物为证,南洋金英教画符,也有受到其他民间道派共通影响,遵守许多催符的规矩与禁忌,以保证符咒“无中生有”的效用。例如,在柔佛的金英教“旺相堂”一脉,其出版文字即有主张画符前的众多规则:首先要清洁沐浴,接着要先在家神前点烛焚香拜请,还要先在符主神点烛焚香;画符则要庄严有念力,不能分心,一笔要画到底,并记得下咒语;同时,要选择“破日”以外的吉日,以及选择阳消阴长、阴阳交除的子时或亥时,或者选较有灵气的午、卯、酉时[7]。当然,如果按照正统的道法思想来说,金英教众很多时候是按照求助者的要求,应急画符,正如全真道南宗高道白玉蟾的立场:“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无疑则心正,心正则法灵。守一则心专,心专则法验”[8]694。依据“心正则法灵”和“心专则法验”的立场,金英教从创教到发展过程,自成一套的设计许多符咒,或者从其他道派或民间宗教吸收改造他人符咒,以至历代教众还各有进入境界中悟得的“符式”,并无不妥。这些符咒配合得灵验不灵验,主要在画符者的存心。所以,教内外讨论金英教众对符法的要求,还得回到“五敬”与“五戒”,强调心识正邪的影响。
萨守坚作为传授“五雷法”祖师,在《道法心传》说:一点灵光便是符,时人错认朱与墨,元精不散元阳定,万怪千妖一扫除”[9]652。对比萨祖教诲,重温金英教“五戒”为何是“一戒奸娼”、“二戒淫逸”、“四戒色迷”,就很有意思。金英子想要再演西游,《西游记》启蒙意义在于唐僧求取西天佛法必须一路保住元阳,猪八戒则一再经受色欲的试炼;如果把金英弟子修道比喻为再演祖师“西游”得法,教众要达到历代口传所谓“西天佛法”理想境界,自然也得远离女色。可是金英教弟子不是出家全真道士,难以守元阳;金英教又总不能光是符咒经常出现“五雷”名称,却不顾“一点灵光”;这一来,其教派五戒关注“奸、淫、色”,隐约还表达着遥接全真南宗雷法渊源的痕迹,又是以修炼符法加强教众修身的要求,规范教众正常家庭生活与家庭外的两性关系。
若是从文化传播角度去看,包括金英教等近代闽粤民间道派,符式盛行讲究“符头”、“符身”、“符脚”的结构,甚至还有配合线条画出人形、葫芦形的,也不是没有传承的。这些符式可能用上很多地方俚语,或是不同年代屡经增删形状与内容;可是它们不见得违反白玉蟾“心正则法灵”或萨守坚“一点灵光便是符”的原则,反而其符式包含着许多文字或图像,更有助一般民众具体明白每种灵符用途,更方便说明与传播信仰文化。若依《道藏》,宋元时代许多符式犹是使用部首、偏旁或单字结合的“单字符”,常见有以“雨”字为冠,或者以无头撇“鬼”字为符座;例如,在无头撇“鬼”字左脚空间填上“斗”字符窍,本就是古老单字符,至今许多符箓还是常见这个无撇“魁”。但金英教跟随华南近代流传的画符结构,往往先以“符头”表示“奉”天命或某神令,或以某神名义“勅令”较低级神灵,再在底下称“符身”或“符腰”的部位用文字与线条组成“要字”,申明灵符需要达致的效果。最后,到了底下符脚的部分,是画上符令架子催动灵符,以后在上边填写一个接一个俗称花字”或“入神字”的秘字,加强制煞、消灾、斩鬼等符令要求。这种做法目的在复合宋元时期单字灵符多种功能,很多“花字”毕竟还是宋元两朝常见的单字符,它们被一笔笔重叠写在符脚上,形成看不到字划的朱砂或墨迹圆点。也有些花字,规定不能用笔墨,必须以指头、手印或者香火在符上虚画。
值得注意的是,金英教用符并非纯靠神仙显灵,画符过程其实也涉及医道。正如《本草纲目》所言:“诸纸,甘,平,无毒。楮纸:烧灰,止吐血、衄血、血崩、金疮出血。竹纸:……止虐。滕纸:烧灰,敷破伤出血,及大人小儿内热。衄血不止,用古藤纸(瓶中烧存性)二钱,入麝香少许,酒服。草纸……最拔脓。麻纸:止诸失血,烧灰用;纸钱:主痈疽将溃,以筒烧之,乘热吸患处,其灰止血。”[10]2194金英教和其他民间教派供人食用符纸,也延续同样道理。不管青符或黄符,制作原料不外是清热解毒的竹纸、滕纸和蔗纸,本就可入药。其符色原料,青符是用竹叶染青、倚赖的是竹叶对抗烦热、风痉、喉痹、呕逆等症,以及对治咳逆上气、溢筋急、恶疡,并有杀小虫的作用;黄符是用黄姜染黄,它的功效原本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功能祛风、治气滞、痈肿、风痹、跌打等。一般人身体发热,或因热病而呓语,乃至见神见鬼,符纸其实作用在镇痛和杀菌,调理生理机制。而朱砂或称“丹砂”,《新修本草》总结前人对它的一再肯定,说它“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通血脉、止烦满、消渴”[11]86。至于墨汁,功能止血和消肿、又能治吐血、衄血、崩中漏下、血痢,痈肿发背,清朝汪绂在《医林纂要》里头说它味道辛苦,平,入心、肝二经:“古用松烟,性近温,今用桐油烟,性近寒,然气味清虚,俱不失为平。珍之者加入珠、金、冰、麝,陈久为良。”②
根据以上,金英教弟子入教,从一般的“过教”到“过大教”,还有初一十五、祖师诞,会涉及生吞各种符纸的修炼步骤,其实亦是寓调养五脏情志于神秘仪式中。这些符纸犹如保身成药,教众定期吞食符纸的结果,会作用在身心与情志平衡,也就保障应急时“百打百胜”的概率。而金英教日常应付群众求助,其用符之道,也如《祝由医学十三科》建议的“如阳症用好米醋或用井水,阴症用姜汁、或酒、或水。风用竹沥姜汁”[12]345,应付某些症状,是以能治病的草木石头材料配符。例如配合“发冷咒语”,就有用线缠蛋三十六圈,将蛋壳也研粉食下,再把线条缠在左右手脉。这里边,涉及摄取鸡蛋的营养、热量,补充钙质流失,以及简单刺激阳池穴位,多管齐下。
如此,从金英教画符材料,可以明白,很多时候,其符即药。画符的过程,往往配合制符原料药效,不离朱砂镇心火安气神、清热解毒,或者以墨汁通经脉祛内伤、解郁闷;或与各种一般有效单味药微量结合。这些符虽然不是中医精致层次的“君臣佐使”配方,不一定能对症下药,但可能有效稳定情绪,并发挥调节人体功能的引药作用。古代乡野,中医不多,生熟药材供应渠道也不完整发达,中医药依然是昂贵且不一定有供应,教派符咒正如民间流传的草药单方、验方,且是以比单方、验方更快捷、便宜的方法,服务病黎。所以,在乡野医药两缺的年代,各地金英教坛提供群众各种用符,不仅是信心治疗,像似西药里的安慰剂,而且是以简单复方,偶尔还配合穴位刺激。其中诀窍还包括某些符纸必须低温烧成碱性白灰配合阴阳水发挥效用。群众信仰金英教符法之能够稳住病情,导致教派在地方上以刀枪不入、治病救人流传至今,缘于符法神秘面纱背后带有医疗实践的物质基础,确能调动病人求生意志与生理自愈能力。
尤其在先民下南洋开垦蛮荒之时,即使是华南山区的草药知识也不一定有用武之地,符咒自然就成为救命求生的途径。教派符咒流传广泛,是时代背景所使然。
然而,金英教符咒当初传播于中下层农工与小贩商之间,其后必然会出现普及化与民俗化的演变。这会有利教派以及所承载传统信仰文化深入民间基层,而教派也因此有需要随顺民间教众/信众寄托鬼神力量的倾向,产生某些对儒释义理的通俗与方便解说。例如槟城抄本的《太极令》,若以客家话唱诵咒语“太极初生一点灵,我是日月未光明,世间问我年多少,先有我身后有天”,它是押韵的,阐释“太极”概念通俗易记;但是咒语话锋一转说出“现今弟子请吾降”,就把华夏宇宙生成观提到的“过程状态”,神格化为“神仙”了。另外,金英教内部陆续出现的许多“花字”,其中一些以“雨”冠在无撇“鬼”字,合乎传统的单字符结构,但中间填上神灵名字,就不一定是传统的释道传承所能接受的,包括倾向“西天佛祖”说法而出现的符咒,当中还出现以“阿弥陀佛”名义号令的符式,又为佛名号增加佛典本无的“口”部首。
三、补论与小结
依照《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朝自道光元年以来,限制各地清微、灵宝道脉授箓,下令要火居道士“还俗”,“年老不能还俗者,不许招徒”。在华南法教中,很多道教名山的传承,在乡野地区演变为延续其名称的俗家“法教”,也是在这以后。新兴法教,主要为了确保民间庙宇能够延续,所以训练在家弟子有能耐处理一般信仰事务,填补道士难以深入与散布乡野的缺憾。南洋许多教门自称“茅山”或“六壬”,又如从莆田流传南洋的“金轮法院”自称“武当别院”,这些法教弟子提到祖师往往至多只能追溯到明末,这可以理解为他们可能是道光年以后方才兴盛于乡野地区的法教传承,有时还会带着许多“祖山”未曾有过的符箓下南洋。然而,这显然解释不了“类似”法教的金英教。
说金英教“类似”法教,是由于其教内师徒传授,并没有严格的谱系制度区隔历代弟子的道名。金英教正如“茅山”道教流传在华南地区演变的法教传统,只要求任何一代弟子都必须把名字中间改为“法”字,作为“法名”,或自选中间有个“法”字的名号。可是,对于茅山法教来说,它之所以如此,是明确地知道教中的胡老祖师原是在茅山学过道的,从“法”字应用,可以区分出弟子是属于学道谱系的道士,还是在家助道的门人。而在金英教,虽然林显江祖师号称“五岳五观”,金英教显然不属任何原有道派分支出的新兴法教,而是在各道教名山分支的法教弟子以外,自成体系。因此,其弟子在原名中间改称“法”字作为法名,很可能是由于教中承继“茅山仙师”的道法,方才引进的规则。
事实上,不论林显江本人的详细生平,抑或金英教创教真正年代或名称如何演变得来,迄今也一样难找充分文献对照。正如上述甲洞抄本提及“五学五观林太祖师称(亲)口传教陈飞龙,亲口传教陈法辉四郎”,以其文字对照常见的《罗浮山白鹤寺金英传序》,林显江很显然是清末民初的人物;而“五岳”与“五学”若是两个传播相通意义的不同称谓,则可证明金英教的祖师所学极杂。但是,金英教开教神话,是说祖师赤膊金英子八岁成道,双手各握日与月,形象保持童颜。这位金英祖师本源何山何派、他的真相是哪一时代人,其教法和哪一地区哪一阶段的“茅山”结合,真是扑朔迷离,有待考证。而林显江又是如何在修行境界感通金英祖师、茅山仙师、潮源洞师三师,以至承接与传播此一道脉,恐怕更是详情难解的神话,难以进行历史或地理考据。
另一方面应注意,其时在英殖民地中,华人开拓矿区主要以客家人为主,主导的社会组织又是洪门会党的各房分支。客家人在清代陆续大批到南洋垦荒,他们主要是开发矿区与种植区,在各地逐渐形成以客家方言为主的乡村城镇。而且,源自不同祖籍的客家群体,往往亦是根据原乡或方言群结合,借助会党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与异姓结义的凝聚力,合理化与神圣化那最初以集体力量开拓地区的武装自治社会。这些客家地区,通常是将家乡神明香火南迁,通过家乡神明落地生根成为地区的佑护者,使得大众深感异地无殊原乡;同时,神道设教,又是民众自祖辈以来传承集体价值观的共同表征,神明也就成为人事以外公道的社会秩序、文化风气的监督者。[13]140-146
根据金英教众回忆当年乡区弟子学习请神附身联系“神打”之盛,其中有“梁法龙”(梁少雄)弟子赵坤利描述其师主持乡村神明巡境的盛况的回顾,说:“已故梁少雄师父属武功,善于表演神功和符法,当众神出巡旺村出游时,上童者脸颊串青竹,吊香炉,吊西瓜,吊黄梨,穿银针从鼻孔而过,上三层楼高的刀梯,在刀锋最高处半身仰贴在利刃上摇曳摆动,坐钉椅腿钉住棺材钉,让前后四位善信,抬着出游。”[14]166可见,金英教传播南洋,凭着其咒语、符箓原本承载的客家色彩,并不是提出许多新的鬼神灵取代民众原来信仰的鬼神世界,它叙述的神灵世界也是民众熟悉的,所以它才能首先进入客家地区,从教派视角提出如何沟通鬼神与人利益,不会受到当地太多抗拒,甚至也有协助地区上的庙宇庆典活动,如训练以神灵附体姿态出现的“上童”。而神迹表演不是为了娱人,而是表达神灵世界的不可思议,警诫村众遵守神灵代表的道德价值,也鼓舞村众相信神临本村,保佑大家安居乐业、安身立命的自信。
由于南洋各地在清代曾经历列强的瓜分,到现代又是经历了历次战乱与政治变迁,金英教南传也没有具体的组织协调,目前已经难以完整理解其教众分流的路线与过程,也难以追踪各地教坛的分布、兴衰与演变。较具体的理解是,上述甲洞抄本所提到的陈飞龙师傅,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罗浮山白鹤洞身带教法南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门下弟子较多,是本地传承较广的一脉。像上述梁法龙,即是其数传弟子,且后人能说出较完整的当代传承谱系:“前传教陈飞龙,传教陈法郎,传教唐法贵,传教钟法飞,传教梁法龙,亲口传教林振华,林政安,赵日春,饶耀基……。”[14]166如此,若能将南洋各分支的这类记录整合,还是有机会发现金英教在南洋各地广泛传播的路线。不过,单是观察上述谱系的个别弟子,从他们的个人背景,实可说明金英教开放性。教派固然传自客家地区,随着村镇社会演变和社会交往频密,其学法弟子已经多有来自其他籍贯的。像上述赵坤利,他是泉州人,同样也有过教茅山教。
从金英教的开放性,以及它在南洋长期传播、落地生根,还可发现此教派与时俱进,有些符咒是针对源自当地其他族群的降头巫术,充分表现出教派有意识地回应地方上大量先民下南洋的地方需要。但组构这类符箓的思路,符上请来“九天玄女”与“五鬼”作为勅符的压阵神灵,前者是战斗、破阵与扭转变化的高阶女神,后者有回击鬼魅与干扰致灾的作用,依旧能表达出设计者对道教文化有所认识。
古人清楚医道同源,从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到李时珍,名道也是名医,各道派分支其实既传医术也传符咒,并知道如何分别或配合应用得当。白玉蟾《道法九要序·行法第六》便提出过:“若治病之法,以仔细察其病症,次当给以符水治之”,并提出病人往往是“或嗜欲失节,或心意不足而成邪,故邪气侵则成病”[15]678-679,首要任务是“仔细察其病症”,其次才决定是否辅以符水。同样的道理,也见于金英教内部。许多地方的金英道坛,其实都趋向态度开放。他们除了继续招收新教众画符念咒,教众处理符咒与医药关系的态度,也不离古道宗旨,是主张“正常情况的事件或病症,都是奉劝善信最好是带医生诊治,获得正常医护理之同时,给予灵符相助,以使健康情况早日复原”[7]。只是,到了今时,医疗工作的现代格局讲究科技专业的基础,一般道坛毕竟不能兼任其责。
随着当代医药服务发展与普及,病人也会自己寻找专业的中西医以及各种替代医疗体系,不一定再像老一辈那样首先想到上门求符。一些教坛更进一步的表现,则是关注地方福利需要,在自己力量范围内设立免费或低廉价格的中西医服务站,或请来西医义诊,或和医疗机构合作提供免费验血服务等,还有就是提倡与主办各种保健讲座、气功功法班。也有道坛,会趁着神诞,发动捐献社会福利与地方医疗服务的筹款,表达延续教派与神明慈悲为怀的教导之意。流传到南洋的教派,毕竟也是要与时俱进了。
注释:
①在槟城的天衡山派道观,开山创教,也如金英教一般,强调三教,传播法教道术,自称本宫道观为“清观寺”。
②清·汪绂《医林纂要》所说墨块药用功效,是针对古法以松烟、骨胶、香料制墨而言。
参考文献:
[1]王琛发.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与实践[M].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2006.
[2]王琛发.有道有理[M].吉隆坡:马来西亚道教学院,2006:29.
[3]佚名.金英教之起源概述[J].马来西亚旺相堂柔佛总坛庆祝25周年银禧纪念特刊,2001:69.
[4]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M]∥王见川,林万传.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158 - 159.
[5]王琛发.青莲教下南洋:马来西亚最早期的瑶池信仰[J].台北:华人文化研究,2013,1(1):56.
[6]王琛发.分裂的认同:重新解读19世纪槟城国际港口的客家社群[J].嘉应学院学报,2013(1):123 - 133.
[7]佚名.符咒知多少[J].新山旺相堂15周年纪念特刊,2001.
[8]白玉蟾.海琼白真人语录:卷四[M]∥正统道藏:第55册.影印白云观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694.
[9]道法心传[M]∥正统道藏:第54册.影印白云观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652.
[10]李时珍.本草纲目:第三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2194.
[11]苏敬.唐·新修本草[M].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86.
[12]祝由医学十三科[M]∥藏外道书:第二十六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345.
[13]王琛发.先贤、神圣香火、开拓主权:华南原乡与南洋信仰版图的互相呼唤—以马来亚客家先民为主例[J].嘉应学院:客家研究辑刊,2012(1):140 - 146.
[14]赵坤利.马来西亚道教神打的修行[J].吉隆坡:马来西亚神庙大典,2002(4):166.
[15]道法会元:卷一[M]∥道藏:第二十八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678 - 679.
【责任编辑:刘桂林】
The Alasuoja,Health and Social Function of Kim Eng Spells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
WANG Chen-fa
(Xiao En Cultural Foundation in Malaysia,Kuala Lumpur,Malaysia)
Abstract:Kim Eng spread to Southeast Asia region from the local sect of Luofushan Hakka,acknowledging so far that its teaching inherited from the three mythical founders of "Buddhism,Taoism,and fairy" in swearing brotherhood to create religion. Based on the Confucian values,Kim Eng teaches its followers to comply with the "Five Respects" and "Five Precepts". The sect c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in the pas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mainly because the native dialect Hakka was used in ceremonies and chanting mantra,and its initiation ritual implied national interests,which could easily arouse people's hometown memories and cultural feelings,and the myth of its religious creation was also favourable for adding the sacredness and reliability among ancestors with a strong faith atmosphere. In addition,in the township area in the past where modern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was not necessarily popular,Kim Eng’s teaching and spells,coinciding both in materials and therap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ay after all be accepted as the simple and practical choice in line with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in dealing wi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llness,or shelling wounds. Today,the original Hakka denominational clergy and believers have become pluralistic ethnic,and their ideas of health and social positioning are also clearly adjusted,yet it still needs more effort to study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Kim Eng sect.
Key words:mythology of creating religion;religion mouth prequel;Lin Xianjiang;Jin Yingzi;spells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5934(2016)01 - 0001 - 09
作者简介:王琛发(1963 -),男,马来西亚槟城人,教授,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总裁,道教学院董事会主席,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学术暨课程委员会主席,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宗教与南洋华人。
收稿日期:2015 - 11 -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