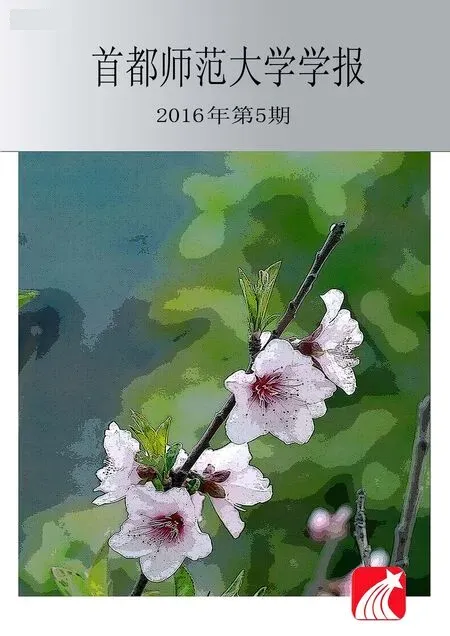文学中的器物形象及其审美价值
——重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2016-04-13王玉屏
王玉屏
一、引言
王安忆的《长恨歌》自1995年问世以来,屡获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也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誉,是当下文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综合各家之言,笔者发现,《长恨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历史怀旧角度阐释作品。“《长恨歌》发表之初,《钟山》杂志曾专程到上海召开了作品讨论会,而与会的评论家也大多将它看做是一部好看的怀旧小说”①陈思和:《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页。。1996年,罗岗撰文对《长恨歌》的怀旧主题进行了深度解析②罗岗:《找寻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二是从城市主题角度阐释作品。华霄颖把《长恨歌》置于上海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深入探索了上海市民文化尤其是弄堂文化对作品的影响①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陈思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刻意地为上海这座城市立像,她不但写出了这个城市的人格形象,也刻意写出了几代市民对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繁华梦的追寻”②陈思和:《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三是从女性叙事角度阐释作品。1998年,南帆撰文提出“《长恨歌》的城市是一个女性视域之中的城市”,这种女性视域的运用使得小说“同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疏离了”。③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王安忆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第176页。张浩指出《长恨歌》“将城市从男性的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用女性鉴赏的眼光描写了城市的种种趣味,以及女性对这个城市的感觉”④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王安忆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第287页。。四是从叙事学角度阐释作品。《长恨歌》独特的叙事技巧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南帆发现“《长恨歌》的文本出现了某种奇异的特征: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地填塞于人物动作的间隙”⑤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王安忆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第175页。。颜琳认为《长恨歌》“是对传统小说成规和构成要素的又一次反叛”⑥颜琳:《沉入常态叙述与呈现诗性情怀——论九十年代中后期王安忆小说叙事策略》,《王安忆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第409页。。五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把王安忆与张爱玲进行对照。1996年,《读书》杂志刊登了王德威的《海派作家又见传人》⑦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安忆论》,《王安忆研究资料》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该文开启了国内张爱玲与王安忆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外还有论者从宗教文化、悲剧意识、人物塑造等多个方面解读作品,拓展了《长恨歌》的阐释空间。
再一次细读文本,笔者发现,《长恨歌》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这就是器物的大量描写。据不完全统计,《长恨歌》涉及的器物数量不下20种,大致可分为衣物、食品、用具三大类,有的贯穿全文,有的只在某一个阶段出现。王安忆曾说“器物是小说很重要的一部分”⑧王安忆:《王安忆接受早报专访谈新长篇小说〈天香〉》,华夏经纬网,2011-02-24。,那么在《长恨歌》中,这些数量众多、频繁出现的器物究竟有什么意义?它们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还是被作者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内涵?这些器物与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以及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本文拟从“器物”进入《长恨歌》,重点选择“金条”、“服装”、“家居”三个类型作为分析范例,尝试着从细微处打开一条通向文本深处的通道。
二、金条:关乎小说的说服力
熟读《长恨歌》的读者不难发现,在王琦瑶波澜不惊的人生中,穿梭过很多人。有的转瞬即逝,仿佛过眼云烟;有的短暂停留,然后不知去向;有的来来去去,最终选择离开。掐指数去,唯有一盒金条,在王琦瑶的人生中静静地守护着,不离不弃,相伴左右,直到生命的终止。这一盒金条,在小说中无疑成了仅次于主人公王琦瑶的一个重要角色。
金条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一部行将结束的时候,时间是1948年。一个漆黑的夜晚,李主任将一个装有金条的木盒放在王琦瑶枕边,此后俩人再无聚首。带着这盒金条,王琦瑶走进了新时代。
金条第二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二部快要结束的时候,时间是1965年,与第一次出现,中间隔了快二十年的光阴。未婚的王琦瑶生下了来路不明的女儿,因为孩子出麻疹,手头紧,托人兑换了一次金条。
金条第三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第一章,时间是1977年,与第二次出现,相隔又有十余年。这一次王琦瑶动用李主任留下的金条,并不是生活窘迫,而是为了购买衣物,追赶时尚。
金条第四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第二章,时间与上一次相隔不久。王琦瑶这一次兑换金条,原因是女儿的男友小林被大学录取,为了表示庆贺,她打算出钱让小林带女儿去杭州旅游。
金条第五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第四章,王琦瑶的故事行将结束,时间是1985年。年过半百的王琦瑶为了留住比自己小一轮的男人,拿出装金条的雕花木盒,可老克腊并没有接受金条,而是选择逃走。
金条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结尾。这一回,金条要了王琦瑶的命。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一个叫长脚的年青男子潜入王琦瑶的卧室偷盗金条,被发现后,用手掐死了王琦瑶。
作为物质形态的金条为什么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它与王琦瑶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它又是如何转化为小说叙事的内在肌理?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何谓小说的逻辑、情理与说服力。王安忆曾以小说中的“生计”为例,专门探讨过小说的逻辑、情理与说服力问题。她说:“小说中的‘生计’问题,就是人何以为衣食?讲到底,我靠什么生活?听起来是个挺没意思的事情,艺术是谈精神价值的,生计算什么?但事实上,生计的问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的内容。”①王安忆:《小说的当下处境》,《王安忆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一个作家“如果你不能把你的生计问题合理地向我解释清楚,你的所有的精神的追求,无论是落后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说服我,我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②王安忆:《小说的当下处境》,《王安忆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谢有顺充分肯定了王安忆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作家,都在写一种都市男女的时尚生活,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出入高级酒店,住昂贵的房子,开好车,穿名牌衣服,喝洋酒,到国外度假,过着很奢华的生活,可是作家从来没有对他们的生计和收入作合理的解释,他们何以有这么多的钱来维持这种奢华的生活?作家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③谢有顺:《小说的物质外壳:逻辑、情理和说服力——由王安忆的小说观引发的随想》,《王安忆研究资料》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9页。王安忆和谢有顺虽然谈的都是小说中的“生计”,实际上关乎的却是小说的逻辑、情理与说服力问题。一部成功的小说必须在现实的合理性尤其是情感的合理性中让人物立起来,否则的话,就会失信于读者,大大降低作品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因为一个简单的细节,常常隐含着生活的常识和逻辑,最能见出作家的功力。《长恨歌》中的金条就是如此。它是李主任留给王琦瑶的最后礼物。从李主任的角度来看,时局动荡不安,自己来去无定,俩人总是聚散无常。也许是预感到生离死别的到来,也许是为了补偿王琦瑶的感情付出,也许是希望自己离开后王琦瑶的生活有个保障,李主任把一盒金条交给王琦瑶。于情上,这是说得通的。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④王安忆:《上海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而王琦瑶又是书写上海的最佳人选,这里有一个问题作者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即王琦瑶的“生计”,因为它关系到小说的说服力问题。作者安排李主任给王琦瑶留下一盒金条,于理上,这是必须的。
王琦瑶原本是上海弄堂里颇有姿色的一名女子,因缘际会,参加“上海小姐”竞选,获得第三名,继而成为军政要员李主任的外室,过上了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小说第一部围绕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的事件前后,“使一个城市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通过自己的血肉之躯内在地展现出来”⑤陈思和:《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可是好景不长,李主任因空难身亡。按理说,王琦瑶完全有可能像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那样,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生活陷入困顿之中;或者像曹禺《雷雨》中的鲁侍萍那样,为了生存,四处奔波。这样一来,王安忆借助王琦瑶书写上海的愿望就要落空。因为上海市民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精致优雅,如果让王琦瑶像玛蒂尔德或者鲁侍萍那样,沦落到社会底层,每天为生存忙碌,饱经风霜,恐怕她就不能承担起为上海塑像的责任了。实际上,在小说中,搬离爱丽丝公寓、住进平安里的王琦瑶,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与娘家也不怎么来往,又没有丈夫可以依靠,还要独自抚养私生女儿,却把日子过得精致优雅、从容闲适,五十多岁了还风韵犹存,被年轻人推崇为老上海的生活指南,并且还与比自己小一轮的老克腊发生恋情。王琦瑶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她抚养私生女、追赶时尚的底气从何而来?这就不能不提李主任留给她的那盒金条。
1949年之后,失去李主任的王琦瑶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沦落到社会底层,除了帮人打针之外,终日与几个闲散人员在家打麻将、喝茶、喝咖啡、聊天,还要变着花样准备点心。1960年代初,饥荒席卷中国大地,单身的王琦瑶生下来路不明的私生女,不但没有半点慌乱,为钱所困,反而还有闲心与康明逊藕断丝连,谈情说爱。文革结束后,年过半百的王琦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购置新衣裳,外出旅行,出入高级餐厅。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闲适生活是需要经济基础做保障的,资本家太太严家师母和资本家少爷康明逊每月有定息,生计自然不是问题。王琦瑶并没有很高的收入,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她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王安忆倘若不能交代清楚,王琦瑶的生活恐怕缺乏现实依据了,小说的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小说中有这么几段话很值得思考:“当时李主任离开之际,留给她的那盒子里,是有一些金条,这些年都锁得好好的,一点没动过,作不备之需”①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当王琦瑶明白嫁人的希望不会再有的时候,这盒金条便成了她的后盾和靠山”②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原来作者早就安排好了,所有的问题因为有了李主任的那盒金条都迎刃而解。
王安忆之所以要让李主任为王琦瑶留下一盒金条,并且在小说中贯穿始终,用意是很明确的。她不希望李主任死了以后,王琦瑶的生活像玛蒂尔德或者鲁侍萍那样发生重大转折,以至于沦落到社会底层,生活艰难窘迫。王安忆必须把王琦瑶的生活来源向读者作出合乎情理的交代,让读者相信王琦瑶的生计根本不是问题。唯有如此,失去李主任的王琦瑶的故事才有可信度和说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金条不仅仅是李主任对王琦瑶感情付出的补偿,更是王琦瑶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是王琦瑶的定心丸。它不仅关系到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还决定着作者为上海塑像的愿望能否实现。
三、服装:见证时代变迁
谢有顺曾说:“当代作家写历史,一般都不敢写器物”,“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即便写,也写不好。像苏童的《妻妾成群》,可以把那种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木三分,但他还是不敢轻易碰那个时代的器物”。③谢有顺:《小说的物质外壳:逻辑、情理和说服力——由王安忆的小说观引发的随想》,《王安忆研究资料》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4页。王安忆却有些不同,她比较喜欢通过一些器物的描写来表现某个时代的风情。在《长恨歌》中,人们穿戴衣物不仅仅是蔽体御寒,还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内涵。尤其是主人公王琦瑶的着装,生动地演绎了上海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浮华沧桑,见证了这座城市40年的历史变迁。
《长恨歌》第一部讲述的是老上海的故事。王安忆本人没有这个时代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但她借助一系列器物的呈现,把上个世纪40年代老上海的城市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随处可见的体现老上海元素的弄堂、石库门、有轨电车、留声机、照相馆、电影、旗袍、咖啡等器物,生动地为读者勾画了一幅老上海的清明上河图。尤其是关于旗袍的描写,更像一个道具,引领读者进入旧时光的戏剧中。小说第一部的时间跨度大约3年,旗袍的出现频率不下8次,远远超过第二部和第三部出现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王琦瑶的每一次重要出场都是身着旗袍,并且颜色和款式各不一样。提着花书包走出弄堂的王琦瑶穿的是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走进程先生照相间的王琦瑶穿的是家常花布旗袍,参加女同学生日晚宴的王琦瑶穿的是素色旗袍,参加上海小姐选美比赛的王琦瑶穿的是缎面绣花的粉红旗袍,从女同学家落荒而逃的王琦瑶穿的是短袖月牙白绸旗袍,出场为百货大楼剪彩的王琦瑶穿的是粉红缎旗袍,约会军政要员李主任的王琦瑶穿的是白色滚白边的旗袍……
旗袍是民国时期中国女子最为风尚的服装。1921年,旗袍在上海妇女界流行,继而迅速扩大到全国各个阶层。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将其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在老上海的斑驳光影中,旗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是这个城市最贴身的美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女性十之八九穿着旗袍,旗袍成为当时女性衣橱中不可或缺的服饰。1930年代的电影明星、月份牌时装美女画和各大报刊杂志的文化传播中,无不以旗袍作为重要元素。以至于在人们心目中,描写老上海风情,绝对少不了旗袍。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出品的民国电视剧《上海滩》在大陆热播,女主人公冯程程的旗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7年,香港导演李安执导的以20世纪40年代上海为背景的电影《色·戒》,在演绎老上海风情时,也选择了旗袍。有人计算过,女主人公王佳芝在影片中前前后后共换了27件旗袍。总而言之,几乎所有讲述民国时期上海故事的文艺作品都有旗袍这个标志性元素。旗袍已经超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服装概念,而上升为一种文化象征,它是老上海都市风情的生动演绎。王安忆幼年时期来到上海,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路段生活了半个世纪,自然清楚地知道旗袍之于老上海的意义。因此,在《长恨歌》第一部,当王安忆让王琦瑶穿着旗袍出席各种聚会和宴席时,老上海的独特风情也就扑面而来。
《长恨歌》第二部讲述的是上海解放到文革结束的故事。这一段时期,虽说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服装的标准,但随着意识形态的更迭,人们的服饰审美标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49年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人们的服装还保留民国时期的样式。尤其是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城市和中国的时尚之都,服饰上还带有缤纷的格调,女子穿旗袍依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思想有了紧密联系。解放区的服装款式色调随着大军南下或西进传遍全国,旗袍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特别是文革期间,穿衣打扮不再是与政治无关的个人行为,旗袍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情调和封建糟粕而受到批判。此时的上海,不再是众人瞩目的时尚之都,体现这座城市独特风情的旗袍完全受到冷落,被迫退出日常生活,另一种体现革命思想的新型服装“列宁装”、“人民装”等成为众人追逐的时尚。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借王琦瑶等人的穿着表现了时代的这种巨大变化。
小说第二部的时间跨度将近30年,王琦瑶穿旗袍的次数只有两次,时间都是50年代,地点还是在家里。第一次王琦瑶穿一件素色旗袍去给离家不远的病人打针,第二次穿的是一身布的夹旗袍,外面还套了一件毛线对襟衫。如果是外出应酬,王琦瑶绝对不穿旗袍。有一次,王琦瑶去国际俱乐部喝咖啡,上身穿的是夹袄,下穿一条薄呢西裤,颜色都是浅灰。小说中与王琦瑶交往密切的几个人,只有程先生总穿着一件带有老上海意味的旧西装,让人觉得不合时宜,最后落得个自杀身亡。其余人在穿衣打扮上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昔日过惯了繁华生活的资本家太太严家师母穿起了短夹袄,过去是有钱人家儿子的康明逊穿的是蓝咔叽人民装,原先是资产阶级小姐、后来投身革命的蒋丽莉总是穿着一身列宁装和咔叽裤。在这里,王琦瑶的穿着虽说还有一点老上海的余韵,但已今非昔比。穿旗袍的次数明显减少,色彩也低调很多,花色旗袍彻底退场,具有时代色彩的灰色成为首选。不管王琦瑶对老上海有着怎样缅怀的心情,新时代的政治风云还是从服装的款式和色彩上透射出来,王琦瑶的朋友们穿的“列宁装”和“人民装”更是深深地打上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烙印。
《长恨歌》第三部讲述的是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的故事。改革开放之后的上海,思想观念的禁锢逐渐得到解放,服装的世界也开始繁荣,一些不同于列宁装和人民装的新款式出现在街头,色调也从千篇一律的蓝色和灰色向多彩发展。比如套裙,作为上海流行女装中的主要品类跨越整个80年代,中式棉袄则是冬季流行女装中的主要服装款式。曾经辉煌一时的旗袍被冷落30之后,并没有在80年代再度流行,它的鼎盛时代已经远去。改革开放之后的上海再一次迎来经济的腾飞与文化的繁荣,但是,它不可能回到老上海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将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辉煌。对于这一点,王安忆应该是清楚的。因此,在《长恨歌》第三部,王安忆没有让王琦瑶再次穿上旗袍。只有一次,王琦瑶想起曾经参加选美比赛时穿的那件粉红色缎旗袍,还试图让女儿薇薇试穿,结果徒增惘然,此后渐渐就把它忘了。在现实生活中,王琦瑶穿起来了带有这个时代特点的套裙和中式棉袄。旗袍是老上海的象征,而作者笔下的王琦瑶并不是老上海的代表。确切地说,王琦瑶应该是上海弄堂文化的代言者。上海和老上海是有区别的。老上海指的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而上海包括解放后直至今天的上海。如果王安忆在《长恨歌》第三部让王琦瑶再度穿上旗袍,那她真的就成了老上海的代言人。很显然,这是违背作者本意的。难怪当评论界把《长恨歌》看作是一部好看的怀旧小说时,王安忆忍不住站出来反复申明这不是怀旧。
《长恨歌》的故事横跨了中国历史的数段重要时期,重现了三个历史阶段中不同的上海,“但许多重大历史叙事的关键词——内战、解放、大跃进、文革、毛泽东、邓小平、改革开放——在小说的叙事中都被一一隐去”①吴赟:《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王安忆巧妙地将那些历史的巨变投射到人物的穿衣打扮上,政治的起落和时代的变迁自然也就寓含在服装的变化和时尚的更迭中。此时此刻,人物的服装已不仅仅是蔽体御寒的物质外壳,而是具有了某种符号象征意义。正如王琦瑶所言:“时装这东西,你要说它是虚荣也罢,可你千万不可小视它,它也是时代精神。它只是不说话而已,要是会说话,也会说出几番大道理。”②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四、家居:彰显身份地位
器物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工具和物质条件。作为物质的一种,器物具有它的物理属性或自然属性,但是,器物又不仅仅是作为物理的或者自然的东西而存在,它还具有符号象征属性,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具体到在家庭陈设中,家具及装饰物等器物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们常常是空间的代言物,构成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文化隐喻。比如《红楼梦》对日常用具中“所有那些世所罕见的外来器物的大量使用,是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锦衣玉食、温柔富贵的生活场景的重要构成部分,显示了他们作为上层社会贵族的生活质量和对社会时尚的追逐,是其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是其作为上等人的符号”③王洁群:《晚清小说中的西方器物形象》,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雅舍》中“一几一椅一榻”的简单陈设,透露的是梁实秋知足常乐、随遇而安、豁达开朗、苦中作乐的情怀。王安忆的《长恨歌》在描写微观空间的家庭居所时,也赋予了家具及装饰物等器物特定的精神内涵。
在上海这座城市,区域空间的级差是很分明的。不同的居住地代表不同的出身和阶层,比如淮海路一带,聚居的大多是中等及以上的市民家庭,而苏州河沿岸和闸北、杨浦一带,则是社会底层的劳工流民的栖身之地。不同的出身和阶层又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南下干部家庭虽说工资待遇不错,但大手大脚过日子,生活比较粗糙;上海老市民家庭穿衣吃饭都很讲究,日子过得精致实惠。在上海弄堂长大的王安忆,自然对区域空间的这种级差有着贴肤的感性认识。在《茜纱窗下》一文中,王安忆这样写道:“如我父母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全是两手空空,没有一点家底。家中所有什物,多是向公家租借来的白木家具,上面钉着铁牌,注明单位名称,家具序号”,“上海的中等市民家中,都有樟木箱”。④王安忆:《茜纱窗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在《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一文中,王安忆看到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客厅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⑤王安忆:《上海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不同的室内陈设,彰显的是不同阶层的生活图景和生活品质。这是上海市民文化的真实存在,也是王安忆上海书写的重要内容。在《长恨歌》这部小说里,王安忆以委婉细致的笔调,通过家庭陈设中的器物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市民文化的这种层级差异。
比如蒋丽莉家的客厅:挂大衣的“衣帽架”,摆了水果点心的“长餐桌”,立在屋角的“钢琴”,打开的“落地窗”,铺地的“花砖”,垂着的“枝形吊灯”,留着残渣的“咖啡杯”。⑥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5页。欧式的风格显示出这是一户有点洋派的上等阶层家庭。
爱丽丝公寓的陈设:“细细的柚木地板打着棕色蜡,发出幽光。家具是花梨木的,欧洲的式样”①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澡盆前是绣花的脚垫,沙发上是绣花的蒲团,床上是绣花的幔帐,桌边是绣花的桌围”②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这是王琦瑶做李主任外室时的家庭摆设,贵重高档的实木家具和花团锦簇的绫罗绸缎透露的是富贵奢华的生活。
严家师母家的布置:“厅里有一张椭圆的橡木大西餐桌,四周一圈皮椅,上方垂一盏枝形吊灯,仿古的,做成蜡烛状的灯泡。周遭的窗上依然是扣纱窗帘,还有一层平绒带流苏的厚窗幔则束起着”,“床上铺了绿色的缎床罩,打着褶皱,也是垂地”,“茶碗是那种金丝边的细瓷碗,茶是绿茶,又漂了几朵菊花”。③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154页。这又是一个富丽堂皇的世界。
上文已经提到过,上海的阶层分野是很明显的。尤其是老上海时期,企业主、银行家、买办、公司董事等组成一个上流阶层,过着锦衣玉食、奢靡繁华的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权的更替使得城市中各阶层的差距在缩小,但基于统一战线的政治需要,“中国革命并没有消除企业家阶级,而是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④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作为补偿,他们可以按照资产比例领取定息。虽然调查委员会会经常低估他们的资产,但大企业主得到的定息,足以保证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这是上海的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⑤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直到文革爆发,他们的家产被抄,亲人被遣,昔日的美好时光不再重来。《长恨歌》对蒋丽莉家、严家师母家以及爱丽丝公寓的贵重家具和流苏装饰等器物的描写,显示的正是这样一群作为上流阶层的生活画面。
当然,上海的社会阶层中不只有上流阶层,还有底部阶层,住在棚户区或者弄堂后厢房的保姆、小商贩、民工等就是社会的底部阶层。《长恨歌》对这一阶层的人物也有关注。
比如张永红的家:“这门里黑洞洞的,没有后窗,前窗也叫一块早已变色的花布挡着,透进朦胧的光线。倘若开了灯,便可看见那房间小得不能再小,堆着旧皮鞋或者皮鞋的部件。中间坐着的修鞋匠,就是张永红的父亲。迎着门,是一道窄而陡的楼梯,没有扶手的,直上二楼。说是二楼,实在只是个阁楼,只那最中间的屋脊下方,才可直起身子。”⑥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274页。
还有长脚的家:“床前是吃饭的方桌,桌上总难免有一些油腻的气息。床的上方是一长条搁板,夏天放棉花胎,冬天放席子,还放一些终年不用却不知为什么不丢的杂物。”⑦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变色的花布窗帘、狭窄陡峭的楼梯、油腻的方桌、放置家当的长条搁板,显然和柚木地板、花梨木家具不可相提并论。后者彰显的是华丽富贵与精致高雅,前者折射的是清贫和粗鄙,但这也是上海,“简陋的物质和杂乱的放置方式透露出此类空间中贫穷和没有文化的气息”⑧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在上海的阶层分野中,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即中等市民家庭。这里的居民成分比较复杂,有像王安忆这样的南下干部家庭,也有中小产业主,还有私人医生等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王安忆对这个阶层最为熟悉,在所有关于上海的小说中,主要用墨也在这个阶层。他们居住在公寓大楼或者淮海路的弄堂里,家底殷实,追求精致实惠的生活方式。《长恨歌》中的小林家就是属于这个阶层。王琦瑶之所以急着促成女儿薇薇与小林的姻缘,原因是“小林家住在新乐路上的公寓房子里”,“不用进也知道,只凭那门上的铜字码便估得出里面生活的分量”。⑨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铜字码”指的是钉在门上标明街道名称和房子号码的铜质材料的牌子,精明的王琦瑶知道,高档铜质材料做成的门牌意味着家境的殷实。在这里,“铜字码”不仅仅是标明位置和供人辨认的门牌,更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家庭陈设中的特定物品常常是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标识。一堂红木家什意味着殷实,一套装饰着麻织流苏的窗帘、桌布和沙发透露出华丽,而一张陈旧的白木条桌显示的是清贫。《长恨歌》在书写上海市民文化的级差特性时,选择家具及装饰物等家庭陈设中的器物进行描写,完全是一种聪明的做法,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五、结语
《长恨歌》中的器物形象除了金条、服装和家居之外,还有汽车、咖啡、电车、钢琴、照相机、留声机等不下20种,它们在小说叙事中同样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情感寄托。比如李主任出场,无论何时何地,汽车是必不可少的。汽车作为一种现代交通工具,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02年,袁世凯为了取悦慈禧太后,花费巨资从香港引进了一辆由美国人设计、制造的汽车。即便在本世纪初,汽车也不是一般老百姓使用得起的。1940年代,汽车绝对是权高位重或者家财万贯的象征。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并没有介绍李主任到底是何许人,但出入都有汽车,读者自然也就知道他的身份与地位了。在这里,汽车不仅仅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已,它被作者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具有人物塑造的功能。再比如咖啡,恐怕是小说中除金条外,另一样贯穿全文的器物。1940年代,资本家小姐蒋丽莉过生日喝的是咖啡,外滩工作的白领程先生和王琦瑶约会喝的也是咖啡;上海解放后,王琦瑶与一群闲散人员在家聚会喝的是咖啡,到国际俱乐部就餐喝的还是咖啡;1980年代,一群年轻人聚集在王琦瑶家,喝着小壶咖啡,吃着精致点心,感叹人生的美好。咖啡原本是一种外来饮品,但对上海而言,咖啡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是都会摩登生活和中产阶级情调的一种象征。难怪李欧梵在分析上海都市文化的背景时,专门选择咖啡馆作为个案进行研究①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王安忆的《长恨歌》在讲述王琦瑶的故事时,总有咖啡的影子若影若现,这就把上海都市风情的韵味表现出来了。诸如此类的器物还有很多,本文不再一一罗列。总而言之,《长恨歌》中的器物形象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是研究上海物质文化和城市文化不可缺少的醒目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