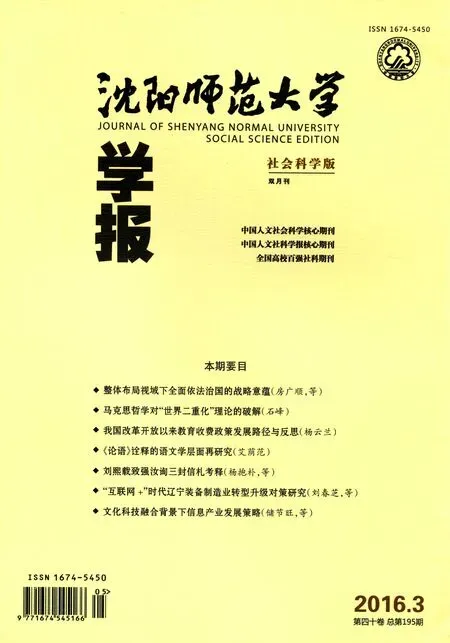安德烈·纪德“道德三部曲”中的“自我与上帝”评析
2016-04-13景春雨
景春雨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安德烈·纪德“道德三部曲”中的“自我与上帝”评析
景春雨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安德烈·纪德在早期创作中致力于探讨自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伦理问题,其中《非道德的人》《窄门》和《田园交响曲》三部作品集中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这三部作品通过阐释“非道德”主义肯定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由批判盲目追求道德纯洁性而否定了主体对宗教教义的盲从,进而揭示了主体因伦理诉求与道德规范冲突而导致的困境。这些问题反映了纪德对自我与上帝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既是其个人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重建过程,也是主体自我认同重新确立的途径。
安德烈·纪德;自我意识;道德困境
法国现代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创作中总是尝试从不同角度展现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变化,以表达相应的伦理诉求。他曾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在我们的全部西方文学,不仅仅法国文学,如小说,除了极罕见的例外,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感情或精神的联系,家庭关系,各社会阶级的关系,但从不涉及,几乎从不涉及个体与自身或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这种关系是优先于任何其他关系的。”[1]正因如此,纪德特别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本人的关注点即是个人与自我及上帝的关系,这个主题也恰恰是纪德进行思考和创作的起点。在《非道德的人》(L'immoraliste,1902)、《窄门》(La porte étroite,1909)和《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1920)三部作品中,纪德尝试通过不同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不同选择来探讨自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对个体伦理诉求的集中关注及相互间的关联性,这三部作品普遍被视作其道德三部曲。“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而道德则是“伦理中的成文或不成文规例”[2]。可以说,伦理问题关注的是个体内在的意愿和感受,而道德问题关注的是群体性的外在规范。因而伦理诉求,尤其是个体伦理诉求总是以潜在的道德规范为表诉对象,它反映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确立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试以纪德这三部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其中的主题意义解读纪德的伦理观。
一、“非道德”主义:自我意识的显现
《非道德的人》这部作品取材于纪德本人的真实经历,在多处情节设置上有迹可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纪德早年的精神自传。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人的目标是上帝”和“人的目标是人”一直是困扰着纪德的两个主要命题。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尼采进入了他的视野,尼采的思想使纪德有了方向感,使他坚信人的目标只能是人本身。纪德说:“我相信这个问题的转移指出了在我写作生涯初期,当我写《非道德的人》时,我的思想所经历的演变。我过去觉得人的目标可能是上帝,而渐渐地,我终于把问题完全转移了,并且得到这个有点过于自信的结论:不,人的目标是人,并且用人的问题代替了上帝的问题。”[3]因此,我们在这部作品中能够看到,主人公米歇尔的“非道德”化转变是一种个体内在的自我逐步肯定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也是纪德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
与纪德的北非之旅如出一辙,主人公米歇尔也在类似的一次旅行中遭遇了生死考验。病愈后重新回到生活中,米歇尔从精神到肉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那个循规蹈矩的学究式人物变成了无所顾忌的“非道德”主义者。死里逃生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对生活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了不同的标准,米歇尔发现,原来在生活中显得重要的事物其实没那么重要,比如社会性的道德规范;而原来那些被忽视的事物反而才应该珍视,比如内心深处被压制的欲望。米歇尔认为,这次经历给予他一种力量,掀开了自己精神上原有的涂层,使被遮蔽的自我得以显现。他认为,“从那时起我打算发现的‘那个',正是真实的人、‘古老的'人,《福音》弃绝的那个人,也正是我周围的一切:书籍、导师、父母,乃至我本人起初力图取消的人。……从此我鄙视经过教育装扮而有教养的第二位的人。必须摇掉他身上的涂层。”[4]这个所谓的“涂层”就是主人公原来所要遵从的宗教教义和各种社会道德规范,《福音》与上帝的无处不在使得个体的自我需求不得不受制于外在的规范而沦为“第二位”的人。这次病愈使米歇尔发现了那个被掩盖的自我,他决心要“摇掉”自己身上的涂层,做一个“真实的”“古老的”“非宗教化”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米歇尔看到了自己生活中的矛盾之处,原来视作行为依据的宗教教义和社会规范此时反而成为他实现自我的最大阻碍。为此,他选择以自己的“非道德”主义向原有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宣战。
“非道德”主义不同于反道德主义,其目标并不是要否定社会道德规范,也并非刻意在个体伦理诉求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形成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而是试图通过无视已有的社会道德规范来使其失去根本效力。在实践“非道德”主义的过程中,主体对既有的社会道德规范采取的是规避的态度。米歇尔发现,自己在实践“非道德”主义的过程中陷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道德困境之中。这种困境突出表现为在原有社会规范中业已形成的自我形象恰好与觉醒后的自我之间形成了一种否定性的对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米歇尔逃离了自己原来生活的社会环境,试图以此来摆脱那个曾经循规蹈矩的自己。最终,米歇尔那个新生的自我破茧而出,实现了从精神到肉体的完全自主。
纪德在1885年左右开始接触尼采的思想,他在创作《非道德的人》这部作品的时候,正对尼采的思想陶醉至深。纪德认同尼采的“超人”思想,以及“一切价值重估”的哲学理念。他赋予主人公米歇尔一定的“超人”个性,并以“非道德”主义阐释了自己对“一切价值重估”的理解。米歇尔为了实践自己的“非道德”主义原则而变得极端自利,他通过极大满足自我内在需求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身上的一切可能性,诠释了“人的目标是人”这一伦理命题。他的“非道德主义”强调个体实现自我内在需求的正当性和绝对性,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纪德通过米歇尔这个思想实验品,探讨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及其现实可能性,尽管其结果可能并不圆满,但纪德依然执着于其具有可能性的存在形式,使其成为探讨自我与上帝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窄门:上帝的法则
《窄门》是与《非道德的人》同时构思的,但比后者晚了七年才发表。如果说《非道德的人》表达的是纪德对“人的目标是人”这个命题的探讨,那么《窄门》则以否定“人的目标是上帝”这种形式间接肯定了前一个命题。纪德认为,如果此前不是《窄门》已经成竹在胸的话,他根本无法创作《非道德的人》这部作品。在他的构想中,《窄门》是作为《非道德的人》的平衡性力量而存在的,因为有《窄门》作对照,所以他才得以创作出《非道德的人》。表面看来,《窄门》与《非道德的人》是一种对立关系,但究其实质,《窄门》表达的是纪德在不同向度上对同一个问题的思索,其伦理诉求具有同一性。
《窄门》这部作品篇名源自《圣经·福音书》。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路加福音》中,当有人问耶稣将来得救的人是否很少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窄门》的题记即为“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这句话凝练地诠释了女主人公阿莉莎的一生。在作品中,阿莉莎为了和恋人热罗姆在死后都能进入所谓的天国“窄门”而否定了现世的爱欲,使其陷入一种对道德纯粹性的极度迷恋中。她将人的灵魂与身体视为完全对立的两个范畴,只有禁绝由欲望带来的感性快乐,对身体加以折磨才能使灵魂变得更加纯洁,最终进入天国以实现永生。海涅曾将禁欲主义称为基督教培植的一朵花,“这朵花绝不难看,只是鬼气森然,看它一眼甚至会在我们心灵深处引起一阵恐怖的快感,就象是从痛苦中滋生出来的那种痉挛性的甘美的感觉似的。在这点上,这朵花正是基督教最合适的象征,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正好是在痛苦的极乐之中。”[5]阿莉莎的困境即在于罔顾生命主体的内在需求,因盲目追求禁欲而放弃了人的法则,执着于一种近乎神性的圣洁。纪德试图用阿莉莎孤独离世的人生悲剧说明,在人身上附加诸神的法则,进而追求一种极端的道德纯粹性是一条不可行的窄路,这条路窄得甚至容不下正常的人性。
阿莉莎的悲剧不在于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异常虔诚,而是她错误地理解了上帝的法则,并为此放弃了人的法则。在此基础上一味否定个体内在的生命需求,把禁欲视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当这种态势发展到极端时便成为一种反人性的畸形生活形态。在纪德看来,阿莉莎的这种做法是以上帝作为人的目标,其结果即是以上帝的法则取代了人的法则,个体的生命力也因这种沉重的精神枷锁而逐渐消亡。阿莉莎自愿选择给心灵戴上这副枷锁,但是作为生命本体所具有的爱欲本能却无法被束缚。困境中的阿莉莎在生命本能的驱使下不断挣扎,一方面她在心灵深处还保有对恋人深厚的情感,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违背本意压制自己的爱恋,这种矛盾心理给她带来极大的痛楚,并最终将她的生命力消耗殆尽。阿莉莎在形容这种痛楚的时候说:“当我们自愿受束缚而向前走时,我们并不感到有束缚;但当我们开始反抗,并远离它时,我们便十分痛苦。”[6]阿莉莎的道德困境也曾是纪德本人感同身受的。纪德的矛盾在于,是顺从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还是听命于长久以来一直无法摆脱的新教道德。他一面用不同的作品进行思想实验,探讨各种存在形式的可能性,一面质问:“你以什么神的名义,以什么理想的名义,禁止我按自己的天性生活?”[3]222纪德在《窄门》这部作品中表明,唯有顺从个体的生命本能,承认主体的生命感受,在人自身的法则支配下选择生活方式,才能避免陷于这种困境。
三、选择性失明:在自我与上帝之间
与前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田园交响曲》中的牧师也徘徊于自我与上帝之间,宗教伦理与个体伦理之间的冲突是他痛苦的主要根源。牧师收养了盲女热特律德,并在其后的教养中爱上了她,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有悖宗教伦理,但是他又无法压制自己的感情。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的理由,牧师便从世俗意义的层面上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他告诉后者,“上帝的法则就是爱的法则”,而“爱里面没有罪恶”[6]370。牧师一方面以此安抚热特律德,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试图减轻自己道德上的负罪感。热特律德察觉到两种“爱”之间的不同含义,她感觉到牧师和牧师的儿子雅克都爱她,但是她更想明白的是,哪种爱带来的幸福才是上帝的法则所允许的。她对牧师说:“我觉得您给我的全部幸福,是建立在无知上面。……这样的幸福我不要。……我宁愿了解真相。”[6]381牧师借用基督的话安慰她说:“你们若是盲人,就没有罪了”。牧师说服热特律德接受他这种不同寻常的“爱”,也任由自己在这种“爱”中沉沦。牧师试图用曲解教义这种方式消除自我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紧张状态,也在这种欺骗和自欺中找到了暂时的平衡点。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热特律德在生理上的失明和牧师自己在宗教教义上的选择性失明。
热特律德是双重意义上的失明:一方面她在生理意义上是真正的“盲”;另一方面,由于她无法看见周围生活的真实样貌,因而她的心智对道德是非的分辨能力也处于蒙昧状态。相对于热特律德的失明而言,牧师是一种选择性的失明。无论就生活的实际状况还是宗教教义而言,他都十分清楚自身所处的境况,但他却选择欺骗热特律德。热特律德复明后,最先映入眼帘的却是自己和牧师之间所谓的“爱”造成的过错和罪孽。在她看来,从前她没有罪是因为她根本看不见那些罪。但是,现在她看得见了,所以她自觉罪孽深重。在热特律德身上,伴随着生理性复明的是心智中道德意识的觉醒,因而她无法再忍受牧师的欺骗行为。她对牧师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6]383对热特律德来说,眼睛的失明与复明和心智的无知与澄明是同步的,而心智的无知与澄明也是与道德上的善与恶直接相关的。因此,她几乎在眼睛复明的一刹那就看清了自己深陷其中的道德困境,她用自杀摆脱困境也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结局。牧师的悲剧在于,有意在“人的法则”和“上帝的法则”之间不做选择,试图以此来模糊道德判断的标准,从中得到暂时的逃避。而一旦这种模糊的状态被破除,他们也必然要做出抉择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纪德通过这部作品表明,没有一个纯粹的道德中间地带,人必须为自己做出抉择,并在这种抉择中体现出自主性和对自身法则的肯定。在纪德看来,人的最终目标只能是人自身,个体也必须在自我完善中实现救赎。正如他早年在《大地食粮》中阐明的一样,他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上帝每时每刻都显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纪德看来,上帝的意旨就是要让人按照本性自由地生活。自我与上帝并非一种对立的关系,一切以上帝的名义发出的道德指令都是对人性的扭曲和束缚,他深信这绝非上帝的本意。在他的自传《如果麦子不死》中,纪德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深信每个人,或者至少上帝的每个选民,都要在世间扮演某种角色,确切地讲就是他自己的角色,与其他任何人的角色是不相同的。因此任何让自己服从于某种共同准则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叛逆,不错,是叛逆,我将之视为反对圣灵的这样一种‘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因而使个人丧失了自己确切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丧失了他那不可复得的‘味道'。”[3]214在纪德看来,在自我与上帝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存在是为了使自我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更为自由地依照自己的天性来生活。而每个人的天性是上帝早已设定好的,一味违背自己的天性去服从某种社会群体的共同准则才是违背了神的法则,是造成自我与上帝对立的主要原因。每个个体理应在保存自己天性的前提下顺从自我意志,这种自我抉择也是遵从了神的法则,是个体实现自我认同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米兰·昆德拉认为,“世界的非神化是现代的特殊现象。非神化不意味着无神论主义,它表示这样一种境况:个人,即我思,取代作为一切之基础的上帝;人可以继续保持他的信仰,在教堂里下跪,在床上祈祷,他的虔诚从此只属于他的主观世界。”[7]纪德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无论是“非道德”主义还是极度追求圣洁的禁欲,亦或是在两种对立立场下的摇摆不定,都源自对《福音书》和上帝存在意义的曲解。这种对上帝形象的僵化膜拜、对自我与上帝之间关系的不恰当理解是这种困境存在的主要原因。它们都直接导致了对真实个体意愿的有意遮蔽,僭夺了人的自主权。纪德说:“当我以新的眼光阅读它(《福音书》)的时候,我会看到思想和文字突然被它照得通明透亮。对于教会对福音书的解释,对于经过教会的解释,福音书的神圣,教诲我几乎辨认不出来了这个事实,我既感到遗憾又感到愤慨。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我们西方世界正因为看不到这一点,而正在消亡。这已成为我的深刻信念,揭露这种弊端的责任落到了我头上。”[3]284正是怀着这样一种责任感,纪德把笔触伸向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深处,以切实的道德关怀展现出现代人的精神处境。纪德在作品中对个体伦理诉求的表达,真切地反映出“非神化”现代社会情境中的精神现实,也显露出其自身的现代性特质。
[1]安德烈·纪德.陀思妥耶夫斯基[M].沈志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4.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3]安德烈·纪德.纪德文集·传记卷[M].罗国林,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351.
[4]安德烈·纪德.纪德文集(一)[M].桂裕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45.
[5]海涅.论浪漫派[M].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
[6]安德烈·纪德.纪德文集(二)[M].桂裕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3.
[7]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7.
“Ego and God”in the Moral Trilogy of André Gide
Jing Chuny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
André Gide began to probe in to the relationship of ego and God and other ethic problems in his early works,which was particularly shown in his work L'immoraliste,La porte étroite and La symphonie pastorale. In these three works,Gide approved of self-consciousness awakening through his interpretation of“immoralism”,and showed his denial attitude to obeying blindly religious doctrine by criticizing the blind pursuit of moral purity. Which revealed the dilemma caused by the confliction of personal ethic appeal and social moral rule.All of them showed a relocation of Gid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ego and God.It is not only a course of reconstructing personal values and morality but also a way to reestablish self-identification.
André Gide;self-consciousness;moral dilemma
I106
A
1674-5450(2016)03-0099-04
2016-01-20
景春雨,女,辽宁辽阳人,上海大学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赵践责任校对:赵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