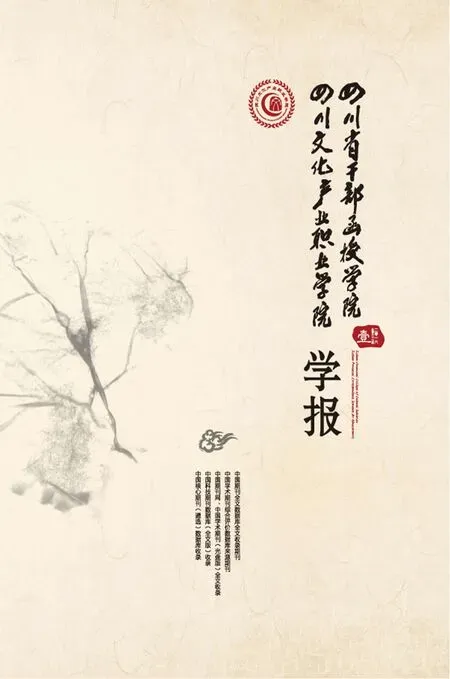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双重社会影响
2016-04-13石立春田雪梅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611756
石立春 田雪梅(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56)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双重社会影响
石立春田雪梅(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611756)
【摘要】在网络时代,民粹主义在发挥其关注弱势群体、监督社会精英、鼓励民众政治参与等积极效应的同时,其所具有的破坏秩序、颠覆权威,热衷于群体极化与零和博弈的特征也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挑战,在客观上将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最终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亟待有效应对。
【关键词】网络时代 民粹主义 社会影响
田雪梅(1970—),女,重庆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
新世纪以来,“民”、“粹”、“民粹关系”以及“网络”基本上构成了网络时代民粹主义的生发土壤与生成背景。然而,作为社会矛盾的一种“应对之策”,网络民粹主义本身也对“民”、“粹”乃至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运动),民粹主义在某些方面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而这种消极影响因网络的催化作用而愈发明显。
一、新世纪以来的“道德情感主义”
在网络时代,作为一种“泛道德化”的民粹主义,其强调对民众的极度美化和对权贵(精英)的极度妖魔化,认为民众是真理与道德的化身,而权贵(精英)都是肮脏的、可鄙的。这种“泛道德化”的民粹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以“人民之大旗”宣扬社会公正,这对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新世纪以来,网络民粹主义事件往往以“关注弱势群体”的面貌来颂扬社会正义。在民粹主义事件之中,草根群体充当着主力,而当代中国社会的草根阶层往往又是社会弱势群体。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相对而言的,比如相对于官民冲突中的行政官员、贫富对抗中的富人阶层、警民冲突中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房屋拆迁中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劳资纠纷中的包工头等,普通民众、贫困阶层、被拆迁户、农民工、小商小贩以及下岗职工等都可以称作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弱势群体往往不占优势,即“(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弱势群体虽然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机会,但即使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一道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运行,也会由于其先天不足或后天发展缺陷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与其他社会成员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竞争中获胜的希望就更加渺茫”[1],这导致弱势群体往往在强弱群体博弈过程中不占优势,但是,网络改变了这一切。
处于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不仅为民众提供了发泄负面情绪的现实“虚拟空间”,还给民众提供了进行社会抗争的重要工具。在网络中,普通网民掌握了草根言论的区域,其或是自发的,或是在少数“意见领袖”(可能是体制内,也可能是体制外,具有卡里斯玛气质的少数份子)的带领下,通过网络来聚集起来,使“民粹主义之民”在数量上永无边界的增长。通过网络,成千上万的底层民众联合起来,具备了人多势众的巨大优势,并通过“网络曝光”→“网民关注”→“扩大影响”→“相关部门介入”→“真相大白”的线路在网络形成压倒话语的巨大优势。网络民粹主义事件的这种极具社会轰动效应的特征,导致其拥有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得权威(精英)不得不在“民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诉求”下关注弱势群体,以维护其合法利益。纵观近年来的网络民粹主义事件,正是迫于强大网络舆论压力的影响,匪夷所思的“躲猫猫”(2009)而死、邓玉娇案(2009)“故意杀人罪”才改变为狱霸行凶杀人、“防卫过当罪”,而其他事件诸如“(上海)钓鱼执法”(2009)、“开胸验肺”(2009)、“跨省追捕”(2010)等也在网络舆论压力之下真相大白,而“我爸是李刚”(2010),“李天一诉讼案”(2013)以及“韩红违规”(2013)等事件也得到相应处理,民众维护弱势群体、颂扬社会正义的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二)对社会精英的监督与警示
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主义”,处于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在监督社会精英、涤清社会风尚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民粹主义与生俱来的批判性以及解构权威等特性赋予其鲜明的指向性,即“人民对应着当权者”[2]。通过对网络民粹主义事件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从周久耕“天价烟局长”(2008)到陕西“表哥杨达才事件”(2012),从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2009)到“郭美美事件”(2011),从胡斌杭州飘车案(2009)到“韩红违规”事件(2013),从“罗彩霞冒名顶替案”(2009)到“3.15打假:大概八点二十分发”(2013)等等,网络民粹主义将矛头直指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对其政治立场模糊、学术科研相互抄袭、基本道德素养存在问题以及经济上贪污腐败等问题进行严厉批判,这对社会精英们构成一种监督,有利于约束和扭转各种不正之风,引导社会朝着健康和谐方向快速发展。
网络民粹主义对社会精英的警示还表现在它是社会矛盾的外在体现,这有助于引发社会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反思。当前,网络民粹主义事件频发在本质上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而导致社会矛盾滋生的原因,除去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国家发展战略和分配政策的相对局限等客观性因素,精英集团利益链条的客观存在也是重要因素,它往往引发社会民众的仇视。一般来说,精英集团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利益链条中,政治精英一般充当着“保护伞”的角色,经济精英则为之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文化精英则从道德上或者是法律上赋予其他精英相应行为的“合理性”,同时,三类精英还可以相互转换。精英阶层利益链条的客观存在。
导致社会资源分配日趋不合理,进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新世纪以来,网络民粹主义事件频发,这既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主流社会精英支配社会资源现状的不满,也表达了草根阶层对自身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情绪发泄,这有助于唤醒社会权威阶层(精英)对弱势群体与草根阶层的关注,以及对产生弱势群体和草根阶层社会背景的有效反思。在这一过程中,网络民粹主义充当着“社会警示灯”的作用。
(三)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锻炼
作为一种“反自由而非反民主”和“反体制而非反政治”[3]的社会思潮(运动),民粹主义极为强调人民的直接参与,这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在此,笔者以“温州7.23动车事故”(2011)为例分析网络民粹主义事件对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锻炼。温州动车脱轨事故发生之后,网民根据乘客以及事故发生地附近居民上传的图片、文字、视频等资料,迅速作出反映,纷纷要求彻查事故真相(对此,官方媒体是同样主张)。随后,民众通过网络对事故进行了广泛关注,而互联网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提供了信息支持,还提供了供民众参与政治的“虚拟空间”,尽管民众仍然在“虚拟空间”中不断进行谩骂,但与之前相比尽显“理性思维”,比如《一个司机对动车追尾的分析》、《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等有价值的文章比比皆是。在这一事件中,平民参与政治的能力得到相应的锻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新意见阶层”的中国网民正在逐渐形成具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的“压力集团”。
二、新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带来的纷扰
在网络时代,民粹主义往往是打着“人民”或“大众”的旗号行事,但其并非真正地代表民众利益,而是由介于执政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精英分子领导下、打着“人民”的旗号、民众普遍参与的反对统治精英的运动。对此,有学者曾谈到:“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策略,即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为寻求政府权力而通过基于直接、无中介地从大量无组织的追随者中获取体制外支持”,“这是精英为获取大众支持而施展的政治策略,并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事实上,民粹主义是一种精英主义”[4],这种将民粹运动当成一种策略,来发泄对体制的不满情绪抑或谋求权力的行为,必然会给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一)破坏秩序,颠覆权威
现代化的顺利实现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作为信奉“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的民粹主义,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与冲击。当前,民粹主义的发酵与发展和网络技术有着紧密联系,尤其是Web2.0时代以来,作为根植于“人民”的“民粹”主义,其有着鲜明的草根性、非理性和批判性色彩,反体制性则是这三大特点的集中表现。
民粹主义的反体制性表现在其与代议民主制之间的矛盾。诚如塔塔特所指出的:“民粹主义者对政治的厌恶部分源于一种与制度的交锋,特别是与代议制政治制度的交锋,这种交锋隐含的感觉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只能是不好的结局。”[5]首先,这包括民粹主义具有反对政党政治的传统。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方面政治派别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没有一个派别敢于对外承认自己是一个派别,有明确的党性、派性,敢于对内建立一套作为严格意义的约束型纪律和组织结构”[6]。其次,这还表现在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制下的自由主义立场抱有敌意,并往往与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共同反对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形式。最后,民粹主义与代议民主制的交锋还表现为二者的直接对抗,这主要是指民粹主义崇尚直接民主,强调零和博弈,但民粹主义所强调的这种直接民主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民粹主义的反体制性还表现在其对法治权威的颠覆。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一切社会秩序都是应当破坏掉的,尤其是法治权威。民粹主义热衷于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滥用私刑来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暴力行为,崇尚对现有秩序不满情绪的发泄,崇尚在虚无空间的极度狂欢。以2009年的“邓玉娇案”为例,邓玉娇在案中防卫过当证据确凿,然而法院却因社会上民粹舆论的强势施压而免其刑事处罚,这突出表现了民粹主义对法律的蔑视,对法治的纷扰。
(二)群体极化与零和博弈
网络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平民主义思潮,其十分强调民众的直接参与性和“革命道德的至上性”,即广大民众是社会历史评判的标准,民众的意志可以超越一切程序、超越一切法律,并热衷于暴力革命与对社会的“颠覆性”批判。网络民粹主义这种群体极化和零和博弈的趋向,导致人们往往非理性的面对各种社会矛盾,以感性、暴力的手段谋求解决问题,并热衷于对弱势群体的绝对维护等。网络民粹主义在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纠纷时,往往是对弱者进行绝对同情,对另一方则进行肆意污蔑。比如人们在面对各地存在的拆迁问题时,往往认为是开发商为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地实施拆迁行为;人们在面对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往往认为城管在进行强势的暴力执法;人们在面对矿难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时,则往往认为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黑幕行为等。网络民粹主义这种群体性极化倾向以及热衷于零和博弈的做法在客观上将会导致并加剧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最终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的分裂。
网络民粹主义因其以公平、正义等为旗帜,抑或披上“正义之士”的外衣,迷惑了社会上部分民众的眼球,刺激一些底层民众的神经,使其平民性群众基础得以不断扩张,并以群体极化式的多数暴政排斥其他社会阶层、否定社会权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等,极大地危害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此外,在组织公民参政的技术性手段上,网络民粹主义排斥代议制,往往热衷于直接参与和直接决策,而在当下的中国,直接参与和直接决策一方面会因制度的不成熟与不完善,导致“参与的内爆”而打乱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强调直接决策的导向有可能增加公民之间的对抗情绪。不可诉求的利益群体将争夺可能的决策权,因此,民主将陷入到一种此赢彼输的零和博弈中,这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7]”
(三)处于梦游状态的“道德十字军”
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主义”,民粹主义者,尤其是处于“大众时代”与“网络时代”历史交错时期的民粹主义者,更愿意赋予自己“道德警察”的角色,这从侧面反映出民粹主义者“虽缺乏语言表达但却真实存在的精神困境”[8],即民粹主义者是一支正处于梦游状态的“道德十字军”。
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者规模巨大,参与者则是五花八门,这反映出人们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所固有的多重焦虑或危机意识,比如对“官”、“富”、“警”的极度仇视,对社会公正的期待;对主流话语的怀疑,对“弱势群体”的“力挺”等。在这些事件中,民粹主义似乎共同承担了比颂扬社会正义更为庞大的、更为朦胧的,说不清道不明但确实客观存在的一种道德焦虑。这种道德焦虑感因长期压抑以及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等,而导致民众通过网络进行意见表达、进行道德评判,甚至是开展“杭州飙车案事件”(2009)中的“贫富思维下的舆论审判”运动,抑或“我爸是李刚”事件(2010)中的“官民对立”话语下的网络暴力运动。这些运动的开展并没有解决民粹主义者“现代道德词汇匮乏”抑或“道德干渴”的现实困境,只是一次又有一次地以“人民”抑或“底层大众”的旗帜重复着“社会正义”的字眼——民粹主义者正处于“梦游状态”。民粹主义者作为一支正处于梦游状态的“道德十字军”,在给社会造成道德评判标准不明等纷扰的同时,还导致自我陷入道德上的迷茫,并在网络这一现实的“虚拟空间”中日益堕落,甚至是进行违法乱纪活动。
(四)民粹主义的泛滥考验全球治理,冲击着国家治理
“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上徘徊。十年前,当新兴国家获得独立后,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有多少会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这个在当时非常有道理的问题现在听起来显得过时了。新兴国家的领袖所拥抱的意识形态更倾向于拥有民粹主义特征。”[9]这是吉塔·艾尼斯丘(Ghita Ionescu)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40多年前所做出的观察。时至当代,民粹主义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并进的社会思潮(运动),对此,如同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布热津斯基在“阿拉伯变局”如火如荼、“占领华尔街”运动一触即发之际所谈到的:“我们正迎来一个新时代,这不是民主的时代,而是民粹主义的时代”[10]。
自1969年,盖尔纳等学者发出“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上徘徊”的感叹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民粹主义并未因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经济一体化而消失,反而呈现出周期性复发的态势,这昭示着全球治理正面临民粹主义的考验。当前,在欧洲,右翼极端民粹主义极度泛滥,有学者谈到的:“中西欧(CEE)将会越来越多地面对这些(民粹主义)政党”[11];在拉美,民粹主义则呈现出周期性复发的演进态势,即“该地区长期遭受高度贫困和分配不均的缠绕,民粹主义能够吸引众多的拉美民众已是不足为奇”[12];在亚洲,民粹主义政策对韩国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即“韩国自1995年起施行的交通违章赦免等政策已经成为民粹主义政策的代表,这不仅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比例逐年上升4.3%,还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13],而台湾地区民粹主义与选举的高度融合则让台湾政坛喜忧参半。民粹主义的全球泛滥给人类历史进程带来“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同时也对我国国家治理产生巨大冲击。
三、结语
自俄国“到民间去”和美国人民党运动相继爆发一个多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全球化泛滥及其区域化、本土化进程便开始周期性复发。因此,驯服民粹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道难题,因为与民粹主义的博弈是“一场激烈而不能肯定取胜的斗争”。加之民粹主义的影响又因“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无限扩大,这无疑给当代中国社会和全球治理带来巨大的纷扰。对于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双重社会影响,我们则是需要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对其加以审视,需要从“民”、“粹”、“民粹关系”、“网络”等方面对其滋生原因加以研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责任编辑:吴妮徽】
参考文献
[1]陈第华.特殊保护弱势群体:公共政策之公平性考量[J].江汉论坛,2014(2):83.
[2]John B.Judis,Ruy Teixerira,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M].New York: Scribner,2002.转引自林红.民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1.
[3]Bojan Bugaric,2008,Populism,Liberal Democracy,and The Rule of Law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J].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41,pp.191-203.
[4]Morgan Alissa Weiss.Opposition Politica and Popu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uth American Populist Governments[D],the Thesis for Master Degree of Art,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2009,pp.1-10.
[5][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N].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44.
[6]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北京:三联书店,2003:227.
[7]徐家良,万方.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创新分析——以湖南“献计献策”活动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8(4):72.
[8]赵刚.民粹文革十五年:重思红衫军及其之后[EB/OL].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9]G.Ionescu,E.Gellner,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M],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9,p.1.
[10]雷墨.民粹主义考验全球治理[EB/OL].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11]Ben Stanley,2011,Populism,Nationalism,or National Populism? An Analysis of Slovak Voting Behaviour at the 2010 Parliamentary Election,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44,p.257.
[12]Morgan Alissa Weiss.Opposition Politica and Popu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uth American Populist Governments,the Thesis for Master Degree of Art,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2009,p.1.
[13]Yongsun Kwon,Seung Hun Han,Changi Nam,2012,Estimating the Costs of Political Populism : Traffic Violation Pardons in Korea,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46,p.1449.
★历史·社会·管理★
作者简介:石立春(1990—),男,河南周口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思潮与当代中国;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心“高校大学生理性爱国观的引导机制探讨:以成都高校为例”(项目编号:CSZ11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7-08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784(2016)01-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