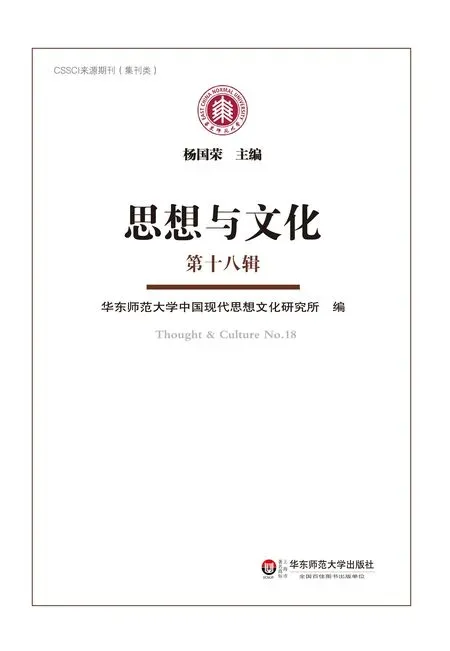“道学学生”一变而为“新青年”?
——“五四”时期单不庵门生施存统的精神世界与《非孝》的制造
2016-04-12马楠
马楠
前言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讲,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陈望道: 《“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本文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向陈望道访问后整理而成,载《杭州地方革命史资料》1959年第1期。杭州的一师*下文均简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一师”。能够在“五四”期间成为地方趋新反旧的重镇,并借“五四”暴得大名,很大程度归功于一师学生施存统那篇发表在《浙江新潮》上题名为《非孝》的小文。耸人听闻之题目、出人意表之刊载,随之搅动思潮,起轩然大波。彼时杭城内外的读书人,有的视他为反抗礼教之死士,有的骂他为倾泻“洪水猛兽”之狂人。一个小小的师范生因这篇出于一己之愤所作的小文,随即被时人视为思想激进的新青年,施也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在北京、上海之外的地方代表之一。
学界关于青年施存统的研究并不稀见,其中以叶文心教授《乡人的旅行: 文化、空间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Wen-Hsin Yen,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书对青年施存统的研究最为卓越。在该书中叶氏对“五四”前后施存统思想由旧转新给出了较为完整的解答: 在叶氏看来,正是杭州乃至浙江特殊的地域文化以及此种地域文化之上所孕育的新派人士*其作出的解答,笔者归纳为四个方面: 受深具共和理念的校长经亨颐的影响,对民初共和的失望;“五四”期间代表新派教员的“四大金刚”(即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陈望道)在一师宣传新文化;结交浙江省教育会《教育潮》杂志主编沈仲九,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感化;贫困与滞后的故乡金华和富庶与现代的省城杭州二地巨大的差异在施存统心中产生剧烈的碰撞。最终在“五四”前后将施存统导向了趋新守旧的道路。叶文心的研究似已面面俱到,然而如何能让“五四”期间同学眼中规行矩步的“道学先生”一转而为“新青年”,恐怕依然不能忽略与施存统关系最为密切的、距离最近的人与事件所施加的影响。
除了既有研究已述及的杭城新派人士促使施存统趋向激进之外,笔者以为恰恰是与制造“新文化”的北大学者有千丝万缕联系并教导施存统做理学工夫,在“五四”期间被“四大金刚”赶跑的所谓“守旧”宿儒单不庵,对施存统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叶氏研究“‘五四’在杭州”并以此批判“定于一尊”的过去主流“五四”叙述方式时,我们却不能忘记“五四”时来自北京、上海的新思想正是沿着某种人际网络,以我们不可察觉的方式迅速传递到地方。此外本文将进一步呈现《非孝》一文的产生过程以及施的同学凌独见,这位被隐匿于一师历史中的人物对于《非孝》的批驳,亦将会为施存统趋向激进给出答案。本文以为,与其将《非孝》一文视为“道学先生”施存统一变而为“新青年”的标志,倒不如通过《非孝》一文来窥察“五四”期间不论是风行草偃的新思想还是困守一隅的旧思想,是如何被施存统这样一位地方的读书人拿来作形形色色的利用借以纾解其内心的苦痛。表象上发端于北京的“新文化”在地方上如火如荼地开展,实际上对于彼时被称为“新青年”的地方读书人而言,此种身份多来自上海趋新报刊文人的“炒作”,他们在利用新思想新观念制造文本时依然出于他们自身特殊的缘由。但也正是这种出于个体特殊缘由的借用,遂使得“五四”新文化在各地“丰富多歧”地铺展开来。
一、 施存统之师单不庵: “孔老夫子”还是“老新人”?
在《新青年》还只是一份“普通刊物”,尚未发展成为“新思潮”的一块“金字招牌”*王奇生: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3页。之前,入一师头一年的施存统就已经接触到了《新青年》,彼时服膺孔孟之道的存统阅罢陈独秀《复辟与孔子》一文,心中大怒,大骂陈独秀无礼,不该诋毁万世之师,即弃书而走。*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8页。但数天之后,因为“由于好奇心的冲动,要看看他究竟怎么样骂法”,遂重新拾起阅之,此后一发不可收,从起初的一时兴起,到像阅读小说那般乐此不疲,再到民国八年下旬,全然接受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的观点。施从对《新青年》大怒大骂到对《新青年》佩服得了不得,*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8页。只经历了短短一年。短短一年的时间,施存统就与他的一师好友周伯棣、俞秀松、傅彬然等人就由同学口中的“理学信徒”一变而为“新青年”,而且二者角色变换幅度如此之大变换速度如此之快,颇令人难以理解。
五四浙江新思潮运动过后,尤其是1920年一师“留经”运动之后,时人都视代表新文化的一师“四大金刚”教员和《教育潮》主编沈仲九、上海《星期评论》社沈定一在施存统等人激进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但回归历史现场,不难发现,一师的“四大金刚”教员除了最为温和的夏丏尊长期身在一师做舍监之外,刘大白于1918年始受聘一师任国文教员,*刘家思: 《刘大白年谱简编(1880—1932)》,刘家思: 《刘大白评传》,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59页。李次九于五四这一年(1919年)来一师任教员,最后一位陈望道更是在北京五四运动发生以后,才从日本学成回国,担任国文教师。*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2—146页。而沈仲九与沈定一,前者的影响力更多集中于浙江五四运动的后期,*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后者与戴季陶等共同成立的星期评论社于1919年六月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第162页。此后才与施存统等一师学生发生联系。由此看来,上述被时人誉为转移东南风气的新派人士在关键的时间点上与转变期的施存统并无多少交集,他们在施存统由旧转新的过程中也未施加过多的影响。
当我们谈及“五四”期间杭城师范学校师范生的思想变化,必须注意到,这些师范生、中学生与北京大学的师生不同。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刚满二十岁,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岁,大部分都是十七八岁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年轻人。这批1895年前后出生的世代,入过书塾,背过《百家姓》、《千字文》,翻过《幼学琼林》、《大学》、《中庸》,乃至《论语》、《孟子》,但即将接受更加深入的传统学问之前,却须共同面对科举停废、新式学堂兴起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尚年少的他们被草草地扔进传授不中不西亦不古不今学问的新式学堂里,通过考试颠簸辗转地来到彼时被誉为浙省第一学府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但相较于一师绝大多数的师范生,施存统入学伊始便一同成为一师校内兼考据、辞章于一身的硕学宿儒单不庵*单不庵(1877—1930),又作不厂,名丕,字诒孙。祖籍萧山,父单沅华、伯父单棣华均以治宋学闻名。不庵继承家学,深研宋理学,却又重考据,长训诂,尤擅长校勘学。著有《宋儒年谱》、《二程学说之异同》、《宋代哲学思想史》。的入室弟子。*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在新式学府中却接续童騃时在书塾中的旧学训练,反倒在同学眼中成了颇为格格不入的“道学先生”。*傅彬然: 《回忆浙江新潮社》,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384页。
单不庵入室弟子之一,施存统的同学曹聚仁评价单氏在治学方面可以称之为清代考据学的正统派。其考据之精审,在杭州范围内一时无二。*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第154页。1920年,单不庵离开一师北上,接替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久升任教授。与陈汉章一道,被北大师生美誉为“两脚书橱”,其在校勘学、目录学方面深为彼时身处学术场域中心的胡适推重。*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 《胡适答单丕》、《胡适致单丕》,选自《胡适书信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2—443页。单卒后有遗藏八千余册,皆经其亲手朱墨点校批注。北京大学特为此设立“单不厂遗著整理委员会”,与此同时,单又是规行矩步,目不斜视,做慎独工夫的理学家,施存统等单门弟子正是在单不庵的要求之下实践躬行理学的。*曹聚仁: 《曹聚仁杂文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36页。但颇为微妙的是这批单氏门下的“理学信徒”在“五四”期间能够成为最为趋新反旧的“新青年”,并参与到杭州城内各种激烈的学生运动中。恰恰也是单不庵本人及单不庵的人际网络起到了比校长经亨颐、浙江一师“四大金刚”教员、浙江教育会《教育潮》主笔沈仲九等人更为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单不庵虽以理学知名于杭州,但单之姊单士厘乃是钱恂的妻子,而钱恂则是彼时在北大与胡适、陈独秀一道引领新文化的干将钱玄同的兄长。更为重要的是,单与钱玄同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就已订交,订交之后彼此保持长期通信,成为拥有二十五年交谊的密友。*钱玄同: 《亡友单不庵》,钱玄同: 《钱玄同文集第二卷 随感录及其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284页;二人保持长期通信,尤其在钱早年,单不庵与钱玄同隔数天即有信件来往。可见杨天石主编: 《钱玄同日记上(1905—1922年》(整理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这样一个深研宋学同时又讲求汉学考据的地方宿儒却与北大新文化名流钱玄同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正是通过钱玄同的介绍,单不庵才与胡适相知,由此进入到北京的学人圈之中。祖籍萧山的单不庵出生在嘉兴海宁的硖石镇,其家与硖石当地的望族徐氏又是世交。单妻兄廉臣又与徐志摩之父徐申如、徐志摩的老师张仲梧交好,徐志摩遂以叔伯辈视单。正基于此,当施存统与曹聚仁在1918年秋得知北京大学诸先生正在运动“新文化”的讯息时,会有如下的对话:
我*“我”指的是曹聚仁。看见他的枕下,摆着几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随手拿来看了几篇,不觉有些异样的感觉。……我问他: “存统,我们的单老师看了,他会有怎么样的想法?”他说: “单老师,也未必会反对的!《新青年》中的写稿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先生,他还是北大的文科学长呢!”*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好友与姻亲“不能破”的关系常常会弥补彼此思想间的张力,单氏不能也不会明确反对北大朋友们的观点,反而因这层与北京新文化名流的特殊关系,以及北大这块在地方读书人心中闪闪发亮的金字招牌,单门的理学弟子反倒比一师的其他同学有着更为方便的渠道得到来自北京的《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从而比其他同学更快地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更何况这位学生眼中的理学家*曹聚仁: 《曹聚仁杂文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36页。却在密友钱玄同的叙述中是个“表面上虽像一迂拙的老儒,实际上却是一个头脑极新颖,言论极激昂的人”。*钱玄同: 《亡友单不庵》,钱玄同: 《钱玄同文集第二卷 随感录及其他》,第285页。辛亥之前,单不庵就热心于新教育,不仅自修日文并根据日本教科书编了一部《幼稚字课读本》,而且广读当时流行于中国的欧陆海尔巴脱、廓美纽斯、裴斯太洛齐等诸人的教育学说。*钱玄同: 《亡友单不庵》,钱玄同: 《钱玄同文集第二卷 随感录及其他》,第286页。
1906年3月,单不庵与蒋觐圭东渡日本,协助彼时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宪政的钱恂编译政治书籍,是时钱玄同亦在日本。单在日期间,钱玄同、钱稻孙与之形影不离,尤其钱玄同常至单在日本卧处谈天,良久始归。*杨天石主编: 《钱玄同日记(1905—1922年》(整理本)上》,第29页。单虽以协助钱恂帮同编译书籍为名,实在是利用游日期间搜集新式学堂各类讲义和教育参考书,*钱玄同1906年4月25日中途回国成婚,单不庵赠他半年的早稻田中学讲义,借作纪念。杨天石主编: 《钱玄同日记(1905—1922年》(整理本)上》,第38页。除此以外,单对新学中的植物学一科发生浓厚兴趣,钱稻孙当时正翻译植物学书籍,单不庵趁此机会,遂与钱稻孙一起研究植物学,此后单氏一生都对植物学兴趣不减。单对新学问的接纳由此可见一斑。*杨天石主编: 《钱玄同日记(1905—1922年》(整理本)上》,第34页。单在日本停留时间虽然不长,至夏即返,但这段时光,在钱玄同的日记记载里却给出了一个与“五四”时一师师生口传中截然不同的单不庵形象: 他常邀钱玄同到一家名为“维新”的料理店小饮。樱花盛开的季节,则会前往钱氏兄弟的住处,与钱恂、钱稻孙、钱玄同畅谈中文西文难易的问题,其言: “中文同类之名词类皆以其物质总名为偏旁,而右旁之字则取谐声,此睹其偏旁而可知其为何类之物,睹其右旁之字而可读其音也。西国则否,字各为字,各不相侔,如OX、COW之类是也。惟中国音学久废,设能修其废官,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难也。”钱玄同听罢单氏见解,不觉拊掌赞叹。谈中文六书中形声之构字与古音之废,可见单不庵汉学小学的工夫;谈西文构词法,又可见单氏对字母文字如何创词亦有关注。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地找新学制下的各科讲义,则是他在日本的生活主题。单的理学家身份虽属不假,但在晚清东南(尤其浙江)一片趋新的背景下,单也绝非是一个“守旧”的宿儒,相反,在辛亥以前单不庵就已在知识层面上接纳了新学新知。
“五四”新思潮席卷杭州期间,单不庵因与浙江一师诸多教员意见不合,遂辞职而去,因此被校内外不熟知单氏的新派人士目为“守旧”。而他门下的弟子也喜称其为“孔夫子”,遂造成了单不庵“旧学宿儒”的这一形象。但单不庵对“新文化”的真实态度却在“五四”运动后一年告知于钱玄同:
(当时)浙江鼓吹新文化的人,实在浅薄得很。近年出版的新书报,有许多我早已看过,他们都还没有知道。我看他们并没有什么研究,不过任一时的冲动,人云亦云罢了。至于文化革新的运动,我是很以为然的。譬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新方法新眼光来说明旧材料,我是十分同意的。我自己今后治学也要向着这条路上走。*钱玄同: 《亡友单不庵》,钱玄同: 《钱玄同文集第二卷 随感录及其他》,第289—290页。
这番心迹的表露,不仅表明的是理学家单不庵绝不守旧,甚至“近年出版的新书报,有许多我早已看过,他们都还没有知道”和“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新方法新眼光来说明旧材料,我是十分同意的”,此两句话正是单不庵趋新的夫子自道。单在“五四”期间与新派教员的冲突并非缘于双方对新文化所持的立场不同,而是在单看来,正是这些“五四”期间突然涌现出的新派教员和学生的假“新”与不够“新”,“不过任一时的冲动”,才使得他不屑与此辈为伍,负气出走。民国初年,“新学”成为一个众说纷呈的语汇,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物均出于各自的见解与利害判断来诠释“何为新,何为旧”,并且又都坚持自己才是“真新”,自己的所知才是“新学”。然而若仅以纯粹学问来界定“新学”,经过严格西方学术训练的傅斯年可算是承担“新学”的代表人之一了。以傅斯年苛刻的眼光,连昔日“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诸多北大教员在他看来都是“守旧”,他们从事的学问也非科学的研究。*傅斯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 《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82页。傅并不视此辈为自己的同道,但却独独对单不庵另眼相看,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草创,就拟聘请单不庵为该所得通讯员。当得知彼时在浙江图书馆担任编目的单不庵与馆长杨立诚不相得之后,傅甚至还去信蔡元培,称“单先生版本目录知识,次日中国,极为难得”。希望身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能够聘单为中央研究院的图书员与编辑员,相信单若在史语所工作,必有成绩。*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 《傅斯年遗札》(第一卷),第109页。由此可以推断,在傅斯年的认知中,单不庵乃是其史语所的同调。连傅都认为单是其同调,单又怎么会是一个旧派人物呢?
而单在一师的门下弟子喜欢称他为“孔夫子”,其背后所凸显的问题,恰恰无关于单不庵个人的趋新抑或守旧,而是“孔夫子”这一称谓所指涉内容的变化。清季,时人言谈之中戏谑称呼某人为“孔夫子”或“道学先生”,往往用该词指涉以理学自居并以理学自限的读书人,但步入民国,“孔夫子”所指涉的内容不仅包括不喜新学(这其中囊括既不喜新学,也不懂汉学)的读书人,亦包括学生眼中持身严格,规行矩步的师长。但持身严格,用以身作则的近身指导来教化学生的“孔夫子”,却并不与“守旧”截然划为等号。以民国初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修身科教员的杨昌济为例,他被他的学生称作“孔夫子”,乃是因为其早年留学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王兴国: 《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61页。回国任教湖南一师,以个人自主意志的自我实现为期许,以严格律己的态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专心投注于工作与教学,才会因此被毛泽东等人,送上“孔夫子”的名号。*[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谭伯牛校,《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单不庵个人的知识背景、求学经历虽与杨昌济不同,但相同的是,在同样的“孔夫子”名号的背后,“孔夫子”所指涉的内容无关新旧,而是指向在学生心中单、杨二人略显刻板的行为举止。但行为举止刻板的单、杨二人,在思想上却是“老新人”。在曹聚仁的表述中,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等浙江一师学生跟着单不庵居诚存敬,做慎独工夫。自己却是野狐禅,不像施等人那般拘谨,思想颇为活跃。隐隐约约之间,也透露出一点讯息: 施存统等人居诚存敬的表象下,却正吸纳着远自北京而来的新思想。
由此可见,作为单门入室弟子的施存统在“五四”期间由“理学信徒”突然转向“激进青年”,虽颇使外人有错愕之感,但回归到真实历史的现场,正是作为单门弟子,施存统才不仅比周遭同学有着更为便捷的渠道去获得北京、上海两地“新文化”的讯息,而且跟随假旧真新的业师身边耳濡目染新思想、新方法。原本笃信理学的施存统早已在思想上受到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彼时的观者与当下的研究者往往将“五四”时施存统思想取向的转变归因为一师“四大金刚”甚至更为外围的沈仲九、沈定一的作用,却忽略了他们的业师单不庵所施加的重要影响。正是“五四”运动前他们形影不离跟随着的宿儒单不庵,使得他们在做理学工夫*曹聚仁: 《曹聚仁杂文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36页。的同时,早已与京城学子同步地接触到了新思想。
二、 趋新还是泄愤?——《非孝》文本之外施存统的真实思想态势
处在历史暗处的单不庵也许相较于“五四”时处在浙江新文化风口浪尖的所谓新派师长,对施存统的激进化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但停留于师长的影响来分析青年施存统迅速的角色转变仍然是不够的。我们仍须依托《非孝》这篇小文的产生过程,来窥探“五四”时施存统所谓激进的真实思想态势。
施存统与他的一师同学在“五四”期间,同处于青春期阶段。来到一师,施存统与周伯棣、俞秀松、曹聚仁等入单不庵门下,被周遭同学目为“道学先生”,他们对孔孟程朱的认同也毋庸置疑。若借助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论*“自我同一性”在埃里克森看来,是自我在漫长岁月中始终保持的连续性和同一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一方面是由本人完成,另一方面也指他人对此的认知。这种“自我同一性”能令人体验到一个前后一致,“本色不改”的自我,并将其作为行动的依据。“自我同一性”即个人积聚起来的一种信心: 他人眼中的我的连续性与本色与真实内在的连续性与本色必不相悖。见Erik H. Erikson,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9。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主要是在青春期进行的,是一个心理社会性过程,这个过程又分为8个发展主题阶段,“自我同一性”发展的第一个主题是原始信任vs原始怀疑;第二个主题阶段是自主决断vs羞愧自惭;第三个主题阶段是初始能动性vs罪恶感;第四个主题阶段是自我价值感提升的、目的明确的成就感vs自惭形秽;第五个主题阶段是青春期来临时自我同一性vs同一性迷失;第六个主题阶段是亲密vs孤立;第七个主题阶段是缔造繁衍vs停滞不前;第八个主题阶段是完满vs绝望。本文主要借用埃里克森第五个主题阶段“自我同一性vs同一性迷失”来进行分析。来分析,施存统与他的同门在青春期之前,已经对理学信条产生了认同,即接受了某种“同一性”。但是,“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美]埃里克·霍弗: 《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年轻人处青春期,常会盲信一套价值系统,并以此作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之全部真理,“但他们很快会发现,对这种确定性的把握,最后只能不断成为自己心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裂变的牺牲品”。*[美]埃里克·埃里克森: 《青年路德》,康绿岛译,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6页。在校园里刻意将理学义理付诸实践,也因为此种实践而被同学戏谑为道学先生的施存统,恰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对理学的深沉体悟,而是表现出了他们尚游离于传统学问门径之外的刻意与死板。也因此,表面看似坚定不移的认同会随着“五四”和“青春期”的双重到来而剧烈动摇。但西学之于他们,其实又多了一层隔膜,只是一句又一句接踵而至的“口号”。有史家注意到口号利用青年的这一面向: 这些口号形成一种“态度与指涉的结构”,这些新概念、词汇,形成一种高度目的论意义的境界,创造一种“向上”的轨辙,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向往意识,并且带来一套“激发视野、塑造实践”的性情。*参见李有成: 《在理论的年代》,台北: 允晨文化,2006年,第246页: “若干符码、意象、词汇、信念、以及这一切所构成的文化价值,无不属于这些‘态度与指涉的结构’,这些结构形成某一时代的精神意向或意识形态环境。”转自王汎森: 《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台北: 《政治思想史》,总第1期,2010年1月,第16—31页。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青年利用口号的另一面向: 在旧有的认同被他们自己摧毁掉之后,他们“无法确认自己应当如何选择,无法定位自己使命所在”,*[瑞士]维蕾娜·卡斯特: 《依然故我——自我价值感与自我同一性》,刘沁卉译,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59页。所以他们利用口号来实现肆无忌惮的情绪发泄,发泄他们对于彼时生存、学习状态的愤懑与不满。正如对施存统、周伯棣、俞秀松等学生最为了解的单不庵所言,他们激进地趋新“不过任一时的冲动”罢了。表面上他们用新语汇、新概念来批判旧伦理,支持新道德。实质上,他们在“五四”期间迷失了自己,“五四”以及“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没有能力像其他常态社会那样,给予他们心理“暂停”*埃里克森是这样阐述关于“暂停”的概念: 一种文化最好能够故意创造出这样一个时期或经历,使年轻人可以在成为一名合格的成年人之前“找到自己”。见[美]埃里克·埃里克森: 《青年路德》,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09页。的机会,让他们有一段平静的时间来反思和调整自己,直到内心足够清晰地确定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美]埃里克·埃里克森: 《青年路德》,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09页。不论这种东西到底应该是属于新抑或属于旧。
施存统作《非孝》,当然“指向那操纵人伦关系的道德说教”,期望“孝”完全脱离僵化的儒学教义,走向孝道自主,以重获其伦理道德自我实践意义。*[美]叶文心: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胡少诚,田嵩燕,刘文楠译校,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2页。但对于彼时的施存统而言,他作《非孝》的动机,更多的还是利用思想来纾解自己精神上的苦痛。*周伯棣: 《“五四”前后在杭州》,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405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篇文章的价值也只有“反抗精神”四个字”。*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373页。正是在这篇“为了纾解,也为了反抗”的文章中,他不仅利用了新思想,同时也利用了旧思想。
《非孝》一文“事实性刺激”*援用施存统自己的说法,见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前的我》,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374页。是: 1919年十月,存统接到家信,获悉其母病危,遂急忙回家。回到家中,看到卧榻之旁垂死的母亲,“只穿一件破单衣,吃着是一些冷硬饭,没人医治,没人照料”。忧心如割的存统质问其父为何不请医生医治?为何不拿棉被给母亲盖?为何不拿厚衣给母亲穿?施父答以“活人要紧,你母亲横竖是要死的,不必给她厚衣棉被了”。*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前的我》,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375页。存统眼见其父如此虐待其母,愤不欲生,却受困于自己理解的“孝”之观念,不敢悖逆父亲的安排。为免自己在家中“气杀、闷杀”,施存统含泪抛弃垂死的母亲。决然作一“忍心、无情”的人,*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前的我》,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376页。与家庭决裂,首途回校,写下了《非孝》一文。
与一师大多数学生一样,施存统少小离家,十二岁进初小,寄住于外祖母家,十七岁入县城长山高小,寄宿学校。高小毕业,报读一师之前,存统也未返家,而是寄住在杭州的舅父*施存统舅父为忠厚的长者,是曹聚仁的父执,还是杭州下城第一师的团长。见曹聚仁《悼施存统(复亮)》,曹聚仁: 《听涛室人物谭》,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62页;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第132页。家中达半年之久。*楼子芳、楼芳兰: 《施存统年谱(1899—1970)》,来自政协浙江省金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金华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第118页。近十年在外求学与父母聚少离多,过得是校园中的集体生活,本无多少尽“孝”的时间亦无多少受“孝”压迫之机会。施存统本人实际受到父亲的压迫有多少是个值得存疑的问题。此外,施存统出身于钱塘江中上游乡镇地区*这些乡镇地区所属的县份包括诸暨、嵊县、东阳、金华、义乌、浦江,在1919年一师三百多个学生之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上述地区,其他学生虽然隶籍浙西、温州、宁波及绍兴,也大部分来自这些城市各县的乡镇地区。见[美]叶文心: 《史学研究与五四运动在杭州》,郝斌、欧阳哲生主编: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01页。原子式的“小家庭”*来自于县镇和乡村,多属三四口之家。,而“五四”时成为新派人物言说对象的“家庭问题”、“‘孝’的问题”,多与世家宗族挂钩,是巴金小说《家》所描述的大家庭中存在的问题。在宗族(大家庭)组织中,父子关系是为首的人伦规范,*吕妙芬: 《孝治天下: 〈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研院丛书,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35页。父亲是整个宗族的首领,而家庭是“通过约定俗成的规则将许多观点歧异的家中个体联系在一起,亦是紧张、自私和束缚延伸出来的复杂社会网络”。*叶文心: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第174页。新青年需要冲破的牢笼,正是这样的“大家庭”。其实青年学生对于“大家族”的批判,早在辛亥之前就已有之,1904年,江苏留日学生发行的《江苏》杂志第七期,就有一篇题名为《家庭革命论》的文章,文章虽从兴国权、造国民国家思想的角度来批判家族主义,将家族视为国家的对立面。*张枬、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833页。但在文章的背后,也应看到正是因为苏南社会宗族组织发达,才会使得苏省的留日学生在提倡国权、国族时,有家族主义之“靶”可打。也因此,按照新派人物的观点,父亲对儿子的压抑、儿子对父亲的反抗,更多的应该显现在出身于世家的一中学生身上,比如与施存统同为浙江新潮社的阮毅成。杭城阮家,乃苏省睢宁之望族,溯其祖,原籍绍兴,数代游幕于江苏,在苏、浙两省均有田产商铺,毅成父性存活跃于杭州政界,以兴办新式企业(如浙江印刷公司)及国民党而著名。*叶文心: 《史学研究与五四运动在杭州》,郝斌、欧阳哲生主编: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101页。出生于如此世家,阮毅成又自小在家中接受父亲给予的严格教育,*阮毅成: 《三句不离本杭》,杭州: 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56页。并常随侍父亲左右形影不离。毅成于其父有生之年,读书游学工作都唯性存耳提面命,但是父子之间父严子孝,并无发生任何“非孝”抑或“逃离家庭”的问题。施存统发表《非孝》之后,同为浙江新潮社成员的阮毅成视存统为“犯思想偏激病分子”*阮毅成: 《关于浙江新潮和新吾学会》,百合书店,第11页,民国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杭出版,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避之唯恐不及。至少在杭城,时人心中“非孝”、“反家族”的问题,并非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最厉害鼓吹“非孝”和“反家庭”的师范生往往离家最远,不受父母管束,受家庭迫害最少。而最应该站出来呐喊“非孝”的世家弟子,却与父辈一同生活在杭城的家中,父父子子,彼此相契。“五四”新文学中时常出现的出身于大家庭的“新青年”与“古板守旧”父亲对抗的场景,在1919年的杭州却并非是典型现象。由此可见“五四”时期诸多新观念往往与真实的社会存在相去甚远。新观念与其说是治疗当时社会问题的良方倒不如说是青年人借以抒发个体不满情绪的工具。这种不满情绪未必一定与该观念、词汇所指涉的社会存在明确相关,北京、上海、杭州诸地的新青年在用同样的一套新文化的话语表达时,他们表达的却并非是相同的社会事实。但历史的吊诡处就在于“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小册子充斥于读书人各个生活场域中,而在这些小册子里,又充斥着各种类似存统《非孝》那样批驳旧式家庭伦理的文章,使得这些“观念上的真实”成为了“五四”时期读书人心中普遍的“感觉结构”。将并不真实的“观念上真实”问题变成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问题。
1919年母亲病体垂危,给了暑假返家的施存统难得践行“孝道”的机会。施存统即按照宋明理学家的要求,一板一眼地“事亲以敬”。母子之间往往亲密无间,侍奉母亲,施存统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礼。但是面对性格乖戾一怒之下就对存统拳打脚踢的父亲,性格伉直偏激的儿子却很难做到恭敬从命。然而,《二十四孝》中的故事*《二十四孝》依然是当时一师国文、修身课所要上的内容之一。见陈范予: 《陈范予日记》,[日]坂井洋史整理,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7年。,《论语》、《孝经》中孔子的教诲、宋明理学家的笃行、单师不庵的“割股疗母疾”都使“孝”之理念化为一种深刻的印记,使得对理学义理并不完全理解却盲从信服的施存统将对父的“孝”直接与“从父之命”划为等号,即便处于青春期的存统内心中对其父多有不满,并且已然感受到“孝”之理念与“孝”之实行之间,有着难以避免的张力。但他仍然要求自己,对其父尽力做到依顺敬爱。于是,存统的“孝道”笃行,更多了一层刻板和不得不为之的色彩。当卷入“五四”趋新反旧思潮中的施存统,于1919年十月之际,再次返回与杭州生活方式绝然不同的家中,看到绝情的父亲不做任何努力,任凭垂死的母亲在榻上奄奄一息,忍无可忍的他终于爆发了。
从《非孝》的内容*《非孝》原文现已无从可考,但却可以通过施存统、曹聚仁和当时一师的教员姜丹书的回忆可知文章大致的内容。见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第126页;姜丹书: 《〈非孝〉与浙江第一师范的反封建斗争》,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418页。大意可知,施存统所遇到伦理难题与其说是中国家庭制度、“孝道孝治”理念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倒不如说是施存统个体在“孝道”践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施存统心中所困苦的是,面对其父虐待其母,他认为自己难乎为子: 顺父逆母,不孝;帮母斗父,亦不孝,然则如之何而后可?施存统自以为发现了旧伦理的矛盾,随即又联想到用刚刚习得的无政府主义平等、互助、博爱之观念来代替旧伦理,恰好能补旧伦理之不足。于是,在一千字的小文中,施存统提出了自己新的伦理观:
家庭制度利用名分主义不知造了多少罪恶!假如我和我父没有名分的关系,则对于我母的事尽可自由处理,现在有父亲拿名分关系从中作梗,便使你动弹不得!“孝”是一种戕害人性的奴隶道德。假使没有这种道德的束缚,吾父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而平日父母子女之间,一定能够和和乐乐。……人类是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当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373页。
然而,不知道施存统是真的忘记还是故意忘记,是真的不解抑或假的不解,《孝经》谏诤章第十五,就已经为存统的困境注解了答案:
曾子曰: 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唐]李隆基注,[宋]刑昺疏: 《孝经注疏》,邓洪波整理,钱逊审定,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儒学讲子对父孝,并非要求子对父完全没有意志的“从父之令”。“孝”是一个至高的价值,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动,因为是实践行动,所以面对生活中各种疑难困惑,怎样“为孝”亦有其特有的技巧策略。类似存统之父苛待病危存统之母的行径,便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身为儿子的存统,不仅应当向父“直言谏诤”,另其免于不亲不义,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孔子给出了“父陷不义,子争于父”方是“为孝”,“父陷不义,子从父之令”才算“非孝”的清晰答案。
施存统不可能不明白这些道理,即便他对儒学义理再怎样不求甚解,被誉为“道学先生”的存统只要平心静气地思考,就能知晓他所身陷其中的囹圄并非由旧伦理中“孝”自带的原罪所建。在真正儒家所企图构建的人伦关系中,“孝”应该而且可以做到至情至理。但身处青春期的施存统借着“五四”激进之风,却一发对其父郁结于胸长久的愤懑之气。他从“顺父逆母,不孝;帮母斗父,亦不孝”这组矛盾中得出“孝”是“一种戕害人性的奴隶道德,是家庭制度利用名分造成”的结论,随即便用刚刚习得的西学来加以应对,以为“自由”“博爱”“平等”“互助”的新伦理便可以化解旧伦理的危机。但《非孝》一文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与其说他是为了“非孝”,倒不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借用批判“孝”的方式来释放其对父亲的满腔怒火。
《非孝》一文刊出不久,引起轩然大波,攻击之声,遍及全国。一师之中,便有一生,办报对《非孝》加以反对,此人便是凌独见。凌独见本名叫凌荣宝,“五四”之时,刚进学不久,乃是一师二部的学生。凭一己之力办了一张和《浙江新潮》同型的周刊与之针锋相对,报名即叫作《独见》,由报名可知,凌氏需要彰显自己面对彼时新思潮澎湃汹涌,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依然坚持独立见解之立场。从此凌荣宝亦以“凌独见”之名见知于时人。《独见》周刊所有文章均由凌独见一人执笔,每一篇文章又以批驳《浙江新潮》之论点而写,从以攻击施存统《非孝》而写《辟非孝》伊始,一期、二期、三期,一直批驳下去,共办了十期。*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第139页。遂引起一师内外新派师生之“公愤”。“五四”期间在一师校内主编《钱江评论》的曹聚仁便认为凌独见是省教育厅长夏敬观派到一师来的细作,*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第139页。浙江新潮社社员的夏衍以为,办《独见》周刊的绝不是凌独见一个人,所谓“独见”也非一人之见解,在凌后面,显然还有一个有力的杭州“校长团”守旧势力的背景。*会林、陈坚、绍武编著: 《夏衍研究资料(上册)》,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28页。与存统一道的单门弟子傅彬然觉得,凌的背后有旧派教师或校外什么人支持。*傅彬然: 《“五四”前后》,沈自强主编: 《浙一师风潮》,第392页。一师激进学生甚至为了发泄积愤,向一师学生自治会提出控诉,把凌视为学校公敌,学生会随即推举自治会主席曹聚仁为审判长,审理凌独见。*此时,施存统已退学离校。一位所谓的旧青年,面对一群新青年,毫不畏怯侃侃而谈,把公审场地变成了自己的演讲堂,最后弄得曹聚仁无从判断,不了了之了。*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第140页。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一师内外趋新青年众怒所归,把凌独见看成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事实上,激进青年与其说凌独见有所谓守旧派的势力背景,倒不如说这是他们对凌氏“独见之行为”做出自我心理投射的分析。彼时正是激进青年他们自己,背后享有所谓旧派师生所没有的新势力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于杭城一师内的师长、一师外的省教育会,还有来自上海的星期评论社与《新青年》杂志社主笔。
相较于外围所谓守旧人士视施存统为洪水猛兽,外围趋新分子对凌独见口诛笔伐,身处漩涡之中的当事人双方施存统和凌独见,互相反倒颇有敬意。施存统后来回忆:
……大名鼎鼎的凌独见先生。他虽在文字上如此攻击我,但我精神上却没有因他感受一点痛苦。许多人都疑心他有作用,受运动,我却没有疑心这一点。他这人很有趣。我看见《独见》第一期之后,写一封信去质问他,他便叫我去谈话。开头第一句就是: ‘我对于你很佩服!’接着就说: ‘我想你一定不会做这种文章,这决不是你良心的主张,希望你做一篇忏悔文,在我的《独见》上发表!’我说: ‘忏悔文我不会做,我只能做我良心要做的文章。你那篇《辟非孝》,所辟的还是你的非孝,和我的非孝没有什么相干!’我于是便把我要非孝的道理当面讲给他听。他说: ‘你的话也不错!但是你可以非孝,我却一定要辟非孝的,不过我很希望你再把你的意见做一篇文章在我的《独见》上发表。’我当时便答应他说: ‘我一定要做一篇《我为什么非孝?》的文章,请你指教指教!’这事后来因为没有功夫,所以也就罢了。至于我对凌先生,实在没有什么恶感。*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沈自强主编: 《浙江一师风潮》,第373页。
施凌双方颇为客气,远没有外人所想象那般彼此视对方“千刀万剐不足以蔽其辜”。*曹聚仁: 《听涛室人物谭》,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且互相尊重对方立场,虽有意见之争,却非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二人更像是达成“吾‘非孝’,汝辟‘非孝’”的君子协定,不以意气相压而是各抒己见。在彼时众多施存统的批评者中,凌独见毫无疑问看懂了《非孝》一文。他对存统的遭际表示同情,对他的行为也表示“佩服”,但是,他以为施不该用“非孝”的方式,不该借助批判甚而推倒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方式来纾解他个人的不满与愤懑。而施存统对凌独见一番“尔为尔,我为我”“你作‘非孝’,我辟‘非孝’”的回答,亦可透露其自身也明白以道义而论,他的“非孝”并无十足理由,存统之所以要“非孝”到底,是因为他不希望他一己之悲惨故事继续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中复制。而独见,虽然对施存统的运命和遭际表示同情与理解,但是仍然为了“翼教卫道”,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辟“非孝”到底。他们二人互相坚持自己对“孝”之理解来批判对方,但也或多或少地认可对方关于“孝”的部分观点。
三、 外围造势: 《非孝》成为舆论大波
然而身处沪上的陈独秀等人却通过舆论造势将一个师范生强烈个人情绪的抒发变成了一件在公领域具有巨大影响的趋新反旧行为。其实若根据施存统本人二十年后的陈述以及彼时阅过此文的一师师生回忆,《非孝》的内容远非如其标题那般“标新立异”,实际上,也早已有人在报刊上书写过与《非孝》相类的内容。1908年,身在法国的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其刊物《新世纪》上就发表过署名为鞠普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论习惯之碍进化》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家族未废,则孝亦本乎人情。然古有诤子,固不徒以顺亲为孝也。自忤逆之说出,以顺为孝,而几谏之义亡。且孝之于亲,宜无所分别也。乃世之言者,重父轻母,而孝之真义又失。夫以劬劳言,则母有孕育哺乳之苦,而父无所事事也。以慈爱言,则母之爱常真,而父之爱多伪也。故不言孝可也,言孝而重父轻母何也?*张枬、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98页。
上述的内容岂不是与施存统在《非孝》中表达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吗?而在另一篇愈加鲜明地展现无政府主义反家庭立场的文章《毁家谭》中,鞠普直接写道:
原人之始,本无所谓家也,有群而已。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妻,于是有夫权。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子,于是有父权。私而不已则必争,争而不已则必乱,欲平争乱,于是有君权。夫夫权、父权、君权,皆强权也,皆不容于大同之世者也,然溯其始,则起于有家,故家者,实万恶之原也。*张枬、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93页。
而同期的另一篇文章,自谓为“四无”的作者在其《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毫无疑问,《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此一标题远比《非孝》更加大胆。一文中更是写道:
惟“父”之根据于爱情,而为强权所利用者。……人类者,当改良而为完全有爱情之一物,其时不但父子可废,即朋友之名,亦在消除之数。*张枬、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203—212页。
这些远比《非孝》更早且更加大胆的言论,虽因《新世纪》这份杂志远在法国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言说的影响力,作为报界先行人的陈独秀却不可能不知晓这些文章的存在和这些文章在辛亥之前的影响力。但对于彼时已随他的《新青年》一同南下上海的陈独秀而言,他需要的正是类似《非孝》这般能够带来广而告之效应的激烈言论,从而充分彰显新派之新,以求新旧之间作最为彻底的决裂。谁能起而响应他,与他一道趋新反旧,谁就是他陈独秀的同志。因此,陈独秀与他上海的新朋友,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沈定一、李汉俊等人,早在浙江新潮社成立伊始,就通过通信慰问,寒暑假邀请一师学生施存统、周伯棣、俞秀松到星期评论社,或到陈独秀位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家中做客的方式,对一师学生任何激进反传统的行为表示鼓励和支持。当存统《非孝》一文刊出后不久,陈独秀便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写了一篇题名为《〈浙江新潮〉——〈少年〉》的随感录,说《浙江新潮》的议论比《新青年》更加彻底:
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我祷告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扬《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独秀: 《随感录七四: 〈浙江新潮〉——〈少年〉》,《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7卷第2号。
而当凌独见自创《独见》周刊,刊出《辟非孝》一文之后,陈独秀又很快写了一封讽刺凌氏的信,让一师的学生刊在继《浙江新潮》而起的另一份刊物《钱江评论》上。更加值得玩味的是,陈独秀好友,《星期评论》的主笔戴季陶,态度暧昧地一面鼓励欣赏施存统,*有材料表明,施存统受戴季陶影响巨大,并对戴近乎崇拜,而戴对存统亦爱护有加,存统后来东游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即是受戴推荐。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 1990—2002年》,2003年第411页;[日]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3—304页。一面又去信凌独见,支持凌独见的主张,批评了施存统,并让凌将信刊在《独见》周刊上。施存统的“非孝”受到了陈独秀、沈定一的支持,凌独见的“独见”又受到了戴季陶的赞许,而陈、沈、戴彼时尚属于同一阵营的同志好友。文本之外的人际网络不仅纷繁复杂,甚至相互重叠。互为对手的施存统与凌独见,私下里互有敬意,针锋相对地笔战背后,却共同分享同一人际网络的支持与批评。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读书人思想中有着一种模糊、附会、改换、疏忽不定的特质,处于潜流的“左”与“右”思想在刻意炮制的“新旧对立”思想主题面前还能结为求同存异的盟友,尚未分裂为日后不共戴天的两翼。1918年同为《新青年》阵营的钱玄同与刘半农自导自演的一出“双簧戏”*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并列刊出了两封信件。一封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全信以文言写成,共4000余字,故意以一个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说话,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而另一篇《复王敬轩书》署名“本社记者半农”由刘半农执笔,通篇所举观点都与前文针锋相对。全文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王敬轩(鞠)、半农: 《文学革命之反响: 王敬轩君来信》,《新青年》1918年3月,第4卷第3号。仿佛一年之后,又在陈独秀和戴季陶之间上演。正是这些身处上海的新文化先驱者的支持、鼓励、反对、批评,乃至“炒作”,使得施存统出于一己之愤所作的《非孝》、凌独见出于一己之义所作的《辟非孝》,越出一师之外,越出杭州之外,与发轫于北京、上海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思想进行形形色色利用”以宣泄自己精神苦痛的存统被诠释成为“反传统斗士”,在众口言新的潮流大势中仍然坚持独见的凌独见被诠释成为“旧势力代表”。而最终,归因于“五四”后“新战胜旧”、“启蒙战胜保守”线性进化的历史书写,作为“旧势力代表”之凌独见逐渐隐匿在时间长河中,而施存统与他的《非孝》一道,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部分。
但是,所谓旧青年凌独见,在真实的历史中却在鼓吹白话文方面比施存统走得更远。1920年,已经卸任的浙省教育厅长夏敬观向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推荐凌独见,张元济就在他的日记中称赞独见“善写白话文”。
……剑丞荐凌荣宝,浙江师范毕业,继往龙门师范,今年毕业,善白话文。此事久已忘记,昨日检出,附入叔通信,请交伯俞。*张元济: 《张元济日记(下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63页。
1923年三月,凌独见应浙省教育会国语传习所之邀,授讲“国语文学史”,遂本着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对话的初衷,自己编了一册《新著国语文学史》,在书中,凌氏对“国语”的定义,较诸胡适之更为新颖,与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一道,打破传统的文学史编写观念和体例,从“白话文学”的视角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推向文学史的中心。此书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为中等学校所备的国语教科书,对彼时的中学生,颇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若单从白话文一面观之,凌独见不仅不该算旧派,更应属新派了。
结语
正是由于沪上重要舆论人士的“炒作”,《非孝》一文才在杭州引起轩然大波。1919年12月底,在浙省督军卢永祥和省长齐耀珊,以及省议会多位议员的联合压力下,一师校长经亨颐不得不令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傅彬然自行离校。施随即前往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自北京回来后,施存统在上海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工作,思想才真正趋向无政府共产主义。“五四”前在不仅是新派经亨颐、沈仲九、沈定一、刘大白更是在业师单不庵的影响下,施存统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在出于一己激愤所作《非孝》之后,施存统与一师其他的单门弟子、凌独见一道被卷入到激进化的浪潮中,一方扮“新”,一方演“旧”。而把他们推到历史舞台上,并烘托他们成为杭州新文化运动主角的正是彼时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沈定一、戴季陶、李大钊等人。施存统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一路扶摇,却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脱离中共。而辟非孝的凌独见于施存统离校后一年从一师毕业,此后的人生履历从编书撰述到记者、编辑,从记者、编辑再委身公务,最后在家乡的城中开了一家书店,自己当起了老板。*凌独见: 《怎样做人·再版代序》,江山: 独见书店,1942年,第3页。其所经历的身份变换也不可不谓之多。二十多年后,抗战军兴,曹聚仁随军来到凌独见的家乡浙东江山,故友重逢,谈起往事,凌独见对曹聚仁说: “年轻人真是不懂事,那时候,我只要去孝顺父母就行了,何必跟别人吵嘴呢?到了今天,我们又不想儿女怎么孝顺我了!”当是时,曹聚仁打听到施存统恰好在离江山不远的金华乡间闲居,特地派人请他入城,与凌氏再叙一面。可惜存统已早一周前往赣省九江了,施氏后来与聚仁相见,叹息错过如此机遇,而凌氏一生亦以再未谋存统一面为恨事。*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第140—141页。
二十年前,施存统、曹聚仁、凌独见这些原本应该在一师校园里磨砥私行的“道学先生”,因为各自不同的缘由,被裹挟进二十年前那阵激进化的时风中,随之,他们也就成为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他们二十年前的思想与行径亦被后来的解读者“千百其意”了。但不论后来的解读者是用“新青年”抑或是用“理学信徒”,是用“激进”抑或是用“保守”,是用“迷失”抑或是用“觉醒”来看待1919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中的这群读书人。恐怕我们最好说,他们永远只该属于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