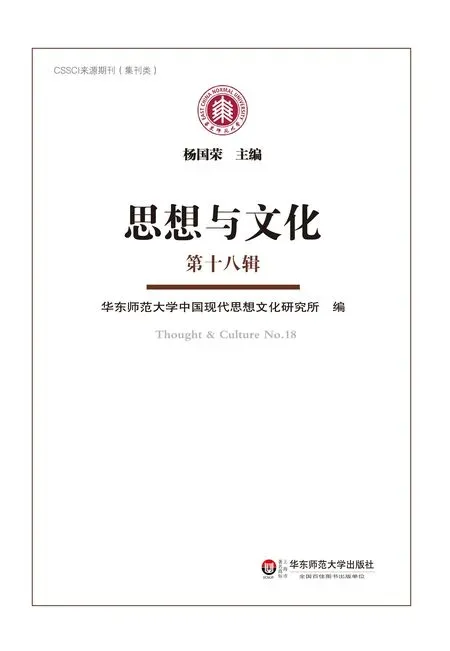从保罗到克尔凯郭尔: 信仰的荒谬问题史*
2016-04-12王佳音
王佳音
“荒谬”(absurd)与“悖论”(paradox)是克尔凯郭尔思想的重要关键词。它们不仅覆盖了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方方面面,尤其在谈及信仰的时候,作者更是大胆而略带冒犯地说出了“信仰的对象就是悖论”*克尔凯郭尔: 《哲学片断》,王齐译,《克尔凯郭尔文集4》,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4页。的话语,直接在“悖论”与“上帝”、基督教之间*克尔凯郭尔: 《基督徒的激情》,鲁路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82页。划上了关联符,进而将“荒谬”当成了信仰的重要依凭*克尔凯郭尔: 《畏惧与颤栗》,京不特译,《克尔凯郭尔文集6》,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神圣的上帝变成了“既是又不是”*克尔凯郭尔: 《基督徒的激情》,鲁路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的悖论,虔诚的信仰等同于荒谬的行为,这样的思想显然是不能为正统的教会所接受的。但事实上,深入到基督教思想的内部,我们会发现,克尔凯郭尔的“奇谈怪论”并不是突然地出现的;将荒谬与信仰间建立关联的做法,有着漫长的历史,它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保罗那里。本文拟结合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论述,来梳理“荒谬”是如何在有关信仰的思想中出现的;以及,从保罗到克尔凯郭尔,关于信仰的荒谬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立论转变。
在从保罗到克尔凯郭尔的这条荒谬思想的线索中,尽管经历了不同时期话语中心的偏移,但有一个核心的信念却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对个人主体性的主张。换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荒谬或者悖论之所以会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正是由于它看似荒诞不经、毫无价值的表面之下,蕴藏着“因信称义”的深刻思想。人在上帝面前是卑微而虔诚的,但同时他又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并凭借自己的信仰而获得与作为超越者的上帝的沟通可能性。
1.从保罗到德尔图良:打破必然性框条的荒谬
公元1世纪左右的使徒保罗,被认为是一个站在多重话语体系聚集的交汇点上的重要思想家。在他的身上有着犹太、罗马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是在罗马(外邦)长大的犹太人,同时又有着希腊文化熏陶、教育所留下的深刻烙印。或许也正是因为兼具犹太、罗马和希腊的特征,使得保罗在基督教的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基督教普世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27卷新约中有13卷是保罗与他人来往的信件。在整个新约体系中,从体量上来说,除去四部福音书,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些保罗的书信了。
在保罗的诸般主张中,最重要的是“因信得救”——信徒信仰基督即可获得神的恩典,而不必先受割礼再获得基督徒的资格,“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么”(罗马书2: 26)。在犹太教传统中,割礼是律法权威的象征,否认割礼也就是间接否认了律法之于信仰的必然性。这一点对当时的犹太人教团而言,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因为伴随着外邦人不行割礼就可以信仰,犹太人作为选民的特殊地位就不复存在了,“神并不偏待人”(罗2: 11),“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罗3: 9)。保罗认为,比之律法和血统,内心深处的真信才是上帝遴选被拯救者的依据,“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3: 24),“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罗3: 25)。
不仅如此,保罗还进一步地认为,人对上帝的信仰是因为神的“义”,而不是“按照真知识”(罗10: 2—3)。保罗区分了“从上头来的智慧”和人自己心中生出的智慧,并将各种纷争与冲突归咎于人心的智慧(雅各书3: 13—16)。显然对于保罗来说,上帝的“义”不是世俗社会的知识,也不是世俗社会的智慧,而是建立在恩典与救赎基础上的清洁、和平、温柔良顺、怜悯、善果和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3: 17)。可以说,在保罗这里,上帝的义之中有着明确的善恶区分,人的信仰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温驯,并且悔罪。上帝将依凭人的信仰之行为本身来给予恩典。
之所以说保罗是信仰的荒谬路向的开端,是因为在保罗那里,人对上帝的信仰是无条件的,不需经过任何特殊的律法的认可,也不能从自己的知识和智慧里找到信的依据,而仅仅只是因为恩典;与之相应的是,上帝对人的救赎和赦免也是平等的、无分别的,仅仅只是根据人的信仰本身。人日常的判断和评估,在对上帝的信仰上毫无用武之地,因为人人平等。可以说,保罗所言的信仰,既违背了当时的常理与习俗,同时也打破了犹太民族在信仰上的特权——上帝不必然赐福给奉守教义的犹太人,人也不必然通过特殊的认定仪式(割礼)来表达信仰。在上帝和犹太民族间的必然性联系,被那位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信徒斩断了。对原本作为犹太教分支的耶稣教派来说,保罗的因信得救是荒谬的,因为它竟将上帝对其选民的优待给抹除了,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面前具有同等的地位。这种不强求特殊性而以平等为基础的救赎观念,事实上也为基督信仰和犹太信仰的彻底分道扬镳埋下了种子。
同时,在保罗的思想之中,还蕴藏着一个更大的“荒谬”因子,即人的知识或智性在信仰面前的毫无用处,相反,福音的要义是“愚拙”,“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哥林多前书1: 17)。在这部为哥林多教会所写的书信中,保罗明确地提出,神乐意去拯救那些在神面前愚拙却虔信的人(林前1: 21),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林前1: 18)。
保罗还很明确地提出,“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林前1: 22—23)。犹太教、基督教和希腊哲学就此成为三条迥然有别的生存路径。保罗对基督徒发出了警惕哲学的严正警告,“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 8)。通常,在基督教思想里,保罗被认为是信仰主义的先行者。信仰主义,也就是将信仰置于理性之上,强调信仰不需要理性为据的一种观念。
这种将信仰区别于理性和智慧的观念后来为德尔图良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位拉丁神学之父总结着说出了第一句明确的荒谬之言——惟其荒谬,故而可信。这句话的原句出自《论基督的肉身》一文,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上帝的儿子死了,因为这是荒谬的,所以无论如何这是可信的”;紧接着的下文是,“并且,他被埋葬了,又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如何它是确凿的”*冈察雷斯: 《基督教思想史》第一卷,陈泽民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8年。。作为上帝的儿子,基督是可以不死的,然而他却死了;作为死了的肉身,他被埋葬了,但又复活了。这种死而复生的神迹,对没有虔诚信仰的普通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在常识或理性的尺度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理智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称其为“荒谬”,正如柏拉图主义的传人塞尔苏斯(Celsus)对《约翰福音》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记载所作的攻击那样,这些充满着“神奇”光环的事迹在理性的视域内,是绝对荒谬的。塞尔苏斯称“道成肉身”是“恬不知耻”、不值一提的。
德尔图良相信神能够创造奇迹,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作为基督教的信徒,人要做的事就是信仰神能,也就是相信救赎。正因为上帝的伟大超出了人的想象力,所以依靠自身的理性去认识上帝才是不可能的。那些宣扬对上帝理性认知的学说,在他看来,就是真正的“异端”,完全违背了保罗传福音的初衷。因此,他认为,所谓斯多葛学派的基督教、柏拉图学派的基督教、辨证法的基督教等,都应该“统统见鬼去”。相反,正因为“道成肉身”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荒谬,所以才彰显出了神能的伟大。因为信仰不是知识或智慧的较量,而是对虔诚的考验,正如经书上所言,只有“简洁的心灵才能寻求主”。
德尔图良对“荒谬”不容置辩的虔信,使这个遭到哲学鄙弃的异物,在神学的庇护所内找到了容身之地。站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不可弥合的裂隙上,“荒谬”绽露了源初的魅力之光。它的存在昭示了一种真正的生存自由——那是成熟、去魅的精神承载物,在领悟了人性之外有着不可抵达的浩渺深邃之后,对“理性”这位训导师说“不”的自由。这份向着绝对自由不断掘进的思想荣光,后来为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路德、帕斯卡尔所继承,并最终在生存哲学的吊诡基调中获得升华。
从保罗到德尔图良,早期基督教思想中的荒谬因子活跃跳动着,它们在甫一开始就从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开出了一条有悖于必然性逻辑的特殊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荒谬虽然都是为了反抗必然性而出现的,但实际上经历了从反犹太习俗传统到反古希腊理性传统的转变,而这一转变背后的动机,却是为了实现基督教普世的共同理想。以哲学的术语来说,从保罗到德尔图良,信仰的荒谬反必然性,但却并不反同一性,他们所寻求的,正是普罗大众的共同信仰。
2.从路德到帕斯卡尔:强调个人选择性的信仰
中世纪的哲学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天下。所谓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都还只是概念、范畴内的争论。这些争论虽然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尤其在证明上帝存在的问题上,但这一切与人的生存似乎毫无关联。人依然在暗昧、混沌之中,对自身的力量知之甚少。
在这个历史时期,哲学家唯一关心的就是上帝的存在,他们力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形式是符合逻各斯的完美,但却并不关心个人的生活或者行为。人的日常生活,遵守的是教会制定的法则。而教会对人的生活制定的规划,就是通过忏悔赎罪,回到天堂。他们把上帝视为善的化身,而人类却是罪人;但人类只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诚心忏悔,恳请上帝的赦免,就能赎罪。消除罪孽,回到天堂,就是人在世生活的唯一目的。教会在个人的生存领域里,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这之中,荒谬也是不被承认的,因为一旦承认了教义里的荒谬,那种权威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改革家路德的出现,在教义的层面上又再次唤醒了荒谬,他重新提出了“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观念。顾名思义,所谓“因信称义”简单来说就是以信仰为辩护词,即以信仰作为接受审判的唯一凭据。当马丁·路德言说信仰的时候,他实际上完全地无视了那些《圣经》文本之外的哲学思辨以及道德伦理。在这个神学的布道者眼中,荒谬比理性更能接近神。因为神不会使用人的逻辑、人的语言来进行恩泽,而荒谬又恰恰是在人的理解能力之外的,它或许能够和神之间产生共同的语言。信仰的荒谬里,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中文里的这个“义”,不是指社会的公平或正义,而是指人—神关系之中的正义,也就是上帝对人的审判和裁决,决定这个人是得到恩典还是下地狱。“欲要升高之人必被降卑,而欲降卑之人必被高举,但现在上帝之义的全部精髓就在于降卑自己至深渊。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被高举,因为他首先降至深渊”*Martin Luther, “Luther Works”, Lewis W. Spits, ed., Vol.10, Saint Louis and Philadelphia, 1955.,转引自: 张仕颖: 《论马丁·路德的基督教正义观》,《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406页。在此路德所例证的与其说是人与上帝的地位的悖谬,倒不如说是上帝之义的不可思议。
在上帝与人的对置关系中,还矗立着基督。基督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他代人获罪,并以自己的肉体受死来赦免人的罪,为救赎和恩典留下了可能通道。上帝的正义是严厉的、不容置辩的,因为他要宣判人的罪;基督的正义则是慈爱的、悲天悯人的,因为他要赦免人的罪。这是多么有意思的悖论啊。如果说人是被自己的信所决定的存在,那么毫无疑问,他从一开始就处于神所设定的悖谬境遇之中: 既有罪又能被赦免;既是罪人又能成为义人。换而言之,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全都是因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而上帝的恩典,其本身是不能为人所理解的悖谬,这一点在基督的死而复活中得到了反映——先设定了人的罪,让人受到惩罚,无人可以幸免;却又给人留下恩典的希望,通过圣子的复活来象征最终的救赎。人的罪孽没有因为基督的受难而进一步地加深,相反却随着他的复活而完全地被赦免了。
牺牲自己的子嗣来救赎被自己宣判为有罪的人,这种完完全全的救赎在人类的逻辑思维中,是难以想象的。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人被设定的罪是一定的,他所获得的恩典则是可能的。救赎不是必然的,即便是虔敬的信仰,也未必能换来上帝的救赎。对人类而言,这感觉到不可思议、有悖常理的恩典,就是荒谬。既然“因信称义”的“义”是荒谬的,那么人是否还有必要去“信”呢?
在路德那里,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义是荒谬的,人无从去揣测上帝,但恩典之所以是恩典,是上帝给予某些个体的特殊福音,就在于它的不可测度。人不可能理解恩典,却能接受恩典;甚至,是那些活在绝望、痛苦之中的人,不可理喻的人、荒诞的人,比一般的常人更有可能接近恩典——“并不是那认为自己是人群中最卑微的人,而是那视自己为最丑陋之人在上帝眼里视为美善”*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che Gesamtausgabe, Bd.3, Weimar: Herman Bhlaus, 1883.,转引自: 张仕颖《马丁路德与神秘主义》,《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道德的评价不能成为恩典的依据;相反对于恩典来说,它做出选择的理由则是是否能够与上帝沟通。恩典选择那些能够听“懂”上帝话语的人,因为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上帝是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面对着上帝,唯有信仰,别无他途。
“因信称义”实际想做的,就是剥离人的日常行为中那些附着在信仰之上的污垢,将信仰回复到“唯《圣经》一个是真理”的地步。因为上帝是在理性之上的“荒谬”,所以他的“义”也是荒谬的。人只有把自己放到一个“荒谬”的位置上去,放弃世间的准则,不作智慧的思考,只凭借《圣经》的教义来实践信仰,才能得到救赎。
继德尔图良之后,马丁·路德再一次地把“神”的荒谬当成了信仰的根源。但有所不同的是,德尔图良一直试图为荒谬寻找合理化的解释,来达成和人的理解力的某种和解;马丁·路德则拒绝了这种和解的可能性,巧妙地把人—神之间的关系严格限定为契约的关系,从而避免了“神如果是善的,为何要使人陷于罪孽惩罚的折磨中;如果他不是善的,却为何要牺牲自己来救赎人类”这样尴尬问题里的逻辑陷阱。
可以说,路德对“因信称义”的强调,实际上为后来的信仰之路开辟出了新的可能性。当上帝的“义”可能是荒谬的、悖论的,人不一定从上帝那里获得恩典,那么人是否还有必要去相信呢?这个问题到了帕斯卡尔那里,就演变成了是否值得去博弈的赌博论。
帕斯卡尔是一种自由跳动的精神。当上帝的存在成为一个命题,被摆上知识精英的圆桌,任由理性主义的逻辑反复论证的时候,信仰主义只能龟缩进异端的晦暗心灵,变成了被体验的神秘启示。而那些认定自己中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背离了理性之光的指引,毅然决然地跳进内心幽眇的深渊中,听凭精神在上帝的名义下,无拘无束地做出各种“反常理”的跃动。让后来的非理性主义者感慨的,并不是帕斯卡尔对科学的怀疑精神,而是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他竟能从伟大的科学成就中探索出一条反科学的生存哲学和信仰主义的思想脉络来*威廉·巴雷特就曾在研究存在主义的专著《非理性的人》中提到,基尔克果和尼采站在哲学的圈外,从宗教和艺术的立场上审视了哲学;而帕斯卡尔呢,则走得更远,因为他是从科学的立场上出发来看哲学的(可参阅: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但帕斯卡尔的哲学,非但不具有科学的严谨和逻辑的严密,相反是反传统哲学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嘲笑哲学的,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这是非常罕见的思想个案。
对于无限的世界而言,人类的出现和诞生,并不是必然的,人也不可能是宇宙的主人;相反,他只是宇宙中最脆弱的一根苇草。从几何学精神*“几何学精神”和“敏感性精神”是帕斯卡尔对人的思维特征的区分。几何学精神依靠公理、原则和方法,能够推导出一系列的科学成就,但源初的那个公理,却是不能推导,也无法证明的,而只能依靠人为的定义(也就是语言学角度的命名)。源初定义的源泉,是人复杂而多变的内心,这是理性无从涉足的,只能靠“敏感性精神”去细腻感知。的视野来说,人的这种矛盾、怪异、混乱,就是不可理解的“奇观”;而人生存状态的无常、无聊和不安,则更是只能依靠“消遣”方能得到排解的虚无。
然而,人这般荒唐、矛盾而无序的存在物,还有思想!他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这才是荒诞真正现身的时刻。理智总是有限的,但思想是无限的。当思想的苇草漫无目的飘荡的时候,不仅会遭遇到宇宙的崇高和伟大*帕斯卡尔: 《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8页。,还将可能遇见超脱必然法则之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神奇事物。当思想和人性以外的神圣照面的时候,选择的问题就摆到了面前: 是去相信,还是不相信?
对人性怀有矛盾看法的帕斯卡尔,对神性同样不能确实。“上帝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不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灵魂和肉体同在,以及我们没有灵魂;世界是被创造的,以及它不是被创造的,等等;有原罪,以及没有原罪。”*帕斯卡尔: 《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7页。既然理性无从认识上帝,上帝的一切都在人的能力之外,那么人是否还要去信仰呢?于是,信仰就变成了一道选择题,甚或一场未知的赌博。而人的博弈对象,就是上帝。
上帝的存在与否不是一道逻辑命题,而是生存的可能境遇。在这种未知的可能性面前,任何人的遭遇都会是选择性的: 要么去信,要么不信。但不管信还是不信,选择的背后都没有必然律的支撑。徘徊在信仰门前的这种犹疑,在帕斯卡尔的眼中,和赌徒面对轮盘时的患得患失是完全一样的。由此,信仰又成了一种荒谬。
如果说德尔图良、路德们强调的是,荒谬值得被信仰,不管信仰的对象多么荒谬都要去信仰,是极端的虔诚的话;那么,帕斯卡尔则是把信仰的行为本身变成了荒谬。信仰就是荒谬的,因为信仰的对象是人所未知的,去相信可能性会变成实在,这就是赌博。
熟谙在世“消遣”之道的帕斯卡尔,曾专门深入研究过赌博的学问。在和另一位数学天才费马关于赌博输赢概率的交流中,帕斯卡尔发现过“运气”的踪迹。“运气”就是哲学上的可能性,它总是来去自由、毫无道理的;但它又确实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赌局中的每一个参与者。没有运气的成分,事物就成了百分之百的必然,赌局也就不存在了。
在人与上帝的可能关系中,选择是自由的,概率是相等的;最终影响人下注的,除了“运气”的成分以外,还有每种选择背后的赔率对意志的“引诱”。所谓赔率,也就是下注以后我能获得怎样的收益。对毫无信仰的“赌徒”来说(已经有信仰的人是不需要选择的),最终收益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下注的选择。作为冉森派的信徒,又对赌局的设计技巧了如指掌,所以,帕斯卡尔在布置关于上帝的赌局时,当然会把重要的砝码放到信仰的一边: 开始信仰以后,将有获得无尽幸福的可能性;世俗生活的快乐当然也会时时出现,但幸福的终极一定是和上帝在一起的;赌上帝存在,其实是赌获得最大幸福的可能性。这种最大的幸福也只是可能性,但它的风险却是最小的,因为即使赌输了,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既然如此,人何不放手一搏呢?
对上帝缺乏信仰的人,当然也可以设计另外的赌局,并把砝码全都扔到不信的一端,或者强调信仰以后会带来怎样的不幸后果。但打赌说的重要性显然不在于赌什么,而在于赌博的行为本身。
把信仰当成一场人生的赌博,揭示的其实是生存有着多样面孔。上帝本身,已经不是“是”或“非”的必然判断,而是绽开人生之花的一个际遇(或者用克尔凯郭尔的术语来说,是一种机缘)而已。对遇见上帝的人来说,信仰就是必然;而对没有遇见的人来说,生存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否遭遇上帝,只是一种偶然,人完全可以在上帝隐身,甚至狂暴的前提下依然选择信仰。极端境遇中的生存论言说,就常常颠覆上帝的“高大全”形象,将人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来探求生存的极境,以及极境中的信仰可能。
帕斯卡尔的打赌,再次把信仰投进了荒谬的怀抱。只不过这一次荒谬的是信仰自身。人可以把信仰变成赌博,虔诚消失了,荒谬成了信仰的修饰语;这也就意味了即使在上帝的面前,人也有了选择的可能性。这是人的意志自由对必然律教条的又一次沉痛打击。
3.克尔凯郭尔: “既是又不是”的矛盾综合体
从保罗开启的不可理喻的信仰之路,经过德尔图良、路德,到了帕斯卡尔那里的时候,信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可以被情感或意志所选择,却不能被理性或智力所判断的一种生存方式。正如信仰行为本身是一次未知的旅途,信仰的对象也早已不再是那个光辉、至善的、决定人的命运的神,而是变成了充满着矛盾与悖谬的,不为人的理智所解释的奇特性存在。但在正统的思想之中,尚未有人敢明确而清晰地喊出“上帝是荒谬”这样的口号;即便是非理性的人,他们可以相信或者怀疑上帝的存在,却不能去言说上帝是什么,因为要么上帝根本不存在,要么他存在但却并非人可以评价或判断。
将上帝和荒谬间划上关联符的人是克尔凯郭尔。几乎全部克氏的哲学思想著作,都在论说着“上帝是悖论”“信仰是荒谬的”,以及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应当如何生存的问题。可以说,克尔凯郭尔将上帝与荒谬等同起来的观点,比那些质疑上帝存在的思想更为令人震惊。因为对于某些生存个体来说,上帝可以是不存在的,这不会对他的生活或者工作产生任何的困扰或影响,反而可能令其在精神上轻松而没有负担。但承认上帝的存在,却又说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悖论,也即是说上帝是自相矛盾的存在,这无疑会给人信仰的信心及意志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那样的话,上帝就不再是真、善、美的完美化身,反倒成了会令人感到难受、不快的奇崛的怪物。一个怪物如何可能会是普罗大众共同的信仰对象呢?去相信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很有可能,人们会因为悖谬的不合情理、不可理喻而将上帝拒之门外。由此而论,悖谬才是信仰里最危险的事。
然而,克尔凯郭尔却将悖谬的信仰视为真正的信仰。在他看来,正因为上帝是令人感到不适的悖论,所以信仰才是难的,真正的信仰才是难能可贵的;在上帝是悖论的语境下,“谁不对基督教感到不快,谁就是幸福的”*克尔凯郭尔: 《基督徒的激情》,鲁路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80页。。显然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信仰作为人生诸多道路中的一条,作为人生诸多选择中的一个,是最为艰辛而不易的。或许正因为此,克氏才把信仰置于人生道路三阶段中最高的阶段,而且只是寥寥无几的少数人凭借着意志方能通达的。
其实对于上帝本身而言,是无所谓荒谬与否的;因为信仰中的上帝是外在的超越者,他并不在人的语言逻辑之中。因此说上帝是悖论,这更多地只是出于人的主观判断,而和上帝本身无关。“悖论”并非上帝的性质或特征,而是人的语言方式在表征上帝的过程中因不能完全抵达对上帝的理解而产生出的意义消歧。换而言之,真正悖论的是人的语言,它在表征上帝的过程中不能言尽其意,无法将外在的超越者彻底包容在内,因此才会产生了自相矛盾、既是又不是的局面。更进一步地,语言作为人的主观精神的折射,它的歧义反映的是精神世界的分歧、矛盾与冲突。
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悖论,其本质的特征就在于承认思维中“或此或彼”、既是又不是的二元对立。在同一哲学的视野中,二元并置是一种错谬,因为人的精神不可能一分为二,因为人是一个单个的实体,它的本质属性只有一个。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同一的哲学,他试图通过辩证法来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并最终达到和谐的绝对精神。而克尔凯郭尔的二元论,正是与黑格尔的思想针锋相对的。他认为现实世界的矛盾,以及逻辑上的悖谬并没有因为辩证法而被克服掉,人的精神是芜杂而多变的,矛盾双方并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真理,以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相反,精神的活动因着主观的自由而充满着各种的可能性,它是根据现实世界而瞬息多变的。那被设定为理性的辩证法的精神,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概念的精神,它无法顺应生存状况的复杂,更无法对生存的实际做出任何的行动。行动必须依照现实的状况来做出,而现实恰恰是不可预测的,充满着未知的可能性。正是在可能性的意义上,克尔凯郭尔的悖论彰显其之于生存的深刻意义——生活尽管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但它却并不是已经被决定了的定论;生存于其内的个体完全能依据自身的状况而做出各种可能的选择。甚至,从突破了思维和逻辑的局限的角度来理解悖论,悖论就是一种精神的奇迹*克尔凯郭尔: 《哲学片断》,王齐译,《克尔凯郭尔文集4》,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对上帝的信仰,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其实信仰的正是那未知的可能性。因为神能的无所不能,故而上帝就是象征着充满了“奇迹”可能性的未来。信仰上帝,信仰作为悖论的上帝,实际上就是去相信精神里的可能奇迹,这种奇迹在必然性之外,也在人理性理解能力之外。它必然不是人的创造物,而只能是属于未知的神性的。
可以说,信仰的荒谬到了克尔凯郭尔这里,已经变成了生存的可能境况,它所彰显的,也不再是神对于人的绝对压倒性权威,不再是人的渺小与神的伟大之间的震撼性对比,而是人的主观意志对于自我命运的决定权。信仰与否完全可以凭主体自己来选择,选择了信仰上帝,也就是选择了可能性,选择了突破各种桎梏的大胆尝试。对生存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