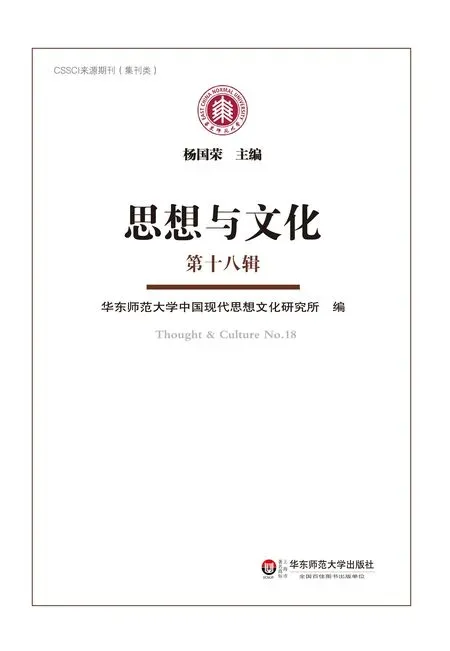论“淡”
——从道家出发
2016-04-12贡华南
余莲(通常译为“于连”)以“淡”来刻画中国思想与中国美学*余莲将“淡”视作中国文化的精髓,认为“淡”是纵贯儒道,横贯中国思想与艺术者(包括绘画、音乐、诗文等),同时又是人格之最高气象,交往之最理想的原则(参见余莲: 《淡之颂》,卓立译,台北: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夏可君承袭余莲这个观念,并在《平淡的哲学》(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对此观念作了大幅发挥。,由此使“淡”这种味觉性范畴进入现在哲学的视野。如我们所知,中医药“四性(气)五味”说中,“四性(气)”为寒、凉、温、热,而称寒热偏性不明显的为“平”。“五味”为辛、酸、甘、苦、咸,而称不明显的味为“淡”。“四性(气)”与“五味”相通*“性味”在中医药中一直被当作药物的基本(甚至唯一)性质。传统医学中“气味”一词与“性味”意义大致相同。李时珍曰: “寇氏言寒、热、温、凉是性,香、臭、腥、臊是气,其说与《礼记》文合。但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难改易,姑从旧尔。”(李时珍: 《本草纲目》序例第一卷上)“气味”既包括性,也包括味。单说味,则即包含了气(性)与味。明医家缪希雍注意到: “炎黄言味而不加气性者何也?盖古文尚简,故只言味。物有味,必有气,有气斯有性,自然之道也。气味生成,原本乎是。”(缪希雍: 《神农本草经疏》,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有味则有气,有气则有性,言味即是言气言性也。,“平”与“淡”通,都是描述与规定万物性质的基本范畴。从先秦始,“淡”由事物之“滋味”转义,被广泛而自觉地用来描述与规定思想品格。尤其是道家,推崇“淡”,欣赏“淡”,将“淡”作为高明的精神境界,以致“淡”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标志。但将“淡”视为中国思想之基本特征,显然不合乎中国思想之实情。与儒家占据中国思想主流一致,“温”一直构成了中国思想的基调。美学方面,“温柔敦厚”之“诗教”一直占据着中国美学的主流。所以,我们可以用“淡”来概括道家的精神基调与气度,但不能把“淡”当作中国思想的概括。确切地说,儒家以“温”(“温柔敦厚”)为其基本品格*可参看贡华南: 《从“温”看儒者的精神基调与气度》,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道家以“淡”为其思想基调,佛家以“凉”为其基调。据此,我们可以“温”来说儒家,其人其思皆然;以“凉”来说佛家,以“淡”(不温不凉)说道家。看(听)儒家思想,看(听)着看(听)着就温暖起来,甚至热起来;看(听)佛家的思想,看(听)着看(听)着就凉下来;看(听)道家的思想,看(听)着看(听)就淡然起来。其人其思,无温,何以叫儒?不凉,何以入佛?远离淡,何以称道?世态炎凉,儒释道各适其用。温、淡、凉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之味觉中心主义特征。
一、 淡乎其无味
“淡”在《老子》中出现2次,其中一处以合成词“恬淡”出现。二者含义一致,都与“道”内在相关。
《老子》第三十五章: “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淡”首先是一种可出入于口的“味”*如河上公注曰: “道出入于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咸甘苦辛也。”(《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 中华书局,1993年,第139页)。,它不像“五味”那样对人有明显的刺激,而表现为对人无刺激,或刺激几乎为无的“味”。“乐”以美声打动人,“饵”以美味打动人。“止”不是“留步”,而是指停留并聚集于此,不再他往。美声美味打动人的感官,移易人并能聚集人。“道”与乐、饵完全不同,道无声、无形色,它不能打动人的耳目,故不能令过客停留于此。道虽无形、无声,但却可以为人所领会,并通过人的“口”(“言”)而呈现,作用于人。因此,“淡”虽“无味”,但仍然是一个味觉概念,是与乐、饵那种令客止等强烈刺激完全不同的味。“出口”(或“出言”)而无味,即“无味之味”。六十三章说“味无味”,表达的就是以玩味、体味的方式领会、把握“无味之味”。“淡”即“无味”*王弼注曰: “以恬淡为味。”(《老子注》第六十三章)即以“无味”为“恬淡”。,“无味”即“淡”。“淡”由“道”出,与“道”内在相关联,通过“淡”,我们可以更真切领会“道”。
“无味”与“淡”实质为一,即都被用来领会道之异于乐、饵的特殊品格。但二者的实际使用效果却有差异。“无味”与无形、无名一样,表明不能用对待有限的、具体物的方式领会道。道之“无”不是逻辑上无任何规定意义上的“无”,也不是断灭意义上枯死之“无”,而是根柢大道,能生“有”,生“万物”之“无”。不过,粘滞于“无味”之“无”却有将道带入无任何规定意义上的“无”,或断灭意义上枯死之“无”等歧途之危险。从“无味”返回“淡”至为重要。从“淡”来领会道,也能够避免误入歧途的风险。“淡”是“有”,确切说是非现成的“有”。“味”总是在人与对象相互接触、碰撞时呈现,作为“味”的“淡”亦是如此。“淡”在道与人、万物零距离接触时呈现。道与人零距离而相互作用,道以恍惚寂寥、平夷柔弱的方式不断触及人的身心,不断创生、护持人、物的素朴之性。不断生成的“淡”表明,“道”不曾离开过人,不曾离开过这个世界,她一直且总是在。
如果说三十五章的“淡”还粘连着具体的“滋味”,那么,“恬淡”一词则已经转义表达着修道者的精神品味。“恬淡”一词出于《老子》第三十一章: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恬淡”,帛书本作“铦庞”,或解为“锐利坚实”*张松如: 《老子说解》,济南: 齐鲁书社,1998年,第182页;徐志钧: 《老子帛书校注》,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非是。或认作“铦袭”,解为“恬淡”*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6年,第390页。。这与王弼以来诸传本一致,含义也能够与《老子》主旨相贯通,较可取。“恬,安也。”(《说文解字》)“恬,静也。”(《方言》)“恬淡”的意思是,安静自持,不热衷于兵争之事。河上公解“恬淡”注重其实质内容,所谓“不贪土地,不利人财货”。*《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 中华书局,1993年,第126页。释德清的解说类似: “恬淡者,言其心和平,不以功利为美,而厌饱之意。”(释德清: 《道德经解》,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页。)吴澄则注重其意向: “‘恬’者不欢愉,‘淡’者不浓厚,谓非其心所喜好也。”*吴澄: 《道德真经吴澄注》,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页。近世学者高亨以公私态度解之: “恬,指内心没有私愤。淡,指内心没有贪欲。”*高亨: 《老子注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这些解释都注意到“恬淡”乃修道者应有的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也就是“道”所主导下的在世态度。在这里,“淡”已经由事物之滋味转变为一种精神态度、精神之品味。“兵”是修道者所面对的万千事物之一种,因为其乃“争”之具,故更能体现修道者的真实态度。“争”的实质是屈人就己、扬己抑人,“兵”助“争”而让自己的意志、目的、欲望得以实现。相应,“恬淡”所展示的即是“不争”之态度,即抑制、退隐自己的意志、目的、欲望,安于自身素朴之性,不屈人就己,不扬己抑人。不凸显自身,不与人争,自在自足,“恬淡”展示的不仅是在世态度,更是修道者一贯的在世姿态。显然,《老子》所尊崇的“恬淡”深深扎根于“道”,从大道中获得了丰富而深沉的精神义蕴。
作为一种“滋味”,“淡”不刺激人的感官的味,或为味之缺失,也就是“无味”。因此,“淡”与“五味”相对。在中国文化中,“五味”咸为首,“淡”与“五味”对,就转而与“咸”对,“淡”即“咸”之不足,为“不咸”或“无咸”。“咸”的基本特征就是刺激身与心,无味之“淡”相应指对身与心无刺激者。不刺激人的身心,对身心不损不益,也就是,不移易人的身心。“淡”由“道”出,为“道”的基本品格,由此使其越出众味之上。修道者修此“道”之“淡”的品格为自身之德,“淡”即成为人的品性、态度,此即“恬淡”之“淡”。“淡”一方面表明淡者自觉退隐自身、不凸显自身,不会引起他者注意;另一方面,表明淡者对控制人、占有物也不起兴趣。作为由道主导、规定的在世态度与在世姿态,“淡”与道的谱系中的诸德内在贯通。比如,“淡”与“慈”“俭”“啬”内在一致,它不是超然物外、无动于衷的冷淡、冷漠,也不是无端的敌意与冷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刍狗”为祭祀之物,其特性有二: 祭祀时为神圣之物,人对其态度为“敬”;祭祀结束,则失去效用而为人所弃,实即“不用”。相应,“不仁”就包含这两层意思: 爱(敬)而不用,而非冷酷或无情。。“淡”中包含尊重、怜惜、不扰等含义,“淡者”柔弱、平夷,故能救人、救物。因此,“淡”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而是不造作。淡之人依道而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那么,对“淡”者而言,世间有“有余”则损之,有“不足”则补之。“淡”者不以己意施加于他人、他物。对于被增益者,则可以损之又损。当然,“淡”与诸德之间一直以隐蔽的、迂回的方式深深勾连,对它们之间勾连明晰的表露尚待开启。
二、 游心于淡
《庄子》继承《老子》“淡”的思想,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度的引申与发挥,将其提升为道家的基本观念与核心价值。在《内篇》中,《庄子》有一处谈及“淡”: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这里的“淡”已经不是“滋味”意义上的“无味”,而是指一种精神品质与精神境界。“游”的意思是不为一时一地、一事一物所限,从容地展开,“游心”指心灵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事一物,自由自在地展开自身,“游心于淡”就是心在“淡”之场域自由自在地展开。“淡”之于“心游”,为基调与场域,更为前提与保障。即是说,唯有“淡”,才能真正保障“心”不受时、地、事、物的限制,才能保证“心”顺畅无阻地“游”。具体说,“淡”可打破“心”的“自我”中心倾向,以及由此造成的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对立与系累。比如,追求效率、功利、欲望,以控制物,满足一己之欲。以“淡”来给“心”定基调,主导“心”的活动,或者说,心就在“淡”之境展开。“合气于漠”之“漠”同于“淡”,指“不着意”“不造作”。“气”既指形体,也指心理、精神。“合气”指生命保持完整存在状态,不分化、不散开。“游心于淡,合气于漠”,整个生命就在淡漠之境展开。人以淡在,以淡显现,对人淡淡,对物淡淡。这里,《庄子》虽从“治天下”角度谈“淡”,但以“心”之“淡”与“气”之“漠”来去私、顺自然,已然使“淡”具有了超出治理而具有更一般的存在义蕴。
作为一种在世态度,“淡”对人对物首先表现为不过度施予各种情绪,特别是不会依据自己好恶待人待物*《大宗师》描述得道者情绪之发: “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情绪与天地四时相通,即出于天归于天,而非出于人归于人。。如《老子》所示,“淡”不是“无所谓”,更不是冷漠。道无弃人、无弃物,以淡在世的人亦无弃人、无弃物。淡者尊重、爱惜万物的素朴之性而舍不得利用、干扰之。与《老子》一致,《庄子》亦推崇“恬”,比如主张“以恬养知”“以知养恬”“知恬交相养”(《庄子·缮性》)“恬”被当作修道者主导的情感态度: 也就是自安于己,无待于外。具体说就是,既知己守己,不施加于人,不施加于物,不损人,不损物,不益人,不益物。同时知人、知物之道,尊重(顺)人物之道,又不为人、物所益,不为人、物所损。故在《庄子》中,多以“恬淡”合用。
《庄子·天道》进一步将“淡”置入“天”“地”“万物”及“天下”构成的宏大视域之下进行了深度论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圣道”承顺“天道”“帝道”,万物无足以铙其心而静。“鉴”“镜”乃是圣人之静心,天地万物随静心而呈现。圣人心静,由此开显出天地万物之自然真性,也开创出天地万物与人的崭新交往境界。“静心”本身并非僵死,经过天道、帝道、圣道之充实、扩展、升华,它遂显露出“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多重复调,尽显堂阔宇深。“淡”“恬淡”被编织进“虚静”“寂漠”“无为”等道家核心观念群中,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内涵: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平”为“准态”*马叙伦认为,今本“天地之平”的“平”是“本”之误: “案‘平’《刻意》篇作‘本’,今本误作‘平’,当从之。下文‘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是其证。‘平’‘本’形声相近而讹。”(严灵峰编辑,无求备斋《老庄列三子集成补编》(三七),《庄子义证》,台湾: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第380页)此说为陈鼓应等学者接受,影响较大。“平”与“淡”意思接近,魏晋合为“平淡”一词,被理解为“道”之重要特征。显然,马叙伦没有领会“平”之妙义。,“天地之平”就是天地之“准则”。圣人之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可以呈现天地之准态,或者说,可以让天地呈现出准态。那么,四者如何呈现出天地之准态呢?“虚”即自觉地排除自我,自觉远离“满”“实”“坚”“强”而持有的心灵状态。“静”是“归根”,即自觉皈依、返回大道。“虚静”是虚化自我而归于大道。“恬”是不欢愉亦不沮丧,“淡”是不浓厚亦不浇薄,“恬淡”是无心自若。“虚静”为根,“恬淡”为“用”。“寂”是“无音声”,“漠”是“无形体”。“寂漠”是自我完全的隐退,“无为”则是无自我而以道展开自身。成玄英疏曰: “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四者异名同实者也。”四者其义虽有差,但同时又内在相互贯通,故成玄英说四者异名同实。人能“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则能够自觉依道而思,循道而行,实现、完成真正的道德(道德之至)。不扰天地之运行,不失天地之生机,故可为“天地之平”。
在这个大道主导的语义丛中,“恬淡”与“虚静”“寂漠”“无为”内在贯通,其侧重的是与人、物相交接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可感姿态,但“虚静”“寂漠”“无为”却让其获得了深沉的品格。“恬淡”者“虚静”,也就是能够自觉排除自我而皈依道;“恬淡”者“寂漠”,也就是自身在他人他物那里不会引起任何注意;“恬淡”者“无为”,也就是能够不以自己的意志、目的、欲望施加于他人他物,不屈他人他物就己,不取物归己。“恬淡”者自己既“实”且“得”,于他人他物则可“任其责”。自己素朴本性能够得到完整保存与自然展开,他人他物之素朴本性也能够得到完整保存与自然展开。恬淡者有此境界与姿态,无论身处哪个位置,都能够与人、与物和。己朴素、人朴素、物朴素,各个皆美,各守其美而无所争,此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基于此,“恬淡”与“虚静”“寂漠”“无为”一起被推崇“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万物之本”。将“恬淡”理解为“道德之至”,这不难理解: “恬淡”作为“道”的具体呈现,不仅标志着道显现于人,也因人向道而生、依道而在,而使天地万物的素朴本性得以完整保存与顺畅展开*天地万物在其展开过程中都不会偏离其自然本性,人有“我”、有“私”,不仅自己会偏离人之自然,而且会将自己的意志、目的、欲望施加于天地万物,损益天地万物,使天地万物偏离自己的自然本性。人能去“我”、去“私”而恬淡无为,自觉收回自己的意志、目的、欲望,则天地万物亦无失去自然之虞。。人之“恬淡”担保了天地万物之素朴,在此意义上,“恬淡”不仅成为道德之极致(“至”)与道德之实质(“质”),也能够成为“天地之平”与“万物之本”。
与天地万物相交“淡”,与人相交也“淡”。“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淡”“甘”是交往、交接的原则与姿态。“甘”指态度上亲近,甚至枉道而屈己就人、抑己扬人,其实质是给他人“名”“利”。相应,“淡”在态度上表现为自觉地收敛自身、与他人他物保持一定距离,依道而不扬己抑人、不扬人抑己,其实质是远离“名”“利”,淡泊“名”“利”。无“利”,故不能快捷地打动人,吸引人,不能使人亲近。但是,以“利”使人相亲相合却往往陷入利害关系而彼此以“利”决绝,即所谓“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淡然远“利”而相交,却可以彼此不扰、不损、不益,由此彼此不弃不离,即所谓“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在儒家经典《礼记》中也有类似表述: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礼记·表记》)儒家之“淡”由“仁道”所规定,“淡然相接”之内涵为依照仁义原则与人相交接;道家所说的“淡”由“自然之道”所规定,“淡然相交”之内涵为依道而交。二者之归旨显然不同,但二者亦有一致之处,即都表现出对“利”的淡化与超越。。
《刻意》对“淡”“恬淡”也有类似集中而深入的论说: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惔矣。平易恬惔,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虚无恬惔,乃合天德。”“淡然”是自我退隐而不着意于所对、所为,即“无不忘”。“无极”即超越极限、没有极限,“淡然无极”即下文所谓“淡之至”。“众美从之”即众美随着人之“淡然无极”而涌现,此即“无不有”。此“有”非人所有,而是万物万美自有。淡然对天,不与天斗;淡然对物,不屈物,亦不为物屈;淡然与人交,不扬己抑人,不屈己就人,如此,便能“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淡者”能对一切身心之困扰免疫,比如“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淡者”德全而神不亏,因此,“淡者”并非缺失,而是完整且充实。
一人淡固好,人人能淡,则天下真能常自然矣。在《缮性》中,《庄子》带着诗意刻画了人人能淡的世界图景: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淡漠”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自觉散发的“精神”,也就是道的自觉显现。“淡漠者”不凸显自身,不以己加于物,不与物争,由此,“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天地万物之自然得以保障。
可以发现,欣赏淡、推崇淡构成《庄子》的基本立场,而守住淡、修淡养淡、成就淡,成为《庄子》基本课题。淡之德,有诸己而形诸外,接人待物淡淡。“淡”构成了得道者真实可感的存在,也是真实存在的直接显现,俨然成为道家思想的鲜明图标。
三、 平淡
《庄子》已经将“淡”由具体的“滋味”直接提升为一种可感的精神品质,其他学派对“淡”亦时有精彩论述。比如在《管子·水地》中,“淡”已经由与“五味”并列之“味”上升为高于“五味”者: “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管子·水地》)“诸生之淡”即“诸生之中”。在这里,“淡”首先被规定为“五味”之“中”,也就是“五味”的标准(“宗”)或基础(“质”)。“淡”已经被提升为比“五味”高一级的概念,《管子》以“淡”通“中”,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淡”被提升为“五味”之根本,这似乎表明《管子·水地》与老庄思想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有些学者将《管子·水地》认作“稷下道家”的著作,也注意到了这层关系。可参见陈鼓应: 《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年。。
儒家亦关注“淡”,不过,他们依然执著于将“淡”作为诸味之一种。比如: “君子之道: 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中庸》)“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荀子·正名》)与“不厌”相对的“淡”,指的是滋味之“清淡”*对此句古注有: “淡,其味似薄也。”(郑玄注、孔颖达正义: 《礼记正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45页)另外在注解“君子淡以成”: “淡,无酸酢少味也。”(《礼记正义》第2092页)今人王文锦译解为: “君子之道,清淡而令人不厌。”(王文锦: 《礼记译解》,北京: 中华书局,2001年,第799页)“味薄”“清淡”皆指滋味之量之少,更多是喻指,而不像《庄子》将其明晰确立为精神品格。。荀子明确把“淡”当作一“味”: “淡”乃是与甘、苦、咸、辛、酸、奇等“味”并列的一种“味”,而不像《庄子》把“淡”当作精神之味。在秦汉之际成书的《素问》中,“淡”与“五味”相对,如: “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淡”与“咸”对,指“不咸”,即“味”之薄者,少味者。而在《素问·九针论》中,“淡”依然被当作诸味之一种: “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味。”“淡”与“酸”“辛”“苦”并列,分别对应于不同脏腑,“淡”就是“淡味”。
将“淡”拔高于诸味的趋势在汉代得以延续,比如“大味必淡”(《汉书·扬雄传》)。“虚而能满,淡而有味,被褐怀玉者”(《淮南子·缪称训》)。《淮南子》将“淡”作为最重要的一“味”来追求,这似乎是汉人的共识。“淡”之所以被当作“大味”,无疑与时人对大道品格的理解有关。比如,《淮南子》明确以“恬淡”作为得道之态: “今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拊而毛修之哉!”(《淮南子·泰族训》)“静漠恬淡”乃得道心神之安宁自足之态。内在心神恬淡,即能保障身体机能良善(邪气无所留滞)与四肢九窍百脉正常运行。不同于《庄子》把“恬淡”规定为“精神”层面的品格,《淮南子》对“恬淡”的理解明显停留在与身体同层面的“心理”。正是将“恬淡”置于“心理”层面,不难理解,《淮南子》明确反对以“恬淡”为“本”*如: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淮南子·要略》)而坚持以“道”为“本”,这与《庄子》将“恬淡”作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拔高“淡”的观念在魏晋得到呼应与强化。刘邵说“淡”依然与“咸”相对,指“淡味”,比如“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淡而不,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人物志·体别》)但他却首次将“四性五味”中的作为“性”的“平”*“平”义为中准、无偏颇之性。《素问·六节藏象论》: “帝曰: 平气何如?岐伯曰,无过者也。”“平”即无过、无不及。具体到“四性五味说”,“平”即不温不凉、不寒不热。与作为“味”的“淡”合用,即以“平淡”概念讨论精神品格。与《管子》以“淡”说“中”思路一致,刘邵将“中和”与“平淡”贯通,所谓“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人物志·九征》)“平淡”首要的特征是“无味”,尽管刘邵还没有把“无”明确拔高,但“无味”显然已经与“五味”拉开了距离,而且明显高于“五味”。作为“中和之质”的显现,“平淡无味”高于“众材”,即高于具体的要素,因此能够“调成五材”,就是能够居高临下地主导、安排众材。所谓“主德者,聪明平淡,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人物志·流业》)。“与一材同好”即与具体的某个品格处于同等序列,其结果是失去“众材”。高于众材、“平淡无味”之“道”才能“达众材”。不难发现,刘邵将“平淡”理解为“道”的品格,而其“道”既与儒家的“中和”相关,也与道家的“无味”相通。在《人物志·材理》中,刘邵曰: “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道理”高于“事理”“情理”“义礼”,能通自然的“平淡”成为最高的品格。就视“平淡”为最高的气质而言,刘邵的观点无疑接近老庄了。
四、 “不温不凉”之“淡”
如我们所知,在中医药理论中中,“平”被规定为寒、热、温、凉之外的一种“性”,即不热、不寒、不温、不凉之性;“淡”被规定为咸、甘、苦、辛、酸之外的一种“味”,即无味之味。在中医药理论中,不热、不寒、不温、不凉之平性是与寒、热、温、凉并列的性;无味之味的淡乃是与五味并列的一味。刘邵把“平淡”与“道”直接勾连,拔高了“平淡”的地位,王弼则将“然”自觉升腾至“所以然”,并以此角度讨论“五味”“温”“凉”“淡”问题。他在诠释《论语》“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时曰: “温者不厉,厉者不温。……至和之调,五味不形;大成之乐,五声不分;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论语释疑》)这里,王弼以“至和之调,五味不形”来解释“温而厉,威而不猛”之完满精神境界,其所注重的是二者形式上的相似性,即二者乃中和之德而不偏于一端。“五味不形”是说“至和之调”不咸、不酸、不辛、不苦、不甘,这也就是《老子注》所表达的“(不炎)不寒,不温不凉”(《老子注》第十六章)。换言之,在王弼的解释系统中,“温而厉”等同于“不温不凉”: 它们都属于“所以然”层次,而高于温、凉、热、寒的层次——“然”。如,王弼明确将二者确立为二个层次: “大象,天象之母也,(不炎)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主若执之,则天下往也。”(《老子注》第三十五章)“大象”即“道”,描述“大象”的“(不炎)不寒,不温不凉”,并非指与寒、热、温、凉平行的一种“性”,而是说,道乃一整全者。整全者与某一性不是同一序列,前者为高一层次者——“所以然”,后者为“然”。也就是说,寒、热、温、凉等性乃“然”,大象或道则指“所以然”,即“故”(根据)。王弼所说的“包统万物”是就“所以然”而言。在《老子指略》中,王弼细致地区分了“然”与“所以然”之间的关系*如: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克,乃反其名。……安者实安,而曰非安之所安;存者实存,而曰非存之所存;侯王实尊,而曰非尊之所为;天地实大,而曰非大之所能;圣功实存,而曰绝圣之所立;仁德实著,而曰弃仁之所存。故使见形而不及道者,莫不忿其言焉。”(《老子指略》)“实安”与“安之所安”“实存”与“存之所存”“实尊”与“尊之所为”“实大”与“大之所能”“实著”与“之所存”,等等,皆是“然”与“所以然”关系。。作为“然”,有形必有分,有分者乃确定的、有界限者,所谓“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作为“之所以”的“道”无名无形、无分无属,故“不温不凉,不宫不商”,方能为万物之宗。
道与形反,“温凉”为实实在在的“形”,“不温不凉”为“之所以形”,为“体”*王弼所说的“体”乃作为“故”(所以然)的“体”,如“形虽大,不能累其体”(《老子注》第四章)。“体尽于形,故不欲也”(《老子注》第三十九章)。。王弼将“不温不凉”升为“本”,将“温凉”降为“末”。将“温凉”理解为“体”(根据)之“形”(现象),将“不温不凉”规定为“体”(根据)。“不温不凉”虽必通过温凉而得以畅达,但执著于温凉则失其本,遗其母。王弼对待“本”与“末”的态度非常鲜明,那就是“崇本息末”。真正的“本”是作为“所以然”的“自然”*《老子注》第二十五章: “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词也。”“道”*《老子注》第二十五章: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自然已足,为则败也。”(《老子注》第二章)“崇本”就是崇自然、崇道: “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注》第二十九章)于自然,因之、顺之是最好的态度。“因”“顺”也就是“无为”。人无为,则万物各依其理而自化,由理而在,无不自然。“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老子注》第五章)“自然”在价值上自足,在现实性上内在和谐,一切的“人为”都意味着败坏“自然”。“崇本”即“无为”,即顺应万物自然之道,见之于言与行,即为“淡”。“道之出言,淡然无味,……若无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穷极也。”(王弼: 《老子注》第三十五章)“淡言”呈现的是完整的自然之道、自然之性。“无所中然”即不能中(满足)过客之耳目,但“淡”言却可以护持自然之道、自然之性的完整性,因此其用不可穷极。“淡然无味”在此表述“道言”自身没有陷入含义、边界的确定性、有限性之中,故而不能吸引过客之注意力,娱乐过客之耳目。另则,道言自为自足,不为他者改变自身。于“末”,王弼以“息(末)”“忘(象)”的方式对之,此亦为“淡然无味”之一种表现。“息(末)”“忘(象)”意味着不着意于,甚至自觉略过现实事物及一切实存,包括圣、智、仁、义等。“夫圣智,才之杰也;仁义,行之大者也;巧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兴此三美,害犹如之,况术之有利,斯以忽素朴乎!”(《老子指略》)“圣智”“仁义”为“末”,“素朴”为“本”,有“本”则“末”美,无“本”则“末”为“害”。对“本”“末”有“崇”有“息”,此正是王弼思想中“淡然无味”之真实蕴含。不过,王弼沟通“温而厉”与“不温不凉”,实质上是以“不温不凉”遮蔽了“温而厉”。王弼的这个立场与《论语》《中庸》《春秋繁露》及朱熹所秉持的将“温”视作儒者在世基调之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楼宇烈: “‘温’有‘善’、‘柔’、‘厚’等义。……‘凉’有‘不善’、‘刚’、‘薄’等义。”(楼宇烈: 《王弼集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第38页)王弼之“不温不凉”实际上超越了善与不善,因为,“善之所以然”与“不善之所以然”无分别,也就是说,在“所以然”层面上,善与不善之分际不复存在。。
作为所以然的“淡”乃诸味的根据,它以“无”为特征,我们不能直接把握,就此而言,“淡”无疑失去其可感特征。在王弼思想中,唯有通过努力返归虚无,努力与道同体,逐步“体无”“体道”(《老子注》第十六章),我们自身能够恬淡,也才能把握“淡然无味”之“道”。
王弼将“淡”上升为“所以然”的“体”,主要侧重“道”的超验特征。郭象对“淡”的论说依托《庄子》,与《庄子》一样侧重从人格形态思考“淡”,或者说,“淡”主要表现为修道者的在世态度与姿态。如:
“遗身而自得,虽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郭象《庄子注·逍遥游注》)
“苟知性命之固当,则虽死生穷达,千变万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庄子注·德充符注》)
“其任性而无所饰焉则淡矣。”(《庄子注·应帝王注》)
“虽波流九变,治乱纷如,居其极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为也。”(《庄子注·应帝王注》)
“无利故淡,道合故亲。”(《庄子注·山木注》)
“淡然无欲,乐足于所遇,不以侈靡为贵,而以道德为荣。”(《庄子注·则阳注》)
“淡”的特征由“不待”“忘”“任性而无所饰”“无利”“无欲”等刻画,表现为一精神境界,即自得、自足、自若之态。表面上看,郭象所说的“淡然”与《庄子》所追求的“淡”似乎一致,都在试图消解意志、欲望构成的自我(无欲),消解自我与他人、他物之对待关系,而使得自己的自然之性自得自化。不过,郭象改造了老庄的“自然”概念,而将“人为”充实进“自然”,他说: “知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庄子·大宗师》注)人之自为是自然,人与万物交往,顺物之性而为,对物来说也是自然。也就是说,人之所为也构成了万物之自然。他说: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驱步失节,则天理灭矣。”(《庄子·秋水》注)“走作过分,驱步失节”不能与物冥合,虽是人为,却非物之自然。人为而能“与物冥而循大变”即为物之自然,像“牛马不辞穿落者”也不违牛马之自然。以“人为”为“自然”,“淡然”也就仅仅成为心的境界。基于此,郭象始终强调“无心”: “至人无心而应物,唯变所适。”(《外物》注)“神人者,无心而顺物者也。”(《人间世》注)“夫无心而任化乃群圣之所游处。”(《人间世》注)“无心”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无意识”,或“无自觉意识”。“无心”与“有心”相对,二者被认为是“淡”与“不淡”的标准,有为而无心亦是“淡”。以此为前提,似乎只要无心于此,就可“淡然自若”。这样,一方面先秦道家所推崇的“慈”“啬”“无为”等精神在此观念下被遗弃;另一方面,先秦道家所追求的“无为”“无事”“无味”乃高度自觉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有心而为者”。高扬“无心”精神,也就将这些自觉的精神统统弱化,继而被“无心”遮蔽。枉道而屈人就己、取物归己,也就逐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就此而言,郭象所谓的“淡然”实则已经远远背离老庄以“淡”救人救物的态度与立场了。
余论
魏晋之后士人颇喜“淡”的格调,后人往往以道家或隐士*道家与隐士的区别是: 道家以大慈之心对天地万物,善救人无弃人,善救物无弃物;隐士欲洁一身而避物避人,成小伦而乱大伦。情怀目之。陶渊明隐居而嗜酒,其隐为洁身而非为救人救物。“悠然见南山”之平淡乃以“心远地自偏”为其精神准备,这表明,陶氏之“淡”更接近郭象“无心”之“淡”。在唐宋诗论中备受追捧的“淡”或“平淡”大体亦在此彀中。比如,司空图喜爱“淡”,自觉追求“淡”的艺术作品境界。他论王右丞、韦苏州曰“澄淡精致,格在其中”(《与李生论诗书》)。在《二十四诗品》中,司空图多次以“淡”论诗,同时也自觉构建了“冲淡”之境界: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冲淡者”自身独立而不改(“饮之太和,独鹤与飞”),以“素”“默”“微”在世,不凸显自身而自觉退隐。于人于物,“冲淡者”都若有还无,可遇可即,轻轻拂过最浅的外层(“遇之匪深”“犹之惠风,荏苒在衣”)而不会触动一丝真身(“即之愈希”“握手已违”)。“淡者”将自身深深扎根于宇宙本根处(“饮之太和”),其将生机自觉含摄、遮隐(“默”“微”“希”),不凸显自身,不走出自身,故自身总是生生不已(“独鹤与飞”)*如《绮丽》: “浓尽必枯,淡者屡深”,“清奇”: “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屡深”“不可收”表达的都是对“淡”的力量的揭示。。在《典雅》品中,司空图尝试以具象表达“淡”,如“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菊”在群花烂漫的春夏如百草一般安静地生长,在果实累累的深秋静静地开放,不争艳、不屈俗。“菊”之象所揭示的即是“淡”之“素”“默”“微”“希”等具体内涵。在《二十四诗品》中,司空图对与“淡”类似的品格(如“素”“清”等)也表达了欣赏与期待。总体上看,司空图对“淡”的刻画形象且鲜明,其对“淡”的根基、特征及“淡”自身的穿透力的领悟自信且深刻。不过,司空图对“淡”的理解与规定似乎并未逸出郭象之思域。
在宋明人的观念中,“淡”同样被认作极其重要的精神品质。周敦颐以“淡”论“乐”,将之视为“乐”的两大特质之一: “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淡者,理之发;和者,理之为。先淡后和,亦主静之意也。”(《通书·乐上》)有意思的是,周氏以“理”释“淡”,将其视为“理之发”。“淡”基本特征是不妖淫,其功能为“欲心平”。陆象山将“淡”与私欲对立,所谓“淡味长,有滋味便是欲”(《象山语录》下)。“淡”同样被理解为“理”之境。苏轼以“淡”论文,其曾有书与其侄云: “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此语出自宋人周紫竹《竹坡诗话》,明人董其昌在其著作中所记与此语有些微出入: “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董其昌: 《画旨》,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平淡”乃绚烂老熟之上的格调。董其昌在谈到诗文书画创作时,将“淡”与“工”对比。他说: “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董其昌: 《画旨》,第149页。董其昌论画之“南北宗”说,以“淡”标示“南宗”: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画旨》第37页)董氏推崇倪云林,多以“淡”赞之: “古淡天然,米颠后一人而已。”(《画旨》,第52页)“以天真幽淡为宗,要今所谓渐老渐熟者……自成一家,以简淡为之。”(《画旨》,第116页)“淡胜工”,“工”即规规矩矩,或依据规矩而为;“淡”则是工夫熟练到家,眼心手合,规矩被磨平,自由创作而自然合于规矩。“淡”因此被认为是诗文书画最高的境界。
诚然,文如其人,作品的“淡”源于创作者的“淡”,她首先显示为一种对人情、事物的态度: 保持距离,无意于亲近,无心施加或减损。进一步说,“淡”乃是对名利、俗情的自觉规避、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格调之“淡”表达出作者无意于聚集物、人,当然也包括无意于控制、支配物人的意趣。但是,作品格调之“淡”不是自觉的“无为”或对物、人的“放手”,而是自觉选择、注目若干意象,同时自觉地在精神上悬置其余的万物与人*“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梅尧臣: 《赠杜挺之》)就诗文创作说,“平淡之境”以平淡的胸襟与气度为前提,即需以自足于内,与物无争为其精神准备。同时,平淡之境也需要作者用词圆熟,若出天然。但并非用“拙易语”即“平淡”,用词圆熟,至于天然亦非“平淡”。平淡的精神以平淡语出之,方成平淡之境,故有“造平淡难”之叹。。在此意义上,作为艺术作品境界的“淡”不是老庄意义上守护万物素朴本性、有心而无为之“淡”,而更接近隐士或郭象意义上的无心(有为或无为)之“淡”。
从“滋味”之“淡”转到作为精神境界的“恬淡”,从作为道的品格之“淡”到作为人的气质之“平淡”,再到作为作品境界的“冲淡”“平淡”,“淡”的精神在中国思想中不断生长,展现出绵延不绝之生机。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淡”乃中国思想的基本维度,它与温、凉一道构成了中国思想完整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