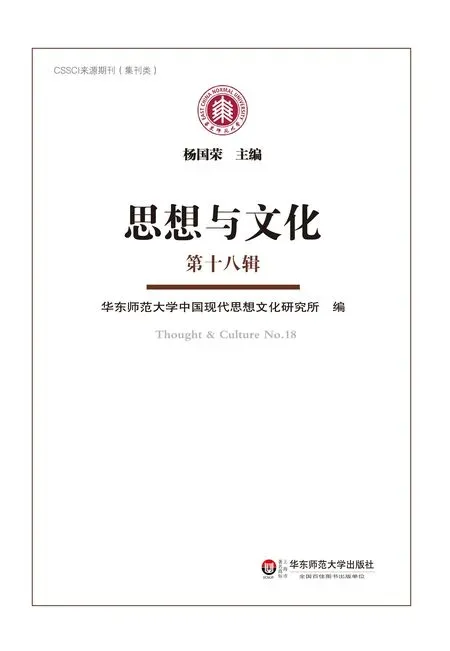《管子》四篇中的政治权威思想*
2016-04-12尚建飞
尚建飞
从理论的层面来讲,《管子》四篇研究伦理问题可以看作是其阐释政治主张的前奏。而且,为了使伦理与政治两个领域得以融会贯通,《管子》四篇选择圣人作为自己的关注焦点。对于《管子》四篇而言,圣人既拥有完善的德性,同时能够成为人类社会的理想统治者。换句话来讲,圣人拥有政治权威的原因就在于他顺应了民意、能够制定和运用的社会规则体系是守护人的生命。*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权威是指: “作为政治哲学家使用的规范性概念,指的是一种以道德主张形式呈现出来的‘统治的权利’(right to rule)。”([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 《政治学核心概念》,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一、 天下因圣人的无私而归服
在《管子》四篇看来,人们之所以服从政治权威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或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作为与政治权威相契合的人格形象,圣人恰恰是因为能够确保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利而获得合法性的权力,并且在引导百姓满足其生理需求的过程中展现出自己的无私品质。
从其肇始以降,道家始终将保全百姓的生命确定为政治权威的核心内涵。老子曾指出,在“道”生成天地万物的宇宙论图式中潜藏着层次分化的可能性: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作为是天地万物的统一性根源或原理,“道”在逻辑上优先于任何一种具体事物。而在具体事物当中,由于天、地和王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所以三者也享有类似于“道”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河上公对“四大”的解释是: “道大者,包罗天地,无所不容也。天大者,无所不盖也。地大者,无所不载也。王大者,无所不制也。”(详见王卡点校: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 中华书局,1993年,第102页。)需要说明的是,“四大”之一的“王”与圣人可以被用作同义词: 前者表示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圣人,后者则特指“王”必须具备的完善德性。*高亨认为: “老子之言皆为侯王而发,其书言圣人者凡三十许处,皆有位之圣人,而非无位之圣人也。”(高亨: 《老子正诂》,北京: 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2页。)其后,庄子对老子的这一主张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庄子·天道》)对于老子和庄子而言,作为“王”“帝王”的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四大”之一、会受到敬仰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效法地、天的无私、公正,而且最终会像“道”那样把生命本身视为目的,不去干涉他人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
《管子》四篇赞同老子和庄子关于政治权威、圣人的评价方式,与此同时又试图立足于人的生理需求来对这一主张加以修正。《管子》四篇认为,保全百姓的生命有其特定的含义: “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心术下》)*文中所引《管子》四篇原文均出自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的《管子校注》(中),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用“精气”或“道”来充实人的身体即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它构成了人们保全自身生命的本能。因此,能否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也就应该成为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本尺度。正是由于明白抟聚“精气”或“道”、满足生理需求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所以圣人据此建构起为他人所普遍信服的行为规范。*尹注认为,“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的意思是: “充不美则气邪,故心乱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则邪枉,故人不服。”(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 《管子校注》(中),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778页。)尹注已经注意到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与社会规则体系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在价值论的层面,圣人是把统治人类社会的权力视为抟聚“精气”或“道”、满足百姓生理需求的工具,其所追求的目的则在于像天地那样用无私的态度来保全百姓的生命。相反,如果圣人利用统治人类社会的权力以实现一己之私利,那么百姓因自身生存权利受到损害而拒绝服从圣人的命令,由此将会扰乱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于《管子》四篇而言,圣人不仅明白满足生理需求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而且更加擅长于运用恰当的方式来满足生理需求。《管子》四篇认为,虽然满足生理需求是人的生命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不对其加以调节,那么只会适得其反,导致生命的终结: “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内业》)人的情感体验展现了其对待生理需求的真实态度: 忧虑代表着生理需求始终没有受到重视,愤怒源于放纵生理需求,抑郁则表示生理需求处于压抑的状态。*石一参指出: “知由思生也,知喜知怒知忧知患,其原皆起于心之失平而好动。然如废置其心而慢易不思,则患从此生;放任其心而暴傲不加思虑,则怒从此生;抑制其心而忧郁未之深思,则疾从此生,皆失其心之正也。”(石一参: 《管子今诠》,北京: 中国书店,1988年,152~153页。)处于忧虑、愤怒和抑郁等等状态之中的人们,通常会因疾病侵扰和遭遇生存困境而丧失生命。上述案例表明,人只有对饮食、情欲等生理需求加以调节才有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此处所谓的“思”是指情欲,例如尹注就将“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解释为: “思欲不舍,则五藏困于内,形骸薄于外也。”(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 《管子校注》(中),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945页。)在人类社会当中,只有圣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准确满足生理需求与守护生命之间的因果关系: “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内业》)圣人知道,抟聚“精气”或“道”、满足生理需求人的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也清楚享乐意愿对于自身生命的危害。换句话来讲,圣人是将人的生命当作目的本身,所以他既可以避免享乐或放纵生理需求对于身体机能的损伤*“心全于中”是指“精神集中、全神贯注,不为外界物欲所引诱”。(详见钟肇鹏、孙开泰、陈升: 《管子简释》,济南: 齐鲁书社,1997年,第366页。),同时又有能力卓有成效地回应生存情境的挑战。
立足于其对生理需求之功能的理解,《管子》四篇中的圣人提出了自己所特有的政治主张。首先,圣人注意到,与其通过后果去评价人们满足生理需求的方式,不如主动地告诉人们如何使用正确的途径满足其生理需求: “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内业》)作为一种调节行为的手段,奖赏与惩罚仅仅关注的是人们的生理需求,然而却并不能促使人们把握住满足生理需求与守护生命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圣人所追求的是,一方面赞同满足生理需求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另一方面又帮助人们消解享乐意愿的遮蔽,明白满足生理需求是以守护人的生命作为目的。*石一参指出: “刑赏皆外来之物,能外著之行,而不能劝惩其心。故不如正心养气而诚意无伪者之易为天下听从而心服也。气得其所养,则意不外驰;心得其所安,则意无旁挠。天下虽大,以心印心而道在于是矣。”(石一参: 《管子今诠》,北京: 中国书店,1988年,第151页。)其次,圣人知道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或政治权力的道德理由: “昔者明王之爱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恶天下,故天下可离。故货之不足以为爱,刑之不足以为恶。货者,爱之末也;刑者,恶之末也。”(《心术下》)圣人的明智之处就在于,他不会像暴君那样践踏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是承认满足生理需求是人的生存论前提。并且,只有在圣人的引导下才能够实现其守护自身生命的目的,所以人们会自愿地归服圣人,把服从圣人的命令视为自己的政治义务。
按照《管子》四篇的看法,无私地守护百姓的生命不仅使圣人获得统治天下的合法权力,而且也赋予了他颠覆暴政的权利。《管子》四篇确信,尽管圣人打破了权力世袭的传统,然而他依然会得到百姓的认可: “天之视而精,四璧而知请,壤土而与生。能若夫风与波乎?唯其所欲适。故子而代其父,曰义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白心》)统治天下的王者应该精通天道,深知祭祀上天是为了给百姓祈福、确保后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尹注认为,“四璧而知请”的意思是: “四璧,《周礼》所谓‘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于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则祭以四璧,而祈请其福祥也。”(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 《管子校注》(中),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807页。),所以他会像水波受风的驱使那样顺应百姓的欲求。与此同时,王者的子嗣继承其政治地位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王位的继任者专横残暴、背离道义,那么臣子就有权利取而代之以契合百姓的意愿。实际上,武王伐纣的案例证明,即便是臣子也可以凭借无私地守护百姓的生命而享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权力。
在理论论证的层面,《管子》四篇显然具体化了道家评判政治权威的标准,即无私地守护百姓的生命必须把满足其生理需求当作逻辑起点。作为政治权威的化身,《管子》四篇中的圣人一方面把统治人类社会的权力视为抟聚“精气”或“道”、满足百姓生理需求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能够消解享乐意愿以及暴政带给百姓的危害。
二、 从“执一不失”到“名正法备”
如果说无私地守护百姓的生命使得圣人赢得了民意,那么认识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则确保他有能力为人类社会建构起理性秩序。依据《管子》四篇的观点,因为知道“一”,即公正、无私地守护生命是天地万物运行的统一性原理,所以圣人的命令符合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利,能够制定出有效地维系社会秩序的规则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家一致主张圣人或王者有能力掌握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例如,老子的“四大”学说和庄子关于“帝王之德”的论述表明,圣人或王者有能力效法道、天、地所象征的统一性原理。老子认为,在掌握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之后,圣人或王者不仅可以公正、无私地守护百姓的生命,而且将会为人类社会制定出合理的政治制度: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老子·第二十八章》)针对道德品行、职业分工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圣人构建起了尊卑等级以引导人们达到至善,也就是在尊重人的生命或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推论出整合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换句话来讲,圣人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可以消解“道”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张力: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老子·第三十二章》)圣人并不是利用尊卑等级名分来谋取私利、操控他人,而是将其当作守护百姓的生命所必须借助的手段。*王弼关于“始制有名”注解是: “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 《王弼集校释》(上),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第82页。)另一方面,圣人的这种卓越品质也被称为“守朴”,即是能够像“道”那样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人们天性的多元化现象。虽然“守朴”不如智力、勇武、技巧、体力等品质那样更易于为人所觉察,但圣人却正是凭借它才得以确保拥有上述诸多专长的人们从事适合其天性的工作。*“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的意思应该是: “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朴之为物,愦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 《王弼集校释》(上),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第81页。)
在老子之后,庄子对于圣人构建尊卑等级制度的观点展开具体阐释: “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庄子·天道》)君臣、父子、兄弟、长幼以及男女夫妇之间的先后次序源于自然法则,因为它们是由圣人效仿天尊地卑、四时交替的现象所制定。更为重要的是,庄子不仅延续了老子把尊卑等级制度视为工具的立场,而且有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合理论证: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庄子·天运》)关注人伦毁誉、区分远近亲疏和尊卑先后是整合人类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但这些评价尺度或行为规范却有可能会遮蔽人类生活的真正目的。相反,至人即圣人认为,仁义所象征着的尊卑等级制度只是守护人的生命的手段。所以,他会突破尊卑等级制度的限定,并将公正、无私地守护生命确定为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在庄子的语境当中,至人、神人、圣人被用作同义词。成玄英对这句话的注释是: “知止知足,食于苟简之田;不损己物,立于不贷之圃。而言田圃者,明圣人养生之地。”([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 《庄子集释》(中),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520页。)
与老子和庄子相同的是,《管子》四篇仍然相信圣人有能力认识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不过,同老子和庄子相比,《管子》四篇更为明确地界定了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以及圣人所应该具备的能力。首先,就其自身而言,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是由四种因素构成: “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内业》)“道”提供了生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或精气,天、地体现出了“道”的公正和无私,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只有接受“心”的调节才能与道、天、地保持一致。*石一参对“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的解释是: “不偏不倚之谓正,均一之谓平。此假天地之道以喻人道。”(详见石一参: 《管子今诠》,北京: 中国书店,1988年,第145页。)其次,圣人的过人之处就体现在能够使其“心”遵循道、天、地所象征的统一性原理: “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内业》)圣人懂得,四时有规律的变化、大地育出丰饶的物产和人的谋划是守护生命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所以,奠定在公正、无私和有效调节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圣人的“心”会把守护生命确定为目的本身,从而可以用健全的身体来积聚精气或道。
在《管子》四篇的话语体系当中,涵盖了道、天、地和人的统一性原理也被称为“一”。并且,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使用“一”保养个体生命优先于根据“一”整合人类社会秩序。实际上,《管子》四篇正是据此来探讨“一”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唯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内业》)在治理人类社会之前,君子即统治者应该学会利用“一”以回应外在情境的变化,由此能令其体魄强健、拥有智慧。*石一参认为: “一物,谓物虽万,所以应之者一;一事,谓事有万,所以处之者一。……气者,所秉受于天地之正气,聚则在人,散则归诸空间,亘古不易者也。智由性生,性定则智有常度,非关后起,故不随外象变迁,所谓不变者在我,变者在物也。”(详见石一参: 《管子今诠》,北京: 中国书店,1988年,第146页。)此外,掌握了“一”便标志着有资格去治理人类社会,因为善于保养自身生命的统治者是用公正、无私地守护生命的态度发布命令和引导他人的行为。
对于《管子》四篇而言,圣人恰恰是君子或理想的统治者,因为他能够正确地运用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或“一”。在治理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圣人最注重的是如何实现“名当”,即可以制定出与事实相一致的行为准则。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圣人需要用“心”思考事物的实质及其得以产生的原因: “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刑,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白心》)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认识了各种相关迹象就能从根源处揭示出事物的实质,顺着事物本身的规律可以对其变化情势进行评判,最终由始末两端来确定“名”或对待事物的合理方式。*此处所谓的“端”是指两端,即始末。(详见钟肇鹏、孙开泰、陈升: 《管子简释》,济南: 齐鲁书社,1997年,第302页。)以此类推,人与万物在天地之间共处,同样是由于秉受了“精气”或道而得以生存*尹注认为: “日,阳也。月,阴也。物皆秉阴阳之气然后化之也。”(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 《管子校注》(中),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788~789页。),所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就必须被视为是最为根本的“名”或行为准则。此外,圣人并没有把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奉为教条: “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白心》)经过在不同情境中的反复验证,圣人会把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相一致的“名”或行为准则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从而构建起了“法”,即可以有效整合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体系。*石一参指出: “此申上文以正为仪之义。正其心以正百物,由正名起,法由名生,故曰圣人以名治天下。”(石一参: 《管子今诠》,北京: 中国书店,1988年,132~133页。)
通过澄清圣人制定“名”“法”的宗旨和方法,《管子》四篇进而推论道,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与现实的人伦规范之间存在着必然性的关联。换句话来讲,“名”“法”就体现在世俗所认可的“义”“礼”和“法”之中: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心术上》)尽管“道”本身有别于具体事物、具有无形无象的特征,然而它却蕴含着“德”,即生成天地万物的功能。而且,无论是“义”或君臣、父子所代表的人伦关系,还是依据尊卑等级形成的礼法规范,它们共同展现出“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用来区分人伦关系和尊卑等级的义、礼、法不仅是整合社会秩序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是以合乎“道”“德”,即守护人的生命作为终极目的。
非常明显的是,《管子》四篇中的圣人并不认为“一”或“道”“德”与“义”“礼”“法”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因为它们共同致力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守护人的生命这一目标。此外,正是由于掌握了“一”或“道”“德”,圣人才有可能制定“名”“法”,为人类社会构建起合理的规则体系。
三、 谁有可能成为圣人?
纵观《管子》四篇对于圣人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其中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议题: 一是圣人所应该具备的德性;一是圣人是否必须具备卓越禀赋。在逻辑论证的层面,前者解释了圣人统治人类社会的合法性,后者则侧重于回答成为圣人的可能性。
在回答什么人有可能成为圣人的问题上,《管子》四篇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管子》四篇承认人皆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具体地讲,人的生存状况与德性完全取决于其对待“道”的态度: “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贼。”(《白心》)作为一切生命的源泉,“道”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本体论前提。这不仅意味着人的健康、寿命同“道”之间存在着必然性的关联,而且能否遵循“道”也被当作评价德性的基本尺度。换句话来说,所谓符合“道”的品质即是用合理的方式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由此可以使其赢得他人的尊重、被冠以圣人的荣誉。相反,背离了“道”将会激起民愤,甚至是演变为整个社会的公敌。
其次,如果就人的天性而言,那么《管子》四篇似乎相信只有被赋予了卓越禀赋的人才是圣人的合适人选。按照《管子》四篇的理解,“道”无声无息地进入人的形体之后就聚集成为“心”,它既是人的生命得以产生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有可能为人的生理需求所遮蔽。《管子》四篇根据这种宇宙生成论把人的天性区分出常人与圣人两种类型: “人者立于强,务于善,未于能,动于故者也。圣人无之,无之则与物异矣。异则虚,虚者,万物之始也,故曰: ‘可以为天下始’。”(《心术上》)常人的天性中充斥着情欲,所以他们保持矜持勉强之心境,喜欢用伪善、自我中心或巧诈来行为处事。*关于“立于强,务于善,未于能,动于故”的考证,详见钟肇鹏、孙开泰、陈升: 《管子简释》,济南: 齐鲁书社,1997年,第293页。)与常人形成鲜明对比,圣人被赋予了卓越禀赋,即能够避免情欲所带来的干扰。正是由于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卓越禀赋,圣人才有能力把握住天地万物之本性及其运行法则,据此获得了统治人类社会的资格。
毋庸置疑,上述两种圣人理论之间存在张力: 人皆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与圣人取决于卓越禀赋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价值主张。对此,《管子》四篇提出了一种调和的解决方案,即圣人取决于卓越禀赋优先于人皆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而且,与之相应的有效性论证也蕴含着双重向度。一方面,依据《管子》四篇的看法,人类社会类似于被放大了的人体。正如人体各种机能互不相同那样,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也与人的天性有关: “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 ‘君’。‘无代马走,无代鸟飞’,此言不夺能能,不与下诚也。‘无先物动’者,摇者不定,趮者不静,言动之不可以观[其则]也。”(《心术上》)*陈鼓应先生认为,“言动之不可以观也”应为“言动之不可以观[其则]也”。(详见《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6页。)“心”的固有功能就在于明白“精气”或“道”是生命的源泉,并且能够将人的生命当作目的本身。虽然“心”不必像耳目那样拥有感官能力,但它却可以主导耳目的运作方式、回应外界带给人的刺激。在人类社会当中,把君主等同于“心”其实是为了凸显卓越禀赋的重要性,或者说,只有被赋予了卓越禀赋的圣人才适合扮演君主的角色。因为要想拥有绝对权力,君主就必须像圣人那样凭借其卓越禀赋以把握住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原理。这不仅使他区别于具备特定技能、承担某种职责的群臣和百姓,与此同时又能利用“心”的固有功能对后者展开合理的评价。
另一方面,拥有卓越禀赋的圣人并不是利己主义者,他能够帮助其他人培养出圣人的德性。作为掌握了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拥有卓越禀赋的圣人没有把符合“道”的品质视为自己的特权: “上圣之人,口无虚习也,手无虚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发于名声,凝于体色,此其可谕者也。不发于名声,不凝于体色,此其不可谕者也。及至于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白心》)拥有卓越禀赋的圣人会尊重他人的天性,因此他所发布的政令绝非空洞的或虚妄的说教。例如,对于天资聪颖的人就可以向其讲解“道”的实质,但生性愚钝的人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而是需要应该根据其实际的欲求来加以引导。*尹注显然注意到天性的差异是圣人发布政令的现实依据: “名声之至,耳听之,内流于心,外凝结于体色。如此者,性之敏惠,故可以德义告谕也。不发不凝,所谓愚鄙者也,故不可告谕也。”(详见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 《管子校注》(中),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802页。)就终极目的而言,拥有卓越禀赋的圣人是希望他人可以自发地运用“道”规范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如果从政体形式的角度来说,《管子》四篇关于成为圣人的理论将会赞同专制主义或专制君主的统治。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就在于,《管子》四篇是把备卓越禀赋的圣人确定为政治权力的始点,也就是只承认具备卓越禀赋的圣人才享有制定和运用社会规则体系的资格。然而,作为君主的圣人又有其道德基础: “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白心》)圣人所制定和运用的社会规则体系是以守护人的生命作为宗旨*石一参认为此句的意思是: “道家致虚守静,伸屈从时。正其心以为仪表,心正则物无不正。又一一以和顺出之,心之用也。”(石一参: 《管子今诠》,北京: 中国书店,1988年,第132页。)其实,此句的主旨是为了说明,圣人运用“心”的固有功能才得以构建起与守护人的生命相一致的社会规则体系。,所以群臣和百姓就有义务服从圣人的命令。就其自身而言,作为君主的圣人既具有了绝对权力和合法性,同时也应该被称为仁慈的专制主义者。*王海明先生指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可以被划分为“霸道的专制主义”(亦即野蛮、邪恶的专制主义)和“王道的专制主义”(亦即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二者区别就在于是否符合道德的前提。(详见王海明: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