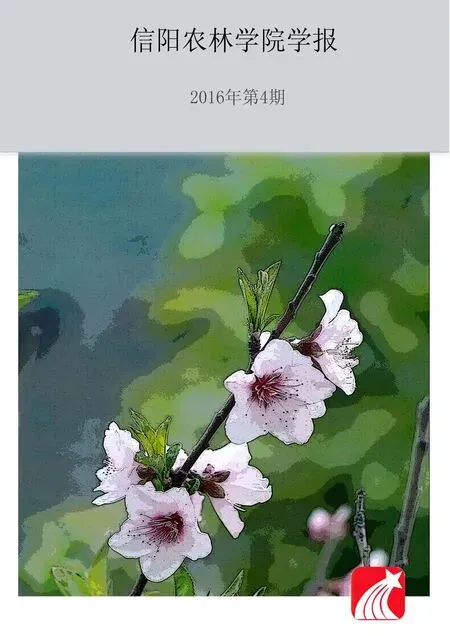苏轼与张孝祥词艺术特色比较研究
2016-04-12丰家喜
丰家喜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语言与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苏轼与张孝祥词艺术特色比较研究
丰家喜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语言与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在宋代的词史上,苏轼是“革新巨手”,张孝祥是“词学奇葩”,都是高标卓立的人物,二人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试图从苏轼与张孝祥词境的构筑方法、词中意象、语言风格、善于用典等方面来比较,进一步阐明苏、张二人词艺术特色的继承发展关系,以及对辛派词风的形成所起的启迪作用。
苏轼 ;张孝祥;艺术特色
1 豪放词风格的同中有异
苏轼与张孝祥,虽然都是宋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词的风格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关注更多的是得到朝廷的重用、经世济民、建功立业以及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苦闷和忧愁。张孝祥在继承苏轼豪放风格的同时,更多地将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激昂与悲愤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而这又开启了下一时期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的创作风格。
北宋时期苏轼以豪放的性格、积极进取的态度,豪迈奔放的情怀,从根本上使晚唐五代以来词人绮丽婉约的风格得到改观,开辟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风格,胡寅认为东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1]。王灼认为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2]。关于苏轼的“豪放”词风,俞文豹认为 “东坡在玉堂,有谋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永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 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倾倒。’”[3]张孝祥创造了更加雄奇阔大的意境,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旷达、豪放的写作词风,更是笔酣墨饱,生动突兀,气势飞扬。
苏、张二人词的豪放风格,其相似的一面也有明显的不同,相似的就是在二人的词作中,“以诗为词”、“以词言志”,变言情为言志,用词来表达救国济世之志、建功立业、报国安民的人生理想;二人变为娱宾遣兴而写词,强调词作关心社会治乱、弘扬民族精神、救国济世的社会作用。都怀着奔放、浓烈的豪情壮志,说明了词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无比热爱的情怀,也正因为这种壮志豪情,成就了苏轼与张孝祥词的独特创作个性和持久永恒的艺术魅力。
由于苏、张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拓宽了词的发展空间,因而,提高并深化了宋词的意境,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内容;两位词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更鲜明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思想情感在词中得到更充分的表现。例如在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词人通过射猎联想到西北与北方的敌人,作者通过艺术想象,将一次普通的打猎活动变成一次具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武装演习。古代人经常借用“出猎”来代替军事演习,苏轼的行为恐怕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因此爱国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张孝祥在《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中,充分表现了他要学习东晋祖逖渡江北伐、乘胜收复失地的决心。张孝祥还对南北割据、国土分裂的局面作了真实的描绘,表达了他坚决抗金、收复失地、恢复民族尊严,至死也不忘统一国家的坚强决心。
由于二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个性经历的不尽相同,在“东坡词”和“于湖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如果说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关注更多的是得到朝廷的重用、经世济民、建功立业以及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苦闷和忧愁的话,那么张孝祥的词在继承苏轼豪放的同时则更多的是融入了“时事政治”,将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激昂与悲愤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而苏轼的性格特点将挥洒自如、豪迈旷达与灵活多变的篇章结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苏词豪放的并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张孝祥因长期国恨家仇的忧郁,自然而然地使他的词一方面充满着慷慨激昂,豪迈奔放,激情澎湃,另一方面又增添了几分忧思悲壮,沉郁苍凉。加上当时朝廷部分主和投降派的排挤打击,残酷的社会现实与远大的政治理想抱负的矛盾,使他的词根本不可能像苏轼那样豪迈奔放、洒脱自如。
2 清旷词风格比较
苏轼的一生多次遭到朝廷的贬谪,人生经历十分坎坷,政治命运几起几落,可以说是饱经磨难、几经沧桑。他性情孤傲、政见独立,做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直言敢议。不论是革新派还是守旧派上台,他都不愿见风使舵、拍马溜须、阿谀奉承、随波逐流,为此还曾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差点因此丢掉身家性命。即使在这种危险情况之下,苏轼依然能引身物外,以豁然达观的态度对待。苏轼正是以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造就了一系列颇具旷达的词作问世。苏轼的这种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表现为:不强求人生完美,辩证地看待得失,身处逆境而心有所系,情有所托。陆侃如、冯沅君曾指出:“所谓铜琶铁板的高歌大江东去者,只能代表苏词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说苏轼给词带来豪放的风格则可,但豪放却不能概括苏词。苏词十之六七是属清旷的。”[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稼轩之词豪,东坡之词旷。”[5]这些评价都是客观公正、名副其实的。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是这样解释和说明“旷达”的: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搏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幕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6]
文中的“旷达”的意思与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意境很是相似,使用无名氏在《诗品·旷达》中的注释来说明苏词的词境是很恰如其分的:“惟旷则能容,若天地之宽;达则能悟,识古今之变。所以通人情、达物理、验政治、观风俗、揽山川、吊兴亡,其视得失荣枯,毫无系累,幽忧偷乐,慨寓于诗,而诗之用不可穷矣。”[7]东坡词中的妙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水调歌头》),“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水调歌头》),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描绘的就是这种旷达的意境。
南宋初期追慕苏轼并继承其风骨者应首推张孝祥。据统计,《于湖词》十有六七都是以“清旷”风格闻名于世的,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也是以此类词为上。“清旷”虽属“豪放”,但有着向“婉约”发展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孝祥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词人,而且是以“清旷”为其主要风格的。这方面,张孝祥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念奴娇· 过洞庭》,在这首词中,作者洒脱的形象,多么像苏轼,而“不知今夕何夕”很容易让人们想起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赤壁赋》,前者很可能就是张孝祥此首作品借鉴和学习的对象。此首词可以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媲美,它们都是中秋词中的千古杰作 ,而且这两首词的风格都是清旷。
当然,张孝祥的清旷与苏轼也有区别。苏轼所处的北宋中期,国家内部和边境较之于南宋初期稳定了许多,苏轼陷入的矛盾,主要是北宋政权内部的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矛盾;张孝祥所处的时代除了内部的政治派别斗争外,还存在着空前激化的民族危机,这就使得他的清旷与苏轼有所不同。苏轼的清旷是从仕途多变、生命无常中完全解脱出来的清旷,而张孝祥在清旷的同时还必须关心社会治乱、弘扬民族精神、救国济世的社会作用,其词的现实性比苏轼的更广泛,斗争的矛头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过洞庭》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前者蕴含的是对整个人生悲欢离合的思考,而后者则较多的反映着自己执著的追求,个人情感在词中有了明显的指向,如“应念岭表经年”一句。由此,当我们读到前者会联系到自己的人生经历由此而产生强烈的共鸣,而读后者则更多的是对作者高洁、磊落形象的观照。
3 词中意象、语言的异样美
张孝祥执意学苏轼,他的最可嘉的地方就是把诗中的意象融入词中、把古人诗句融化其中,同时使自己的词在运用典故方面更加灵活自如,使词在语言方面更加古朴典雅。苏轼以诗入词的典型手段就是使词在语言方面更加典雅化、诗意化,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化用和用典。马丁良在《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浅析苏轼词对唐诗的采融》一文中指出:“苏轼在词作中大量的采融唐诗,用多种手法使唐诗融化到词中,使词改变了其尚艳从俗、柔媚率直的风貌,具有了诗体的含蓄典雅、豪放蕴藉的韵致。”比如最典型的是他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里“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就是巧妙化用唐代诗句《春怨》中“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句。在苏东坡词中有很多这类化用古人诗句入词的现象,他有时还在词中直接化用古人文中的句子,比如出于《论语·公冶长第五》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出现在他的《千秋岁·次韵少游》中“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中;关于用典,在苏轼词中更是举不胜举,且能自然灵活,浑然一体。《词源》卷下云:“词用事最难,要体任著题,融化不涩,如东坡《永遇乐》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此皆用事,不为事所使。”[8]又如他的“问公何事,不语书空”( 《行香子·昨夜霜风》),用晋时殷浩典等;“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恨无人借买山钱”(《浣溪沙·感旧》),用支遁典。在这方面,张孝祥很好地继承下来,让他的词在语言方面典雅蕴藉,意境方面含蓄隽永。例如张孝祥的名篇《念奴娇·过洞庭》就化用苏轼《水调歌头》词和《前赤壁赋》文的意境,这首词不仅语言庄重高雅而且意境空灵高远。张孝祥的《水调歌头·泛湘江》得楚辞韵,用楚辞典。张孝祥巧妙化用唐代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诗意,他直接引用唐代诗人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中的句子,用在他的《水调歌头》(五岭皆炎热)上阕“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以及“雪片一冬深”句,下阕“溪山好,青罗带,碧玉簪。平沙细浪欲尽,陟起忽千寻”。张孝祥深得苏轼的精华,在词中广泛用典、化用,真正做到了入神入化、浑然天成,而且对南宋的辛弃疾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辛弃疾在其词中更是将经史子集诉诸笔端。
苏轼在语言风格方面比较注重吸收陶渊明、杜甫、李白、韩愈的诗句,偶尔也使用当时的口语,一改花间词人错采镂金的风格,给人一种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的感觉。张孝祥词的语言风格在于含蓄典雅、自然清新,这也是其俊逸清旷词风的重要特色。在张孝祥的词里,像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很少见到的。汤衡说他“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9]。张孝伯评价他写词“未尝属稿,和铅舒纸。一笔写就,心手相得,势若风雨”[11]。由此可见张孝祥的创作追求的是自然天成,并不是那种刻意追求工整,从他的词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特点。例如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上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一声长啸暮烟里,袖手西湖归去”,等等,几乎是脱口而出,清新、自然,毫无粗犷之气。另一方面,他的词语言又很典雅含蓄。汤衡曾评价他的词“初不经意,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12]。所有的字都有来处,倒也未必,但由此也不难看出张孝祥对古人诗文语言的消化吸收。他一直都是以较小的篇幅囊括较大的内容,在化用前辈诗文语言时,从来没有生搬硬套之嫌,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总能恰到好处,从而使他的词的意境显得飘逸、高雅。当他写湘江的水流如何湍急时,马上联系起渔父唱的《沧浪歌》;在描写北风凉爽时,又马上联系起稀发的女神(少司命),这是典型的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在景与故事的结合中表达作者的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洁独立的个性,其中包含的意义十分耐人寻味。“稀发北风凉,灌足夜滩急。”“灌足”出自《楚辞》,“北风凉”出自《诗经》。又比如出自谢朓诗句的“余霞散成绮,烟际帆收。” 又如《念奴娇·过洞庭》中“欲乘风,凌万顷,泛扁舟。山高月小,霜露既降,凛减不能留。”很明显是化用苏轼《前赤壁赋》中语句。张孝祥词的用典、化用,仅仅是为了使自己写景、抒情更加含蓄隽永。所以,在词的格调上,张孝祥词的用典就不太可能像一般的豪放词那样凝重、严肃、深沉,更多的是飘逸、清奇,这正体现了张孝祥词在语言上俊逸、清旷的特点。
[1] [英]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序言[A].西方文论选下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9.
[2] 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69.
[3] 唐圭璋.词话丛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6:85.
[4] 俞文豹著.吹剑录[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5]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 [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6] [清]王国维著.人间词话[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7] 司空图,赵福坛.诗品新释[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8] [宋]张炎.词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A]. 文体篇[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74.
(编辑:刘彩霞)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therness Between Su Shi and Zhang Xiaoxiang
FENG Jia-xi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Xin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llege, Xinyang 464000, China)
In poetry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 Su Shi is a innovate expert, Zhang Xiaoxiang is a wizards of poetry, they are all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he paper especially compared four parts between Su Shi and Zhang Xiaoxia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poems, the image of poems, language style, and frequent use of allusions. The paper stated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ir poems which change from vulgar style to grace style.
Su Shi; Zhang Xiaoxiang;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2016-05-22
丰家喜(1978—),男,河南信阳人,讲师.
I207.23
A
2095-8978(2016)04-00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