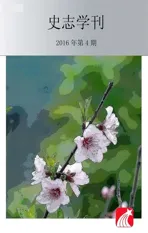浮梁县元代《龙溪忠显庙记》碑浅释
2016-04-11付火水
付火水
(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景德镇333403)
浮梁县元代《龙溪忠显庙记》碑浅释
付火水
(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景德镇333403)
《龙溪忠显庙记》碑,是一通较为珍贵的元代碑刻,反映了元代浮梁地域文化及民间信仰及人口流动等方面的问题,亦可补元朝文献之不足。
浮梁元代碑刻考释
浮梁建县于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新平乡从鄱阳东界析出置新平县。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更名为浮梁,为上县。历史上以茶叶、瓷器生产闻名于世。文化发达,号称文献之邦。即以碑刻而言,经过我们的走访调查统计,共有106通,这还不包括各类题额等史料价值相对欠缺的诸多碑刻。元代持续不及百年,江西出土的元代碑刻较少,因此浮梁县元代碑刻《龙溪忠显庙记》就显得特别珍贵。
元代《龙溪忠显庙记》碑刻现保存在浮梁县博物馆,出土于浮梁县东部王港乡墩口村附近。撰额为“龙溪忠显庙记”,碑文现抄录如下:
龙溪里忠显庙后殿记
赐同进士出身从仕郎饶州路浮梁州判官李毕譔
朝列大夫同知池州路总管府事杨本书
信武将军饶州路浮梁州达鲁花赤兼劝农事朶见只加篆
江浙名郡,番歙接壤,而浮梁为番大邑,邑东三十里有溪,上流抵歙曰龙溪。阛阓之所,有庙翼然,歙神汪王祠也。祠之建盖古矣。奉祠事金、法显、法荣常念庙庭湫隘,谋剏后殿而宏其规,以便华严经士之岁三集来为王寿。庶几宽容,列坐有次,展敬有所,是以徼神福也。相殿之基屾一间地,适属它姓,未能完美事,姑尼丙寅春卒以己地易得之,议以克合。遂裒众金捐己帤,具木石瓦,甓以其年。立夏日辛未经始,天佑人助,不日而成,复刻圣像铸钟及炉,修门庑、筑毬场,咸一新之。且置田买山入祠,以图日久不朽焉。惟王幼有灵异,能于干戈扰攘之中保有六郡,民赖以安。其殁而为神,庙食百世,宜也。自唐迄今,累朝以来,屡有封锡,英灵烜赫,水旱疾疫有祷辄应,非惟一乡士庶惟神是依,而邻近分祠者且数十庙,于戏显矣。显则祠不可已,立楹曰:天诏加封适至,其时岁且旱,群庙祈迎,不约同集,一时甘雨大注,众莫不嗟异而相谓曰:“自祠之广拓而神效灵如此,无一言以垂后,可乎?且因左右亟请于余,欲书其乐以示求以。盖余之佐治是州也,天旱不雨,宁不忧民之忧,祷而有感,岂不乐民之乐,况王之功德具载青史。
国朝祀典与焉,宜矣。泯敬,事而无斁也。于是作迎享之诗,以记于石曰:
王之来兮,巍冠美髯,英灵昭昭兮,自昔而然。山屾趍兮,水清涟;翼新宇兮;荐豆徼福我民兮,何千万年。
至顺二年辛未岁正月上元日
奉祠事金法显法荣立石
昌江程振翁刊
一、关于撰文、书丹及撰额人
撰文者“赐同进士出身从仕郎饶州路浮梁州判官李毕”,不见史料记载,但《浮梁县志》有浮梁州判官李希贤者,元贞间任,不知是否是同一人;书丹者朝列大夫同知池州路总管府事杨本,浮梁志书中不见记载,但元朝有同属饶州路鄱阳人杨本,可能即为其人。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元铅山州判程先生(养全)行实吴维新
先生讳养全,字子正,其先新安人。自唐司徒公平巢冦捍乡里,生子勋,以金紫光禄大夫行饶州司马兼知银山镇,银山即今徳兴县也,因家凤凰村。……日与郡教范尧臣、同年董宗文、陆元庆、李晋齐、郡士杨本六人讲论[1](明)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M].黄山书社,2004.。
此外,诸多书目丛书也有元代鄱阳人杨本的记载: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四:“苍崖先生《金石例》十卷(元刊本)元潘昂霄撰。鄱阳杨本编辑、校正,庐陵王思明重校正。旧为曝书亭藏书。至正五年,其子诩刻於鄱阳者。此书,初刻本也,有杨本、傅贵全、汤植翁、王思明序,潘诩跋”[2](清)瞿镛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四.四库全书本.。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金石例》原序:“金石例者苍崖先生所述也。……至正五年春三月鄱阳后学杨本序”[3]钦定四库全书·集部·金石例.。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潘昂霄《金石例》十卷,济南人,集贤学士,谥文简,旧以为杨本著,本鄱阳人,盖常校其书”[4](清)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
杨本无在浮梁州仕宦的经历,书丹可能更多是出于乡谊(鄱阳和浮梁同为饶州路)了。撰额者朶见只加,《浮梁县志》有浮梁知州朶见只加的记载,为“蒙古人,元贞后任。”[5](道光)浮梁县志[M].广陵古籍刻印社,2007.
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诸如杨本等人,参与龙溪里忠显庙碑记的撰写,其动机和意图尽管不明了,无论是顺民意、从民愿,抑或教化地方,正如陆九渊的再传弟子袁甫说的那样“牧民无他伎巧,从其愿而已”。总之地方官员支持或默认地方神祠信仰,有利于汪王信仰的传播和扩大信仰圈。
二、龙溪里与墩口
龙溪里即现在之墩口,据《景德镇市地名志》载:“墩口,北宋鲍氏由安徽青阳县迁此建村,因地处龙溪两侧,故名龙溪。后因村中小溪与东河交汇处有三个土墩而改名墩口”[6]景德镇市地名志办公室编印.景德镇市地名志[M].景德镇(内部印刷),1988.。此碑即出土于该村附近,印证《景德镇市地名志》所载不虚。
《江西全省舆图》之《饶州府浮梁县舆地图说》:“县东路,出东门,过渡,七里至三笑亭,又九里至大桥头,又六里至如意亭,又六里至渭水,又六里至墩口,又十六里至庄湾”[1](清)曾国藩等撰.江西全省舆图[M].成文出版社,1985.。从浮梁古县衙出发到墩口,约三十四里,这也与碑刻中“邑东三十里”大致吻合。墩口地处东河边,是徽饶大道(经现景德镇—浮梁县—瑶里镇—安徽休宁县右龙村—休宁县城—屯溪)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明清以来就比较繁华,有“一瑶里、二臧湾、三墩口”之说,是浮梁东部的一个重要集市。
三、汪王祠与华严教
唐宋以来,以崇祀越国公汪华为核心的汪王信仰成为徽州人尊奉的最为重要的神灵:“本郡屡朝祀典,首奉越国公汪华……自有唐至于昭代,世爵世祀,勿替有加,郡志庙志,班班可考”,“环徽之境,民皆戴王如父母,虽饮食寝处必祝”,在徽州的一府六县,以及徽州商人活跃的地区,普遍建有崇祀汪华的庙宇,所谓“江左浙右,庙貌相望,百祀不废”,“忠显有祠遍大江以东”[2]王昌宜.明清徽州的汪氏宗族与汪王信仰[M].宗教学研究,2012,(2).。在徽饶大道的重要节点墩口村兴建扩建汪王庙(忠显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汪王庙是当地著名的祠庙,虽然“祠之建盖古矣”,并无其它文献证明其建庙时间。据《景德镇市地名志》载:墩口,北宋鲍氏由安徽青阳县迁此建村,而且附近几公里没有由皖南在元朝以前迁入建村的记载,因此该祠由鲍氏所倡建的可能性较大。“宋代以来的地方志中,往往专设“祠庙”或“神祠”一门,记载这些佛教寺院、道教宫观之外的地方性宗教活动场所,……宋代以来组织性宗教日益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佛教、道教等组织性宗教与祠庙、神祠中的神灵信仰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界限逐渐模糊,愈来愈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3]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如果这种论断也适合龙溪里忠显庙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既称“汪王祠”,又称“忠显庙”。更为有意思的是“姑尼捐己地”“华严经士之岁三集来为王寿”,透露出佛教僧人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参与和赞助。佛教僧人的这种参与,有借助祠庙弘扬佛教者。考虑到墩口村处在徽商往来景德镇、饶州路的徽饶大道的东河边上,商旅众多,众人“裒众金捐己帤”,地方官员题写庙记,各方积极赞助,寺庙自然香火旺盛,地方也获利。这点宋代人就懂得其中玄机,“窃谓湖右名刹,如汉阳之凤楼。公安之二圣,皆据乎江滨水面。逆流而上,顺流而下,莫不输金施粟。田无丘角,而赡众动以千计。意有阴化嘿助,人办心而神办供者。”[3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表明神明信仰与商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朝祀典与焉”的记述说明其已经纳入了国家祀典,较《元史·顺帝纪》至正元年(1341)闰五月丁丑条记载:“改封徽州土神汪华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还要早十年。
当然,由于碑文的记载过于简单,而囿于缺乏更多其它资料的印证,我们的论证多属于推论。但碑文透露出元代地方信仰、以及民间信仰中的文化、经济变迁和社会流动的丰富内涵,证实该碑刻的重要性。
(责编:张佳琪)
付火水(1972—),男,江西奉新人,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文化。
本文为2013年度景德镇市社科规划项目“景德镇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