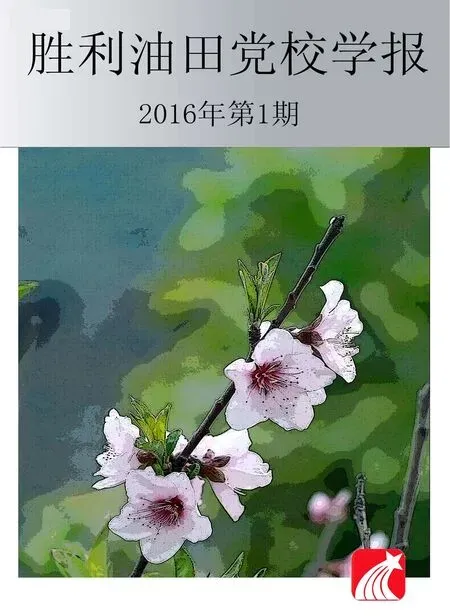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工作的审视
2016-04-11张世定
张世定
(中共甘肃定西市委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甘肃 定西 743000)
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工作的审视
张世定
(中共甘肃定西市委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甘肃 定西 743000)
【摘要】为了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扶贫开发成为当下贫困地区的重点工作。助推扶贫开发工作深入开展,路径选择具有多样性。而文化扶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一种选择。立足贫困文化理论的学术视角来解读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思想观念滞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价值观念消极等因素严重地制约着当地民众的脱贫致富。因此,当地的文化扶贫工作需要从制度的建构、民众观念的改变、文化产业的开发以及教育资源的供给等方面进行理性审思。
【关键词】文化扶贫;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扶贫开发
贫困地区的贫困现象,从表面上看似属于经济问题,但从深层考察却有着极深的文化根源。目前,学术界立足贫困文化的理论认为,贫困地区民众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而逐渐地形成了一套导致贫困得以延存的固化文化体系,若要打破这一体系,就要对其固有存续的习惯、风俗、心理定势、心态以及价值理念加以解构与重构,为贫困文化的彻底转化创造条件,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结构的变迁。笔者在这一学术研究理论框架下,对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进行反思,以勾勒出扶贫开发的有效路径谱系。
一、文化扶贫的历史背景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曾说:“人类越是发动对其古老敌人——贫困和愚昧的战争,也就越是发动了对自身的战争”。因此,摆脱文化贫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贫困地区摆脱贫困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交通不便与文化落后。而一旦文化落后,本区域就缺失了发展经济的潜力,导致了经济贫困,进而为文化扶贫的推进设置了障碍。
文化扶贫是近些年来流行的时髦话题,其主旨就是通过现代观念的养成,使贫困地区的人文素养以及人口整体素质得以提高,其中“扶人”是主要手段,终极目标是人的素质的脱贫。
贫困地区甘肃省定西市2014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1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600元[1](笔者注: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8500元),这一经济状况制约了当地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就基本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来看,定西当地目前共有艺术表演团体6个,文化馆8个,公共图书馆8个,博物馆8个,档案馆8个,有线电视用户9.7万户,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5.79%(全国为98.0%),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6.75%(全国为98.6%)[1]。而地处沿海发达省份的杭州市,2014年末全市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21个,文化馆15个,公共图书馆15个,图书馆藏书1700万册,800余万市民卡用户免费开通图书借阅功能。同时,杭州市还建成街道(乡镇)、社区(村)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427个,图书流通点2166个[3]。与之相比较,有着300多万人口的定西市,基本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是不足的,这对于当地文化扶贫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是巨大的,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提出:初等文化层次的人,劳动生产率能提高43%;高等文化层次的人,劳动生产率能提高300%。若从生产方式考量,手工业者人均产值一般是1000元,传统工业生产者人均产值为1万元,而高科技的产业工人的人均产值则达到10万元。文化扶贫就是从这一思路出发,给人输入文化的因子,进行智力开发,最大限度地输出财富,实现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
文化扶贫是文化力助推贫困地区脱贫的实践尝试,与传统的物质扶贫、政策扶贫等方式相比较,是一种新型的扶贫方式[3]52-55。1986年,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以来,文化扶贫一直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1992年,由文化部发起的万里边疆文化长廊计划,启动了一批文化项目和文化扶贫活动。1993年12月,鉴于文化扶贫的重要性,文化部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专门领导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的开展。此后,文化扶贫工作以项目为依托,深入开展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工作,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文化下乡等。2008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正式启动了文化扶贫工程,具有全球视野和现代理念也更为系统的文化扶贫工作就此推开,十项文化扶贫工程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二、一种文化扶贫的理论范式
1.贫困文化理论的学术意蕴。文化功能主义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包含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即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4]50。长久以来,理论界关于文化扶贫的探讨很多,如有学者认为文化扶贫的目的是提升当地民众的文化素养,有学者认为文化扶贫就是立足当地文化资源存量开发区域文化产业。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贫困地区的贫困根源于贫困文化。所谓贫困文化,是指贫困地区的民众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逐渐地形成了一套固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自卑、无助、缺乏安全、不求上进、固守旧有的生活方式、视野狭窄等等。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历史与文化传统存在多样性。因此,不同区域的贫困文化呈现出差异性,但从根本看,落后的价值理念与消极的人生哲学具有共通性。
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贫困文化的理论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指大多数人达到了中等以上生活水平,但还有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状态,这部分群体逐渐形成了一套导致贫困得以延存的固化的文化体系[5]66;二是贫困文化就是贫困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是指这一阶层人群普遍存在习惯、风俗、心态和价值理念等非物质形式[6]17-20;三是贫困文化是一类根植于贫困经济但又能反作用于经济贫困的文化,贫困经济与贫困文化紧密缠绕、互为因果[7]47-49;四是贫困文化是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贫困的物质形式与非物质形式之间相互制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转化[8]158-162。以上关于贫困文化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贫困的根源,对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富有启迪。
2.贫困文化理论的学术审视。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对贫困现象进行解读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在以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为个案研究的《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研究时他将在社会权力体系中边缘化的、饱受贫困压力的人群被动和消极回应贫困的生活态度称为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认为这种亚文化对其成员和社区产生了一种消极的社会和心理影响。面对贫困,生活在社区中的人群缺乏情爱,缺乏愉悦和满足感。在饥饿的压力下,精神萎靡(malaise),酗酒成风,性行为泛滥,与外界交往时缺少应有的斯文和谦让。奥斯卡·刘易斯得出结论:“在贫困阶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这种病态价值信仰系统的贫困文化,导致了他们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与走向社会上层。长此以往,他们形成的相悖于主流社会的这种亚文化开始固化,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1961年,奥斯卡·刘易斯在《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中对贫穷文化做了进一步阐释:“对那些认为贫穷就没有文化的人而言,贫穷文化这个概念仿佛成了自相矛盾的话语。这也似乎会给贫穷以某种自豪和显要。我的初衷并非如此。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结构,可以世代相传。在用文化这个概念来理解贫穷的时候,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现代国家的贫穷不仅是经济上的无组织状态,更意味着某些积极的成分,它存在着某种结构,某种理据,甚至使穷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某些防卫机制。简而言之,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对家族成员来说,贫穷文化具有自身的模式以及明显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它是影响其融入更高层次的全国性文化的重要动因,是自成一体的亚文化”。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重新审视贫困文化时,认为贫困主体毁灭性的态度和行为不是道德固化的产物,而是由种族和社会隔离导致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J.Sampsonn)聚焦贫困结构研究时提出:“社区无法摆脱贫困陷阱(poverty trap),与社群(community)中人们思想与行动的共同认识相关”。通过考察墙上的涂鸦和垃圾的堆放以及测试邮寄误投等行为,罗伯特·桑普森得出结论:“收入的高低不能完全解释贫富差距,社区的文化规范、价值理念、道德讥讽和秩序混乱程度在评估现实贫困水平方面应该更有解释力”。
3.文化贫困理论视阈下的贫困表现。著名反贫困理论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贫困与民众宿命论观念、对改变观念与制度、维护现代技术、改善卫生条件等的麻木和冷漠相关”。所以,我们从贫困文化的角度出发,发现不同区域的贫困表现具有同一性。一是思想观念滞后。在贫困地区,民众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前,无暇顾及饮食结构是否合理,更谈不上养生乃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受传统观念影响,无后不孝、重男轻女等观念在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生育过多,家庭规模扩大,消费支出上升,家庭劳动强度加大,成员精神负担加重,投入生产活动的精力减少。同时,由于我国开启经济现代化的时间较晚,生产力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再加上受到小农传统思想的影响,民众在生产过程中不考量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继续延续着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恶性循环成为常态,越种地越穷,越穷思想越落后,思想越落后,越害怕风险挑战,迫不得已最后还是选择种地。观念上的这种落后,导致了经济上的贫困。
二是受教育程度低。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中国农民崇文尚贤的优良传统逐步开始消解,读书无用论在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普遍流行,迫使有助于农业生产的现代科学技术游离出乡村场域。国家尽管强制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贫困地区儿童辍学率很高。即使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也是获得了最基本的知识教育,现代科学知识和理念是否武装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是否获得了摆脱贫困的知识与技能,他们是否坚定了锐意进取、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决心,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何况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还需要另论。而要彻底走出贫困,就需要有效地隔离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解构贫困文化复制贫困的功能。
三是价值观念消极。贫困地区由于受到文化贫困的影响,贫困价值理念盛行,主要表现是: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只求温饱的消费观、安土重乡的乡土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这种贫困价值观充斥于社会生活,逐渐消解了农民敬业、创业和节约等精神。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消费社会的出现,它极其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并不断破坏着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
三、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路径选择
美国学者D.P.莫伊尼汉在《认识贫困》一书中研究了贫困恶性循环模式,其主要观点:一是贫困地区的人们,由于长期受到贫困文化熏陶,缺乏积极向上的动力和较高的动机;二是教育资源的欠缺致使受教育程度低、机会少,在就业上没有竞争力优势,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三是较低的收入和较低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化,形成恶性循环。
文化扶贫,就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改造贫困文化,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使形成的文化力反作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在路径的选择上,需要我们进行理性的分析。
1.加强制度设计。有计划、有步骤地构建县、乡、村、组四级文化组织,并做好各级文化组织的在场评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美术馆、文化中心等文化组织,属于公益型事业单位,其所需的基本经费应由财政供给,政府不能放手推向市场任其生死由之。
以马家窑文化的命名地——甘肃临洮县为例。近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先后投资1495.3万元,实施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三馆一站”免费开放等文化惠民项目,并建成17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和324家农家书屋,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城乡全覆盖。并且,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近年来先后开展了大型文艺汇演70余场次、大型书画展36场次,送戏下乡、文艺演出等活动2800多场次[9]。截至目前,全县共投入文化场所建设资金8100多万元,其中今年投入65万元,调动社会资金投入800多万元;建成“乡村舞台”168个,组建文艺团体347个,挖掘、培养群众文艺骨干3400多人,参与群众达30万人次[10]。在贫困地区,当地政府积极在场助推文化建设,有益于文化扶贫开发平台的构筑,也有助于农村文化生活环境和农民爱美求乐精神文化氛围的营造。
在做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各部门理应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和社会需要,可以供给有偿服务项目,通过市场的选择机制把较好的文化产品输送给更多民众。如兴办文化产业,推动文化旅游,既可以获取直接的经济收入,又可以促使各部门自身设计方式的改变,更可以为当地民众的现代公民观念的养成提供环境支撑。
2.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念。将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归结于文化素质低下、观念落后、没有发展意识,已经是一种普遍看法。所以,文化扶贫就不仅要消除落后思想的观念,还要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用现代的价值观念替代原有的思想观念[11]46-54。
当然,现代价值观念的元素很多,最基本的元素包括勤劳、朴实、创新、进取、务实等。“勤劳、朴实、务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精神的高度凝练与生动表达;“创新、进取”是全球现代化背景下时代发展赋予的迫切要求,彰显了时代精神,是破解贫困地区“勤劳而不富”命题的最佳选择。
所以,只有全面培育出勤劳、朴实、创新、进取、务实的新时代价值理念,才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通过树立崇高的理想凝聚力量坚定自信,也才会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激发出个人潜能,更好引导当地民众在思想意识与精神素养方面向积极健康的价值维度转化,塑造出民众的现代文明意识与文化精神,使这种意识成为流动在民众血脉中的一种品格和基因,为实现当地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作用。
3.选好文化载体。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存量。收集、整理、挖掘民族民间音乐、歌舞等非物质文化,开发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开发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经济链条,把贫困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推介给外界,从而助益于地方文化产业的开发。
文化产业是将源于个人的创意和才能,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形成的具有创造财富、提高公众美学素养和提升生活环境的新型产业。从当前社会生态看,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文化形态的保存较为完整,发展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文化扶贫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地处陇中的贫困地区定西市为例,当地被列入国家、省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分别达7项、34项和231项。据不完全统计,仅全市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分为民间口述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民间工艺、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山场民俗等九大类2000余种[12]。这些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4.加强教育供给,剪断贫困文化复制的链条。约翰·梅尔认为:“教育在激起农民思想变化方面作用显著,因为它不仅能够拓展农民自身和子女的视野,还能引起其消费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为农民及其未来提供实行变革的方式,进而激起他们积极主动地开始变革”。
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教育,最关键的是要加大科学技术资源的投入。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他们具备市场思维,实施订单农业,通过市场途径把产品货币化、货币资本化、资本财富化;另一方面,可以重塑他们的心理结构,消除心理羁绊,在乡土文化重建中,形成现代价值理念,以一种健康的心态投身于脱贫致富的变革中。同时,还需要改造贫困文化传递的载体——子代贫困群体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与劳动技能,通过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承彻底实现脱贫并不再返贫。
总之,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人的文化水平与精神层次得到了提升,才会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工作的路径选择需要结合地文特征进行理性思考与设计,这样,才会有助于整体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定西市统计局.2014年定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定西日报,2015-04-01(3).
[2]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杭州市社会经济调查局.2014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杭州日报,2015-03-03 (A05).
[3]李云.文化扶贫: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战略选择[J].民族论坛,2012(22).
[4]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宋镇修,王雅林.农村社会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6]吴理财.论贫困文化(上)[J].社会,2001(8).
[7]李瑾瑜.贫困文化的变革与农村教育的发展[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1).
[8]方清云.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及对策建议[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9]穆军学.临洮:公共文化发展火热[N].定西日报,2015-04-15(1).
[10]于欣雨,汪贵林.临洮:“乡村舞台”助力精准扶贫[N].定西日报,2015-11-02(3).
[11]王建民.扶贫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少数民族主体性讨论为核心[J].民族研究,2012(6).
[12]王栋.努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N].定西日报,2013-09-19(3).
(责任编辑潘京)
The Thinking of 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Poverty-stricken Area
ZHANG Shid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Party School of CPC Dingxi,Dingxi 743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ctively promote realiza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poor areas. To boos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 thorough development, the path selection is diversity. The 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cho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is. Based on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of poverty culture theory to interpret the poverty in poor region, the negative factors like thought idea lag and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values severely restricts the local people out of poverty to become rich. As a result, the local 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will need to change from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people's idea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education resource supply and so on to carry on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so that the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ltimate goal.
Key words: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stricken areas; culture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326(2016)01-0060-04
【作者简介】张世定(1981-),男,甘肃天水人,中共甘肃定西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乡村经济。
【收稿日期】2015-12-28
DOI:10.13600/j.cnki.jpsslof.issn.1009-4326.2016.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