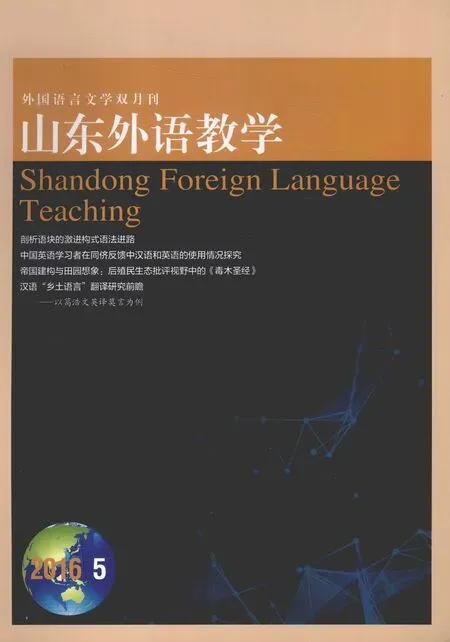“物质无意识”:物质文化视角中的福克纳环境书写
2016-04-10韩启群
韩启群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物质无意识”:物质文化视角中的福克纳环境书写
韩启群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物质文化视角为解读福克纳作品中各种物质细节书写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斯诺普斯三部曲中各种和木头相关的“物质无意识”书写所汇聚的物质体系呼应了南方特定历史时期环境破坏的各个节点,揭示了福克纳对于他所处时代南方腹地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的回应和矛盾态度。此外,和木头相关的“物质无意识”书写标记了以变迁书写见长的大师在宏大变革语境中呈现环境的独特审美意蕴。
威廉·福克纳;斯诺普斯三部曲;环境书写;“物质无意识”; 物质文化视角
1.0 引言
在1996年福克纳国际研讨会上,劳伦斯·布尔在论文“福克纳与自然世界之道”中首先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福克纳《八月之光》的开头:
村里的男人不是在这家伐木厂里做工,便是为它服务。他们主要砍伐松木,已经在这儿开采了七年,再过七年就会把周围一带的松木砍伐殆尽。然后,一部分机器,大部分操作这些机器的人,靠它们谋生的人和为他们服务的人,就会载上货车运到别的地方去。由于新机器总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添置,有些机器便会留在原地……(福克纳,2004:2)
这段不太引人关注的描写原本只是介绍小说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莉娜哥哥的职业和工作场所,但在美国生态批评执牛耳者劳伦斯·布尔看来却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玄机,“书写了南方腹地木材工业从砍伐到运输的简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的过度利用和长久消耗”。(Buell,1999:2)文学作品的背景书写常常不引人注目,布尔却从小说开头和伐木厂相关的细节书写中连根挖出密西西比一段环境改变的历史,着实让评论界“感到耳目一新”。(Kartiganer,1999:viii)布尔的这篇论文发表于90年代末,文学批评中的物质文化视角尚未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物质转向”(Bennett & Joyce,2010:5)催生了文学批评领域对物质细节书写的浓厚兴趣,提醒研究者要像“读书”那样去“读物”,“去理解制造、使用、丢弃物品的人和时代”。(Lubar and Kingery,1993:viii)如何在新的话语语境中重新审视福克纳作品中与特定历史语境相关的物质细节书写,如何借助新的批评视角评价以细腻物质细节书写见长的福克纳的审美格调,这是本论文希望在劳伦斯·布尔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引申的话题。
布尔在研究中重点关注了《八月之光》开篇的伐木厂意象,将此作为密西西比环境破坏的重要隐喻。值得关注的是,福克纳关于南方木材工业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八月之光》小说的开始,紧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开头描述了杰斐逊镇的刨木厂,莉娜一路上看到的也多是“锯好的木材和堆成垛的木板”(福克纳,2004:37);各种和木材工业相关的琐碎细节也不仅局限于《八月之光》这一部小说,比如在斯诺普斯三部曲中,南方腹地的森林、道路两旁的树木、被砍伐的木头、各种木头制品等随处可见。长期从事物质文化研究的比尔·布朗曾独创“物质无意识”(The Material Unconscious)概念来指涉文学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和特定历史时期相关的物质细节,并示范性地运用“物质无意识”概念考察了斯蒂芬·克兰作品中各种日常琐碎物品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如何想象和建构了美国1890年左右的文化历史。布朗的研究引导批评者关注文学文本中物质文化层面,聚焦一个时代的“不引人注目的外表层面的表达”。(Kracauer,1979:75)受比尔·布朗启发,本论文拟从福克纳斯诺普斯三部曲中各种和木头相关的“物质无意识”书写入手,探析三部曲中和木头相关的物质细节如何呈现隐含在文本深层的、和特定时代相关的文化轮廓和意义结构,并以此为切口,透视福克纳环境书写的独特审美意蕴。
2.0 何为“物质无意识”?
在《物质无意识:美国娱乐、斯蒂芬·克兰以及游戏的经济》(简称《物质无意识》)中,比尔·布朗(Bill Brown)创造性地提出了“物质无意识”概念来指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细节,其特点是“各不相同、片断式地呈现、发展不均衡、甚至互相矛盾”,而且在文本中频繁出现、“指涉过量”(referential excess)。(Brown,1996:13)杰伊·沃特森认为在文本中出现的不同方式是甄别“物质无意识”所指涉的物质意象和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题意象(motif)的关键。虽然这两个概念都可以指涉文本中的物质意象,而且都可能在文本中频繁出现,但是,主题意象在文本中的出现往往是有组织、有条理的,隐含着一致感,常常是作者在文本中有意要表现的某个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意象,和主题密切相关。布朗所指涉的“物质无意识”细节常常是前后不一致,没有条理,只是特定历史时期日常生活中各种琐碎物品在文本中留下的物质痕迹,常常缺乏明确的象征意义,“本意并不是要表现主题或情节”。(Watson,2007:15)
文学文本中各种缺乏明确象征意义的“物质无意识”细节在布朗看来有着重要的解读价值。在《物质无意识》的导言部分,布朗梳理了各种和“无意识”相关的话语传统,包括本雅明的“视觉无意识”、马歇雷的“意识形态无意识”和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认为历史不应该只包括马歇里、詹明信所说的关于生产模式和反映阶级冲突的叙事方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应该包括那些“轻描淡写的、‘亚历史’的片段”(undernarrated, ‘subhistorical’ fragments),即一个时代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外表层面的物质细节。(Brown,1996:24)通过考察文学作品中的“物质无意识”,或者说文学文本中那些不引人注意的、不连贯的物质细节和记录,不但可以揭示日用物品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可以重新想像和建构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还可以深入理解作家在文本中传达的对特定时代的思考和探索。
布朗在赋予文学文本中的各种物质细节特殊的认知意义的同时,也相应提出了考察“物质无意识”的批评方法。他用“剩余物质性”(surplus materiality)来概括“物质无意识”所指涉的物质细节的特点,将它们比作“生命短暂却获得历史性的浮游生物”,潜伏在文本中,“一定意义上不被识别,但可以使文本保留现象残余”。(Brown,1996:3-5)因此,他建议批评者在分析某一文学作品时,要做一些“归档整理或考古的工作”(archivalarchaeological task),比如,在文本表层的物质细节之间“建立一系列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一旦被回顾,就在文本中汇聚到了一起”。同时,批评者要进行一些分析工作,要呈现出这些意象的汇聚,这种汇聚能够“生动说明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结构和物质改变”。(同上:4-5)这样一来,那些浮现在文本表层的不引人注目的物质细节就能够揭示出它们所处空间和时间的文化逻辑。由于作家总是处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在作品中出现的日常物质细节往往和所处环境和时代密切相关,因此,布朗认为“物质无意识”的内容会特别局限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和经济的产物。
比尔·布朗的“物质无意识”研究在伊莲·弗雷德古德(Elaine Freedgood)看来是一种“转喻式的阅读”(metonymic readings)方法,即通过汇聚文本中琐碎的物质细节,理解和建构与之相关的整体。在《物中的观念:维多利亚小说的隐藏意义》中,弗雷德古德倡导要尽量摆脱传统批评中类似意象批评的隐喻式阅读模式,将文本表层的物质细节书写看成是历史文本的转喻。而且,在转喻式阅读中,“物被从自己的属性和历史来研究,然后以此来反观重新塑造小说的呈现或主导叙述——只关注主体的”。(Freedgood,2006:12)由此可见,布朗的“物质无意识”概念要求批评者汇聚那些在文本中前后不一致、看似显得“过度”或“多余”的物质细节,并从这些细节入手,通过物质体系、或者物品之间的关系来“挖掘出那些潜伏在被忽视的意象、习惯和物品中的历史”(Brown,1996:5),通过物质细节汇聚后的象征体系来揭示小说的主题表达。
比尔·布朗的“物质无意识”概念为深入解读作家作品中各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细节提供了新的批评路径,也为本论文重新反思福克纳如何借助物质细节书写诠释南方社会转型期的独特历史语境提供了新的视角。
3.0 与木头相关的“物质无意识”书写
斯洛普斯三部曲包括《村子》、《城镇》、《大宅》,因主要讲述贫穷白人弗莱姆·斯洛普斯的发迹史和衰落史而得名。作为福克纳后期重要作品,三部曲的创作语境主要对应了詹姆士·C·考伯(J.C.Cobb)所归纳的“第二个新南方”时期。这一时期“自二战后就不断显现出来”,“其种族、政治、经济制度的剧烈变革为南方迅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生活铺平了道路”。(Cobb,2005:2)在三部曲中,各种和木头相关的书写呈现出比尔·布朗所提出的“物质无意识”的特征,“对木头和木头制品的描述不断地出现在语言和文本的意象中,常常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但又显得微妙突然”。(Watson,2007:22)不同层面的木头书写各不相同,有的是木头的直接呈现,如树木本身、堆放的木板等,有的是木材加工场所,如锯木厂、刨木厂等,还有的是木头加工后的残渣,如锯木屑、锯木棍等。此外,三部曲中常会不经意地提及老法国人湾的小约翰旅馆、村民们的住房、存放粮食的马棚等都是用木板建成的。小说中很多人物的工作场所都是锯木厂,明克从监狱释放后在回到杰斐逊镇的途中做了短暂的木工,任务是把木头锯成木板。这些散落在文本表层的和木头相关的物的书写是南方特定历史时期日常生活留下的物质痕迹,呼应了20世纪上半叶密西西比地区和木头相关的物质文化。
对于具体作家而言,其所处的物质世界不但是“个人经验的一部分”,也是“写作的一部分”。(Stout,2005:10)密西西比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无疑和福克纳创作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平行,其作品中大量与木头相关的物的书写就是明证。但是,这并不代表福克纳不同作品中木头书写的审美内涵完全一致。杰伊·沃特森认为《八月之光》中锯木厂、刨削车间、刨削机、家具卡车等物的书写“创造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经济微情节”(Watson,2007:29),代表了“关于物的全面而又复杂的现代经济的发展阶段:森林材料的运出——锯木厂将树锯成木料——将木头刨好,增加了价值——木头产品的销售和最终的消费,沿着不断发展的公路和铁路网络”。(同上:25)和《八月之光》相比,三部曲更多地涉及了荒废的锯木厂、废旧的木头、毁坏的木头、木头的残渣等物质细节,如果将这些意象汇聚起来考察的话,三部曲中的“物质无意识”书写不但呈现了不一样的意义结构,而且对于考察福克纳的环境书写很有启发。
首先,作为20世纪众多作家笔下的重要场景细节①,锯木厂意象频繁出现在福克纳多部作品中,三部曲也不例外。和《八月之光》一样,三部曲中锯木厂也是人物刻画的重要手段,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在锯木厂干活或者自己经营锯木厂的经历,人物的对话也常常提到在锯木厂工作的情形。但是,和福克纳早期作品中锯木厂的勃勃生机相比,三部曲中的锯木厂呈现却显得颇为萧条:
奇克索印第安人曾经拥有这一地区,不过在印第安人走了之后.这里的林木就被清理干净,使得谷场的耕种成为可能,而且在南北战争以后,这里就被人遗忘了,仅有一些四处流动的锯木厂,现在这些锯木厂也都不见了,它们的所在地只是由腐烂的锯木屑堆垛标示出来,这些木屑堆垛不仅是他们的墓碑,也是人们不经意的贪婪的见证物。(福克纳,2001:233)
在《八月之光》中,锯木厂是“现代经济的发展阶段”的一个节点,而在这一段描写中,林木已经被“清理干净”,曾经的锯木厂如今只留下“腐烂的锯木屑堆垛”,成为人们“贪婪的见证物”。此处,锯木厂显然和南方破坏的生态环境相联系,成为密西西比森林消失过程中的一个节点。
除了锯木厂,小说中还多处不经意地涉及废旧的木头、毁坏的木头、木头的残渣等各种“工业残余”(industry’s leavings)细节。②比如,《村子》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多和废旧木头相关的书写。福克纳不但提到老法国人湾“藤蔓与柏属植物交错丛生的树林”,也刻画了成为残垣断壁的木头,有的类似“核桃木立柱、螺旋楼梯中心柱”等,50年后会成为古董,而有的则“30年来一直当成柴火烧”。(福克纳,2001:1)此外,小说中多处提到木头被加工后的废旧物品,如锯木堆、碎木头块儿、锯木屑等,这些木头残渣或者被用来烧火,或者被遗弃在布满灰尘的角落。木头的“毁坏”、“废旧”、“残余”成为南方环境破坏的另一个节点,而各种伐木、锯木带来的“工业残余”最后被烧掉的细节则呼应了南方森林一步步被破坏,最后彻底消失的过程。
此外,三部曲中还有一些和木头相关的细节,虽不为人注意,但却非常耐人寻味。比如,小说常常会提及老法国人湾村民们边聊天边削着木头,或者嘴里咬着木枝作为消遣。村民们削木头并不是要将木棍加工成什么工具,完全是出于一种习惯。破坏木头似乎成为南方村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另一个侧面也指涉了南方环境改变史对南方居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中还会不经意地提及南方居民被木头伤害的情形。在《城镇》中,艾克·斯诺普斯在老瓦纳的锯木厂干活时被木头击中脖子,从此脖子上安置了一个固定支撑物。在美国南方,“要想被选进办公室工作,要么抚养七到八个孩子,还要在锯木事件中少掉一条腿或胳膊”。(Faulkner,1957:185)
原木被砍伐、锯木厂加工为木头、木头产生出“工业残余”、“工业残余”的彻底消失、环境对人的复仇,如果将这一系列和木头相关的“物质无意识”书写汇聚起来的话,实际上对应了南方森林如何被木材工业一步步破坏的物质体系。由此,一个隐含在文本深层的特定时代的文化轮廓就慢慢剥离出来,揭示了自内战后南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森林遭受的破坏和南方生态的改变,以及环境改变所导致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深刻变革。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和木材工业相关的物质体系在三部曲中被塑造为密西西比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这种过渡强调如果结合福克纳创作的历史语境来看,也是福克纳对主流意识形态中木材工业积极作用不断美化的独特回应。因此,三部曲中的“物质无意识”书写也为考察福克纳关于南方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的立场提供了重要切口,进而可以帮助透视福克纳如何在宏大变革语境中呈现环境的审美特征。
4.0 福克纳环境书写的审美意蕴
在内战后南方工业化的历史语境中,木材工业为南方社会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原先靠棉花种植业维持生计的贫穷白人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客观上“消除了南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Hickman,1962:251),因此,木材工业在国家宏大叙述层面被赋予了很多积极的意义,一度被美誉为南方“社会经济的安全阀” (social and economic safety valves)。(Clark,1984:34)木材工业也顺应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强调,成为主流文化制造的众多“神话”之一③。
木材工业在福克纳作品中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层面被提及,比如《八月之光》中木材工业的“砍伐—运输模式”(Buell,1999:3),《去吧,摩西》中砍伐木头的火车轰隆隆开进三角洲森林运送原木的场景,而三部曲中则是南方森林因为木材工业而被破坏并最终消亡的各个节点展示。这些环境书写表面上丰富多元,但都将木材工业呈现为生态破坏的始作蛹者;各种和木材工业相关的废旧物品意象和主流文化中树立的木材工业充满活力的正面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了福克纳对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质疑,也体现了他对变革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悖论议题的反思。
毋庸置疑,福克纳对战后南方发展经济过程中过度掠夺环境的行为持谴责态度,这一点从他在描写荒废的锯木厂时用的“墓碑”、“贪婪”等词可以看出。他在多部作品中聚焦了木材工业的破坏作用,表明他对密西西比环境保护的积极吁求。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福克纳因为环境保护而激烈地反对经济变革和技术进步。在随笔《密西西比》中,福克纳一方面质疑了经济变革和技术进步对于地区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改变本身的不可避免。他以一个中年人的口吻表明了自己对于不可阻挡的变革的矛盾态度:
深深地爱着这里虽然他也无法不恨这里的某些东西,因为他现在知道你不是因为什么而爱的;你是无法不爱;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好的东西,而是因为尽管有不美好的东西你也无法不爱。(福克纳,2008:43-44)
同样,他在1947年致信给《奥克斯福鹰报》(OxfordEagle)编辑时一边盛赞该报社“主张保存法院建筑一文精彩至极”,但另一方面他却悲观地觉得这种主张“注定要失败”,因为再“坚强”的建筑也“不如一台现金出纳机响起的铃声坚强”。(福克纳,2008:208)
和激烈反对工业文明的南方重农派作家们(Twelve Agrarians)相比④,福克纳对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态度更为复杂,常常给人感觉“模棱两可”,因此被有些评论者认为“从来就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环境伦理”。(Buell,2001:176)笔者认为,福克纳对于南方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悖论关系的矛盾立场标记了他的环境书写的两个重要审美特征。首先,三部曲中和木头相关的“物质无意识”书写呈现了南方森林被破坏的各个节点,这种节点展示的策略也是一种抓住冲突过程的演示。换言之,福克纳在创作中专注于矛盾本身,意在激发思考,而非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其次,从各种砍木头、锯木头、烧木头、削木头等相关木头书写场景在三部曲中汇聚成的物质体系来看,福克纳特别关注变革带来的景观破坏的过程,尤其南方现代化带来的损失和失败。“毁坏”、“废旧”、“残余”等具有衰败叙事特征的物质细节书写也流露出作家对于环境改变的“注定的荒凉”的一种无奈(同上),正如查尔斯·S·艾肯(C.S.Aiken)所言,“尽管福克纳很少怨恨或抵制各种改变,但是他对某些特别景观的改变会感到悲叹,无论是老密西西比荒野的破坏,还是他喜爱的古老建筑遭到毁坏。(Aiken,2007:15)
和美国文学中的梭罗等作家相比,福克纳算不上一个纯粹的环境作家,他的环境书写更多地可以被理解为他关注南方历史转型期文化变革的一个方面,是他思考南方变革书写的一种方式,因为他的南方书写离不开南方环境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部曲中和木头相关的“物质无意识”书写不但想像和建构了美国南方腹地特定历史时期环境破坏的一段历史,揭示福克纳对于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的回应,也标记了这位擅长变迁书写的大师在宏大变革语境中呈现环境的独特审美模式和文化意蕴。
注释:
① 锯木厂是20世纪多位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意象,比如《飘》中的郝思嘉向白瑞德借钱买下一家锯木厂;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的第一章便出现锯木厂意象;很多作家本身也和锯木厂有所关联,雷蒙德·卡佛的父亲曾在锯木厂工作,海明威传记作家多次提到海明威家的窗子正对着堆木场和锯木厂。
② 劳伦斯·布尔曾用 “工业残余”(industry’s leavings)一词来指涉福克纳作品中各种和枯萎景观相关的意象,认为福克纳用夸张的风格传达了对人类破坏自然的丑陋行径的谴责。此处笔者借助这一术语指涉福克纳笔下各种木头被加工后的废旧物品。参见Lawrence Buell(2001)第174页。
③ 迈克·卡门认为,在历史的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生产出很多“神话”来加强统治,而“1870-1930则是美国神话最多产的一段时期”。 参见Michael Kammen(1991)第28页。
④ 南方重农派作家们在《我坚持我的立场》中激烈地反对美国工业模式中的大众文化,对于主流大众文化对南方传统艺术的影响感到深恶痛绝,希望通过倡导一种南方传统农耕文明来反对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的进步和民主。参见Twelve Agrarians(1977)前言。
[1] Aiken, C.S.Faulkner and the passing of the old agrarian culture[A].In R.U.Joseph & A.J.Abadie (eds.).FaulknerandMaterialCulture[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7.3-19.
[2] Bennett, T.& P.Joyce (eds.).MaterialPowers:CulturalStudies,HistoryandtheMaterialTurn[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0.
[3] Brown, B.TheMaterialUnconscious:AmericanAmusement,StephenCrane,andtheEconomiesofPlay[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Buell, L.Faulkner and the Claims of the Natural World[A].In D.M.Kartiganer & A.J.Abadie (eds.).FaulknerandtheNatureWorld:FaulknerandYoknapatawpha1996[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
[5] Buell, L.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intheU.S.andBeyond[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Clark, T.D.TheGreeningoftheSouth[M].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4.
[7] Cobb, J.C.From the First New South to the Second[A].In C.S.Pascoe, K.T.Leathem & A.Ambrose (eds.).TheAmericanSouthintheTwentiethCentury[C].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5.1-15.
[8] Faulkner, W.TheTown[N].New York:Random House, 1957.
[9]Freedgood, E.TheIdeasinThings:FugitiveMeaningintheVictorianNovel[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10] Hickman, N.MississippiHarvest:LumberingintheLongleafPineBelt, 1840-1915[M].Jackson: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62.
[11] Kammen, M.MysticChordsofMemory:TheTransformationofTraditioninAmericanCulture[M].New York:Knopf, 1991.
[12] Kartiganer, D.M.Introduction[A].In D.M.Kartiganer & A.J.Abadie (eds.).FaulknerandtheNatureWorld:FaulknerandYoknapatawpha1996[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ii-xix.
[13] Kracauer, S.The Mass Ornament[A].In T.Y.Levin (ed.).TheMassOrnament:WeimarEssays[C].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4] Lubar, S.& W.D.Kingery (eds.).HistoryFromThings:EssaysonMaterialCulture[C].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15] Stout, J.P.Introduction[A].In J.P.Stout (ed.).WillaCatherandMaterialCulture[C].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5.1-14.
[16] Twelve Agrarians.I’llTakeMyStand:TheSouthandAgrarianTradition(1930)[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7] Watson, J.The Philosophy of Furniture, or Light in August and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A].In J.R.Urgo & A.J.Abadie (eds.).FaulknerandMaterialCulture[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7.20-47.
[18] 威廉·福克纳.村子[M].张月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9] 威廉·福克纳.福克纳随笔[C].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0] 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M].蓝仁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and William Faulkner’s Environmental Writings: A Material Cultural Perspective
HAN Qi-q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ritings of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connected with wood in William Faulkner’s Snopes Trilogy from the material cultural perspective, explores how the entire wood objects correspond to every stage of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in the specific period of American South and furthermore uncovers Faulkner’s special aesthetic features in writ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The writing of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connected with wood in Snopes Trilogy implies Faulkner’s response and self-conflict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huge social changes of the American Deep South in his time.Faulkner’s special preferenc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environment in a grand context of change highlights his unique aesthetic features of environmental writings.
William Faulkner; Snopes Trilogy; environmental writings;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material cultural perspective
10.16482/j.sdwy37-1026.2016-05-010
2016-02-22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文学的道德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3CWW02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2015年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资助。
韩启群,女,江苏南京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物质文化及批评视角研究、美国南方文学研究、福克纳研究。
I106
A
1002-2643(2016)05-007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