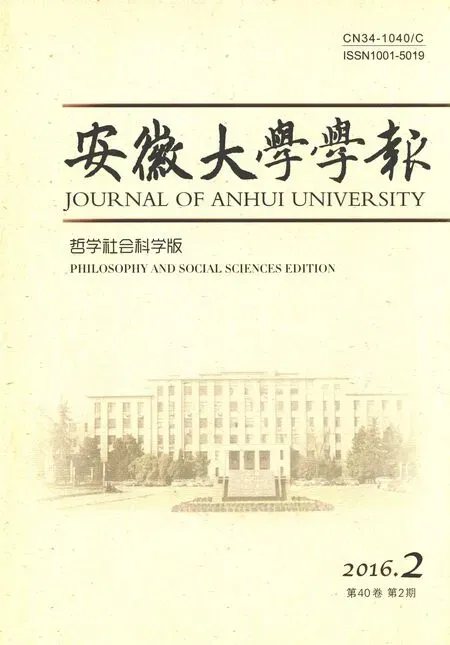唐宋、才学之争的消弭——乾隆间性灵诗学引发的焦点话题
2016-04-09蒋寅
蒋 寅
唐宋、才学之争的消弭
——乾隆间性灵诗学引发的焦点话题
蒋寅
摘要:袁枚性灵诗学整体上颠覆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后,在诗学理论中产生强烈震动,促使学人对传统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重新加以思考。其中与唐宋诗之争、传统和个人才能相关的论争是当时诗坛最关注的问题,许多重要诗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形成乾隆诗学的焦点话题。由唐宋诗之争入手,分析其诗学话语背后的诗歌史和诗学史背景,以及传统的才学之争在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三个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和发展趋向。
关键词:唐宋;才学;乾隆诗学;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
文学乃至艺术的全部问题,就是T.S.艾略特那篇著名论文的标题所概括的《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关系。在叶燮之前,各种诗学的论争都集中于如何在两者间取得平衡。自叶燮取消艺术理想的预设,袁枚整体上颠覆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后*这一问题系我在《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并加以阐述。,诗学的核心问题便由如何实现理想的艺术目标转移到如何发挥个人才能上来,由此产生的骨牌效应在诗学理论中产生强烈震动,引发若干与重新认识传统和个人才能相关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虽有学者提到*如贺国强、魏中林《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李金松《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划分及其诗学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二文。,但未注意到它们与乾隆间性灵诗学的关系,本文拟就此做进一步的阐发。
一、唐宋诗之争的消泯
自宋代以后,唐、宋作为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大高峰,被诗家尊奉为古典诗歌的两大传统,而诗家对唐、宋诗之异同及褒贬则从宋代就开始各执己见,争议纷纭,历元、明而加厉。入清以来,康熙间对宋诗的拂拭和肯定,曾引发折衷唐、宋的趋向,黄宗羲、王士禛、吴之振、宋荦、邵长蘅都是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名声稍亚的,还有魏礼一辈,认为:“唐人之诗尚风格而次脉络,足以移人情;宋人之诗工切而整妥,足以敦吾学。合唐宋之诗之佳,正可兼收也,而杜少陵能之。要之在吾有自得之妙而已。”*魏礼:《答沈仲孚胡若木欧上闲书》,《魏季子文集》卷八,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不过具体到对乾隆诗坛的影响,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有两位诗人,宋荦和吴之振。宋荦在任江苏巡抚期间,编纂吴中文人作品为《吴风》。其中所收不同作者的《宋诗源流论》,很像他在江西任上所试《江西诗派论》,可能也是课士之题*这部分资料为王兵首先注意到,并做初步的研究,参看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第三章“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8~185页。。但用意已由表彰宋诗转向反思宋诗得失及与唐诗的关系,这也是他日常论诗的趣向,否则徐舒一篇不会那么明显地表现出折衷唐宋的倾向,并约略可见叶燮《原诗》的影子:
愚谓论诗无分今古。诗本性情,但取其真而已。能得其真,则自出机杼,无事剽窃,不必学唐而自近于唐,不必避宋而不拘于宋。世之尊唐而黜宋者,固为徇俗之见;而嗜宋而厌唐者,亦属矫枉过正。苟能独摅性灵,不落窠臼,则《三百篇》之旨,当不外是。何有于唐,亦何有于宋哉!*宋荦辑:《吴风》卷一,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这里的“论诗无分今古”“独摅性灵”,都是袁枚性灵诗学的先声。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篇奚士柱之作也提到“抒写性灵”,直接将调和唐、宋与“性灵”联系到一起,预示了后来性灵诗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吴之振则在重刊《瀛奎律髓》序里指出:
时代虽有唐、宋之异,自诗观之,总一统绪相条贯。如四序之成岁功,虽寒暄殊致,要属一元之递嬗尔。而固者遂画为鸿沟,判作限断,或尊唐而黜宋,或宗宋而祧唐,此真方隅之见也。*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1813页。
这一说法随着《瀛奎律髓》流行于世而颇有影响,纪昀批其书,尝称“此论最通”*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附录一,下册第1814页。。要之,从康熙末到乾、嘉之间,论诗不以古今朝代为限,已为诗家通识。正如郭伊云诗所云:“句有劝惩均可取,义归兴比即堪思。性情不以今古异,吟咏岂缘世代歧?”*王奂曾:《郭伊云诗稿序》引,《旭华堂文集》卷四,乾隆十六年刊本。由此出发,“汉魏六朝可以续三百,宋明之诗不可以续三唐乎?”正是很自然的认识。
不过,一种观念要成为流行的主张和普遍性认识,往往需要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加以倡导,将它推到众所关注的焦点位置上。纪昀也曾主张“唐、宋诗各有门径,不必以一格拘也”*纪昀:《删正方虚谷瀛奎律髓》,《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影印镜烟堂十种本,第422页。,并且在实际批评中对唐音、宋调无所偏爱,于其是非得失各有批评*如《纪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郿坞》评:“太涉轻薄,便入晚唐五代恶趣中。”指出晚唐五代诗格调卑下。卷十四《望云楼》评:“纯用宋格,然较胜唐装面空腔。”肯定其为宋格,但承认胜于唐诗的肤廓空腔。。但他终究不以诗名,在诗坛不具有号召力。须待袁枚打出调和唐、宋的旗帜,性灵派诗家群起而响应,这才在乾隆中叶掀起一股折衷唐、宋的诗学思潮。乾隆二十四年(1759)秋,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针对沈德潜的唐宋诗观表达了自己对诗歌因革的看法:
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变而美者有之,变而丑者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变其诗,与宋人无与乎?初、盛一变,中、晚再变,至皮、陆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风会所趋,聪明所致,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尝谓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莫不善于燕哙。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不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册第284页。
在阐明变的必然趋势以及宋、元之变的反常合道之后,袁枚又断然指出:“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弘后始有之。其时议礼讲学皆立门户,以为名高。七子狃于此习,遂皮傅盛唐,扼腕自矜,殊为寡识。”*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2册第284页。此札的写作年月,据范建明《清代诗人施兰垞及其文学活动考论——兼谈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写作时间问题》(《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一文的考证成果。按理说这一论断并不符合诗史实际。唐、宋之纷争明明起于宋代,戴复古从孙戴昺即有《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戴昺:《东野农歌集》卷四,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本。到严羽诗论中乃发展为明显的尊唐黜宋论调。这本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袁枚有意忽略这一点,而将唐、宋门户之启直接与明七子辈联系起来,从而使沈德潜格调派观念的根源与早已为诗家唾弃的陈腐见解捆绑在一起,无须再贴标签,即已满眼臭腐。在随后的《答施兰坨论诗书》中,袁枚更进一步剖析:“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2册第286页。针对施谦来书提到的“唐诗旧,宋诗新”问题,袁枚反诘道:“夫新旧可以年代计乎?一人之诗,有某首新,某首旧者;一诗之中,有某句新,某句旧者。新旧存乎其诗,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谓新旧,仆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奥房,襜襜焉盛服而居;后又有人焉,明堂奥房,襜襜焉盛服而居。子虑其雷同而旧也,将变而新之,则宜更华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压胜矣。乃计不出此,而忽洼居窟处,衣昌披而服蓝缕,曰吾以新云尔。其果新乎?抑虽新而不如其不新乎?”*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2册第287页。后来他又将此意发挥于《随园诗话》中:“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如此一来,唐宋与新旧、工拙的对应关系洒然冰解,“诗有工拙,而无古今”的宗旨从而确立*袁枚:《与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2册第283页。。
袁枚曾说:“杨龟山先生云:‘当今祖宗之法,不必分元祐与熙丰也。国家但取其善者而行之,可也。’予闻人论诗,好争唐、宋,必以先生此语晓之。”*袁枚:《随园诗话》卷七,第168页。他本人的诗歌批评中也随处可见不拘唐宋的论说:
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尝举盛唐贺知章《咏柳》云:“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初唐张谓之《安乐公主山庄》诗:“灵泉巧凿天孙锦,孝笋能抽帝女枝。”皆雕刻极矣,得不谓之中、晚乎?杜少陵之“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琐碎极矣,得不谓之唐诗乎?不特此也,施肩吾《古乐府》云:“三更风作切梦刀,万转愁成绕肠线。”如此雕刻,恰在晚唐以前。耳食者不知出处,必以为宋、元最后之诗。*袁枚:《随园诗话》卷七,第182~183页。
在袁枚看来,诗只有艺术表现的工拙之分,而没有笼统的时代高下之分。他这种不拘唐、宋的观念,固然与乾嘉之际学风融会的大背景有关,但同时也与他诗歌趣味中的一对矛盾相联系。袁枚论诗,注重人生体验和日常生活感受的表达,明显更接近宋诗的精神,可他偏不喜欢宋诗筋骨粗硬的艺术特征,在语言风格上明显倾向于流丽和匀的唐风。口头上不分唐、宋,骨子里其实还是扬唐抑宋,尤其不满于走宋诗路子的浙派*参看《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万柘坡诗集跋》。。只不过这种倾向完全被时人“古人所有公尽有,三唐两宋皆前型”的评价所掩盖*法式善:《读随园先生全集赋呈》,《续同人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在当时的流行思潮中毫不引人注意而已。调和唐宋的话语实在是太强大了。
《随园诗话》卷十六有一段幽默的记载很耐人寻味:
徐朗斋嵩曰:有数人论诗,争唐、宋为优劣者,几至攘臂。乃授嵩以定其说。嵩乃仰天而叹,良久不言。众问何叹,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则宋、元、明三朝诗,俱号称唐诗,诸公何用争哉?须知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也。”众人闻之,乃闭口散。余谓诗称唐,犹称宋之斤、鲁之削也,取其极工者而言;非谓宋外无斤、鲁外无削也。*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六,第402页。
由这则诗话可以知道,当时持类似论调者实夥其人,而且并非都出于袁枚的启迪。袁枚不过借其影响力及《随园诗话》的流行,张扬和传播了这种观念,使论诗只究工拙,不拘唐宋成为诗坛流行一时的时髦话语。程晋芳《邗上酬陶篁村六十韵》写道:“风诗道歇绝,剽窃以市名。选字必六朝,取格希三唐。试观宋金元,一一标奇英。底肯学优孟,衣冠貌行藏。”*程晋芳:《邗上酬陶篁村六十韵》,《勉行堂诗文集》卷十,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85页。曹廷栋句又云:“诗真岂在分唐宋,语妙何曾露刻雕。”*袁枚:《随园诗话》卷二,第41页。王文治《题杭州朱青湖抱山堂诗集后》也感慨:“祧唐祖宋谁作俑,如水趋下无由旋。”*《王文治诗文集》卷二十一,刘奕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页。乾隆五十八年(1793)张问陶作《论诗十二绝句》,其十称:“文章体制本天生,祗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页。至于蒋士铨《辨诗》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唐宋调和论,首先肯定“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一代只数人,余子故多疵”,继而抨击分唐界宋的拘虚之见,倡言兼取唐宋:“奈何愚贱子,唐宋分藩篱。哆口崇唐音,羊质冒虎皮。习为廓落语,死气蒸伏尸。撑架陈气象?桎梏立威仪。可怜馁败物,欲代郊庙牺。使为苏黄仆,终日当鞭笞。七子推王李,不免贻笑嗤。况设土木形,浪拟神仙姿。李杜若生晚,亦自易矩规。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袁枚有《除夕读蒋苕生编修诗即仿其体奉题三首》,其二云:“俗儒硁硁界唐宋,未入华胥先作梦。先生有意唤醒之,矫枉张弓力太重。沧溟数子见即嗔,新城一翁头更痛。我道不如掩其朝代名姓只论诗,能合吾意吾取之。”*蒋士铨:《忠雅堂集》卷二十,邵海清、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册第401页。欣然引为同调。嘉庆七年(1802)焦循《答周己山》云:“诗亦不必分唐、宋,只求其好可耳。”*焦循:《焦循诗文集》,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下册第632页。嘉庆十一年(1806)赵翼作《论诗》云:“宋调唐音百战场,纷纷唇舌互雌黄。此于世道何关系,竟似儒家辟老庄。”*赵翼:《瓯北集》卷四十八,《赵翼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册第986页。可视为这种论调的回响。
袁枚和蒋士铨的议论在诗坛广为流传,或被后学引为口实。李宪乔《与秦希文书》提到:
仆所谓以古为法,法古人之气骨,非必侈言汉魏、盛唐也。谓诗必学汉魏、盛唐,不可落中晚、宋元者,此世俗掎摭道涂之言,仆不敢为是言也。即本朝诗,最推阮亭,乃其诗云:“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是不以汉魏薄中晚也。又云:“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是不以盛唐薄宋元也。近来能诗者,仆谓蒋心畬颇为杰出,其诗亦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奈何愚贱子,唐宋分籓篱。侈口崇唐音,羊质蒙虎皮。习为廓落语,死气蒸伏尸。”袁子才与沈確士论诗,亦力辟门户之说。仆谓二子皆不无所见,至其所造之浅深,各随所得耳。*李怀民:《与秦希文书》,《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144页。
汪嫈《答门人徐玉卿书》也称《随园诗话》“摘录见道语,亦颇增长识见。如谓唐、宋者,历代之国号,与诗无与。诗者,各人之性情,与唐、宋无与。此种妙论发前人所未发,未可磨灭”*汪嫈:《答门人徐玉卿书》,《雅安书屋文集》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刊本。。这不禁让我们推想,乾隆后期消弭唐宋诗之争的意识可能与袁枚及同时性灵派主要诗人的共同主张大有关系。
当时影响所及,上至宰辅公卿,下逮青衿士子,言诗者多标举不拘唐、宋之说。如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六引徐蝶园(满姓舒穆鲁)相国序陆鹤亭《春及堂诗》曰:
今之士大夫竞言诗,或唐或宋,各执所尚,抗不相下。余曰诗以道性情已耳。苟能出于性情,勿论唐可,宋亦可也。如其不出于性情,勿论宋非,唐亦非也。*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96~197页。
同书卷八又载施安《旧雨斋集》自序云:
余幼读司空表圣《诗品》,犁然有会,辄为吟讽。世之饮井水者,或寻味于酸咸之外,引为同调。如以唐宋派别绳我,则直以之覆瓿耳。*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257~258页。
方薰《山静居诗话》又记性灵派诗人蒋绍辉语曰:“人每以气格论诗,是以尊汉唐而薄宋元;若以世风言诗,则代有其诗,平心读之,自知其乘除运会之变。”*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58~959页。一时识者韪之。
置身于这股思潮中,即使是不属于性灵派阵营的诗家,也不能不受流行观念的影响。比如王鸣盛本是沈德潜弟子,所作《碧霞书屋诗钞序》则云:
近日诗教大昌,诗家麻列,然嗜甘者忌辛,好丹者非素,唐音宋调,言人人殊。予尝疑之。盖诗体至唐为备,论诗者以唐为准的是固然,顾或剽窃摹拟,袭貌遗神,斯学唐者之弊也;宋诗自欧、梅固已别开户牖,苏、黄辈出,遂乃掘尽唐人臼科,守故方□,□不可不参以新变。顾南渡以下,俚鄙粗俗,如村谣羌笛,杂出其间,尤而效之,去正声远矣。斯又学宋者之弊也。求其调剂两家,去短集长,洋洋乎会通于大雅者,繄何人乎?*梁昌圣:《碧霞书屋诗钞》卷首,香港:中国艺术家出版社,2008年。
所以他称赞《碧霞书屋诗钞》作者“或唐或宋,惟其所陶冶,而未尝拘于一格也。抑且非唐非宋,自写其心灵悟诣,而不必求离合于古人也。大约学唐而不失之板,学宋而不失之野。大雅之复作也,舍拜善其谁与归?”又如吴锡麒,师从杭世骏、吴颖芳,而尤其追慕乡贤厉鹗,本属浙派诗人。浙派自黄宗羲以降,夙以宋诗为宗尚,厉鹗诗时称“撷宋诗之精诣,而去其疏芜”*王昶:《湖海诗传》卷二,续四库全书本。。但吴锡麒走的却是“熔汉魏、六朝、唐宋为一炉”的路子*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四四引《听松庐诗话》,道光十年刊本。,既对沈德潜固守格调派立场有所批评,说“宗伯论诗龂龂于唐宋之界,若毫发不能假借者”*吴锡麒:《棕亭古文钞序》,金兆燕《国子先生全集》,道光十六年赠云轩刊本。,同时对浙派宋诗风也多有不满。这种不拘唐宋、融合会通的主张在嘉庆以后日渐成为诗坛的主流。伍宇澄论诗云:“不本性求情而专主门户之见者,迂也;不好学深思而但持唐宋之说者,傎也。”*万之蘅:《伍既庭哀词并序》,伍承焕纂《伍任宗谱》卷八,光绪二十年敦睦堂活字本。转引自张廷银《族谱所见文学批评资料整理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上句以性济情,下句折衷唐宋,足见二者本是相通的。这正体现了乾隆诗学在思维方式深处的一致性。
诚如张赓谟《论诗》所云:“秋菊春兰各有姿,诗分唐宋亦犹斯。”*张赓谟:《空斋寂坐万感俱来爰作消闲十二事诗以自遣时丁巳初夏也》,《菉园诗草》卷二,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第13册,第78页。至此,历数百年不息的唐宋诗门户之争终告消歇,这么说不是意味着此后再没有主唐主宋的不同立场,而只是说人们不再需要为唐宋诗的价值高下争辩,主唐诗者无须傲视宋诗,主宋诗者也不必斤斤为它提价,寻找可宗法的理由,人们从此可根据自己的趣味出入取舍,而不必在审美价值的意义上争辩其合法性,这意味着唐宋各擅其胜的诗歌传统观从而确立。清初以来折衷唐宋的思想苗头,经乾隆间性灵诗学催发,在当时汉宋融合的学术文化语境中,与文章学里的融合骈散相互映发,终于结出蕴含丰富的诗学理论果实。当然,唐宋传统和门户之争的泯灭,同时也让诗学的钟摆晃到个人才能一面,使才情与学问的对立、冲突凸显出来,形成诗坛热烈讨论的另一个焦点话题。
二、才情与学问之争的泛起
置身于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烜赫的乾、嘉时代,所有的文人都无法回避如何对待学问的问题。它在两个层面上迫使人们做出选择:在广义文学的层面上,所谓学问在当时就是经学的同义词,选择治经或不治经,首先将戴震、姚鼐、洪亮吉、钱大昕那样的学者型文人与袁枚、蒋士铨、黄景仁这样的作家型文人区分开来;在狭义文学的层面上,学问意味着文学之外的所有知识,选择以学为诗或以才为诗,又将袁枚一辈性灵派诗人与翁方纲一辈考据派诗人区分开来。在乾隆文坛,不只治学路向是个困扰士人、经常带来观念冲突的动因;如何看待才情与学力的关系,也是诗学中难以回避的观念对立。
众所周知,天分与学力之争是个古老的话题,中外文论皆然。在中国文论中,葛晓音认为可以追溯到唐代自然、天真与苦思、修饰的提法*葛晓音:《从历代诗话看唐诗研究与天分学力之争》,《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在崇尚博学的宋代,黄庭坚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的推崇,造成一代诗风朝着以学问为诗倾斜,而“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曾不学,则终不近诗”*费衮:《梁溪漫志》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遂成为文坛通行的看法。刘克庄有鉴于此,曾有“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区判,所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刘克庄:《跋何谦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严羽将崇尚兴趣、妙悟的唐人与“以学问为诗”的本朝诸公对举,更使这一问题明朗化和历史化,引发长久的唐宋诗艺术品位之争。清初诗坛出于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反拨,一致鄙薄枵腹为诗,力主以书卷为诗歌之基石,同时引发对诗与学之关系的反思。“诗人之诗”与“儒者之诗”(钱谦益《顾麟士诗集序》),或“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黄宗羲《后苇碧轩诗序》)的界限,再度成为诗家关注的问题,其核心实质上就是性情与学问孰为优先的问题。钱谦益《定山堂诗序》曾将性情和学问对举,辨析两者的关系:
诗之为道,性情学问参会者也。性情者,学问之精神也;学问者,性情之孚尹也。执性情而弃学问,采风谣而遗著作,舆讴巷,皆被管弦;《挂枝》《打枣》,咸播郊庙,胥天下用妄失学,为有目无睹之徒者,必此言也。*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首,光绪九年龚彦绪刊本。
这是从作家才能的角度阐发性情、学问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徐乾学《南芝堂杂诗序》则直接将性情还原为才的问题,并与学相对而重新作了定义:
所谓才,非特文笔流便而已也;所谓学,非特记诵淹洽而已也。……明达物务之谓才,练晓今古之谓学。两者虽不主于为诗,而非是无以为诗之根柢。*盛符升:《诚斋诗集·南芝堂杂诗》卷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盛氏十贤祠抄本。
他举杜甫为例,认为“少陵之诗雄压百代,岂特格律云尔哉?天宝以至大历,秦蜀以至衡湘,将吏之骄谨,边塞之安危,民物之贫阜,山川之险易,一一籍记而图列之,是之谓诗才,是之谓诗学”。这里将才、学的范围扩大到政治见解和社会知识,超越了前人的藩篱,足以说明才是包容性更大的上位概念,比性情更适合用来与学相对举。自陈宏谋以降,遂为论者所沿袭*陈宏谋:《培远堂文集·培远堂偶存稿》卷二《张西清泛槎吟序》云:“嗟乎,论诗者往往曰才曰学,然才非特声调流美,学非特记诵淹洽而已。盖明达物务谓之才,贯流古今谓之学,两者不主于为诗,而诗之根柢实在于是。”盖全袭徐氏之语,仅改易数字而已。。
鉴于占据明代诗学主流位置的格调派观念与严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清初诗论家多集矢于沧浪诗说,以正本清源。萧正模《施用文诗草序》云:“吾未见夫诗之可以无学而工也。夫古人以所学尽资之为诗,谓诗不关学,严沧浪之此语其亦足贻误后生也。”*萧正模:《后知堂文集》卷二十二,康熙五十六年刊本。朱彝尊《楝亭诗序》更断言:“今之诗家空疏浅薄,皆由严仪卿‘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一语启之。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九,康熙刊本。类似的批评还见于黄道周、毛奇龄、周容、汪师韩等人的议论中,现在看来很可能与世传《诗辩》“非关书也”误作“非关学也”有关。其实严羽并不是一味反对学问的,只不过不愿人堆砌书卷而已*郭绍虞:《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一文对此已有辨证,见《艺林丛录》第五编,香港:商务印书馆,1964年。。但这已无关紧要,对严羽的批评最终磨砻出唐孙华“学问、性灵缺一不可”的折衷之说:“有学问以发抒性灵,有性灵以融冶学问,而后可与言诗。”*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三引,龙威秘书本。这是非常通达的见解,足以消解人们在才性和学问关系上的纠结。但遗憾的是,到乾隆诗坛为实证学风所笼罩,以考据为诗的学人诗风盛行一时,而引起诗坛对其流弊的警觉与反思,就不能不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才与学的关系,从而导致新一轮才性与学力之争的勃兴。
在格调派主导诗坛的乾隆初,不只是沈德潜的诗学已冒出学人之诗的苗头,另外一些著名诗人在才学关系上也较偏重于学,如李重华说:“人谓诗有别才,非关学力者,只就天分一边论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学力断不能成家。”*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32页。与袁枚有南北随园之目的边连宝*李銮宣:《道出任丘县向邑令索得边随园诗集携至高阳旅舍挑灯展读率成二律题集后》:“一时南北两随园,各有澜从舌本翻。瀛海诗人工乐府,仓山仙吏富词源。使才毕竟由天授,学舌谁能见道原。寄语骚坛后来者,莫教此事独推袁。”《坚白石斋诗集》卷十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2页。,论诗也主学力,认为学力终胜天分。其《病余长语》评骘李杜曾说:“金、陈之时文似李杜,大士似太白,正希似子美,一以才胜,一以学胜。人定胜天,故李不如杜,陈不如金。”*边连宝:《病余长语》卷八,天津图书馆藏稿本。《示廷征》诗又云:“所以严沧浪,言诗有别悟。又云非关学,此语乃大误。人生具夙慧,譬之地敏树。慧以植其根,学以勤灌注。恃慧而废学,究竟成蔫箊。王孟与韦柳,妙质标天素。实于淡寂中,藏有书四库。”*边连宝:《边随园集》,刘崇德主编《边连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后来桐城派宗师姚鼐论诗也崇尚诗中有学,曾于《敦拙堂诗集序》述其旨曰:“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神鬼,反覆乎训诫,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可并论也。”*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9页。但另一方面,就在乾隆初彭端淑的《文论》中,我们也看到对刘知几“史家三长”的重新思考,将三长并重引向独尚才情的方向:“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所以辅吾之学识以达于文者也。有学有识而才不至,则无以达其所见,以行于自然之途,使天下后世厌心而悦目。顾才有小大,授于天而不可强者也。”*彭端淑:《白鹤堂文稿》,同治六年丹林彭效宗重刊本。到乾隆中叶,随着袁枚性灵诗说日益风行于世,论诗尚才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任瓣芸《诗人》写道:“诗人如美人,倩盼天赋资。傅粉非不佳,涂抹从后起。所以随园诗,声声发清徵。读破万卷书,笔下无秽滓。”*任兰陔等纂:《萧山任氏家乘》卷二十《遗芳集》下,同治十三年任氏永思堂活字本。转引自张廷银《族谱所见文学批评资料整理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任氏显然是袁枚诗论的响应者,认定诗人必有美才为质,然后济以学问,这才不至于满纸糟粕掩抑性灵。

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
诗学中有关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区分,本质上起于对诗歌审美特性的反思和确认。其雏形已见于汉代扬雄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对举,托名白居易《金针诗格》“诗有二家”条因有“诗人之诗”与“词人之诗”之辨:“诗人之诗雅而正,词人之诗才而辩。”*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4页。在北宋作家对杜文、韩诗、苏词非“本色”的一派批评声音中,李复《与侯谟秀才书》也论及:“子美长于诗,杂文似其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李复:《与侯谟秀才》其三,《潏水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1册第51页。到南宋,张栻又提出“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的分别:
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咏愈久,愈觉深长。”*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页。
这里的学者之诗,正如学界一般认为的那样,应指邵雍一辈理学之士的诗风。张景阳序张夏诗集回应李复对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区别,将两者的特征概括为:“诗人之诗精而深,文人之诗辨而理。”*陈应行:《吟窗杂录》卷三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47页。后来刘克庄跋何谦诗又以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对举,作了总结性的表述:“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刘克庄:《何谦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此后,明代还有孙承恩辨析“儒者之诗”与“诗人之诗”,为钱谦益所响应,但影响不大*贺国强、魏中林:《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一文对此有细致讨论,可参看。。明末徐世溥《溉园诗集序》又提出一个“才人之诗”的概念:“诗本自然,要归至极。弗事乎此而能者,有圣贤之诗,有豪杰之诗,有隐士逸人之诗,有妇人女子之诗;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诗,有词人之诗,有诗人之诗。而是数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七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册第2863页。清初费经虞《雅伦》将“诗人之诗”“才子之诗”“笃学之诗”“闲适之诗”并举*费经虞辑:《雅伦》卷十六,康熙四十九年刊本。,成为“中国诗学史上最早将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概念相提并论的诗学文献”*李金松:《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划分及其诗学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应该说,有关三个概念的源流,先行研究已有细致梳理,不过乾隆间对三个概念的讨论,还留有需要进一步阐发的问题。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辨析,之所以会在乾隆间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是因为这一话题虽远溯宋人,近承费经虞,但同时又的确是特定诗学语境中形成的理论命题。张健曾举杭世骏(1696—1772)《沈沃田诗序》*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11~612页。,认为杭氏从理论上正式提出了学人之诗的口号:
诗缘情而易工,学征实而难假。今天下称诗者什之九,俯首而孜孜于学者,什曾不得一焉。……《三百篇》之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于商,则正考父;其在于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于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己,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后人渐昧斯义,勇于为诗,而惮于为学,思义单狭,辞语陈因,不得不出于稗贩剽窃之一途。前者方炽,后随朽落。……余特以学之一字立诗之干,而正天下言诗者之趋,而世莫宗也。*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十,光绪十四年刊全集本。
如果就问题的提出而言,更早涉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论辩的人可能是方贞观(1679—1747),他在雍正十二年(1734)六月前撰写的诗话《辍锻录》*此书通行之本无写作年月,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册页末有“雍正甲寅六月为蜀泉老侄”落款,知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六月之前。,开宗明义首揭诗分诗人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之旨:
才人之诗,崇论闳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得之顷刻。然角胜于当场,则惊奇仰异;咀含于闲暇,则时过境非。譬之佛家,吞针咒水,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
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
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
方贞观教人“作诗未辨美恶,先辨是非”,是非者即诗性之谓,“会乎此可与入诗人之域”。考虑到地域小传统的有力影响,他的说法很可能又是本自邑先辈钱澄之。钱氏《说诗示石生汉昭赵生又彬》云:
文章之道,至于诗而才与学黜焉。非谓才与学不足以为诗,谓诗非才与学之可以为也,而有其才焉,有其学焉。有才人之才,有诗人之才;有学人之学,有诗人之学。才人之才在声光,诗人之才在气韵;学人之学以淹雅,诗人之学以神悟。声光可见也,气韵不可见也;淹雅可习也,神悟不可习也。是故诗人者,不惟有别才,抑有别学。*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二十六,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506~507页。
他不仅发挥严羽“别才”之说,更提出学也有“别学”,这就顺理成章地导出一个结论:“夫诗人之诗,何尝不以才为之?学为之?而决为诗人,非才人、学人之所可为!”*钱澄之:《说诗示石生汉昭赵生又彬》,《田间文集》卷二十六,第507页。可见到清初,才人之诗、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名目都已见诸诗论,三者的分别也隐含在钱澄之的意识中,尽管还没有像方贞观那样清楚地加以辨析申说。与方贞观同时的太仓人沈起元(1685—1763)在《梅勿庵诗集序》里也提到:“昔之论诗者曰,有诗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余谓才人以气雄,学人以材富,诗人以韵格标胜。”*沈起元:《敬亭诗文》文稿卷二,乾隆刊本。这里既称是传述昔人之说,当然不会是受自方贞观,如果不是本之钱澄之,那也可能是受费经虞的启发,或综合了前人的说法。
《辍锻录》在方贞观生前并未梓行,稿本后为金楷购得,直到道光十四年(1834)才由广陵聚好斋刊刻行世。但他的学说在乡后学间已有影响,并通过他们传播于诗坛。自称“余之诗盖出于桐城两方,兼采其说而学焉”的程晋芳*程晋芳:《南堂诗钞跋》,《勉行堂诗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797页。,在《望溪集后》中写道:
夫诗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而必以诗人之诗为第一;文有学人之文,有才人之文,而必以学人之文为第一。*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第771页。
程晋芳此说很可能即本自方贞观。无论如何,才人之诗、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分别在乾隆诗坛已很流行,这是可以肯定的。当时论及这个问题的批评家,现知尚有数位。朱景英《萝村诗选序》云:
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诗人之诗。骈花俪叶,妃白偶青,獭祭心劳,鹤声偷巧,弓衣而织白傅,团扇而画放翁,既锢阏其性灵,徒求工于章句,此诗人之诗也。以观者为之目眩,以崇论闳议为奇横,以钩字棘句为博奥,险摄牛蛇之魄,丽矕龙虎之皮,读者至于舌挢,此才人之诗也。若夫学人之诗,上薄风骚,根极理要,采经史子集之菁华,味兴观群怨之旨趣,必有为而作,无不典之辞,庶几司空表圣所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者乎!*朱景英:《畲经堂诗文集》文集卷四,乾隆刊本。
作者的倾向明显推崇学人之诗,这在考据学风浓厚的乾隆时代也是很自然的事。同调有阳湖兼工诗的学者赵怀玉,其《焦里堂诗序》有云:
夫蕲于工而工者,斤斤于格律,屑屑于字句,殚精力而为之,以是专门名家,取誉传世,诗人之诗,世所同也。不蕲工而自工者,施之则有本,言之则有物,出余事而为之,以是畅怀舒愤,塞违从正,学人之诗,君是也。*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70册第49页。
始终倾慕袁枚的性灵派诗人李调元,虽发挥严羽“诗有别才”之说,但同时也强调学问的重要,要人“多读书,多穷理”*詹杭伦、沈时蓉:《雨村诗话校证》卷八,第188页。,还称赞以制义著名的刘岩《贺楼村移居》诗“意真语挚,所谓学人之诗也”*詹杭伦、沈时蓉:《雨村诗话校证》卷十一,第259页。,在性灵派诗人中可算是异数。后来对学人之诗的尊崇,还有孔宪彝《郑子斌诗序》:“诗以言志,志存乎人。而人有才有学,故诗亦适如其人。尝以此衡当世之贤者,其空灵飘渺、望若神仙,则才人之诗也;其沉着痛快,华实并茂,则学人之诗也。然才人多而学人少,才人而能为学人者,尤不概见。”*孔宪彝:《韩斋集》,《清代稿钞本》,第37册,第27页。尽管他是在才人和学人两者间较量,但既然感叹学人之诗少,则其可贵不言而喻。
尽管不乏类似的尊崇学人之诗的说法,但终乾隆一朝以至清季,持这种立场的批评家终究是少数,反对者才是诗坛主流。袁枚《随园诗话》刊行虽晚,但他毫无疑问是拒斥学人之诗的代表人物,《诗话》中再三流露出对学人之诗的厌恶。如卷四称:“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或诵诸诗:‘秋草驯龙种,春罗狎雉媒。’‘九秋易洒登高泪,百战重经广武场。’差为可诵,他作不能称是。”*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第89页。直说学人之诗读起来沉闷不堪,毫不宽假。补遗卷一又道:
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诗,必须穷经读注疏,然后落笔,诗乃可传。余闻之,笑曰:“且勿论建安、大历,开府、参军,其经学何如,只问‘关关雎鸠’‘采采卷耳’,是穷何经、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诗独绝千古,而‘读书不求甚解’,何不读此疏以解之?”梁昭明太子《与湘东王书》云:“夫六典、三礼,所施有地,所用有宜。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竟同《大诰》。”此数言振聋发聩,想当时必有迂儒曲士,以经学谈诗者,故为此语以晓之。*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第424~425页。
这是批评当时学人之诗以经学为诗的习气,由此引出如何对待考据题目的问题。他在另一段诗话里曾借圣人编《诗》先列《国风》的权威例证来申明诗以性情为尚的观念:“考据之学,离诗最远;然诗中恰有考据题目,如《石鼓歌》《铁券行》之类,不得不征文考典,以侈侈隆富为贵。但须一气呵成,有议论、波澜方妙,不可铢积寸累,徒作算博士也。……圣人编诗,先《国风》而后《雅》《颂》,何也?以《国风》近性情故也。”*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第461页。与此相应,他也没忘记通过特殊人物的具体诗作来张大“诗人之诗”的旗帜:
宜兴储氏多古文经义之学,少吟诗者。吾近今得二人焉:一名润书,字玉琴,《赠梅岑》云:“一曲吴歌酒半醺,当筵争识杜司勋。天花作骨丝难绣,春水如情剪不分。话到西窗刚近月,人于东野愿为云。应知此后相思处,日日江头倚夕曛。”又句云:“山气作寒啼鸟外,春阴如梦落花初。”其一名国钧,字长源。《梁溪》云:“纸鸢轻扬午晴开,杂沓游人傍水隈。多半画船犹未拢,知从池上饲鱼来。”《即目》云:“日午横塘缓棹过,风吹花气荡层波。依篷不肯轻回首,近水楼台茜袖多。”晚年漂泊,《六十自寿》云:“谁言老去离家惯?转恐归来卒岁难。”窘状可想。他如:“树凉宜散帙,梅尽始熏衣。”“烟消松翠淡,雪堕柳枝轻。”“酒旗翻冻雪,土锉燎征衣。”“岚翠忽从亭午变,扇纨都向嫩晴开。”“银筝度曲徐牵舫,镜槛悬灯不隔纱。”皆诗人之诗。*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第99页。
做学人诗者自命为诗人,而所作离诗殊远;从事古文经义之家,却能作诗人之诗。然则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其辨幾微。袁枚早年作《续诗品》,第三首《博习》也曾诫人作诗必根于博学,所谓“不从糟粕,安得精英?”后见近时作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深恐前言误人,又作《论诗》申明其立场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袁枚:《随园诗话》卷五,第111页。这是当时对学人诗最严厉同时也最为人熟知的批评,前人多以为矛头指向翁方纲,虽难以坐实,但在当时确实反响很大。王玮庆《论诗八绝句》其二云:“獭祭讥同字贯鱼,水中盐味悟何如。篇章笺释康成事,莫把吟诗当注书。”*王玮庆:《蕅唐诗集》卷八,嘉庆二十五年蕉叶山房刊本。明显是在响应袁枚的论调。
在这种形势下,章学诚《韩诗编年笺注书后》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停*章学诚:《韩诗编年笺注书后》:“大抵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各有所长,亦各有其流弊。但要酝酿于中,有其自得而不袭于形貌,不矜于声名,即其所以不朽之质。”邓实辑《古学汇刊》第四编下,民国二年国粹学报社排印本。,即使假定它体现了乾隆诗坛的多元化倾向,也很难相信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夙慕袁枚性灵诗学的法式善,在《容雅堂诗集序》比论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不同旨趣,说“学人之诗,通训诂,精考据,而性情或不传”,明显是贬抑有加。袁枚门人孙原湘《黄琴六诗稿序》析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不同特征,说:“言志之谓诗,而所以文其言者殊焉。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同一言德行,而《抑》戒,学人之诗;《雄雉》,则诗人之诗。同一饮酒,而《伐木》,诗人之诗;《宾筵》,则学人之诗。此辨之于气息,辨之于神味,不当于字句间求之也。”*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88册第326页。玩此四诗,《抑》《宾之初筵》为赋体,多议论;《雄雉》《伐木》,工于比兴,富于情味,高下不待缕析而立判。乾隆间有关才性与学问之争最终走向了融合,但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争辩却没有归于调停和并举。也就是说,论诗重视学问是一回事,而反对学人之诗又是一回事。毕竟,学人之诗不只是一种创作观念,更是一种有悖于诗歌本性的可疑实践,得不到诗坛的普遍认可,乃是很自然的结果。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例子是陈文述《顾竹峤诗序》,它也持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三分之说以裁量古今诗流:
汉魏以来,陶之冲淡,鲍之俊逸,小谢之清华,王、孟、韦、柳之隽永澄澹,诗人之诗也;陈思之沉郁,康乐之生新,太白、东坡之旷逸朗秀,才人之诗也;韦孟之讽喻,张华之励志,少陵之时事,香山之讽喻,邵尧夫之温厚,陆放翁之忠爱,元遗山之眷怀故国,学人之诗也。国朝诗人辈出,踵武前代,亭林、桴亭为学人,愚山、渔洋为诗人,梅村、迦陵为才人。乾嘉以来,于斯为盛。并世诸贤,略可屈指:为诗人之诗者,则有我师仪征阮云台先生,无锡秦小岘司寇,蒙古法梧门祭酒,山左李石桐、少鹤兄弟,莱阳赵北岚,山阴邵梦余,嘉兴吴澹川,长洲王惕甫、彭秋士、吴枚庵,太仓彭甘亭,华亭姚春木,江西乐莲裳、吴兰雪,吴江郭频伽,海昌查梅史,钱塘厉樊榭、袁简斋、吴谷人、朱青湖、马秋药、钱谢庵东生、叔美兄弟、屠琴坞、从兄曼生;为才人之诗者,则有武进黄仲则,阳湖赵瓯北、洪稚存,湘潭张紫岘,会稽商宝意,大兴舒铁云,嘉兴王仲瞿,扬州汪剑潭、竹素、竹海父子,遂宁张问陶,金匮杨蓉裳、荔裳兄弟,金华周蓟云,丹徒严丽生,常熟孙子潇,吴江赵良夫;为学人之诗者,娄东萧樊村一人而已。*陈文述:《颐道堂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05册第553页。湘潭,潭原误作谭。
此序意在表彰顾竹桥的学人诗,但能举出的同道仅萧樊村一人,即便说物以稀为贵,也与诗家的一般价值观相去太远。对清代诗论中这些有关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的辨析,李金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由此形成批评话语中的核心概念,给诗史认知带来新的诗学视野,我非常赞同,但同时对这些概念的实际批评功能也略有一点保留看法。这个问题似乎需要分开来看,学人、才人、诗人之诗作为诗歌创作理念的划分是有意义的,但若用来衡量诗人的整个创作,甚至以此来分群归类,就难免有方枘圆凿、削足适履之弊。尤其是用于前代诗人,差互更大。历数陈文述所论列的古今诗人,唐宋以前诸家,任何要在陶渊明、白居易、苏轼之间画出界线的理由都是很让人怀疑的;而并世诗人中,无论厉鹗、袁枚之合,还是阮元、赵翼、吴锡麒、洪亮吉之离,也都是难洽人意的。撇开前代作者不谈,陈文述这段评论的意义,与其说是用三个特制的模板区分了诗坛的不同群体,还不如说是根据他对不同诗人群体的了解给他们贴了一个未必合适的标签。其中,学人之诗他所认可的只有萧樊村一个人,如果他意在标举学人之诗,那就自立于反普世价值的立场上了。文中所列举的师友,自阮元以降都麇集在诗人之诗的旗下,无论以什么理由,要将学人之诗高置于诗人之诗和才人之诗之上,都是很荒唐的。这正是我说此序的反讽之所在。
直到晚清,诗论中尚才尚学之争也未停息,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高下得失已不待辩。朱一新《无邪堂问答》有曰:“诗有别才,严沧浪之言诚然。专由学力入者,多工赋体,于比兴之义,终少妙悟,乃学人之诗,非诗人之诗也。”*朱一新:《无邪堂问答》卷二,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刊本。按古来传统观念,从艺术表现上断言“于比兴之义,终少妙悟”,就等于是宣判了学人之诗不入流品。职是之故,尽管同光体作家力图折衷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将两者合而为一,却也不敢公然标举学人之诗的概念,而只能像沈曾植那样,将“雅人深致”与“风人之致”相并举,以暗推学人之诗的潮涌*关于沈曾植“雅人深致”与学人之诗的关系,可参看贺国强、魏中林《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一文的论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学人之文在文章论中却占有明显强势的地位。王鸣盛《问字堂集序》称:“夫学必以通经为要,通经必以识字为基。自故明士不通经,读书皆乱读,学术之坏败极矣,又何文之足言哉?天运循环,本朝蔚兴,百数十年来,如顾宁人、阎百诗、万季野、惠定宇,名儒踵相接,而尤幸《说文》之岿然独存,使学者得所据依,以为通经之本务。孙君最后出,精骛八极,耽思旁讯,所问非一师,而总托始于识字,于是一搦管皆与其胸怀本趣相值,洵乎学者之文,迥非世俗之所谓文矣。”*孙星衍:《问字堂集》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页。以汉学为依托的强大舆论使学者之文的主张在清代中叶以后明显呈一面倒的趋势,恰好与学人之诗的弱势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我们在谈论乾隆朝诗学的观念之争时不可不知的。
乾隆诗坛的才、学之争,说不上有什么重要的理论成果,但重新明确了两点认识:一是才与学同为诗之根柢,即陈宏谋《张西清泛槎吟序》所云:“论诗者往往曰才曰学,然才非特声调流美,学非特记诵淹洽而已。盖明达物务谓之才,贯流古今谓之学,两者不主于为诗,而诗之根柢实在于是。”*陈宏谋:《培远堂文集·培远堂偶存稿》卷二,临桂陈氏培远堂刊本。二是才受于天,学本乎人,二者交相为用。如吴镇《张玉厓集句序》云:“夫作诗之根本,才与学而已,才赋于天不能增减,学则经史子集皆宜钻研。今第读诗而作诗,固无所为诗也;然未读诗而作诗,讵反有诗乎?”*吴镇:《松厓文稿》,《松花庵全集》,乾隆刊本。上引乾隆间诗人的议论,无论主才性辅以学问,还是主学问陶冶才性,其实都默认了一个前提:诗才本系天生,无天分不足为诗;然有天分而不济以学力,同样难以奏功。后来陈仅在答侄问性灵、学力之分时,清楚地阐述了这一辩证关系:
性灵,即性分也。学诗者,有天资颖悟,出手便高者,是性分中宿世灵根。摩诘所谓“宿世本辞客,前身老画师”,沧浪所谓“诗有别趣”,此种人学诗最易,然往往缺于学术,转至自误;其由学力进者,多不能成家,以性情不相入也。故两者必相须而成。*陈仅:《竹林答问》,周维德校注:《诗问四种》,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90页。
结论虽然归于天分、学力相辅相成,但首要的显然还是天分,而且陈氏根本认为无天分而仅凭学力多不能成家。同时代人林寿图也说“诗才自天分中带来,有是种方有是树”*林寿图:《榕阴谈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抄本。,这可以说是后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最终结论。无论古今中外,毕竟学诗者多而杰出诗人少,这还不足以说明,诗决不是光靠苦学就能写得好的?但确认这一点,并不能阻止许多没有天才的人继续写诗,尽管天才不可习得,人们所能希求的仍只有以学济才。于是乾、嘉之后诗学的主流观念就定型为主才而尚学,带有鲜明的折衷色彩。如梁章钜《退庵随笔》所记方长青之言曰:“诗必以造语为工,而造语必以多读书善用事为妙。……盖钟(嵘)严(羽)所言,专以性灵说诗,未为过也。乃言性灵而必以不用事、不关学为说,则非矣。”*梁章钜:《退庵随笔》,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953页。李树滋《石樵诗话》卷一记邑前辈周伯孔语亦云:“以才运书,则可道河源于腕底,规建章于砚北;以雅资博,则酌群言而攻瑕奏新,准至理而露文抒性。”*李树滋:《石樵诗话》,道光五年李氏湖湘采珍山馆刊巾箱本。这是对的,在西方论文中,“诗人这个概念和成为诗人的必要条件历来就包括道德品质和学识造诣。尽管始终提到需要天才和灵感,但批评家坚定不移地强调艺术(意即艺术手法)、科学和知识的作用”*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卷第30~31页。。美国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针对过多的学问会使诗人的敏感性变得迟钝或受到歪曲的问题,也肯定地回答:“在他的必要的感受能力和必要的懒散不受侵犯的范围内,一个诗人应该知道的东西越多越好。”*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页。
四、结论
唐宋诗之争和才学之争及由此衍生的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的分辨,虽都是古老的诗学话题,但直到乾隆间才在性灵诗学语境中引发深入的讨论和理论反思。性灵诗学整体解构传统诗学观念带来的强烈震动,促使诗坛对传统诗学的基本问题及现实的取法路径重新加以思考。其中唐宋诗之争、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关系成为诗坛关注的焦点,许多重要诗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并形成乾隆诗学对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三个概念的辨析。经过乾隆诗学的陶冶,这些持续久远的论争基本得到消解,不同的诗学立场在交流、沟通中达成理解和融合,由此推动乾隆诗学由对立、冲突走向吸收、融合的历史进程。性灵诗学引发的上述焦点话题,也只有放到乾隆诗学的特殊语境中,才能理解其背后的诗歌史和诗学史背景,看清它们在新的历史层面和理论平台上展开的过程,从一个侧面认识古典诗学在乾隆时代获得的深化和成熟。
责任编校:刘云
作者简介: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安徽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安徽 合肥230039)。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2-0053-14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2.008